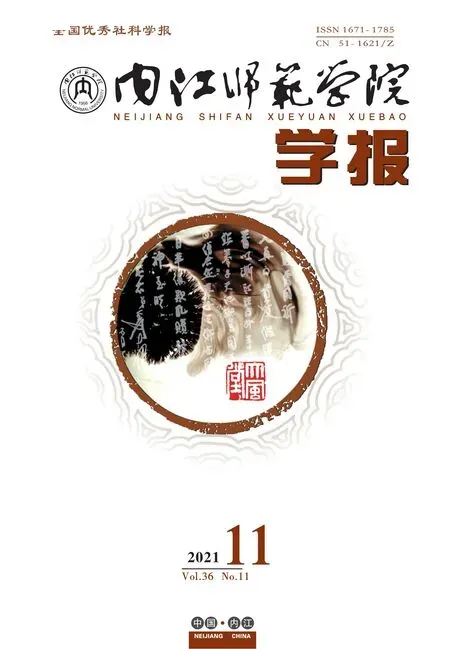云南历程与中国之爱的深化
——重读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
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而举世闻名,但他的云南游记,迄今还未引起足够关注。1930年11月底,斯诺由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12月初乘火车进入云南,翌年3月由云南进入缅甸。他把沿途观感写成系列文章,陆续发表于1931年6-10月的纽约《太阳报》,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中文版游记《马帮旅行》①。周良沛先生在《马帮旅行》“书前”中曾写道,虽然此书远不如《红星照耀中国》产生的影响广泛,甚至并不为许多读者所知,但却是斯诺创作的“一个不一般的开始”,“从文学上看,是本很有光彩的随笔散文”。他还很有见地地认为,虽然斯诺在《马帮旅行》中所写的,无法与《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相提并论,“但无疑是他年轻时浪漫于旅行、冒险、色彩绚丽动人的最佳部分。……他这段人生体验,也无疑是他后来预测、判断中国一些重大事件、是非的智力储备”。确乎如此,《马帮旅行》为斯诺更好地认识并热爱中国,为其以后写下彪炳后世的《红星照耀中国》,做了很好的奠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妨视为后者的“前传”,也是现代游记文本中的经典。本文尝试从探险精神、“跨文化”边地想象、幽默艺术几个角度,对《马帮旅行》的独特魅力,予以阐释和发掘。
一、得其所哉的探险之旅
《马帮旅行》给读者最鲜明直观的印象,就是作者特别沉醉于在云南的高山密林中,享受探险的巨大乐趣,这与中国传统游记文学创作颇为不同。
“斯诺喜欢冒险生涯,往往一时冲动便去做冒险的事。”[1]5从《马帮旅行》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斯诺的确天生具有探险家气质。他的云南之行本身,即有很强烈的探险动机:“云南(云之南)的名字与亚洲高原狂风怒号的风貌是分不开的。它地处中国边远的西部,在高耸入云光彩夺目的西藏雪山山脉之下。……这个名字有着呼风唤雨的魔力。”[2]20无论对于云南有多少主观幻想的成分,斯诺对于这片陌生的土地充满好奇心的探险心理,是极为明显的。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云南地区所有运输几乎全靠人畜之力,马帮更是担负起了商品贸易、联通外界的重要作用。马帮所经之处,便有闻名中外的“南方丝绸之路”。自古以来的云南马帮旅行,既由于穿越许多自然风光美丽、民族风情独特的地区,留下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动人传说,亦由于所经之处地形复杂、土匪肆虐、猛兽出没、瘴气弥漫,而被很多旅者视为闻风丧胆的畏途。而甘愿选择马帮旅行,同样也是斯诺独具的探险心理使然——“马帮,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字眼。它蕴藏着神秘,蕴藏着不可知的推动力。”[2]73正是这样的强烈愿望,促成了斯诺的云南之行。也使得一种无所畏惧的探险精神,在斯诺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旅程正式开始,斯诺开始深深体会到了艰辛,与此同时也展现了他不畏艰险的勇敢:“十天以来,我就是沿着这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踏着无数马蹄印,无数草鞋印,不停地走着,爬着,滑着,时而也骑着。”[2]60“大部分铺过石板的道路,石头已经破损,往往是石片口子锋利的一面朝上,所以每走一步路都有可能扭伤或擦破脚踝。在根本没铺过路面的地方,路上有许多坑坑洼洼,这是因为骡子往往总是踏同一个地方而造成的,有的窟窿有一英尺深,这路云南人叫做‘梯子路’,意思是说,走这样的路,就仿佛‘爬楼梯’一般。”[2]60-61
绝妙的是,斯诺为西方读者,找到了特殊的表达方式,助其理解非同一般的马帮旅行:“做这样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滋味,你不妨做下面的这个实验,就可以了解一二。找一栋纽约市的摩天大楼,再弄来整整一列火车的石灰和碎石头,从楼梯的顶部倒下来,让每一级楼梯都盖满了这些东西,然后拉一条消防皮管来喷水喷两整天,让石灰和碎石头的混合物阴干。于是在顶部吹凛冽的寒风,在底部把蒸汽管开得大大的。你用羊皮把你自己裹起来,开始爬上爬下(你想骑马也可以),每天爬八个小时。这样一来,你就不难领略到在云南的皇家古道上登山的乐趣了。”[2]61把边地崇山峻岭,与现代城市文明并举,这种独特的“跨文化”比拟方式,可谓新鲜奇妙,前无古人!在带给读者全新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使古老的马帮旅行,平添了不少魔幻般的现代性魅力。同样,斯诺作为探险家既勇敢顽强又乐在其中的个性,尽现其中。
马帮旅行尽管艰苦异常,但在斯诺看来,却完全值得——云南大地的诸多神奇风光,足以让他沉醉不已。在他的心目中,若非亲身经历,既看不到地平线上云雾覆盖着远山的美景,也看不到沿途野玫瑰恣情怒放的镜头,更听不到马帮悠扬的铃声和赶马人美妙的歌声。显然,热衷于对神秘未知世界开拓探险的心理,加之特有的豁达洒脱的性格,使斯诺在风餐露宿、惊险不断的马帮旅途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乐趣。
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天,斯诺在滇缅边界遇到了克钦人的打劫。危急关头,他仍旧表现出非同凡响的“享受”心态。“他没有瞄准克钦人,只是对着他们前面的土地连开四枪,克钦人被吓跑。”[2]117这次遇险,给斯诺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马帮旅行,画上了句号——他随后进入了缅甸。
显然,斯诺在游记中体现的探险精神,与中国作家具有显著不同。自古以来,中国游记蔚为大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绚丽多姿的自然风景,成为历代作家情与物发的最佳触媒。不过,“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礼乐传统,以及“逍遥游”的超脱精神,毕竟影响深远。众多文人墨客的山水游记所传递的主旨,或是怡养性情、解忧除困,或是神与物游、陶然忘机。即便命途多蹇如因遭遇贬谪而颠沛流离,心底有着无限的创痛忧伤,但在嗟叹命运的羁旅愁思中,他们往往也寄沉痛于悠闲,把陶渊明式的归隐田园,视为人生的皈依——“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韦应物《东郊》)这在《桃花源记》等经典作品中,已可见一斑。总之,除却徐霞客这样极少的乐于探险的大旅行家的作品,其他中国游记,大多以天人和谐为旨归,常把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与灵魂的抚慰、安顿,作为表现的主题。
在现代文学史中,在诸如鲁迅、郁达夫、巴金这样具有激烈抗争精神的作家笔下,即使蕴蓄着无尽的愤怒,但是由于深受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对于旅程中自然风景的书写,也都较为含蓄内敛。当然,忧患意识也是中国文学传统之一。不过,即或在现代云南游记中,当涉及到山川险恶、兵匪肆虐的时候,虽然作家对于世事艰危、政风恶劣的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如斯诺这样,源自探险精神而乐在其中的旅途书写,实属罕见。
或许不同的文化环境,孕育了斯诺热衷于探险的性格。西方文学中对于探险的书写,源远流长。《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是对特洛伊战争中富有探险精神的英雄的礼赞;《奥德赛》更是以奥德修斯这一人物形象,开启了西方文学个人漂泊流浪、探险开拓的英雄主义模式。其后的《埃涅阿斯纪》《贝奥武甫》《熙德之歌》《尼伯龙根之歌》《伊戈尔出征记》等史诗,都洋溢着对于勇敢探险精神的歌颂。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虽然以对骑士文学的讽刺为初衷,却塑造了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经典冒险者形象。17-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兴盛,随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与探险有关的文学经典层出不穷,诸如《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兰登传》《汤姆·琼斯》等。美国文学也延续了这样的传统,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以及詹姆斯·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等,都有对于来到美洲新大陆的先民之探险、开拓精神的传神写照。
受家人影响,少年时期便热爱阅读的斯诺,对于有关探险的故事情有独钟,对于上述作品应不生疏。他对《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等小说中惊险浪漫的情节尤为着迷。而《马可·波罗游记》,则使他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充满了好奇。可以说,斯诺从小便在阅读中,有了对神秘异域的探险热情,这无疑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历程以及写作,埋下了伏笔。
除了阅读的影响,斯诺的探险精神,还与其自儿童时期便深深培植的军人崇拜情结息息相关。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93年3月4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斯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曾如此归纳“斯诺精神”:“埃德加·斯诺的精神是密苏里堪萨斯城的鹰军精神。”堪萨斯城有著名的培养童子军,即鹰军的传统。鹰军的教育理念,即培养孩子从小就做一名勇敢的探索者,至少要在本地区出类拔萃。1920年,斯诺便成为堪萨斯城“出类拔萃的鹰军”中的一员[3]。斯诺一直把荣获鹰军勋章,视为少年时期最值得骄傲之事。军人勇敢顽强、不怕牺牲、追求正义的精神,也在无形中成为他的人生准则。
斯诺一生的冒险经历,数不胜数。14岁那年,他决定离家到远方闯荡一番。途中虽然与小伙伴走散,遭遇了劫匪袭击,却让“斯诺第一次品尝到了艰苦冒险旅行的乐趣,开始发现大自然和人生竟是如此丰富多彩。他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漂洋过海,到大洋彼岸去看看那未知的世界”[4]。就在23岁的时候,斯诺的世界旅行之梦得以开启,并延续一生。
斯诺在《马帮旅行》中,所传递的特有的探险精神,对于他个人来讲,不容小觑。堪萨斯乃至密苏里人特有的气质本身,便蕴含着向未知领域探险进军的精神。探险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事实真相永不停止的探询——这岂非是曾被誉为“记者之王”的斯诺的职业素养的基石?在20岁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读书后,斯诺即成为《堪萨斯星报》的校内通讯员,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在采访报道中,“斯诺超越意识形态不同的限制,为追求真理,将生死置之度外”[5]。1936年,他到中国苏区的旅行,便充满种种危险。可是斯诺说:“在中国内战中已有了千千万万人牺牲了性命,以一个外国人的性命去冒险,以求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还有比这更值得的吗?”[6]7为探求事实真相,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冒险精神,已然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密不可分。斯诺的一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充满生命危险的战争前线。唯其如此,他才创作出大量真实有力、生动翔实的作品。总之,斯诺具有新闻记者不怕牺牲、勇敢无畏、追求正义、探寻真相的职业素养,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探险精神之于斯诺的人生经历,可谓契合无间。
可以说,正因为斯诺骨子里的探险精神,与艰险异常而又充满活力的云南边地若合符节,才诞生了《马帮旅行》这部绚丽多姿的经典游记作品。
二、浓缩厚望的边地想象
《马帮旅行》处处流露出斯诺对于中国的无比热爱,也隐现着他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关注。由于从异域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斯诺对于1930年代初的云南大地,有许多独特的理解,尽管其中不乏“跨文化”旅行产生的错位。但是,在斯诺的他者眼光中,即使对云南的错位想象,亦有令人深思的独到价值。
写到乘火车从河内出发快到昆明时,斯诺对于久闻的美好风景无暇顾及,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中国士兵身上。“他们心地善良,有着中国农民粗犷而慷慨的作风。”[2]30从这样的概述,完全可以看到,作者已经无形之中把对于中国农民充满个人感情的先在理解,赋予了这些士兵。这就不同于一些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往往把“兵匪”并列,予以批判性描写的做法。
从《马帮旅行》的许多细节都可以看出,斯诺对于中国的热爱,似乎是发自本能的。这种热爱,贯穿斯诺的一生。像他这样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以及中美人民友好交往事业的外国友人,并不多见。“这是来源于他本人朴素真诚的品德,那种主张正义,希望看到人类进步的思想。”[7]与近代以来许多西方传教士以劝慰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等待上帝拯救不同,新闻学院出身的斯诺,更着眼于现实。来华之前,受国内舆论宣传影响,他曾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而在亲身感受到民不聊生的悲惨命运的同时,斯诺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对政府极为失望之余,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的惨相,使斯诺首次产生了渴望自己有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想法。而在很快意识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之后,斯诺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百姓自身。他曾为古老大地上的国民不知反抗,而感到愤怒——“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6]207可见,斯诺已经开始隐隐预见到,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拯救中国。斯诺在马帮旅行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无不与此紧密相关。
在决定到云南探险之前,斯诺对于这里的土著居民曾有过如此想象:“在这一片狂暴而凶悍的原野上,居住着狂暴而凶悍的人,他们饱经风霜,穿着家庭自制的粗布衣服,骑着健壮的小马,或者赶着鬃毛蓬松的牦牛,攀越风雪怒号的崇山峻岭,跨过黑沉沉的激流。”[2]20正如萨义德所言,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神秘的东方”,总有一种先在的想象的理解,即这里居住着原始的或野蛮的民族[8]。尽管斯诺此前在中国的经历,已经令他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深深的同情,但是对于云南这一等待他来探险发掘的他者,还是有着潜在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先在认识——此地乃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而这些,可能并不适用于真正的边地云南,一切还有待于他的亲身体验。
在真正走进云南之后,斯诺良好的记者素养渐渐发挥了作用。因为有了在上海的体验,在进入云南唯一的大都市昆明后,斯诺对这座较早沐浴欧风美雨的城市,予以近乎直觉但不失精准的概括,注意到昆明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2]40这就以外来者的视角,敏锐地对于昆明的文化环境做出了判断——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昆明虽然已经开始接近现代文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日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里陈旧落后的痕迹依旧明显。作为在精神与文化上统领云南的桥头堡,昆明并没有令斯诺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这也为其接下来深入云南大地的探索,埋下了伏笔。
无论怎样,斯诺对于中国总体的友好态度,还是一贯的。尽管发现昆明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丑陋黑暗的现象,但他还是为这里美好的景致和气候所陶醉。在昆明古城墙外,他用美妙的笔触,描绘了如诗如画的图景。不由如此感慨道:“尽管她有种种苦难,但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中国多么可爱。”[2]50这种由自然环境而产生的爱屋及乌的感受,进一步强化了来云南之前,他对于中国早已滋生的爱。
斯诺爱云南这方土地,也爱这里的人。作为一位“跨文化”的旅行者,斯诺对边地原住民极具好感的书写,许多出诸外来者“想象的他者”视角,即更多建立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之上,也许与原住民的内质有所错位。但这种错位,恰恰确证了斯诺深挚的中国情结。
在大理,斯诺结识了一个叫寿珠的年轻人,二人在旅程中产生了浓厚的友情。在腾越,寿珠因不愿继续前行,而与斯诺分别。为此,斯诺很是惆怅:“说真的,这些日子以来,他不仅是我的仆人,而且是我的旅伴。为此我非常怀念他。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他用他们民族的传说故事帮助我打发了多少时光,(还有其更重要的一点)他非常愉快地听我讲述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分手时,我们都十分难过。”[2]103这样的文字,既令人感到忧伤,又夹带着丝丝暖意——斯诺真正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受。由此可见,斯诺不像一些来自西方世界的外来者,具有本能的地域、民族优越感,而是真正把寿珠作为兄弟般的知音来看待,这在当时实属可贵。他对于中国的深挚情谊,也许正是在寿珠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培养起来的。
结束在大理的旅行,来到永昌地界,斯诺见到了旅程中所遇到的最大一个马帮。而对马锅头的描写,令人拍案叫绝:“他的座垫是一块美丽的西藏毛毯,他骑在马上胳膊肘向外伸开,这是典型的云南姿势。他的双肩上,一边挂着黄色丝巾,另一边挂着一长串银珠子,腰间挂一把银剑。还有头上,老天爷,他头上才叫好看,他头戴一顶软皮帽,帽沿上插着一根雉鸡毛,好一副豪侠气概!他从我旁边走过,笑着向我打招呼,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知道,他是多么英俊,多么富丽堂皇。我像看见了罗宾汉似的,大为神往。”[2]91一个英俊挺拔、开朗豪爽、乐观自信的马锅头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典型的云南姿势”更值得回味。总的来看,马锅头固然值得赞赏,但不会代表云南普通民众。当时云南大地上的许多人,尤其是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样貌,想必不会如此潇洒。所以,这一段明显具有“跨文化”意味的想象式描写,大有深意存焉:首先,这与斯诺骨子里的英雄崇拜情结密不可分,对于西方侠盗代表人物罗宾汉的景仰,使他不自觉地为突然出现在崇山峻岭之中,对马帮指挥若定的人物,产生了心有戚戚焉之膜拜。其次,斯诺此前在云南见到了大量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等黑暗现象,此处在一个马锅头身上看到“典型的云南姿势”,虽然看上去倍显突兀,不过也许就在那一刹那,斯诺将马锅头与亟待摆脱贫穷、落后、愚昧的云南联系到一起,充满想象力地欲为边地提供走出困境的良方——摆脱积贫积弱,必先改变人的面貌。理想的人,就应该像马锅头那样,富有活力,充满自信!最后,正是在富有生命强力的马锅头身上,隐含着斯诺对中华民族所寄予的殷殷希望。鲁迅所提出的国家强盛“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目标,在斯诺的马帮旅行中,有了奇妙的对接。
在遥远的边疆,思索中华民族腾飞之路的斯诺的“跨文化”想象,依旧在延续着。来到腾越,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令他难忘的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她以年轻女皇的风姿骑马而过。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腾越。”[2]101这一女子虽然裹着小脚,但仿佛令人看到了梅里美笔下火热奔放的吉卜赛女郎嘉尔曼。斯诺再次发挥了神奇的“跨文化”想象,赋予了云南边地女性神奇的魅力——类似于自由独立的西方女子大方、优雅、勇敢、高贵等气质,并且像赋予马锅头“典型的云南姿势”那样,把女子形象予以升华,即等同于“记忆中的腾越”。
显然,马锅头与女子都是蓬勃的生命强力的象征,也被斯诺寄予了对于云南乃至中国的厚望。不知在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他的眼前是否会闪现这两个令他过目难忘的形象?
在特定的期待视野中,斯诺颇善于在古老的云南大地,发现宝贵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东西。在蒲缥,斯诺这样写道:“在这里,你也许会感到过于粗野和不太文明,但是,那种茁壮的、无所顾忌的生命力赋予这里的一切一种原始的宏伟气氛。这儿的情景,含有一种欢乐时光的浪漫情调和士兵度假时充沛的活力。”[2]95显然,斯诺不是对落后愚昧的现象予以礼赞,而是从丰富多姿、活泼生辣的氛围中,感受到一种郁勃雄强的生命力。这与他对永昌马锅头、腾越女性的书写,可谓异曲同工。
实际上,伟大的中国作家,从鲁迅到莫言,都曾有感于国民性畏葸怯懦的缺陷,而在作品中疾呼一股蓬勃旺盛的活力。斯诺以上种种书写,亦应作如是观。
延续着这样的思路,斯诺对于边地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反思,亦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也认为这里是蛮荒之地的印象。在腾越,斯诺对于长久以来关于汉夷之别的定见——认为类似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属于“蛮夷之地”,从而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色彩——产生了强烈质疑。他认为腾越的掸族(即傣族)文化,可能比汉文化还要古老。
某个以傣族为主的村寨,更是令斯诺大开眼界。当见到会说英语,且能对英、美文化发表独到见解的土司时,斯诺十分惊讶。并且,“这里一切都非常清洁,好像在天堂里一般,世间是很难看到的,连小孩的脸和耳朵都擦洗得干干净净”[2]109。对于当地的音乐,斯诺原本未报以过高的期望,“但我立即发现我错了,这是真正的、地道的部族音乐。那宏亮的共鸣声,既充满活力而又丰满圆润,直在空中缭绕,时而用青春的激情,时而用天生的温柔,震撼着周围的气氛。……歌声清晰可辨,既不高雅,也不粗俗,而是真诚地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情。气质迥异的东方音乐,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得入了迷,压根儿把时间也给忘了”[2]111。在斯诺生花的妙笔中,可以看出,他既对超乎自身理解的村寨的一切表示惊奇,又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之情。进而言之,对于见多识广的斯诺来说,在对傣族村寨极高的甚至不乏理想主义的评价中,蕴含着对于淳朴的边地人民的厚望。倾情讴歌中国革命与人民的《红星照耀中国》,也许就在这样的书写中,已然孕育出了胚芽。
可以看出,斯诺对于云南的认识,也是随着旅程的展开而逐渐变化的。他笔下的马帮旅行,既有“跨文化”视域下的观照,亦有源自亲身体验的感受,更交织着颇具祈愿色彩的美好预期。传奇般的马帮旅行,既促进了斯诺对于云南边地人民的深厚感情,又使其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予以很高的期待,也为他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满贮情谊的幽默艺术
“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斯诺比较天真,也许还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可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1]3-4确乎如此,从《马帮旅行》可以看到,斯诺爱冒险的性格,对于边地每每产生超现实的想象,确乎有些浪漫主义,乃至比较天真的特点。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以传递事实真相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斯诺绝不会沉迷于浪漫的幻想。他会不停地思考,对一些愚昧落后或者不合常情的事物会予以针砭,体现出现实主义作家的清醒,以及特有的批判精神。但是,斯诺的批判,在艺术表现上却独具特色,即并非疾言厉色,而是常常出之幽默的方式,令人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笑。实际上,斯诺的幽默超越了严厉的谴责,是一种温婉的嘲讽。在这样的行文方式中,隐现着他对中国深挚的情谊。
斯诺的基督教家庭背景,使其经常对于亵渎神明的现象予以针砭。对于对待神祇的不严肃现象,尤其是大杂烩式的多神供奉,他总是特别在意,且不以为然。
斯诺曾在老鸦关附近的一处寺庙大殿里住宿,为此留下了十分精彩有趣的文字:“方丈和所有的和尚早已被部队赶走,去到现实主义野蛮的世界中去了。”寥寥数笔,凸显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神圣信仰的缺失和正常秩序的颠覆。不但人去庙空,且大殿里的各种神像,也因缺乏看护照拂而积满了灰尘。“神像跟我是老朋友了,在全中国各地的寺庙里我都见过。我想,我还是要指出我在别处看见的神像衣着都比这里的好,不信神的罪恶影响竟能深入到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我深表惋惜。”[2]57
从神像衣着,斯诺以小见大,洞隐烛微,批判了“不信神”之弊。这里亦隐现着中西信仰的不同。从传统上看,西方基督教教派林立,但是对于上帝的信仰,相对较为单纯、稳固。而在古代包括近代中国,尽管儒、释、道三大文化派别都有众多的信徒,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宗法性的传统宗教。“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祭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祖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成为慰藉中国人的心灵的源泉。”[9]所以,在中国传统信仰中,儒、释、道既经常出现鼎力而逐的局面,又相互融合、吸收,同时又往往与其他种种具有宗法性特征的天神祭拜、祖先祭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柳宗元的诗歌《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有这样的名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意谓世人对佛经不求取真正的本源,而往往追逐一些荒诞之事,暗含对不纯信仰的质疑。
《马帮旅行》接下来对于寺庙里供奉的关帝的描写,同样既幽默有趣,又令人深思:“关帝老爷看上去表情抑郁,丝质头饰早已褪色,破旧不堪,眼神中的炯炯红光已经黯淡,好像成了近视眼。职司财富和人丁兴旺的神祇,躯体非常高大,差不多要碰到屋顶,他手中那个大元宝,因为年代久远也失去了它象征的金色,另一只手握着的那个男婴也亟待修复。神的目光里原有的慈祥,被一滴滴漏进来的雨水所破坏,所以他看上去既悲戚又沮丧。”[2]57-58关羽被中国佛教奉为守护佛法的“伽蓝菩萨”,出现在寺庙中本属正常,但是却以如此狼狈的形象示人,则很耐人寻味。当许多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予以崇敬,而往往带着求取索要之心待之的信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关帝老爷很可能就不招待见了。
斯诺幽默的笔触,既生动地展现了神祇久被忽略的现状,又折射出国人无坚定信仰之弊。他所批判的“不敬神”,也是对于国民应守持信仰底线的呼吁。鲁迅早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便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此处的“迷信”,既指对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文化艺术,亦是真诚的信仰之代称。而“伪士”,则是当时一些打着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既是欺名盗世以谋取私利之辈,当然也是没有任何信仰和特操之类人的统称。不管怎样,斯诺在《马帮旅行》中多次提到信仰问题,呼应了鲁迅的“立人”传统。越是在云南边地这样的偏远地区,他越是认识到了纯正之信仰,对于民众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同时隐含着对于急功近利、伪善欺瞒等不良现象的批判。
不过,斯诺极为幽默的神来之笔,既显现出举重若轻的艺术才华,又体现出一种较为温和宽厚而非鄙薄轻视的态度,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林语堂曾在《论幽默》一文中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斯诺的幽默,讽刺的目的是明显的,但是却不给人尖酸刻薄之感,亦看不出太盛的火气。而“我佛慈悲之念头”,确乎隐藏其间,这大概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马帮旅行》的幽默,总能让人感觉到字里行间的亲切。
斯诺非常注意对人物的观察、揣摩,往往寥寥数笔,便能活化出人物的神韵。由于往往出之幽默的口吻,这些人物总是形象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过目难忘。而其中善意温婉的嘲讽,则是非常明显的。
在老鸦关附近入住大殿之前,斯诺记述了与藏人相遇的故事。四十来个藏人带着礼品,来云南拜见当时的统治者龙云,遭遇了土匪抢劫。英勇的藏人发起反攻,把俘获的土匪交给了当地驻军。“他们满腔愤怒,抗议道:这个地方真不可思议, 护送礼品的人员还得以武器开道,一路打着过来,才能把礼品送给它的统治者。”[2]56这就用幽默的文字,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地政情之弊,同时也对天真质朴的藏人不理解官匪勾结,予以温婉的嘲讽。
再如,对于在大理大年三十街头汉人的描写——“他们没完没了地吹牛,为他们那些并不高明的货物讨价还价,咳嗽,吐痰,哈哈大笑,吵架,骂人,互相对骂,骂部族人,骂小孩;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尽情享受,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这一切多么令人难忘。”[2]69喧嚣扰攘的场景,传递出新年特有的火爆氛围。像吹牛、吐痰、吵架、骂人等,本身都不是什么文明之举,斯诺却予以充分理解,并且说“这一切多么令人难忘”,就有了很强烈的幽默味道。不管怎样,从中看不出丝毫的讽刺意味,却强化了过年的那种狂欢气氛——每个人都在尽情享受,仿佛尼采笔下的酒神精神再现。
在永昌,斯诺下榻在一处“挂着一块充满幻想的招牌”的旅社,名为“赤龙宫”——单凭这个名字就足堪发噱。见到里面卫生条件很差,他要店主人打扫。而年轻的店主人却不相信斯诺说的是真的,因为过去没有一个客人愤怒地提过这样的要求。下面的一幕同样令人莞尔:“我”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受到众人围观,大家纷纷聚在一起打听关于大扫除的故事。这就活灵活现地通过一个侧面,把当地居民不讲卫生的积习,以及对于新生事物无限好奇的特点,巧妙传递出来。很明显,斯诺深知,这一次“示范活动”,对于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的生活习惯,乃至敷衍苟且的国民性格,很难有实质的改变。不过,不同于此前来华的某些西方作者,极力夸大中国丑陋一面的“妖魔化”处理方式,斯诺的批评是一种温和的讽刺,且暗含着一种真诚的预期——发自内心地希望国民改变不良的积习——则是非常明显的。
德宏是斯诺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1931年3月6日,斯诺抵达干崖。当两个傣族青年奉土司之命来邀请斯诺做客时,他又发挥了幽默的本领:“问我愿不愿意赏光?我能不愿意!我太高兴了,仓促之间竟忘记了东方的礼仪,应先推辞三次方能应允,一口气就答应下来。”[2]107这就把东西文化之别,惟妙惟肖地传递出来,虽然带有一定的讽刺,但能让人感觉到毫无恶意。
据曾在燕京大学受教于斯诺的萧乾先生回忆:“斯诺教导我,当的是记者,但写通讯、特写时,一定要尽量有点文学味道。”[10]《马帮旅行》无论是记人、写景、议论,都有声有色、细腻传神,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最典型地体现斯诺艺术风格的,还是独特的幽默手段的运用。在对云南边地一些落后、愚昧以及不合常情事物的针砭中,幽默的笔法常体现出一种善意的嘲讽,并时或包含由衷而发的具有一定建设性的预期。总之,斯诺对于中国所表现出的特有的豁达,在在彰显其对这片土地的深挚热爱。
在勇敢的探险精神驱使下,斯诺以生花妙笔,书写了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云南现代马帮旅行。由于从异域观察者的视角出发,他对1930年代初的云南大地,有许多独特的发现,加之幽默机智、优美传神的文字,使得《马帮旅行》成为现代游记中的经典。在旅行过程中,斯诺既展示了对中国的深深热爱,又思考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文本十分突出的幽默风格,常体现为温婉善意的嘲讽,隐现着对于中国的深挚情谊。总之,斯诺在《马帮旅行》中的所见所感,为其后来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写出不朽的《红星照耀中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充满魅力的《马帮旅行》不应被忽视,而应该被重新发现和解读。
注释:
① 斯诺记述在云南旅行的游记作品,在其生前并未结集出版。1991年,由罗伯特·M·法恩斯渥斯编辑,这些文章与斯诺在其他地区旅行的游记,被首次辑成一书(Journey South of The Clouds),由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帮旅行》,收入了上书中首次被译成中文的有关云南的游记(少部分内容写到进入云南之前经停的越南)。此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即上述作品结集,下篇实为斯诺回忆录《复始之旅》中关于云南经历的内容摘录。本文所探讨的《马帮旅行》,即此书的上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