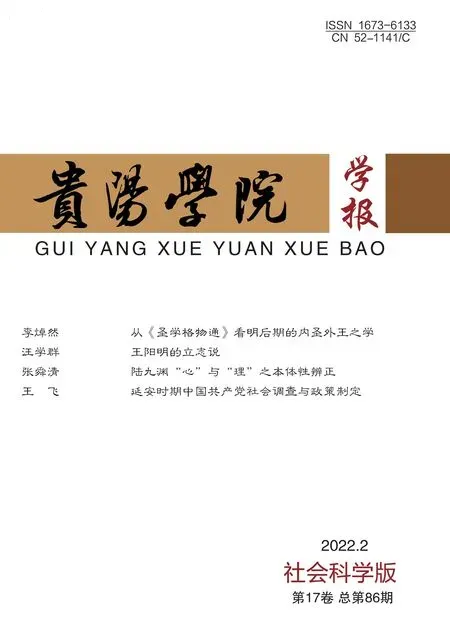多元与同质之矛盾的调适
——论阳明的良知对都市文化内在紧张的消解
蒙莉橼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学者们依自身学术之所长和所处之环境对当代都市文化做了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话语谱系:一方面是以经济学、社会学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认为都市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伴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掣动,这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另一方面是以大众文化、都市文学、都市艺术、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时尚文化等“浅表”,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及政治经济学的眼光与考量,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在哲学方面,一些学者把都市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过融合,研究主要为了解决面对大都市中出现的社会、文化、文学、审美、消费等普遍性问题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在都市化进程中人自身的异化。以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消费、人的全面发展等论述为理论基础,都市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用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生命体验与杂乱的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以期在重重矛盾与困惑中为当代人实现他们的生命自由与本质力量揭示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与哲学相结合更丰富了都市文化的理论内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加速了人口、文化、资源的流动,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都市文化。多元性成为都市文化中重要的特征,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突出,并且主体对象的需求呈现多元性的特点,但在都市空间简化和分类的基础上,人们行为模式同质性增强了,价值体系也渐渐同化,满足方式在都市文化的规范性下形成了同质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多,矛盾逐渐凸显。虽然有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减少都市文化中人自身的异化,却容易过于强调普遍性而忽略了人内在的自主性特点,容易产生“隔阂肤廓之论”。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阳明学良知的普遍性和个体性入手,以及良知本体与工夫的统一的角度,试图将都市文化矛盾放进哲学语境之中,尝试深化都市文化与哲学的融合,以此寻求解决之道促进当代都市文化的整体发展。
一、当代都市文化的存在基础
在都市文化的基本结构要素里,首先与其相关联的是“城市”,不研究城市的原始发生、历史源流、在不同民族区域中的表现形态与内在结构,以及城市自身特殊的发展与演变规律等,就不可能使都市文化模式获得它在质的意义上的规定性。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以城市为依托,没有城市的存在,就不可能有都市文化生产出来。尽管我国自古就有关于城市的描述,但对于城市的定义却一直没有定论。从具体的城市经验来讲,城市不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堆积,而是多种文化堆积并不断进行着新陈代谢的生命有机体,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城市与人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解为一种大型的通过人口集中形成起来的聚落,并且是以非农业活动为主,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空间系统。城市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的,又不同于同样是人工创造的园林、庄园,因此对城市的界定,要考虑历史意识和比较意识。
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其影响早已超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成为全球性的国际枢纽与中心。都市环境产生了都市文化,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多种文化形态。都市文化是在岁月流逝、社会变迁、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形成的普遍社会心理深深地影响与规范着人的内心追求和外在行为。人们在不断向都市聚集的过程中,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蔡尔德指出:“固定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把许多自然活动固定为一种终身职业的概念,束缚于某种单一技艺的概念,大约都起源于城市确立的过程中。”[1]因为人们的活动日渐集中于某种特定的劳动或职业,进而丧失了其他活动的潜在能力。也就是说,人们处在都市中,自身的完整性已经被割裂,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身的个体性,从而保障都市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稳定和协调。所以,都市生活由密集的人口组织起来,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行为和个体性,就需要制度来协调、保障都市生活的有序性,这种制度也是都市文化的体现。但是,人类活动的固定化倾向于简化,简化活动的外在形式会限制城市活动的多样化,导致都市文化的内在活力和机能被损坏。在都市文化多样性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虽然这种需求是多样性的,但满足方式却同质化。多样性和同质性的矛盾在都市文化的发展中进一步加深,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情况增多,但人们所采取的方式又高度一致。看似丰富的都市文化,实则隐含着人们的精神空虚。所以,首先要确立人在都市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满足主体在都市文化中的高层次需求,进而实现个体与规范的统一,并促进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
二、良知观照下当代都市文化的规范性与个性解放
当代都市文化中主体的自我情感意欲和普遍的规范、礼仪具体表现为何种关系呢?如何才能使主体的行为既符合规范制度又不失活动的多样化,同时也不损害都市的活力和机能呢?王阳明指出:“心之本体即是天理。”[2]54用“天理”来定义“心体”,把心提高到天的地位,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而心是人的一部分,所以确定了“心”的主体性,也就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6可见,心还是道德的、价值的存在。当心体发用于“见父”“见兄”“见孺子”之时,心体便自然会作出“孝”“弟”“恻隐”的道德判断。所以,一般的规范制度作为行为的调节者,不是主体之外的异己律令,它只有内在于主体的“心”中,与“心”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规范和调节主体的行为,并充分体现其自愿性。通过这种融合,主体在都市文化中以此获得了双重规定性:一方面是以外在的制度、礼仪为内容,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另一方面又带有主体的个体形式,呈现出个体解放的态势。在以制度、礼仪规范都市人的同时,王阳明肯定了主体具有个体性的方面。个体性首先通过“自思”表现出来,“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2]1077。自思在主体活动过程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通过自思才能对外在的制度规范、礼仪有深刻的认识。主体意识表现在意欲、情感方面。“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2]103主体情感欲望的表现具有因境而异的特点,所以不具有重复性的特殊性质,也正是这样才从另一面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性。
王阳明的良知是普遍的规范与个体的意识的合一。就其本质而言,主体内在的规范不同于外在的规范,它并不是以强制的方式迫使主体接受某种规范,只有把外在的规范变成普遍的道德律转化为个体的信念、情感、意向等内在的道德意识,才能有效地影响主体的行为。伦理观念渗透于个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普遍的规范与主体的情感、意向、信念等相融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融合,外在的规范才获得了内在的力量。如果道德律归结为与个体相对立的强制性主宰,那么普遍的制度、礼仪也就同时嬗变成为毫无生命力的抽象训条。不以普遍的制度排斥、抑制人心,王阳明的良知就肯定了这种普遍之理与个体的道德意识的统一,旨在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制度、礼仪。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体行为通常表现为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一方面,社会形成的普遍的规范,只有内化于个体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行为能力,如果离开了确定的个体的思维,则它对主体来说只是潜在的、抽象的性质;另一方面,个体只有与普遍的规范相融合,才能真正获得理性的品格,使现实的行为符合制度规范。一旦撇开了普遍的规范,它只能是一种无法在主体间加以传递和验证的神秘直觉。所以要把外在的规范与主体内在的意识从抽象的统一上升为具体的统一。在阳明学里,具体体现为通过天赋而达到的吾心与普遍之理的合一。“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2]112天赋予“心”的“理”,在事父、事君的过程逐渐展开,表现为具体的“孝”“忠”的道德意识,这个过程就是普遍与个体从抽象的统一上升为了具体的统一。“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2]91也就是说,循理的过程就是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统一开始摆脱了抽象的形式。理通过对“心”的制约使自身成为普遍之理的现实内容;主体通过循理,又使自身得到了提升。于是,王阳明实现了普遍之理与“心”的合一经历抽象转化为具体的合一。如果仅仅把统一停留在抽象的阶段,而没有将其具体化,则会导向“专求本心”。因此,在当代都市文化中也具有同样的道理,在把外在的规范内化于个体之中后,还要通过现实的行为把外在的规范与主体内在的意识从抽象的统一上升为具体的统一,才能把外在的规范制度的强制性转化为主体内在的制约性。
主体同样具有二重属性,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本质上不是凝固的、未分化的直接统一,它只有通过辩证的进展才能获得具体的规定,而这种辩证进展又往往以对普遍规范的认知在主体认知、评判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实践的辩证进展中,对普遍规范的认知逐渐展示其丰富的规定,普遍规范通过主体的体认融入于主体意识中,并构成其具体的内容。一旦离开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来理解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二重结果,或者普遍性被个体性消融,又或者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王阳明的良知通过对心即理的具体规定,扬弃了普遍性与个体性抽象的统一,也避免了两者的分离。王阳明的良知作为自心与普遍之理的统一,为主体提供了内在的权衡。他首先强调,良知是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2]86把良知看作主体自家的准则,是肯定了主体在判断是非善恶中的能动性,“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2]826。主体对自身行为的动机,并不取决于外在的规范,而主要是依靠主体的自我评判。也就是说,行为及动机往往是千差万别、形式多样的,普遍的规范虽然能为评价提供一般的准则,但它们无法穷尽一切具体行为,这就决定了自我判断不可能完全根据外在的细则条例进行,它更多地与个体的动机、情感意欲、良心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尤其突出了主体性在都市文化中的重要性。
但是突出了个体性的重要性,又难免陷入一己私念之中。因为过于强调个体性就容易单纯地从个体意识出发,而无法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比如:“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2]27也就是说,一旦把内在准则等同于自身,则会对同一对象作出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判断,这不仅会造成阳明学理论上的矛盾,而且在实践上也会导致各行其是。所以,个体性的行为动机和评判标准必须与普遍性的规范联系起来。正如王阳明所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2]1095以良知为准则而做出普遍的是非善恶判断,而这种普遍判断又是以良知“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为前提。换言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而带有个体的形式,但同时又要与外在的制度、礼仪为一,故具有普遍的内容,于是个体就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而成为“公是非,同好恶”的标准。
当普遍性和个体性从抽象的统一转换到具体的统一后,主体以普遍的制度、礼仪为内容,就必须自觉地遵循内在的规范,这就体现了自觉自愿的原则。王阳明对主体行为的自愿选择提供了这样的依据:“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2]68其中“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就体现了主体自觉地以普遍的制度、礼仪为内容规范自己的行为;而“自慊”则体现了主体的行为合乎于自身内在的意愿而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和满足感。主体的行为应该出自于自身内在的意愿,而不是被强迫遵守某些规范制度,只有按内在的意愿自主的行为,才能体现主体的真心。换言之,这种自主自愿的关系表现为:自愿总是以自主为前提,主体的真心就是自主选择的体现,如果主体完全被外在的规范所强制,那就无自愿可言。只有尊重主体的内在意愿,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才能使当代都市文化日有所进。王阳明还以判断是非善恶为例,对自愿原则作了这样的阐述:“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2]90承认主体的自主性,是对主体行为评价的基本前提。只有当主体的行为不受外在的强制,而是出于自愿的选择时,才能对该行为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对于个人愿望的软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本质的残酷,变成对于体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个人的伦理理性的残酷。”[3]所以,自主性是与主体的自愿性相联系的,无视自主性,必然会导致压抑主体的内在意愿,而表现为对主体的否定,这是对主体的残酷。
三、良知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促进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
主体的行为有符合当代都市文化的规范制度的,也有不符合的。这种外在的制度只处于本然的状态时,并未为主体所自觉。就是因为外在的制度还未转化为自觉意识,所以主体虽然明白有规范制度的约束,行为却难免与都市文化的制度规范不符。这就需要主体通过后天的工夫修养,才能由暗而明。在阳明学中,用良知来体现表现为:“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2]44良知只有通过后天的致良知工夫才能由暗至明。实际上,王阳明作了本然良知和自觉良知的区分:对先天良知的自觉把握必须借助后天的致知活动,通过致良知完成从本然良知到自觉良知的转变。换言之,把都市文化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制约之后,再借助于主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从而使主体的行为充分地符合制度又不失自主性。
肯定主体的行为必须出于主体的内在自愿,意味着肯定了个体具有独立的人格,个体的独立人格是相对于都市文化整体而言的,由此就有了“己”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关于“己”,王阳明明确提出:“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2]33“为己”是从主体自身出发,不依附于他人,以此来体现对自我的肯定和重视;“克己”是自我抑制;“成己”是主体的自我造就。“成己”是“为己”的最终目标,“克己”是实现“成己”的手段。人格是主体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人能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资格。随着都市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得到了更丰富的都市文化的内在精神与灵魂。而都市文化的发展以都市为依托,与此同时人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和挑战。在当今社会之中,人格在都市的发展中受到不断地侵蚀。人们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人们的道德意识逐渐被过多的私欲蒙蔽,过多地沉溺于对物质和精神欲望的奢求;抑或是处于都市环境中时,常以牺牲个体性来保障都市整体的稳定和协调。不管是哪种,都无法积极地促进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当代都市文化已经失去了其内含的活力和机能,多样性和同质性的矛盾更为凸显。
王阳明的致良知具有生命的“真己”工夫,它不能停留在嘴上,不能停留在训诂、考据的辨析上,不能停留在理论的凭空想象上,而必须落实到人的现实生存之践履上。于是,王阳明把致良知的实践过程分了两个维度和三个层次。首先要建立起个体的“主体性”,为“个体”转向“主体”提供条件,在人格上才能获得独立、完整。然后通过主体的行为活动把它呈现出来,把它切实地体现到都市文化的日常生活、生产中,体现到各种对象性交往关系的情景中。这样,主体经历着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也促进着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而致良知的三个层次则体现了主体认识水平的逐渐深化:“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2]80一方面,致良知是连续不断的。今天致良知只代表今天修养的长进,不代表明天不需要做,致良知是一个过程,要不断地做工夫。另一方面,在不同阶段,主体的认识水平不同,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不能超越。也就是说,主体对当代都市文化的体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程,当认识日积月累达到飞跃时,不是说认识就终止了,而是进入了新的境界,对当代都市文化的体认达到新的境界时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体的行为能力,从而达到促进当代都市文化发展的目的。
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没有把自己内在的规范切实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致良知”的能力不是人人都具有的,“致良知”是工夫过程,具有过程性。王阳明曾表示:“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2]19这是在说主体对它的把握,总是由粗入精,具体就是“初”“久”“再久”这样一个过程,致良知的过程与内容的深化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当代都市文化里,个体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与对规范制度的体认的深化是存在于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主体的内在规范由潜在转化为现实,具体即表现为“见道日精”,而这种深入又伴随着潜在的内在规范的展开。这样就把主体的内在规范切实地表现出来,并不断深化。
总之,当代都市文化在良知以及致良知的观照下,建立起了个体的“主体性”,不仅展现出了其内在的张力和活力,还在当代都市文化和主体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主体的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提升,达到了主体促进当代都市文化发展的目的。当代都市文化为主体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视域认识与研究文化,还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对象。世界的全球化加速了人口、文化、资源的流动,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都市文化,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减少主体行为的多元性与在都市文化的规范性下形成的同质化之间的矛盾,并充分发挥主体自觉自愿的原则,实现主体与都市文化的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研究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本文以阳明学关于良知及致良知论述为理论基础,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用来整理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个体与普遍的规范制度的关系,帮助人们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以期在重重矛盾与困惑中为当代人实现他们的生命自由与本质力量揭示一条历史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