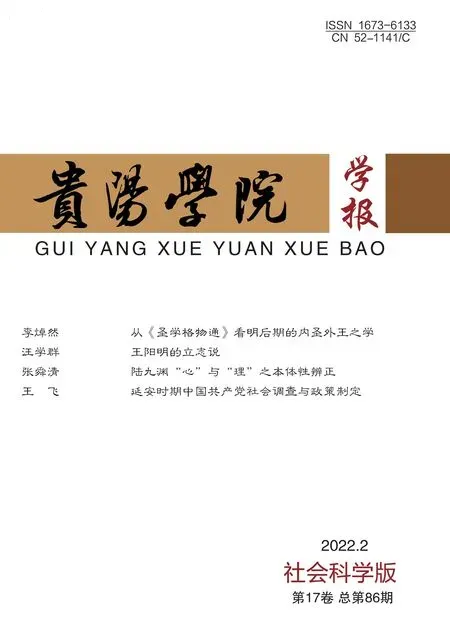新乡贤主体多维构成下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选择
成剑琦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乡贤文化在中国流传已久,是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许多地方积极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将“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学界对于新乡贤的定义及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开了深刻的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视角多为外在层面的制度保障措施和文化氛围营造,鲜有学者从新乡贤主体出发,分析并尝试解决由于其主体的多维构成导致的乡村治理难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乡村中有才德、有经济实力的乡村精英人物,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具独特地位。重新界定新乡贤主体,并对由于其主体多维性造成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新乡贤主体构成的多维性
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许许多多的新乡贤贡献智慧,发挥才能,共建美丽乡村。他们都是有知识、有道德,有经济实力,并积极参与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之中,积极建设善序良俗,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然而新乡贤主体构成具有多维性,各类主体由于生活居住环境、身份地位、职业、特长不同,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根据新乡贤主体所在地域以及其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的利益取向与作用发挥方式等,可以将新乡贤的主体构成分为四种类型。
(一)回乡型
回乡型是指生长于本乡村,因离乡发展,取得不小成就,由于富有深厚的返乡情感,返乡以自身现有成就为家乡建设作出贡献的新乡贤。
回乡型新乡贤一方面在本土长大,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且对本村本地情况十分熟知,有帮助家乡发展的意愿和热情;另一方面在其离乡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充足知识和经济基础,成为其建设、发展本乡文化事业的有力支撑。这两方面使回乡型新乡贤在本村实施各项文化建设措施具有权威性。此类新乡贤主体包括退休干部、成功企业家、青年返乡服务精英等。如安徽省马鞍石市农民企业家鲁礼玉,其在“添绿自然、产业报国”的理念驱动下,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回归家乡,通过在家乡捐资修路,扶弱济困,热心帮助乡亲创业致富,促进家乡建设[1]。以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等在退休后自觉返乡致力于改变乡村落后面貌[2]。
此类新乡贤主体,因乡土情怀的感召和自身强烈责任意识,自觉返乡并以现有成就帮助家乡发展,一方面通过资金投入或亲身加入家乡文化建设,直接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另一方面,以自身不求回报,舍弃优越生活,返乡促进家乡发展的榜样精神,作为乡村道德榜样引领并重塑乡村价值观念,推动形成乡村精神文明风尚,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二)侨居型
侨居型是指在本乡长大,在乡外发展,以投资等不回乡的方式推动家乡思想和文化建设的新乡贤。此类新乡贤因离乡时间长,工作、生活场所固定且不便迁移,只能采取投资建设学校、修建家乡祠堂以及推广家乡传统文艺等方式,帮助促进家乡文化振兴。
侨居型新乡贤因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以及国家号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具有权威性,虽乡土情结不如回乡型新乡贤深厚,但同样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贡献力量。例如:浙江上虞人张杰,虽定居香港创业,但始终心系家乡的教育事业,投入大量资金,在本乡建设教学楼,并成立教育发展基金,以此方式推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3]73。
此类新乡贤主体,因主要生活、工作领域及社会关系固定于乡外,无法回到家乡亲身投入文化建设,但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乡情感,愿意以间接的投资方式帮助家乡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当中。
(三)输入型
输入型是指由国家依据相关政策输入至本地的人才、干部,且在乡村的各方面建设贡献力量的新乡贤。
输入型新乡贤主要是指国家选派到地方的村干部,包括乡村内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一方面具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性权威,“是国家承认的权力机构内的成员”[4]。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具有权威性。相关研究表明:输入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带领村两委班子,立足于文明村建设,进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改造和建设,营造了良好的乡村文化氛围[5]15。
此类新乡贤主体,虽然不在本乡村长大,但是有责任意识和专业知识背景,并且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有长远的眼光,且是根据国家政策输入的人才,能够紧密结合国家政策规划,密切联系政府部门,有针对性、有规划地开展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四)内生型
内生型新乡贤是指土生土长于本地、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热心助人、热心公务、富有正义感,被村民所信服的对象,因此在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中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此类新乡贤主体一般为乡村道德模范或普通村民。有学者在浙江省某镇的调研中指出,该镇普通村民张新芬以帮助村民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传播无私的大爱,推动乡内形成互帮互助的氛围,为本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5]14。此外,全国道德模范林秀贞,也是通过善行义举成为乡村内的道德学习标杆[3]70,以自身的榜样作用,推动村内形成良好风气。
此类新乡贤主体,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经济实力和知识才干,未能促成乡内文化事业大变革,但其基于对乡土热爱,具有无私奉献的真心,以朴素的行动、不求回报的善举,成为乡内道德学习的标杆,促进乡村良好道德形成,同样为乡村文化振兴作出贡献。
二、新乡贤多维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局限性
新乡贤主体的多维性特质造成其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局限性。一方面,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侧重强调新乡贤的经济实力,关注建设性功绩宣扬,忽视新乡贤主体的道德品行要求及其道德模范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新乡贤主体权威来源的复杂性和利益取向的异构性,使得其在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难以形成合力,导致难以实施统一管理。主体多元,标准不明,监管不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新乡贤主体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局限性。
(一)功能定位不明确
新乡贤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面临的首要局限性就是主体多维下功能定位不明确导致其作用发挥混乱。
一方面,新乡贤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的主要功能定位不准确。新乡贤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的功能主要为引导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文化,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而在实际工作中,新乡贤功能多定位于经济领域,过于突出侨居型新乡贤地位,依赖其资金投入,忽视新乡贤主体的乡村道德模范地位和作用,造成新乡贤实际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时具有局限性。具体体现为侨居型新乡贤“不在乡”的特性,不仅导致离开乡村发展实际错误预估村庄发展未来趋势,影响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实际成效,而且长期依赖其资金投入,不利于乡村自身建设能力的培养,影响群众在文化建设上的主动性,制约乡村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存在交叉主体,对交叉主体的功能定位不明确造成其作用无法完全发挥或错误发挥。有一部分新乡贤主体是交叉主体,如输入型新乡贤,虽是国家输入的人才,但也有一部分恰好是本土人士,对乡村情况有足够的了解并且有深厚的乡土情怀。对这一种交叉主体的功能定位不能以偏概全,只发挥一方面功能,而是要详细划分,发挥其最大作用。
新乡贤主体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明确其功能定位有助于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带来的混乱局面,并为实现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奠定基础。
(二)在实践中难以形成合力
各类型新乡贤主体之间既因权威来源和利益取向存在差别具有异质性,又因各类型主体数量分布不均,缺乏主导性主体,作用发挥具有分散性,难以成为力量凝聚的统一整体,因此在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难以形成合力,具有局限性。
一方面,各类型新乡贤主体权威来源、利益取向以及作用发挥方式存在差异,在实践中难以形成合力。通过对新乡贤主体类型划分和具体分析可以明确,新乡贤主体的权威既是一种需要型权威,来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下乡村治理混乱重整的需要,又是一种魅力型、法理型权威,是新乡贤自身的道德水平、政治经济地位获得乡民或是国家的认可而赋予的权威,但是不局限于社会地位以及声望,也不再限制于本土的地域内。
回乡型新乡贤基于自身知识水平、经济实力以及对本乡村的了解程度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具有权威性。侨居型新乡贤则主要基于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除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的利益取向外,其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还包含社会声望的提升和自身形象维护等方面利益因素。输入型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主要由国家赋予,在实际工作中,除振兴乡村的目的外,其行为往往还包含着完成本职工作和创造业绩的利益取向。内生型新乡贤由于村民的信服在乡村治理中具有权威性,往往不求回报致力乡村发展。
不同类型的新乡贤或通过自身知识、经济实力,或通过自身品行获得乡村治理中的合法地位,以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这中间易夹杂不纯粹的利益取向,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以致不同类型的新乡贤主体难以凝聚成为目标一致的整体,共同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工作需要熟悉乡村具体情况的人才,如此才能把握群众思想动态和实际精神文明需要,才能发现本乡村的文化建设短板,高效、精准地开展本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因此回乡型新乡贤和内生型新乡贤作为本乡村土生土长的、具有才能的新乡贤主体,自然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导性力量。他们能够凭借对本乡村具体情况的熟知,整合侨居型新乡贤输入本乡村的资源,引导输入型新乡贤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促使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然而,因缺乏政策扶持且大部分新乡贤工作生活领域固定在城市,自愿回乡者占少数,本村青年人才又大量外流,致使新乡贤主体中的主导性力量缺失。同时,新乡贤主体中,侨居型和输入型占较大比例,其力量不能通过主导性主体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主导性力量的缺失和人员的分散导致新乡贤主体难以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中形成合力,致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效果不符合预期。
(三)难以实施统一管理
新乡贤主体具有多维性,同时多维主体间由于有“在乡”和“不在乡”的差异,难以落实统一管理,造成新乡贤主体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局限性。
一方面,在新乡贤主体多维性影响下,新乡贤主体所处地域具有分散性,呈乡村内外多处分布状态,因此新乡贤主体的数量及其作用发挥的质量难以统计。在此情况下,不仅难以平衡多元主体作用发挥的方式,协调其利益冲突,而且难以保证通过统一管理使其形成有效合力,为乡村文化振兴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由于新乡贤主体位置的分散性,对其工作尤其是侨居型新乡贤投入的资金数目、流向难以落实监督管理。因此,在具体实践中易产生漏洞,给一部分目的不纯之人提供可乘之机,伪装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奉献自身的新乡贤,实则为牟取经济利益,此现象易发生于侨居型新乡贤主体中。侨居型新乡贤多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者,其中不乏有以谋求更高社会声望、更多个人经济利益为目的者参与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当中。此类不良分子在不良动机的驱动下,不顾乡村现实发展,投资建设工程与乡村实际情况脱轨,乃至破坏乡村原本的文化环境,不能真正帮助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同时,内生型新乡贤中包含土生土长在乡村中的,因有经济实力而参与到乡村建设当中去的“富人乡贤”。缺乏统一监管的“富人治村”会带来村民选举中的“贿选”问题,侵蚀村庄民主,导致村民思想、文化需求难以得到真正满足。
由于难以实施统一管理,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易出现漏洞,不但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推进带来阻碍,甚至会影响新乡贤主体的信誉和威望,造成更严重的村民信任危机,使得新乡贤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的号召力、组织力以及道德模范形象受损,给具体工作的展开造成巨大阻碍,产生局限。
三、基于新乡贤多维主体的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振兴呼唤乡贤文化的回归,但在具体实践中,新乡贤多维主体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面临诸多局限。因此,应探寻针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局限性根源,寻求突破,选择路径,为形成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支撑力量。
(一)厘清新乡贤主体的标准和功能定位
新乡贤多维主体间缺乏明确的权责标准划分,权责界限模糊导致相互间产生利益冲突、作用发挥混乱以及监管漏洞产生,给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造成阻碍。因此,当前要发挥新乡贤多维主体有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作用,迫切需要建立标准,明确功能定位和权责划分。
首先,制定新乡贤主体的总体标准,尤其突出道德标准的要求。其一,基于权威来源、作用发挥方式、所在地区厘清并划分新乡贤主体标准。对交叉主体进行专门对接和管理,避免混乱。其二,从总体上设置统一道德标准,防止空有经济、政治地位而缺乏道德素养者混入新乡贤主体,破坏乡村利益,造成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不便。其三,明确新乡贤主体的作用标准、评价标准,确保其作用发挥的针对性、有效性。依据评价标准衡量新乡贤多维主体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价值,实现多维主体作用发挥侧重点的动态调整。
其次,依据标准,划分权责,明确新乡贤多维主体的功能定位。依据新乡贤主体标准,划分多维主体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权责界限,避免由于利益冲突,导致工作局面混乱以及监管漏洞产生,在此基础上明确定位多维主体的功能方向,突出主导性主体的地位,充分发挥回乡型新乡贤的知识才能,侨居型新乡贤的经济能力,输入型新乡贤的工作能力以及内生型新乡贤天生的乡村威望,实现新乡贤多维主体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针对性,促使其在实践中形成合力。
(二)构建整合新乡贤多维主体的专门平台
新乡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作用的发挥需要以专门的平台为载体,一方面确保新乡贤道德品质的培育有集中监督和评价的途径,另一方面通过专门平台的整合,使得新乡贤的多维主体能够以凝聚、专业的状态投入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首先,新乡贤各主体可以依托专门平台实现优势互补。专门平台为新乡贤多维主体提供交流的场所、讨论的空间,不仅方便新乡贤多维主体间沟通交流,同时也是他们了解乡村最新思想动态和发展状况的直接渠道,实现新乡贤多维主体作用发挥的针对性、及时性以及高效性。其次,专门平台提供新乡贤多维主体道德素质培育、具体行为监督的途径,防止混入“伪乡贤”的同时,能够加强对新乡贤多维主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保证其能够成为道德模范,成为影响乡民品行的真正榜样。最后,专门平台也是村民参与活动的空间和提出建议的空间,通过专门平台,新乡贤多维主体能够精准把握乡民的精神文明需要,有针对性地展开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当前,不少乡村已经建立起乡贤理事会等专门平台,并依托平台展开各类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这是应该积极学习的经验。同时,也要针对仍存在的问题对专门平台建设的目标、作用、方式进行调整,且具体平台建设应结合乡村自身特点,使乡村文化振兴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适应乡村发展,体现乡村特色。
(三)推进新乡贤多维主体优势互补
新乡贤多维主体作用发挥分散、缺乏主导性力量,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中无法形成合力。但新乡贤多维主体各自存在优势,可以融合多维主体优势,有效规避主体间利益冲突,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
新乡贤各类主体具有不同的优势。回乡型新乡贤是因乡土情怀主动回乡的特殊主体,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工作能力以及责任心使其具备较强的行动力以及广泛的号召力。侨居型新乡贤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补齐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资源短板。输入型新乡贤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工作能力以及前瞻性眼光,因此不仅能够以自身道德品质引领乡村道德风尚,而且有能力做好乡村发展规划。内生型新乡贤土生土长在乡村,洞悉乡村思想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交往关系,是乡民信服的对象。
因此,推进多维主体优势互补应以熟知乡村各方面情况的内生型新乡贤为指导力量,以回乡型新乡贤、输入型新乡贤为主要动力,以侨居型新乡贤为资源保障力量。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内生型新乡贤的指导,充分发挥回乡型、输入型新乡贤的号召力、行动力、决策力,整合侨居型新乡贤的输入资源以及乡村内部资源,共同建设乡村文化。需要重点关注作为主导力量的内生型、回乡型新乡贤的培育,随着乡村青年人才流失,这两类与乡村联系紧密的新乡贤主体逐渐减少,要建立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提升村庄发展价值前景,吸引人才回流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推动新乡贤多维主体优势互补,不仅可以突破因利益冲突和作用分散导致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振兴难以形成合力、缺乏统一监管等局限性,而且在拓宽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途径的同时,起到整合、凝聚力量,提升作用发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