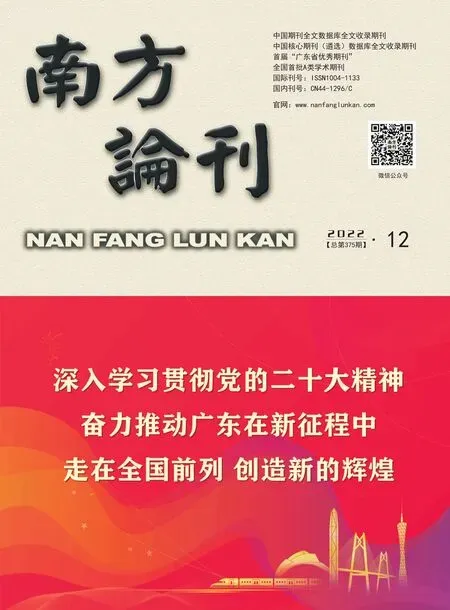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话语的传播、塑造及贡献研究
孙珠峰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一、革命话语勃兴之时代背景
政治学认为话语与政治和政策制定密切相关。话语(discourse)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其拉丁文原意为不受目的和时间限制的夸夸其谈。在法语中,“话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话语一词近似于聊天、即席发言、高谈阔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不经意的、没有经过修饰的一种语言。另一方面,话语是经过人们反思以后所建构起来的一套有着重要知识支撑的体系。这两方面的结合就叫做一种话语。福柯注意到,人们会因对话语的亲近熟悉而丧失反思的能力,这个时候这个话语就已经深深支配了言说者,离开了这一套话语,就不会说话,甚至不能思想,不知道该怎么思想。话语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成为言说者深深依赖的对象。对于要研究政治文本,以及包括革命在内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话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中,“话语”是一项重要权力资源。话语权通常被理解为软实力的一种形式。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政权”指的是“权力”,而借助具有魔力的话语的运用,就可实现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成效。反过来,有了“权威”,即有“权力”在运行的过程中摩擦系数就大大降低了。
何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话语”具有如此重要意义?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正当性的自我塑造”业已成为任何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而正当性的自我塑造正是通过对话语的运用实现的。“革命话语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密切相关。”[1]自我塑造正当性的重要意义凸显,是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政治正当性源头流变导致的必然后果。在传统中国,依照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政治思想,政治的正当性来自于超越的天理,或曰天道。“天理”首先是一个超验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其内涵是相当恒定的;其次,至于“天理”究竟是什么,人们对它如何认识,这是在儒家典籍长期灌输的过程中(尤其在士大夫阶层中间)形成的。人们对它的认知不存在大的差异。且没有任何人能够独享对“天理”的解释权。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马基雅维利时代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传播,人们对政治之“俗性”理解不断加深,“天理”这样一种同道德藕断丝连的概念已凸显出解释力的匮乏,这促使当时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能够为独立的、世俗化的政治空间提供正当性源头的学说。“公理”说便由此浮出水面。1895年,“公理”一词首先被康有为作为政治词汇使用。[2]之后这一概念很快被当时的各路政治思想家援以论说自己的主张。它不再是一个如“天”那样超验的概念,而是指社会层面上的共域性空间,即从社会到国家的各种“群”。“公理”观引入了历史进化论的逻辑,这又进一步使“潮流”成为一种解释正当性的理由。通过宣传打造革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话语”来塑造正当性这项工作的目的,不仅是要实现理论本身的自洽性,更重要的问题是该理论如何实现“社会化”,即最大限度的传播。这正是塑造革命话语必须思考的核心议题。
二、革命话语的本土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了激烈的“革命话语”争夺,争取自身政权和革命行为的合法性。早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逐渐领导了党和红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抗战初期难得有利语境(相对安全的政治环境、国际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全国抗战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的实践一步步地走向成功。”[4]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以广大民众能理解、认可、接受和支持的革命话语进行表达和传播,赢得了民心和民意,为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和善于冲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思想束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5]
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毛泽东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整体性的新话语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与列宁主义话语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高频核心概念使用不同,“人民”是毛泽东话语中的核心词。相比于“阶级”,“人民”具有更强的语势效果。“人民”同样是以“阶级敌人”的凸显而存在意义的。在革命话语结构中,它亦承载着甄别“敌”“友”的功效。
毛泽东是第一个熟练运用白话文撰写政论文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对白话文的出彩运用,使之成为大众化的政治宣传载体。他所创造的“大众化白话文”充分凸显了渲染和造势的功能,这种功效是以文言文或逻辑化白话文为载体的政论无法达到的。毛泽东与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活动家们,身处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即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进程。传统中国上层社会通用的文言文存在的两大问题——首先,文言文同人们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严重脱节,这也造成了上层社会和草根民众之间严重的隔阂;其次,文言文没有严密的语法结构,它是一种抒情文字,重在“以意动人”,而无法实现客观和精准的表达。这两点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至“五四”之际,语言文字要改造,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等个别抵制者。改造的方向是白话文,这一点没有多少争议。然而,至于这个“白话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在文学界是有两种不同声音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类“欧美派”文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使汉语成为一种适应逻辑思考的理性语言,应建立一套规范的语法结构,词语应当去情感化,使之能够价值中立地描述事物;另一派左翼文化人掀起关于“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抨击胡适式白话文是脱离民众的少数城市知识分子的语言,里面充斥着外国词汇和欧化句式。”[6]
大众化白话文得以最大限度地发生效用,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此前十年,虽然毛泽东已对白话文的巨大能量有所意识,但苦于无用武之地,因为倾听者不多,毕竟“苏维埃”“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这些议题在当时的中国形不成广大的舆论市场。而到了日本大举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民众的公共意识被空前激发了,“抗战”成了全民关注的话题。照理说,这本是蒋介石的一个难得契机——在“抗战”的义旗下把全民的民族激情调动起来,以强化自己的领袖地位。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总体来说他是个失败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民党官员一到公众跟前开口还是那套古旧的文言,这使得国民党在同民众,尤其是激进青年学生的互动中处于被动失语的地位。所以,它无力抓住这个塑造“抗战话语”的契机,只能由中共担当塑造“抗战话语”的先锋了。毋庸置疑,谁掌握了“抗战话语”的塑造权,谁就在国内政治角逐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下面我们以1937年10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例,看看他是如何塑造“抗战话语”的。“几个月来的土地丧失和军事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在的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不是人民的抗战。”[7]寥寥数语,“抗日”的主基调就被确定下来:“抗日”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同“革命”“民主”“人民的参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以,抗战的核心问题,并非正面战场上的交锋,而是“人民”参加政府的权利和自发组织武装抗敌的权利是否正在受到限制。因此,国民党向“人民”交出一部分权力,才是确保抗战胜利的首项议程。只要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大动作,那么不管它在战场上如何流血牺牲,它本质上还是“全民抗战”获取最终胜利的一大障碍。总之,凭借“抗战话语”的塑造和运用,中共不但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还俨然成了“全民抗战”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毛泽东成功地使广大根据地人民相信——从日寇铁蹄下夺回的这个中国是属于“我们”的,蒋介石无权分沾——这又为日后的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合法性。
三、作为大众化白话文的创始者,毛泽东独创的修辞特点
大众化白话文一方面保留了汉语本身的情感化、“写意化”属性,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的直接对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具体的修辞实现了具有感染力和凝聚力的革命话语。
(一)人民立场
人民立场是中共近百年历史长河中永恒的主旋律。人民是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赢得了人民就赢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靠人民办。”“我们共产党人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8]黄寿松教授指出卓有成效的人民民主话语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通过人民民主话语建设,中国共产党成功把最广大民众和中间势力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9]
(二)深厚的历史底蕴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首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毛泽东不仅继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推陈出新,在扬弃文言文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话语,表现出超凡的语言才能。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因为中共革命话语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在毛泽东选集中出现了大量的成语典故,如“愚公移山”“为富不仁”“井底之蛙”“实事求是”“重于泰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纸上谈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钦差大臣满天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小脚女人”等等。毛泽东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和格言警句等,并加以提炼改造,使之成为思想宣传的重要工具。中共所推广的革命白话文,创新性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通俗易懂的富有亲和力的形式呈现给人民,消除了与群众接触、沟通、交流、宣传的语言障碍,便利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三)“抽象化”与“再具象化”
斯大林主导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奠定了这样一种叙事传统,即将那些人们可直观体认的事物,上升到“理论”高度,借助抽象的符号系统予以解释。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不管是历史事件抑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必然要找到一个“阶级根源”的解释,然后把这个事件套在阶级斗争的元框架下重述。而毛泽东超越斯大林的独创性体现在,“理论化”之后会再来一个“形象化”。撰写一个个脍炙人口、生动活泼的小故事讲述斗争史,用漫画家的笔锋给反对者“画肖像”,使这些小故事和肖像画广泛流传。“钦差大臣”“山间竹笋、墙上芦苇”“懒婆娘的裹脚布”“下山摘桃子”的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张伯伦。这些形象的比喻已成为一代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语词本身具有的强烈褒贬功能。二十世纪以来的汉语虽不断从西语中大量引入新词,但很多词原本在欧洲语言里是一个中性词汇,一旦被国人使用就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情感色彩(如从“bureaucracy”到“官僚主义”的转变)。所以,在汉语里一个相同的意思通常都会有一褒一贬两个情感倾向截然相反的词汇。汉语具有高度情感化的属性,是无法单单依靠“白话化”加以改造的,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
四、结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有时代赋予“话语”的契机,以及苏俄舶来的革命话语蓝本,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站在时代前沿,熟练掌握和运用白话文这一新生事物,引导它向大众化的路径发展,从而实现与占绝对多数的广大底层群众对接。“话语式的权力战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热衷于追求话语权。”[10]新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成功地建构了赢得民心的革命话语,赢得了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的革命话语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占统治地位的话语,还随着大众教育和各种运动的开展而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今天,其痕迹依然依稀可见。
毛泽东非常具有创造性地、生动地、接地气地充分利用现代白话文促进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广泛传播,巩固和强化了他自己以及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处于极其艰难的困境下,凭借着丰富的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打造出生动的革命话语,难能可贵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大众化,也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软实力。随着新的社交媒体在互联网的沃土上蓬勃发展并渗透每个人的生活,民间语言表达习惯正在发生深刻转型,这一波转型与百年前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需要理论而且能源源不断产出理论的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执政话语和执政金句不断涌现,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