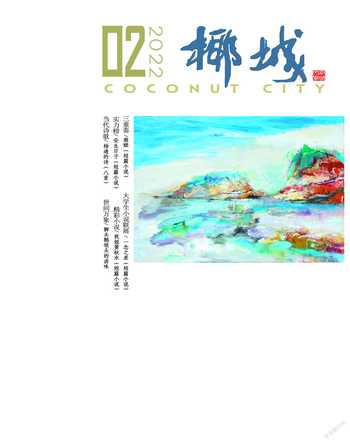狮头鹅领头的卤味
作者简介:鄞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从事散文非虚构写作,作品发表于《散文》《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清明》《黄河》《时代文学》《小说月刊》《星火》《四川文学》等,被《读者》《作家文摘》《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转载,出版《刀耕墨旅》《草根纸上的流年》等8部,散文《流水对账》获得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散文《失忆症》获得第五届大地文学奖;散文《风台》获得第11届“岱山岳”全国海洋文学奖;散文《在庵埠》获得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第五届“九江龙”散文奖;散文集《草根纸上的流年》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尘间·扉》上榜2021十大劳动者好书榜·散文榜;《失忆症》入选2021中国散文年选。
一
卤肉担子的香味从龟桥头那边袅袅飘来,似有似无,更像一妖女的长裳,先拖过这条家汇街。香味预先登场,然后,等待好久的担子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不用说,这是卤伯“开市”了。他的担子从伯公巷出来,当他的身影出现在桥上,卤味也跟随着上下台阶,摇摇晃晃踏上家汇街来。这是他的必经路线。
卤伯姓啥?要是较起真来,还真的没多少人能说出来。姓陈?姓杨?这镇上的姓氏看你居住的位置便可得知,卤伯住的伯公巷恰好是杂姓汇合,好在没人需要知道他姓甚名谁。卖啥就叫啥,后面根据年龄给个称谓,就像馃汁弟,卖馃汁为生,从几岁就随着父亲卖馃汁,人家就叫他馃汁弟,叫到現在七八十岁了,这个后缀都没换下来。
还是回到这掠过我家门口的卤香味来吧!谁家都会卤肉,谁家都必须在各种时节卤些卤味,但不得不说,卤伯的卤味是哪一家都卤不出来的。
他那一大陶砵放在木炭炉上的卤料,从他父亲(有的说是从他爷爷)那时候就没有换过,只有不断地添加,再添加。谓之陈年老卤。
这陈年老卤的香味一出场,就像街口的大榕树,一下镇住所有人的心。香味从你的鼻子进入胃口,进入肠子,你会发觉自己更加饥肠辘辘。卤伯的担子,前面是可以切肉等的家伙工具,后面才是真正的主角,那一大砵热腾腾的卤味,还在文火中,火候极好,极小,保持热度温度,大了耗费碳木,也让卤肉烂了。
所有卤味在家已经制作好了,卤伯挑这担子出来,是需要半天卖完,从头到尾都需要保证卤味鲜美且不煮烂过头了。下面的炭火刚好够上温度,这在他来说熟稔可比《卖油翁》了。卤伯虽然不认识卖油翁,但他熟悉这个镇的所有角落和每户人家。
就像人家熟悉他的卤味一样。
想想,他走了一辈子,哪家有多少口, 哪家卖啥东西,他若不知道,还真的没有人知道了。卤伯的担子里卖的啥卤味,大家也都熟悉,五花肉是主打,还是猪头肉,卤蛋,他的卤砵里的东西,就那几样,甚至没有我们过年、中秋时的卤味多。可他出现在物质疏淡的素日里,那些卤味,更有着朴素里的奢华。
卤伯的担子,填补了各个节庆之间的漫长时段。
担子来到我家门口,基本上该有的东西还是有的。比如五花肉,猪耳朵,拿着盘子出门的邻居,等着他放下担子,掀开后面卤砵的木盖,一股带着褐色的烟随着盖子升腾而出,这股香气毫无商量地串进家里,甚至溜进后院。让做饭的外婆也得为这香味犹豫一下,今天能否多点超支,打点牙祭。
买者点的五花肉被一双长筷子夹上来,放在前面垫板上,被卤成鲜亮的熟赫色猪皮,带着一层白一层褐的肉,微微颤颤地立在主人面前,卤汁顺着垫板流进下面的杠里,五花肉就等着切片,这块半月状的肉一般不用全部切完,只需跟卤伯说大概多少片就行,因着肉刚在砵里捞上来,甚是热,他在切时不是那么快,一刀一刀有节奏地下去,你看差不多就叫停他就行。
剩下的那段肉,回到后面的卤砵里,切好的肉整整齐齐码在买者带来的盘子里,像供奉的祭品一样端正,再给浇上一勺砵里的卤汤,这个节眼上,买者会再跟卤伯多要一勺子卤汁,这个多浇上去的卤汁,足足可以多下两碗饭呢!剩下的那节五花肉放回砵里,继续盖上盖子。粘板前面是各种调料,芫荽、葱粒、蒜泥醋等,葱粒、芫荽继续放在盘里的五花肉上,一下装点得光鲜亮丽。他会再给你的小碟子里装点蒜泥醋或辣椒醋。
芫荽、葱粒叫做“叠盘头”,形容装点门面,也是用这个词:叠盘头。它比“花瓶”什么来得更准确,更具深意和解读。鹅肉、鸡肉等大菜,切好了码在盘子里,也是需要“叠盘头”的,没有“叠盘头”,就像一个女人出行,没有妆扮,素寡了。芫荽、葱粒、芹菜等的妆扮,熟赫的、生赫、橙色、黄色的肉,点缀翠绿的配菜,美色可餐,色先诱人。辣椒醋更是在一旁盈盈笑着,碎红色的笑颜,恁是谁都招挡不住。
哪怕买几片肉,都能让这餐饭充满喜悦和期盼。事实上,我仅仅能得到的是卤汁浇饭,那卤香已经足够开心好几天。
二
像春节、元宵这样的大节庆来临,是有日历里安排的步伐的,各种物品大件小件,大至衣裳,细小至调料、竹箕竹筛工具的准备,阁楼上那些积满灰尘的衫箕、米筛、簸箕、筐头、炊盖、甑笼需要拿出来清洗,它们堆在那里就是等着这一天。
这样的节前,就像要演一出潮剧,让人心里开始生起盼望和喜悦。
节庆期间,一家的重头戏自然是卤味,卤味自是卤鹅卤鸭唱主角,既然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卤味,每天走街串巷的卤伯便被我们忘在西北角,他好像也知趣而回避这大节日。我们自家做的卤味,足够热闹一个月。当我良心发现:卤伯这个时候做什么去了?却是提了个不识趣问题,反正我们每个人都顾不得他了。
具体而琐碎的事情需要我们忙碌,即使是确定新衣服,也需折算布票,扯布、量身、缝纫,即便是讨论今年家里轮到谁做新衣,都是再三衡量确定的,这个周期都需要个把月,此是另话。而卤鹅的共同的节庆,当然它出场自是大的节日:春节、中秋、元宵、六月半……家里的腰包足够时,小的节日也可以做成大的了。
卤鹅之外,充裕点的,再来一只卤鸭,这一大鼎的酱油汁,还有备好的各种卤配料。那可是一堆中草药般的香料,我以为是越多越好:南姜、八角、桂皮、草果、豆蔻、香叶、小茴香、黄栀子、花椒、陈皮、辣椒、丁香等,我无法辨识出那么多,但八角、桂皮、香叶、花椒、陈皮、辣椒是认识的,香料缺少的我们可以从邻居那里去要一点,大的配料如八角、桂皮、草果、小茴香等供销社有卖,这堆东西一直布满灰尘架在柜子最上面,十多二十种,需要什么,售货员会扯下什么,看都不要看,顺手扎成一扎,估量着告诉你多少钱。
酱油呢,也是找供销社打的。每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吃了多少粮食,能使唤了,便叫“打酱油”。当他(她)能打酱油了,说明来此世上开始有一点用处了。我在这个家庭里没白吃饭的体现就是去供销社打酱油,当然还买其它东西。
当我拧着黑乎乎的玻璃瓶往供销社走时,我得边留意瓶子不要碰到地上,有玻璃摩擦地面的感觉时,就得赶紧把瓶子往上一拎。
供销社位于陈厝街和家汇街交叉路口,一排老旧木板拼成的转成90度角的铺面,一盏昏暗的灯光根本覆盖不了半边店,店员反正也不是凭着亮光干活,而是凭着熟悉的记忆在操作。在我心目中,供销社是个什么都有的地方,它聚集了我们日常所需的一切物品,也聚集了整个小镇所有渴望的眼光。
我们的生活与之息息相关,除了需要票的东西,如花生油、肥皂等,我们得攒几个月,才能如遇节庆般大张旗鼓地买。在散淡的平时,我们也隔三岔五与之打交道,自然是很多不需要票证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如酱油、鱼露、盐、醋,还有米酒、茶叶等,供销社最多的供应就是酱油、鱼露了,门面后间的仓库里,黑乎乎地一缸缸酱油和鱼露,缸口用红布扎紧,厚厚的一层灰和泥,这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打出来的酱油和鱼露可香得很。
平日里每次去打酱油一般是打五分钱,五分钱的酱油,是店员手里那把长柄竹探打上来满满的一筒,好的運气就是那把竹探满满的一筒。当酱油随着长柄,在尾端的筒子里,微微颤颤地被提出缸,溢出的多,留着竹筒里就少。而竹筒里的多少我们不能有异议,店员一不高兴干脆不卖给你。
这一竹筒酱油通过漏勺装进瓶子,回到我手里。
我会仔细地对着我家酱油瓶子上的刻度,看看这次打的多了还是少了。虽然少了他也不会给你补,反正5分钱是一筒,1角是两筒。我们的运气全部在店员随意的手抖中完成。
当某个节日嵌入我们的生活,家里觉得要卤一只鹅或鸭子的时候,卤料是少不了的,自然也是在这供销社买,镇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卤料放在哪里,有时候店员傻楞,我们反倒给她指方向,我会踮起脚,手伸向旁边那排木架子,“喏!最上面。”卤味像一堆稻草一样堆在那里,沾满了厚厚的灰尘,终于盼来了见天日的时刻。
再多的灰尘,存放再多的时间,也不妨碍它们被卖出去。八角桂皮草粿花椒等,还有好多不知名的植物,放在这里的都是卤料了。这东西我们阁楼上也堆有一些,所以不用花钱买,不仅是我们家,镇上谁人家里没有几样卤料?这些植物,放在家里又不长虫儿,不用花钱,哪里扯了来,放些备用。
我想这也是供销社那里卤料一直堆放的原因,当然有几种比较稀缺的还是需要专门过来买。
当我拿了一大笔钱,需要妹妹一块帮忙打酱油时,那种奢侈感足够我每一步都把街路跺得响亮。何况我身边还有两个跟班的妹妹,感觉我是个主儿。这不你瞧瞧,家里几个大瓶子都用上是什么日子?我们盯着店员手里的竹探,一次、两次、三次……他必须足足打够十次,才满了五毛钱。
甚至,店员最后还会为这个过程中抖落缸里的酱油,再多打半筒给我。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我会把这多加的半筒酱油不厌其烦地描述给外婆、父亲母亲听、隔壁阿敏听。半筒酱油给予我们的是一年辛劳岁月额外的奖励。
三
酱油来了,各种卤料繁文缛节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那只早已定好了的大狮头鹅,狮头鹅自是我大姨家养的,大姨家就是养鹅养鸭的农户。
每年年初,她会来借钱买鹅仔,说好等养到年底,鹅仔变成大狮头鹅,卖掉之后,就会还钱。可是每次卖了之后,她也就会忘了还钱,自个儿过富足生活。等到隔年又会来借钱时,她好像就忘了去年还有借钱这回事。而这事绝对不会忘了,因为鹅仔的本钱,每年都来一次。
这样一大笔本钱被她拿走之后,日子就成了念念不断的漫长岁月。外婆和母亲开始数着日历,掰着手指算着大姨该卖完了鹅,数着她该赚了多少钱。这钱得还镇上人家了,母亲每次替她向人家借钱,都得许诺大姨还钱的日子,并且把前因后续环环节节都排列清楚。什么节日之前卖完了大鹅,一只大鹅能卖多少钱,到时钱就回收了,就能把这笔钱给还了。因着母亲的面子和信用,每次大姨都能如愿借到钱。
可是,每次她拿了钱就杳无音讯了。而母亲却得在许诺的节日之前,东挪西凑地先把钱给垫还了,还得告诉人家是大姨卖了鹅拿钱还。而节日临近,也是大姨需要准时还钱的时刻了,母亲就开始焦虑不安,开始到处碰撞,为了替大姨垫钱还债而焦头烂额。
而大姨需要借钱的时候才会冒泡。
这样的常态成了我们诟病母亲的理由。我们甚至希望母亲能接受教训,因为外婆已经不再搭理她了,哪怕她再三哀求也无动于衷。
母亲还是认为要跟我大姨买大肥鹅,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何况大姨的狮头鹅确实不错,母亲本着给她赚一点钱的心,我们都赞同了。
宰鹅摊就摆在大榕树下,这行当帮你宰杀鹅鸭都不要钱,一地的鹅毛鸭毛即是他的报酬。轮到我们家这一只狮头鹅,宰鹅的阿坤乜了一眼,用手抓了鹅身,摇了摇头:“这鹅一点肉都没有,太老了。”他还是把鹅给宰了,剥光了鹅毛的白鹅拎给我们看,鼻孔哼出了笑声:“今年你们就吃这个?”
“竟然给了一只这么老的鹅卖给我们!”
一只瘦不拉叽的老鹅耷拉着脖子,老鹅不仅肉不多,而且肉太老咬不动。别说外婆咬不动,就冲那摸不到肉的骨架,外婆气愤得用她的拐杖敲打着地砖:“这个人就是不像话!”母亲一旁喃喃地说:“还卖得比别人贵那么多,本来贵一点也就算了 。”
“下次来我一定要骂她!你等着!”
外婆这股气好像很难撑到大姨下次过来,每天她都指着天花板,又敲打着地砖,走进走出。
外婆不借钱给她,因此也没有来自借钱的气。
我们的一锅卤料就败在这只鹅身上,而我惦记的是她还欠钱的事。大姨来我家只有一个原因:借钱。后来我发现一个:找吃的。那是我外婆去世后,因为我外婆在时会不客气地轰走她。我外婆走后,她来我家就开始开柜子,翻找食物。看来还是我母亲给惯着的。
母亲又是叨念着,借钱这种事是一幕幕雷同的戏,每年都要演它几遍,不仅仅是买鹅仔的时候,而借钱的理由很多。甚至我母亲发工资的日子也是理由。我母亲还没下班,可是,外婆在,外婆怒气冲冲地把她扫地出门:“小妹这个家要钱的时候多着呢!你这么好吃懒做,卖鹅的钱哪里去了?!吃喝完了就来?!回你家去!不许再来!”
大姨只要挨到母亲下班,外婆也就没辙了。母亲准会又借给她钱。
母亲明知她信誓旦旦,但只要钱到手,所有的话语就都烟消云散。“下个月还钱。”“3天后就能还。”“明天一定还钱。”这些都是门口的鸡屎,一瓢水就冲得干干净净了。
母亲一辈子就出不了她的怪圈,总在这个恶循环的烦恼中。外婆反倒干脆,外婆对她的厌恶从里到外,毫不掩饰。外婆赶她走的时候,完全像包拯,铁面无情。
母亲得找时间跑大姨村里去跟她提还债的事,但这需要母亲有空闲时间,一者母亲每天上班还得轮三班倒那种,二者大姨家离我们镇路途遥远,不仅得过公路,还得跑过好几个村落。纯粹靠双脚赶路这时间也摆在那里。
可是那一次是特别的时刻,让心急的母亲随即放下饭碗赶去她家,那还是个晚上。没有路灯的公路和村落,除非实在有十万火急的事,没有人会摸黑这样赶路的。
那是大姨那天来我家之后。隔天,我找不到放在枕头下的瑞士手表。这手表是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XX学校的奖励,爷爷的私房钱,外加一堆亲戚凑起来,给我住宿用的手表,相当于我妈两个月的工资。
这个瑞士手表是那个年代的奢侈。
家里丢了手表这大件事,晚饭时发现、宣布的,还只是在我家餐桌,消息还没扩散到邻里。二层低矮的阁楼,我们睡觉的地方,还有堆杂物。除了我们家里人,还有一个曾经企图从天窗进屋偷东西的贼,他还没进来就被发现了,这是我家族史唯一的事件。
这个阁楼没有外人涉足。
全家人脑子一回放,昨天就大姨来我们家,并且中午她还自来熟,毫不见外地上我们阁楼,钻进我的床铺睡觉。
就她来过。
刚端起饭碗的母亲已经憋不住,她知道她姐的德行,母亲毫不怀疑她干这事。母亲此刻脸色发红,我们全家人的眼光都投向母亲,母亲此刻直接受到了牵连。
母亲三下除二,赶紧扒完碗里的饭,放下筷子就出门,消失在黑夜中。我母亲是怎么赶夜路的,我们竟然只想着那只手表。
半夜,母亲从大姨村庄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瑞士表。
母亲无语地递给我,我们一家默默回归各自位置。
一只狮头鹅,自然无法与那只瑞士手表比。大姨卖给我们家老鹅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好歹母亲对买鹅的事不比借钱那样执迷不悟,我们需要时到大树下就能买到,母亲倒是喜滋滋地:“这鹅肥美,要大要小还能挑,价格还便宜得那么多。”
价格便宜一事被母亲说起,她倒是觉得有点愧疚了,她本意就是要照顾大姨的,谁知弄得一家都吃不好。买鹅这事后来也是大姨漏了嘴,那只老鹅卖给谁,都会被谁找上门退钱的。成了我家年货,顶多挨骂几句,钱还是能收到手的。大姨卖给了我们家,挨外婆骂,我母亲数落,反正脸皮厚点能顶这个钱也值了。
她庆幸的是这只谁都不要的老鹅能把钱换到手。
我差点把饭桌上的盘碗都收起来,还是母亲瞪着眼,我才作罢。吃完饭,大姨又轻车熟路地翻我们家的食柜。我大惊,明天准备去学校的两斤饼干就放在里面。可惜已经被她掘地三尺给找到了。
我默默地盯著她,她在吃,我数到二十块,终于站起来对她说:“我明儿拿去学校的,你干脆吃完吧!”
她的一张长脸漠然地对着我,还真的继续吃。
她是我长辈,好歹我不能说什么,可我妈也忍不住了,凑过来一看:“她明天去学校带着的,要顶一个月的吃,你难道可以把它吃完?”
母亲的声音带着怒气!母亲的话不成理由,而是母亲的怒气才能制止这蚕食。大姨若无其事把这袋剩下的饼干又放进柜子里。
小妹气愤地对我说:我都不敢吃你一块,她竟然给吃了大半。
我自然是不依的,我一个月的干粮这才剩下三分之一。母亲黯然不语,她跟父亲在房间悉悉索索翻箱倒柜后,晚上又跑了供销社,赶在我出发前把那个大缺口的饼干给补了回来。
我们不买她家的狮头鹅,可她照样需要我家的资助。
“我们村很多人盖了房子。我们不盖不行!”
“妈,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漏水呢!你能帮她盖新房?”母亲在我们的怨言中继续添砖加瓦。
“村里有人接了电话,我们可不能落后。”这理由只有电影里才找到,因为我家也没有电话,我们的落后需要自己努力。而借钱的大姨理直气壮,她家需要跟上人家。
只有不买她家的鹅是最好选择,我母亲也就在这事的扭转上显得明智,不至于一条道上走到黑。何况每次买鹅的钱先给了她,却得三催四讨,盼爹爹盼奶奶,在节前的最后一刻,这鹅才姗姗到来。而宰鹅摊已经收工了,虽然最终他还是专门生火帮我们处理好。
后来的节日,我们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在大树下的鹅摊买狮头鹅和鸭子,圈养在溪边,用个把月的时间养它还能增加三几斤。鹅的叫声催促着我们,准备各种粿品,开始浸泡绿豆黑豆,开始去大石臼那里排队舂米,这忙碌的做粿环节产生了很多鹅和鸭的食物,物尽其用不浪费,还能有条不紊地把卤味安排得更加丰盛完满。
父亲看着邻居的灶火都生起来了,越发显得着急,大灶的柴和鼎,一应硬活都是他扛着,而外婆、母亲,我们都分工派活,日子被填得满满的,甚至连夜连日,灶火起了,一般不停息,卤了大鹅之后卤鸭子,还有跟着粿品,打捞的时候竟然还需邻居过来帮忙,他们两人一个环节,动用扁担和梅钩,才能完满挑起大鼎里这只大卤鹅,大鼎接二连三地发挥它的热,灶下的火紧锣密鼓地,我们姐妹两个轮流。“加火”只听父亲一声令,我们必须配和这命令,马上让灶火旺热;“好了,停了。”我们随即熄了烧旺的木柴,却仍需保持灶里的火种。
大灶烟囱的烟在这条街上此起彼伏,基本是步调一直。慢了半拍一拍,这个年也就措手不及了。
正月初一,那是一切都要准备停当,包括春联已经张贴,鞭炮已经挂好,灶台更需要洗刷妥当。
一切都整洁而崭新。
四
一只大狮头鹅,经常要收拾一两天的细毛,虽然摊点给拔好了毛,剖好了。但鹅身上的细毛特别多,这个需要几个人打下手,宰杀好的狮头鹅和鸭子放在矮木桶里,两三只光溜溜的生鲜需要我们几个孩子干去细毛的活儿。双手泡在水里一天,都脱皮了,这个活需要尽快,手里的镊子,一根根把细毛从肌肉里面拔出了,也体会了一把“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这些活儿我们都熟悉了,一股节日的气氛鼓动着我们,累了站起来伸伸腰,真想不明白卤鹅摊的鹅,哪有那么多双手在拔细毛,即使鹅肉那么香,我们还是会自我满足:就是没有我们自己卤的干净,鹅绒毛一点都没有。
据说那些鹅毛随着肉吃下去,是不会消化了,只有等来年的杨梅上市了,吃新鲜杨梅,它就能把一年吃在肚子里的这些垃圾消化掉。
外婆看着我们蹲得都直不起腰,还在认真执着拾镊这一大桶东西,那个对应的借口像是宽慰我们,她对着拔得不干净绒毛的狮头鹅说:“等着明年吃杨梅吧。”可我不愿意那么难得的鹅肉带着不干净的毛,多么败兴!
卤伯的卤担子并没有卤鹅,卖卤鹅的是大榕树下的鹅肉摊。固定的鹅肉摊相对卤伯的挑担,显得气派了。
外婆发了退休工资的头件事,就是支使我去买卤鹅肉。在我們这里狮头鹅只有一种吃法:卤。除了卤鹅,鹅好像没有别的做法了,或许是卤鹅太过美味了,直接把其它做法给消灭了。有时外婆也自己亲自出马买鹅肉,那是我不在跟前的时候。我在跟前,这事情非我莫属了。
我会先在柜子里掂量哪个盘子合适装这四毛钱鹅肉,又能多打点卤汁。然后我一手拿着盘子,一手拿着四毛钱,为什么一定是四毛钱呢?鹅肉摊的鹅肉四毛钱是底线,最少四毛钱他才肯卖。要知道,这是卤鹅肉啊!无鹅不成席的鹅肉!四毛钱我们家可以买两三天的菜了。豪迈的外婆拿了工资就财大气粗,她是一定要打牙祭的。
卖鹅肉也有一套程序。他先切了几片鹅血垫在盘底,然后再看看切哪个部位,从铁钩上拿下已经切开了半截卤鹅,按原先的切口,平行斩开一小截,剩下的这大半只继续挂上去,这一小截鹅肉平放砧板,他的刀花熟练,一片片切了,左手掌张开,配和右手的刀,顺着把鹅肉放到盘子里,鹅肉在盘子里码得整整齐齐,感觉又满又靓,实际上是靠着下面那些卤鹅血在顶着。只有我才知道下面实在没有啥东西了,卤鹅血这个不用钱的东西,外婆会给我一两块下饭。这卤鹅血的味道,只有经常吃的人才知道它是上品。我后来甚至需要看到有卤鹅血,才肯买鹅肉摊的鹅肉,就是为了那入口即化、齿颊留香的卤味道,所有卤料的香气都融入,一下滑进胃肠,人之初的味觉在头顶回荡着。
自家卤鹅,自然也要卤鹅血,这样的工序也不少。即使再繁琐也阻挡不了我们,在我们双手的劳作下,不仅有卤鹅、卤鸭、卤大肠、卤豆腐,还有自家的鸡蛋添加进大砵里,让这个节日的陶砵呈现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这个陶砵,一直延续着节日的味道,主宰着我们的餐桌,直到里面只剩下卤汁,卤汁浇饭,香味依然从鼻孔出来。只是我明白,卤汁过后,陶砵洗干净,我们又需要漫漫时日的等待了。
带着故乡、带着童年前行,我一直浑然不觉。直到在异地,某些远去的卤味又回到跟前与我指认,我才知道,尝遍双脚所能抵达的地方,真正抵达心灵的最美味食物——那些卤味的浓墨淡彩,在人生的起点上向我反扑过来。
卤五花肉、卤鸭、卤蛋,我一直不厌其烦地在记忆里擦拭着那只狮头鹅,把它放进今天的卤砵里。
1601501186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