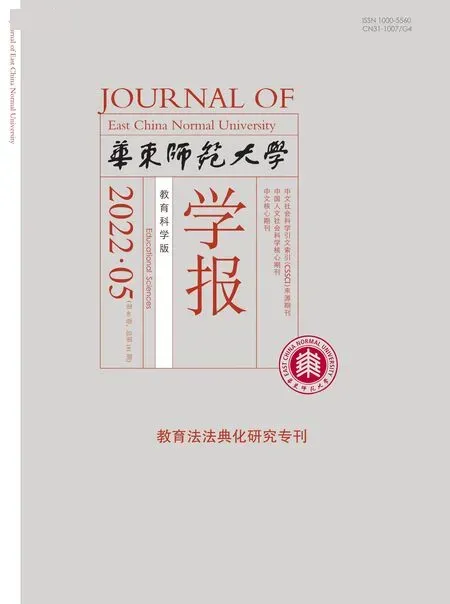论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基于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启示 *
申素平 周 航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一、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是重要的吗?
(一)确立核心概念是教育法典编纂的理性基础
随着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研究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的计划公布,教育法典化正式进入立法机关的视野(中国人大网,2021)。法典编纂不同于法律汇编,它更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体系性。在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或法系中,法典编纂的发展水准代表了其法律技术的高度(陈涛,高在敏,2004)。教育法要实现法典化,必须确保规范编排的逻辑理性,保证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撑,体现系统性与整体性(薛刚凌,2020)。然而,法典化的高度体系性需要有核心概念(zentraler Begriff)或基础概念(primaerer Begriffe)作为“阿基米德支点”,以支撑起整个法典体系的总论,并指引分则的篇章顺序与结构布局。德国19世纪的法学家弗里德里希·萨维尼(Friedrich Savigny)曾指出:“各种法律关系的概念,在一部有关于此的方案和内容的作品中,必定是最为重要的。”(萨维尼,2001,第57页)在法律构成上,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是组成法律的基本细胞。基于法律概念,可以构成法律规范,建构法律体系,形成法秩序,因此对法律适用至为重要(王泽鉴,2019,第23页)。可以说,大陆法系的法典是法律概念规范建构与精准适用的最佳典范。有学者指出,大陆法系国家教育法学科体系主要以法律概念在教育领域的适用为逻辑起点,以教育法规范教育秩序和调整法律关系中教育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学理逻辑为分析框架(秦惠民,王俊,2021)。这种分析视野与研究对象决定了我国教育法必须建立体系性思维,实现概念的精确性、稳定性与阶层化。因此,确立教育法典总论的核心概念是教育法典编纂的必要前提。
(二)确立核心概念是提升教育法学科体系性与科学性的客观要求
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法系一般认为学科的体系化不仅能提升学科的稳定性和规范效能,也能使学科对生动的社会现实保持开放(赵宏,2021,第3—4页)。对于以大陆法系为继受对象并以法典化为目标的我国教育法学科而言,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实现价值统一性和逻辑一致性是其发展的必然需求。在体系化过程中,形成一般性的核心概念是教育法学的基本出发点。在法律概念的谱系中,不同概念的地位并不相同,而核心概念因其抽象性、涵盖性与统摄性最强,因此也最适合作为法体系建构的技术工具与价值载体。在德国,极度抽象的“法律行为”概念是其民法典总论最具影响力、最具特色、最核心的设计之一,被誉为德国民法典的“承重墙”。经奥托·迈耶(Otto Mayer)改造的“行政行为”则是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并成为行政法学总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工具。德国法典的这一路径对我国民法学、行政法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民事法律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也是我国民法学、行政法学体系化所必不可少的核心概念。由此可见,法律概念是我们进行法律思维与推理的基本工具,是解决法律实践问题所必需的工具,也是传递法律语言的基础(许中缘,2007)。在某种意义上,法学是概念的科学、规范的科学与价值的科学,因为法律概念构建了“法律人的世界图像(Weltbild des Juristen)”(考夫曼,2011,第118页)。在法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至今仍具有深刻影响的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就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性概念,建构严密、封闭而无漏洞(Lueckenlosigkeit)的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法律规范(维亚克尔,2006,第415—420页)。
在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上,有学者持“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观,认为概念不过是规范的一种简要表达,但实际上,“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也是进行法律思维和推理的根本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法律概念对于法律体系和法学而言具有根本性,甚至要比法律规范更为根本”(雷磊,2017)。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更是认为法律概念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概念性对于法律的形成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将没有所谓的等同对待,也将没有正义存在。”(考夫曼,2011,第143页)正是如此,我国法学大家王伯琦先生在对德国概念法学的反思中才会说,对于现阶段的执法者而言,“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王泽鉴,2019,第17页)。这一断言对现阶段的中国教育法学而言也是十分中肯的。
就我国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而言,在法律问题、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但尚缺乏对学科体系意义上的核心法律概念的源流发展、规范适用作深入研究,这与民法学对“法律行为”,行政法学对“行政行为”,刑法学对“犯罪”“刑罚”等领域的丰富成果产生了鲜明对比。到目前为止,教育法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如何确定,它是如何利用抽象技术形成的、具有何种功能,又如何统摄整个学科与法典的,这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都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这在以往或许并非紧迫之事,但在教育法典编纂对法体系性提出空前要求的背景下,教育法学科体系化的重担已经落到了肩上。若再忽视对法律概念特别是核心法律概念的研究,不仅会阻碍学术共同体的深度交流,也会在实质上影响着法典编纂工作的开展与法典的最终质量。法典化既是教育法学建设难得的一个发展机遇,也是促进学科体系改革不可多得的良机。若能抓住时代发展机遇,立足未来需求,重新审视教育法学的核心概念,将能大大助益于教育法学的学理革新与知识增长。
(三)教育法典地位、模式与体例的选择离不开核心概念的确立
通过对民法典编纂与行政法体系建构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作为“阿基米德支点”的核心概念选择上,备选方案与终选方案可能会有多个。考夫曼在《法律哲学》一书中梳理了五个最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源、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与权利主体,其中,法律事实最重要的是“法律意义下的行为”(考夫曼,2011,第121—127页)。从法典编纂的经验看,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毫无疑问是法体系化最重要的核心概念。首先,民法典的编纂即是以“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作为核心概念的。选择“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抽象概念使得德国与我国民法典“总分则”的体例得以实现;在各编的安排上,民法典则是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物、债、婚姻、继承等)形成各编。其次,传统上大陆法系的行政法是以“行政行为”作为连接实体与程序、实现行政法学体系化的核心概念。尽管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变迁,不同学者试图提出以“行政法律关系”“行政过程”“行政手段”等新的核心概念弥补或取代单一行政行为模式,但总体而言,“行政行为”仍然是行政法体系的核心概念,只是“行政法律关系”的重要性日渐突出(鲁鹏宇,2009;黄宇骁,2019)。对于教育法典而言,在可备选的核心法律概念之中自然离不开对“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权利”等概念的探讨,也已经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些研究(如任海涛,2021)。
但是,核心概念的选择及其内涵的确定影响着法典化路径的选择,其背后是对本国法治实践的系统思考与体系建构。选择什么样的核心概念并赋予其何种内涵,直接关系着所要建构的法体系路径与法典形式。“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教育法律关系”当然都是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但从民法典与行政法体系化的经验来看(法律行为、行政行为),“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显然是首先应当考虑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这也涉及教育法体系建构的路径选择问题,即选择主观法体系还是客观法体系。以教育法的规范数量和内容而言,毫无疑问其主体规范均为客观法而非以规定主观权利为核心的主观法,因而我们认为相比于主要体现主观权利的“教育法律关系”,“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的概念应置于核心概念讨论的优先地位(可参考黄宇骁,2019)。
由于长期以来“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仅是教育学的学理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在法学领域并未受重视,所以它在法律上的规范含义不明晰,它的概念特性、价值功能也尚待讨论。核心概念在法典中的重要地位与其所体现的高度的工具理性,决定了其具体内涵不能被草率地确定。相反,只有在全盘考虑核心概念在法体系中的地位、功能、价值也即其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后,我们才能确定其应有之义。毋庸讳言,民法学与行政法学总论对体系化与法典化的研究,尤其是它们对核心概念“法律行为”“行政行为”的研究,要比教育法学成熟和系统得多。因此,从“法律行为”“行政行为”这两个核心概念中汲取经验,能够推动我们对教育法核心概念的理解,为我们在核心概念的选择、价值功能的确定以及内涵本质的厘清方面提供帮助。要彻底地理解“法律行为/行政行为”概念,是无法脱离对其概念生成史的考察的。正如萨维尼所说,“一个人必得彻底通晓历史材料的确切涵义,才能将其当作一种工具,运用裕如地借以阐释新的形式”(萨维尼,2001,第92页)。有鉴于此,下文将以“法律行为/行政行为”的概念演变及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功能为出发点,探讨教育法典核心概念(特别是“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
二、教育法典核心概念的生成与演变:以法律行为、行政行为为例
对于法律上的“行为”一词的翻译,曾经在我国引起广泛争议,尤以“法律行为”和“行政行为”为代表,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将德国法中不同层次的与行为相关的概念(Handlung,Handeln,Geschaeft,Akt等)均翻译为行为或法律行为(参考湛中乐,苏宇,2016)。在本文中,“法律行为”指的是Rechtsgeschaeft,“行政行为”指的是Verwaltungsakt,即本文主要从狭义上界定与适用“行为”的概念,这是因为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概念之争背后所突显的不仅仅是翻译方面的问题,更多的是法体系化与法典化路径选择上的差异问题。
(一)民法上“法律行为”(Rechtsgeschaeft)的概念生成与法律功能
1. “法律行为”的概念嬗变与价值定位: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的工具
“法律行为”是德式民法学最为重要的法律概念之一,也是潘德克顿法学最伟大的创造。不过,它在18世纪诞生之初仅是一个抽象性的、一般性的概念。与法律行为有关的术语在当时多用来笼统指称能够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更接近于rechtliche Handlung(法律上的行为)的涵义(朱庆育,2008)。如果法律行为仅具有这一形式含义,那19世纪的德国法学也不可能因它而享有国际盛誉。法律行为(Rechtsgeschaeft)理论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是因为海泽(Georg Heise)、萨维尼、普赫塔(Georg Puchta)以及温德沙伊德(Bernhard Windsheid)等学者赋予了其独特的价值内涵,他们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法律行为理论成为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的基本工具。
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萨维尼格外重视意志的作用,并提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个人意思的独立支配的领域”(徐涤宇,2004),而法律行为几乎与“意思表示”具有一致的内涵。按照萨维尼的界定,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是直接指向法律关系的产生或解除的自由行为。概念法学创始人普赫塔则进一步指出,基于行为人意志而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法律行为(徐涤宇,2004)。这一看法也逐渐成为了19世纪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1896年《德国民法典》规定了“法律行为”这一术语,并做了如下解释:“法律行为是旨在产生特定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示,该法律效果之所以依法律秩序而产生,是因为人们希望产生这一法律效果。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作出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且法律秩序通过认可该意思来判定意思表示旨在进行的法律形成在法律世界中的实现。”(弗卢梅,2013,第26页)德国法律行为理论集大成者弗卢梅(Werner Flume)认为,法律行为是指个体基于法律秩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通过其创造性形成法律关系的一类行为,其目的旨在实现民法的私法自治基本原则,即个体基于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因此,将法律行为(Rechtgeschaeft)视为行为(Handlung)的一种,与其他行为一起被视为法律事实,没有体现出法律行为所特有的基于意思自治创设性地形成法律关系的本质(弗卢梅,2013,第一版序言)。德国另一位民法学大家拉伦茨(Karl Larenz)也指出,法律行为的功能即是“帮助实现权利塑造之意志并令其发挥法律效力的工具”(拉伦茨,2013,第426页)。可见,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根本上是对个人意志的高度重视和对自治空间的尊重与保障,是民法贯彻私法自治的工具。也正是这一超出契约、物权、亲权等具体类型而涵盖整个民法领域的抽象行为,使得私法自治原则得到了全面贯彻。
在对“法律行为”一词的使用上,我国与德国并不完全相同。中国近代民法以德国民法和潘德克顿法学为继受对象,故在法律行为的用法上也基本与德国保持一致。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的继受对象转为苏联(孙宪忠,2008)。苏联法学将民法视为公法,并主张加强国家公权力对私域空间的全面干预,因此其“法律行为”不再是民法学的专用术语,而是上升为法理学的一般概念,指涉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行为,“是最普遍的、最广泛的法律事实”(卢志强,2021)。这种论述事实上取消了作为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的“意思表示”的地位,消弭了法律行为与意思自治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仅仅将其视为法律事实之一,并高度突出合法性特征。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使用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其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法律行为”不再将个人意思表示与法律效果相关联,而是泛指一切能变动法律关系、产生法律意义的行为。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法学者认为法律行为与意思自治相表里,它是承载民法价值必要的概念工具,因此主张恢复“法律行为”的用法(薛军,2007/2008;窦海阳,2016;王洪亮,2016)。在学界的努力下,2017年《民法总则》终于明确将意思表示与民事法律行为联系在一起,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这表明我国民事法律行为也是私法自治的一种工具。
2. “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成与体系化功能
(1)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成反映体系化路径
德国“法律行为”概念的产生,反映出了不同的体系化路径。作为18世纪德国法学的伟大创造,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一开始是抽象、演绎等形式理性与理性法学(Vernuftrecht)的产物。“在整个18世纪,涉及法学主题的著作家都倾向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例行公事地向自然法致敬。”当时的德国法学受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等自然法学家与笛卡尔、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等哲学家影响,试图通过数学化、公理化等自然科学的方式建构法科学(参见凯利,2010,第221—225页)。这一路径所使用的体系化方法是探寻公理式的一般概念(Allgemeinbegriff),再通过自上而下的演绎将其适用于所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按照弗卢梅教授的观点,法律行为并不是对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等各种具体行为类型进行归纳式抽象的结果,而是从“人的行为”概念中演绎推导出的来下位概念(弗卢梅,2013,第33页)。这样各种具体的行为是被内涵于法律行为的概念之中的,由这样的法律行为所组成的民法体系也是一个追求体系完备无漏洞、逻辑一致的形式体系,是“一种理想的、根据演证方法推演出来的非历史的抽象科学体系”(舒国滢,2021,第810页)。
在十八九世纪之交,德国“哥廷根学派”开始反思沃尔夫式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体系,以归纳的方法整理和分析经验素材,使法学摆脱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而具有一定的实证主义特征(舒国滢,2021,第817—837页)。萨维尼进一步批判了沃尔夫以来的那种抽象封闭的概念体系,认为法是由习俗和民众信念产生的,而民族共同法律信念、“民族精神”才是法的终极源泉,并以此建立有机的法体系(萨维尼,2001,第7—9页)。所以其方法是“历史与体系的结合”,即以自下而上的归纳径路抽象提炼形成法律概念与原理,“在体系中自然不应该对法律规则未使用过的概念阐述”(萨维尼,2014,第108页)。因此,萨维尼所使用的法律行为概念不完全是形式逻辑演绎的产物,它同时还是对人们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某类特定的行为体系的归纳与抽象,是对合同行为、物权行为、婚姻行为等具有意思表示属性的行为“提取公因式”的结果,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行为的类型化(谢鸿飞,2003)。在这个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体系,不再是一个毫无漏洞的概念体系,而是在法律实践基础上的可能存在漏洞的有机体系,这也为法体系注入了法律实践与民族价值的色彩。不过,当时德国民法典所遵循的主要还是概念法学和潘德克顿法学的传统,这传统在方法论上与理性法学较为接近,仍是以形式化的逻辑体系为主。
(2)法律行为在法典中的体系化功能
法律行为概念是德国民法典总分则体例的基础。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与《法国民法典》中并不存在总则编,而是以人、物及诉讼(物之变动)为结构,而德国民法典之所以能别出心裁地创造出总则编,法律行为是其中最重要的支柱。通过古斯塔夫·博莫尔(Gustav Boehmer)“提取公因式(vor die Klammer zu ziehen)”的技术方法,将物权行为、合同行为、遗嘱行为、婚姻行为等具体类型纳入抽象的法律行为之中并在总则作出规定,可以避免规范上的赘冗,从而提高法律的逻辑完整性与内涵经济性(茨威格特,克茨,2017,第273页;窦海阳,2013,第44页)。正如有学者指出,法律行为理论奠定了德国民法总论的逻辑基础并由此奏响了《德国民法典》总则诞生的序曲(杨代雄,2005)。
我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体系化功能与《德国民法典》有不同之处。一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民法典总则并不是“提取公因式”技术的产物,而是一种类似于“活页环”目录式的第三体例,因而法律行为所具有的功能仅是立法惯例而已(朱庆育,2020);另一方面,法律行为为我国民法典供给了具有准法源地位的自治平台,可以保证法典自身的开放性,并与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权利一起实现总分则体例的体系性(姚明斌,2021)。与此同时,私法自治、信赖保护与公序良俗等私法价值则构成法律行为的内部体系(杨代雄,2021,第1页)。总体而言,我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制度虽然形式体系化功能不如德国民法典,但仍然为民法典内部价值的体系化奠定了基石。
(二)“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的概念内涵、价值定位与体系功能
1. “行政行为”内涵的不同模式
(1)法国模式
行政行为(acte administratif)是行政法诞生地法国的创造,是对“无数具共同特征,并适用共同规则之行政行为的统称”(成协中,2020)。在19世纪早期,作为一个归纳性、描述性的概念,法国的“行政行为”主要用来指称行政机关进行的各种活动,其目的在于实现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分立,防止司法对行政的过度干预,但这样的定义仅具有形式意义。当前法国主要从功能意义即司法诉讼联结的角度来界定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用以产生行政法上效果的法律行为,以及私人由于法律或行政机关授权执行公务时所采取的某些行为”(成协中,2020)。这里的“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对,指根据行政机关意思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在具体内涵上,法国的行政行为包括单方行为、双方行为与多方行为,既包括抽象行为,也包括具体行为,但是不包括事实行为(王名扬,2016,第105—107页)。法国对行政行为的理解曾受到私法上意思表示理论的影响。从19世纪中期开始,法国学术界开始用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理论对行政行为进行概念化描述,认为行政行为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但由于行政机关意思表示的非自由性,当前法国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不来自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而是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因而意思表示因素已居于次要地位(成协中,2020)。
(2)德日模式
德国学者从法国继受了“行政行为”概念后,将其称为Verwaltungsakt,日本学者则将其翻译为“行政行为/行政处分”,我国大陆有学者称之为“行政处理”“行政决定”等,而台湾学者称之为“行政处分”(参见李洪雷,2014,第272页)。与法国统一的行政行为概念不同,德国的行政行为具有个体化、明确性与司法化特征(赵宏,2012,第55—63页)。根据迈耶的经典界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向人民作出的在个案中“什么是法”的高权宣示(Maorer, Waldhoff, 2020, §9, Rn.2)。迈耶使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目的在于通过行政行为的类型化确定行政权力的内容与范围,从而保障个人权利不受公权力的过度侵犯。德国最初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理解受民法上法律行为理论的影响,单指以意思表示或法效意思作为要素的行政机关行为,而将事实行为、准法律行为作为对举概念。例如,科尔曼(Karl Kormann)直接以“具有法律行为性质的国家行为(rechtsgeschaeftlicher Staatsakt)”称呼行政行为;魏玛时期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即认为行政行为是一种公权意思表示(李洪雷,2014,第274页)。不过这种理解显然是照搬私法理论,并未认识到法律行为的私法属性以及行政行为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差异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彰显公法的自主性,二战后德国法学界逐渐淡化了意思表示的色彩,突出了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这一要件的地位,并从立法的角度确定了该术语的精确内涵。1976年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5条规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规范公法领域的具体案件而采取的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处分(Verfuegung)、决定(Entscheidung)或其他公权力措施(Massnahme)。这其中,处分、决定等是行政行为的例示。这种观点一般称为“客观意思说”,即以行为是否直接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拘束力或法律效果为判断标准,而不太关心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很明显,即使仍有“意思”二字,但这里的“意思”与民法意义上的“法效意思”有着本质区别(李洪雷,2014,第276页)。因此,德国学者将此种在行政法上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称为“法的行为”(Rechtsakt),以与民法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aft)相区别。但是,尽管存在公法与私法的不同,德国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因其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仍然与意思表示有着重要关联。如哈特穆特·毛雷尔 (Hartmut Maurer )等人指出,行政行为具有“调整特征”(Regelungscharakter),而“调整”是一种以实现某种法律效果为目的的意思表示(Maorer, Waldhoff, 2020, §9, Rn.6),尤其是在与事实行为的区分上,意思表示具有重要作用(王锴,2018)。除德国外,日本、瑞士、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行政行为(行政处理、行政处分)的理解大体也恪守其经典理论,即以行政行为特指旨在在个案中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排除事实行为(章志远,2003),由此保证了行政行为理论创建的基本功能与特色。
(3)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概念
在我国,在1983年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一书中,王名扬教授率先使用“行政行为”一词。但学界对此概念的理解则存在很大分歧,先后形成了“最广义说”“广义说”“狭义说”和“最狭义说”。“最广义说”是将国家一切行政管理行为均称为行政行为,但这种宽泛的界定显然不能作为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来使用,因此很快被行政法学界所抛弃。“广义说”认为,行政机关所为的一切行为是行政行为,这样行政行为不仅包括传统大陆法系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事实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甚至也包括行政机关所作出的私法行为。这种以主体或者法域来界定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民法通则》的“民事行为”是一致的,看似无可厚非,实则仅具有形式作用,故也被放弃。“最狭义说”则是认为行政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狭义说”逐渐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的通说,此即应松年教授所定义的“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周伟,2015),但并不包括事实行为和准行政行为。这种观点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指出前者不可诉,后者可诉。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德国法上的行政行为具有相似性。可以看出,相比“最广义说”“广义说”“最狭义说”,“狭义说”具有明显的技术意义与实践功能,故能成为通说并深受司法界青睐。
但是,随着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张,传统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可诉的规定慢慢通过扩张解释与法律修订得到改变。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将受案范围从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而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这里的行政行为包括事实行为、行政协议。换言之,为了适应行政诉讼的功能性需要,我国行政行为的含义进一步扩大,成为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的上位概念,这与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行政行为的经典界定显然有很大不同。不过,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的一般使用中,认为行政行为仅指具体行政行为,或持德国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观的学者亦不少见。
2. 行政行为概念的价值内涵与功能定位
法国与德国的行政行为概念的不同与其所赋予的价值与功能有着重要联系。于法国而言,法国公法学创立之初面临的首要使命是防范司法对行政的干预,同时防范立法权对意志过程的垄断。另外,法国行政法是判例法,并无过多体系化的考虑,奥里乌(Maurice Hauriou)等学者甚至将法典化视为行政法学发展的一种束缚(成协中,2020),因而法国的行政行为概念以客观化、统一化为主要特征。在德国,迈耶所创设的行政行为概念旨在通过“行政行为的司法化”来实现法治国(Rechtsstaat)理念,使行政受到司法的控制。对于行政行为的基本功能,有实体法、执行法、程序法与诉讼法上的多种不同。在实体法上主要是明确公民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法的安定性;在执行法上,则是为执行提供具体名义;在程序法上具有决定程序种类的功能,从而发挥促进法治国人权保障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或大陆法系的行政行为在诉讼法上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最初的行政行为(或行政处分)在诉讼法上主要是具有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功能,即唯有对行政行为不服方可提起诉讼,但由于德国诉讼标准已修改为“一切非宪法性质之公法争议”,不再以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前提,其诉讼法上的功能也转换为“决定诉讼种类”(翁岳生,2020,第600页)。但总体而言,行政行为大体上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即为满足法治国目的而创设的实践概念(赵宏,2012,第6页)。从体系化角度而言,行政行为是德国法治国理念实现依法行政原则的核心概念,其自身的抽象性、统摄性、确定性以及技术化特征为建构行政法体系奠定了概念基础。“它为多样化行政提供了稳定的、型式化的基本活动单元,借由这一单元,复杂的行政被纳入法体系的统一秩序之下。”(赵宏,2021,第25页)。
与前述国家行政行为概念的内涵不同,我国的行政行为由于承载了更多的诉讼前提功能,其内涵不仅仍不够明晰,也随着诉讼需求发展而不断变化,因而司法功能性有余而体系化功能明显不足,“其作为学科基石的原因从未被彻底说明,与之相关联的学理建构也显著地缺乏有机整体的融贯性”(赵宏,2021,第47页)。
三、教育法典核心概念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
从上述关于核心法律概念形成及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如德、法及我国的差异)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德国的理性法学、历史法学对法律行为的不同建构),由于其所欲追求的法律价值与法秩序路径(外在体系抑或内在体系)的不同,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核心概念生成路径与基本品格:一种是理性法学(以及著名的概念法学、潘德克顿法学)基于形式理性主义传统,确定概念的有限、封闭且确定的内涵;另一种则是历史法学尤其是当前占据法学主流的价值法学的路径,注重概念的内在价值与法律实践。在概念法学代表人物普赫塔那里,法律概念是这样诞生的:从调整对象的事实构成中分离出某些确定要素并将其普遍化,再基于这些要素形成类概念,然后通过增添或剔减若干种差特征(Merkmale)形成抽象程度不一的概念,再将抽象程度较低的下位概念涵摄于抽象程度较高的上位概念之下,最终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概念金字塔”(拉伦茨,2020,第549页)。这种以形式逻辑为规则建构起来的概念所组成的体系最突出的优点在于保持体系内部的逻辑一致性,“构成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法律秩序的体系”(梁慧星,2015,第62页)。毫无疑问,“法律行为”一开始即是这种技术的产物。但这样的概念是一个内容空洞、价值虚无的概念,无法承载法实践的价值需求。由这种概念所建构的法体系将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难以涵盖复杂多变的生活事实,而且这种体系化要求法官不得为利益衡量和目的考量,完全以逻辑涵摄取代价值评价(黄茂荣,2020,第392页)。有鉴于此,价值法学的首创者拉伦茨(2020,第550页)指出,在形成抽象法律概念时,法律概念特征的取舍根本上必须考虑规范的目的。黄茂荣(2020,第165—168页)指出,法律概念为目的而生。在建构法律概念时必须考虑所建构的概念是否具备透过其规范机制实现期待之目的或价值的功能。总之“没有特征的取舍,不能造就概念的形式;没有价值的负荷,不能赋予法律概念的实质”。今天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都是如此。由此可见,教育法的核心概念应当是兼具逻辑一贯与价值圆融双重意义的统一体,并承担着体系化功能(梁迎修,2008)。
1. 核心概念应当具有形式理性:高度精确性、明确性与稳定性
作为现代治理的基本工具,法应当具备充分的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其外部体系应当概念清晰、逻辑自洽、结构完整。唯其如此,法的规范性与安定性方能确保,法治国家目的才可实现。因此,相比于一般的学术概念或生活概念,法律概念应更为精确与明确。“理解事实关联的观察方式与理解规范意义的观察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前科学的语言,一个是科学的语言。”(拉伦茨,2020,第257页)尽管法学已经超越概念法学的发展阶段,但概念法学对形式理性的追求始终构成了法学的重要面向之一。法律行为本身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具有高度精密的逻辑构造,我国曾经由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抛弃了经典法律行为理论,但最终难以在逻辑上实现自洽,不得不回归其经典含义。行政行为在日本经历了“最广义”“广义”“狭义”与“最狭义”的争论后,最终选择了回归经典行政行为理论也是如此。此外,作为核心概念,其内涵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边界清晰性。作为基石的核心概念如果内涵过于模糊与多变,将从根本上撼动整个法体系。从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经典理论来看,二者的含义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其具体内涵与解释路径可能随着历史与社会目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其规范对象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由此才能保持法秩序的相对稳定,并以此建构法体系。
2. 核心概念应当具有价值理性:规范性、价值性、功能性
拉伦茨曾将法置于规范性视角之下并由此探究规范之于法的“意义”的学问(拉伦茨,2020,第253页)。这一定义揭示出法与法学的两种品格:规范性与价值性。在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理学著作”—《法律的概念》一书中,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曾经说过,规范性是法律在所有的时空中所具有之最为显著的一般性特征,“其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举止不再是随意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下具有义务性的”(哈特,2018,第54页)。正如考夫曼指出的:“法律必须是规范性的,必须是当为规范的,故其不可能是纯粹的经验概念。所有的法律概念,都会充满‘规范性的精灵’。”(考夫曼,2011,第119页)。一般的概念仅仅在于描述,仅仅具有“叙事价值”,但法律概念“不是设计出来描写事实”,其本质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的行为,而不在于描写其所存在之社会”(许中缘,2007)。法律行为、行政行为从语义逻辑上似乎都应该取广义乃至最广义的理解,但这种界定方式的规范性意义较弱而以描述性居多,所以德日国家均选择以更具规范性品格、更能与私法自治原则相结合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aeft)以及更适应法治国理念司法诉讼需求的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作为最核心与最重要的概念,两国的《民法典》《行政程序法》也是以其作为“提取公因式”的支撑。
价值性既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和共同价值取向,也能够彰显部门法的独特价值偏好。法律概念承载着“承认、共识及储藏价值”的功能(黄茂荣,2020,第170—175页)。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分别构成了民法学与行政法学最核心的概念,也承载着二者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法律行为概念是实现私法自治基本原则的工具,是最能彰显民法作为私法的核心特色的概念创造,也是支撑德国民法的核心骨架。行政行为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关系密切,彰显了行政法学对法治国理念或合法性的独特追求。因此,教育法典或教育法体系的核心概念应当也具备相应特征,彰显教育法的独特价值追求,成为实现教育法基本原则的关键工具。如果只是引入一个具有法理学意义或描述意义的概念,并不能体现教育法的独特性,不过是提出一个形式化的学理概念而已,对于教育法与教育法学的体系化均无实质贡献。回顾教育法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尽管一直有学者在主张教育法学独立成为一门部门法(参见雷槟硕,2021),但由于缺乏自己的理论框架与术语体系,我们仍不得不为各种行为在行政法上的定性(行政行为、行政处分、事实行为)而焦头烂额,因此缺乏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彰显教育法独特的教育品格。一旦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理论框架难以完全描述,我们就只能存而不论。因此,我们更希望以教育法典核心概念的分析作为突破口,建构真正有教育法学独立品格的学科理论体系。
所谓功能性是指法律概念在法律实践或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在司法上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行政行为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从“狭义”逐渐走向“广义”的演变历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实诉讼需求,这也是许多学者主张扩张行政行为概念内涵的缘由。尽管由此导致了概念精确性、稳定性与逻辑性的减弱,但从总体而言,其实践性与功能性得到了增强,且仍然保持了与经典理论的部分对接,例如仍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核心。不可否认,功能性与规范性或逻辑性之间是存在张力的,概念的实践性品格在一定程度上要优先于逻辑性品格,但这不能以概念体系的崩塌作为代价。而我国行政行为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体系的建构,有鉴于此,教育法典在确定核心概念时,应坚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在逻辑自洽的基础上实现法的功能性、规范性与价值性融合。为此,我们需要根据规范目的,在形式与实质之间作出权衡与取舍(吴丙新,2006)。
3. 核心概念应当具备体系化功能:“提取公因式”
正如法律行为、行政行为都足以解释各自部门法领域的大多数行为或规范,可以作为提取公因式的工具,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也应当具备统摄整个或大部分法体系的内容,能够作为教育法学或者教育法典的基础概念工具,能解释大部分教育法中的行为或者关系,应具备充当“提取公因式”技术工具的作用。我们也可将其称之“基础性”或“体系化”的功能。按照卡纳里斯(Claus-Wilhelm Canaris) 的观点,法体系的可能形式有多种:逻辑学意义上的公理—演绎式体系、概念法学意义上的概念体系、利益法学意义上的冲突解决体系、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意义上的纯粹形式概念体系、由问题脉络或生活关系构成的体系等等(这些都具有外在体系特征),但这些都不足以建构真正的法体系。唯有具备了体系开放性的由主导型价值观点构成的、“公理式的或者目的论秩序”的体系,才足当大任(拉伦茨,2020,第221—223页)。实际上这是要求建构一种意义与价值圆融、由法律原则建构起来的法内在体系。这种体系所需要的法律概念被称为“功能被规定的概念”(拉伦茨,2020,第604页),其内容建立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则之上。“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就是标准的“功能被规定的概念”。法律行为的功能是实现私人自治的手段;迈耶式行政行为则建立在依法行政的法治国理念原则之上。教育法体系应当是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的统一,故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既要能保持外在体系的逻辑一致性,更要成为贯彻内在价值体系的核心工具。由此,通过核心概念“提取公因式”,应当是抽出能贯穿法典始终,同时调整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教育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日渐发展的其他类型教育法律关系的共同规则,由此形成总则编,统辖整个法典,并依据总则编的立法目的、原则和理念指导教育法典各分编,以实现价值融贯、规则统一、体系完备的法体系。
同时,我们也需要防范过度追求核心概念抽象化的做法。所谓过度抽象化,指对概念所描述对象的特征作出过多的舍弃。如前所述,法律概念是承载了价值、目的与功能的,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而过度抽象化将会抽离概念的意义内涵使得概念变得空洞与无所适,最终与法律实践或者法律规则脱节。提取公因式并不是追求概念外延越广越好,而是取其共性。不同于哲学体系,实证法体系虽然也关注概念的一般化,但其目的在于适用,因此既要考虑概念的普遍抽象性,也要考虑其内容的实践性。经典的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之所以未被简单界定为民法/行政法上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概念的实践品格,防止过度抽象引发的价值缺失。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或许实现不了如法律行为、行政行为这样的“法典承重墙”的地位,但既然要成为法典总则部分的不可缺的内容,就仍应具有自身的基础性与实践性品格。
四、结语
本文从民法、行政法核心概念的生成与价值功能的角度探讨了教育法典核心概念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尤其是适用于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这一组行为概念),但并未推导得出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的法律含义,其意在于表明核心概念内涵的确定并非可以轻易为之,而应在坚持前述概念品格基础上经系统思考后来决定,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学界来共同参与。法典的编纂是高度精细化、技术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主义的结晶,与此同时,法典的生成又是由“贯穿整个历史的、一种‘民族精神’的、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使之得以有机地培植成长”(茨威格特,克茨,2017,第262页)。精密的技术理性保证着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性与自洽性,民族实践品格则保证了体系的开放性与均衡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仅是对教育法典核心概念的初步探讨,所得结论亦非定论,唯望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界同仁来共同探讨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