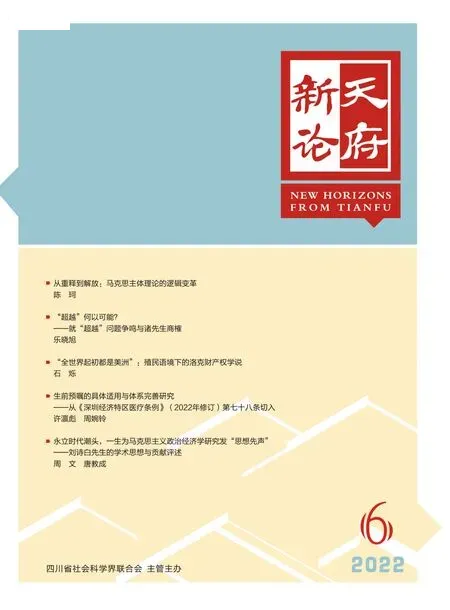从重释到解放:马克思主体理论的逻辑变革
陈 珂
“主体”与“反主体”的悖论已经成为现代性原则所造成的理念与实践矛盾的反映。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代议制民主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体制,似乎使作为启蒙理想的主体普遍解放成了现实;另一方面,以“普遍理性”为外观的资本逻辑成为控制与排斥个体的“社会他者”,又宣告着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危机”。正如巴迪欧所言,上帝已经死去很久,人本主义的人却并没有在20世纪中幸存。(1)Alain Badiou,The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p.166.马克思的主体理论也在当代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验:在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对作为历史“剧作者”的人之主体性的消解,主体清晰、自觉的意识被宣判为意识形态的建构;(2)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在实践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产形式与阶级结构的调整,也使经典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的工人阶级在当代西方思想界沦为一种先验的“政治想象”(3)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因而,在当今解放政治重塑主体的话语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往往是“缺位”的。针对在资本所构筑的经济密网中主体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涌现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以主体间的“多元包容”的交往理性代替认知主体的独断性;二是在“理性的边界”,也即在处于生产关系之外的“被排斥者”中寻求革命的希望。前者使生产领域中的阶级冲突消解于多元文化与包容他者的乌托邦想象中;而后者所重塑的社会身份各异的“边缘群体”因无法走向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只能成为有待于解放的“被解放者”。诚然,经由从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转向唯物史观的科学逻辑,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似乎消解了超越资本主义“不合理”现实的革命冲动。但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双重面向的统一,即确证“经济的社会形态”(4)“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译为“社会经济形态”,德文原文为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它并不是泛指一切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特指由私有制决定的经济形态内在的对抗性。这一社会形态是具有历史性的,其中蕴含着超越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张一兵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自然必然性社会、经济必然性社会以及人类的自由发展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典型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张一兵:《马克思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之历史性与必然性和强调无产阶级超越性的统一。
一、内涵重释:从“认知主体”到“现实的个人”
启蒙哲学的全部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于“人性(或人的本质)”总问题之下。(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3页。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来,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就被确证为主体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示的那样,启蒙的人本主义传统对主体的界定同时建立在两个假定基础之上。一是本质的普遍主义,即“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第505页。。康德以“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确证了抽象的人类主体对社会历史的本原与基础的地位;同时,作为主体的人也被剥离掉了一切具体的、感性的规定性,成为只有理性内核的抽象认知主体。二是个体的经验主义,即“撇开历史的进程……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第505页。。为了论证市民社会中商品交换行为的“自然秩序”,古典经济学派将经济运行中的主体规定为摆脱了一切“人为规定性”、仅关切自身利益的原子化个体。这种以主体的抽象性与孤立性为特征的“主体中心主义”带来了双重解放效应:一方面,每一个认知主体都在法律上被确证为平等与自由的个体,这为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专制的政治解放提供了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另一方面,“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因素。
而人道主义的本原逻辑是作为价值悬设的“人与非人”之间的冲突,当主体性原则与其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时,就会展现出另一幅关于“人”的图景。资产阶级塑造“人的神话”只不过是为了使自身的特殊权利获得普遍性的外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指出,自居于代表精神之普遍本质的启蒙智识同样是以自身的有用性为尺度,使对象世界成为“空洞的客观性假象”与“纯粹的形而上学”(8)《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0-361页,第299页。,因而与意欲彼岸的信仰一样,仅意欲自身的启蒙同样是一种“自身异化了的精神”(9)《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0-361页,第299页。。黑格尔不仅根据主体性原则阐明了现代世界的危机所在,而且试图在主体哲学内部寻求超越理性主体抽象性与压迫性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黑格尔指出,作为现代之精神的主体原则走向实践,并不会带来自由的现实显现,反而使历史呈现出“反精神”的状态。这就是被黑格尔斥责为“自然状态的残余”(10)《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2页,第440页。的市民社会历史阶段。另一方面,黑格尔试图建构主体间性的交往共同体,以超越认知主体意志的独断性。在黑格尔看来,超越市民社会阶段的国家 “把主体性的原则推向完成”(11)《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2页,第440页。。在国家的伦理共同体中,个体既能使自身的特殊利益得到发展,又能获得来自其他主体的承认。尽管黑格尔以对主体性原则的社会性维度理解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自由提供了新的“标尺”,但其问题同样显而易见:黑格尔仅以理性能力界定人的本质,这种停留于思维哲学内部的主体间性建构,不仅无法真正弥合启蒙哲学遗留的“是”与“应当”、合理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而且无法阐明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真正的实践关系。
1845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对主体内涵的根本重塑。即使是当时还停留在费尔巴哈“阴影”下的青年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处在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不同于设定先验主体的异化逻辑,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还存在着另一条理论线索,即萌芽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物质生活(市民社会)基础作用的强调。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普遍本质的价值悬设,对不仅体现在“观念中”也体现在“现实中”的“双重的生活”展开了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为社会的“非人”样态寻求现实根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指出:“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7页,第332页。深藏于认知主体结构内部的理性悖结就体现于主体与其创造物、个体与类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这一由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之总体性形式解决的理论难题,只有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得到了历史性解答。
其一,社会历史不是“认知主体”思维创造的外化显现,而是“现实的个人”能动的物质劳动的实践过程。马克思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界定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质点”在于意识,“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第525页,第519页,第502页。。即使在将视角从“神圣意识”转向“肉体的人”的费尔巴哈那里,启蒙哲学留下的“是”与“应当”的根本理论症结仍没有解决。“‘人’只是概念、观念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历史仍然表现为某种“神圣的东西”或是“人的本质”的代表(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7页,第332页。。在人的理想本质的理论悬设下,现实存在自然成了某种“非人的异化关系”。而当抛弃了基于“人与非人”的先验逻辑悬设转向现实生活时,就不难发现,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主体绝不是某种抽象掉感性存在的自我意识,“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第525页,第519页,第502页。。历史地而非抽象地言说主体问题,使马克思站在新的逻辑起点上揭示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一方面,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界分出社会历史的“主体—客体”。只有“开始生产”,现实的个人才能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人之社会存在的根本规定性。“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不仅“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第525页,第519页,第502页。,确证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而且还界划出了历史客体(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实践同时又成为主体和客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的黏合剂。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主体哲学中思维主体和社会客体之间的理性悖结转化为社会历史领域下历史主体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实践关系。现实历史的发展在马克思这里不是表现以“永恒理念”为表象的对“市民社会的直观”,而是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第525页,第519页,第502页。中把握个体与类的真正统一。因为,只有在客观的物质条件制约与主体的生产活动的辩证运动中,作为人之具体的、历史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形成。
其二,“自主活动”是“现实的个人”之主体性的历史确证。脱离了人本主义史观的马克思,不再从应当存在的理想状态中寻求批判现实的伦理张力,而是以“自主活动”为揭示不合理的现实提供尺度。“自主活动”这一表述虽然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认的体现人类自由自觉“类本质”的理想化的劳动形式相似,其中却内含着马克思理论构架的根本转移。在马克思看来,自主活动既不是来自浪漫主义设想的“原初状态”,也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存在,而是一个在改造外部世界过程中不断确证自身的历史过程。自主活动表征着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导地位,即能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条件下,自主活动的直接表现形式“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又表现为对自主活动本身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主活动不再作为目的本身存在,而是沦为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人的自主活动与主体地位在“物”的生产中被否定了。但是,马克思对于人与人联合劳动的力量“颠倒的表现为物的力量”的历史趋势的揭示,其实既非为了在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角度否定自主活动的主导地位,也非将自主活动视为一种应当存在的本体状态。他只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将现实历史视为“观念”对人的统治,这不仅仅来源于他们对抽象的理论偏好,更是对自主活动以异化的状态展现自身的思想反映。
马克思对以往的主体性叙事的根本超越在于从“思辨范式”向“生产范式”的视角变更,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代替抽象的“认知主体”,从而使封印于理性、自我意识的主体存在根基被揭示出来。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所说的将青年马克思视为黑格尔派只是一种“神话建构”(19)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5页。才可以得到理解。因为两者呈现的是历史过程中两幅不同的“主体”图景。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只是“客观精神”实现自身使命的承担者;而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则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剧作者”与“剧中人”的统一。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主体内涵的重释呢?对于这一问题,思想史上存在两种相反的解释路向:一种路向是传统解释框架,将这一转向视为马克思主体理论的逻辑完成,认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意味着主体成为社会历史“机械”运动的“旁观者”;另一种路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传统,将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现实的个人”仍视为马克思青年时期人本主义的思想表现。(20)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批判了这种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方法。在阿尔都塞看来,以兰茨胡特和迈耶尔为开端的关于青年马克思著作的辩论,核心观点在于将“人的因素”看作“普遍有效的依据”,“马克思从事经济分析的原则则直接产生于‘人的真正现实’”。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社会历史的起点视为“现实的个人”,仍没有走出人本主义逻辑,不过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页。其实,马克思坚持的并非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放弃的也并非对“现实的个人”之生存境况的关切。站在唯物史观这一新的理论地平,马克思以“主体—客体”的双重张力结构提供了一种把握主体性原则的新的理论视角,即站在由物质生产实践形成的现实生活关系的客体向度,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体”颠倒的主体生存境况,“从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来描绘现实的个人”(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7页。。
二、宗旨变更:揭示资本逻辑下主体生存的客观境况
如果说,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为主体存在寻找“物质基础”,那么,随着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从抽象的“物质生产一般”上升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马克思的理论任务也转向了揭示资本逻辑之下的主体“幻象”。为市民社会永恒性立言的启蒙学者往往将脱离特定历史规定性、仅作为精神外化自身的劳动看作主体能力的确证。市民社会由此呈现为一个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平等交换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同样在“生产一般”的基础上将物质生产实践视作“历史中的主体”之能动性的确证,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存在着另一条“批判”的路向,即指认在私有制与分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历史发展的“无主体”性质。马克思指出,人们因共同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力量,即生产力,不是表现为“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转化为“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社会历史似自然性的典型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在人之外”的无主体性称为一种“神秘化”的“自然规律”(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6页,第22页,第22页,第179页,第180页。。因此,在对市民社会的典型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的主体理论从“解释”何为“历史中的主体”转向了“揭示”资本逻辑下“主体消解”的客观境况。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超越启蒙哲学的“主体幻象”所借助的理论工具。正如马克思在回顾自身的理论发展时所指出的,在《资本论》写作的30年以前,他就已经借用费尔巴哈的方法“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6页,第22页,第22页,第179页,第180页。。而在《资本论》的理论视域下,马克思更多的是应用剥离“神秘形式”的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形态”。只有在马克思主体理论逻辑叙事再度变更的基础上,何为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形态”的问题才能被提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体现为“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6页,第22页,第22页,第179页,第180页。。因而,黑格尔的精神“生成”之辩证法有助于揭示资本作为“主体”的自我运动规律。
与绝对精神相似,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也呈现出“无主体”的过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规定为“实体即主体”,“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26)《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页。精神的各种表现形态之所以能以目的论的形式不断趋近绝对精神的原因在于,绝对精神是“活的实体”,即本身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能动的。同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也同时具有实体和主体两重规定性。按照马克思的界定,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物质载体(商品、货币)赋予资本借以显现自身的实体性,其背后布展的社会关系则使资本拥有自动增殖的主体性外观。这意味着,资本的运动就是以社会形式不断统摄和形塑作为客体的物质内容,给其打上价值形式的时代烙印。 因而, 同绝对精神一样, 资本也是一个 “自行运动的实体”。 一方面, 在流通中,资本表现为 “自我增殖” 的价值。在最终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的商品流通(W—G—W)中,货币只是作为流通行为的中介存在;而在最终目的是获得价值“增值额”的资本循环(G—W—G′)中,货币本身就成了交换的目的,循环的开端与终点都是形式上相同、只有数量上差别的货币,甚至商品也只是价值“化了装的存在方式”(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6页,第22页,第22页,第179页,第180页。。因而,价值就在资本追求增殖的无限过程中“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6页,第22页,第22页,第179页,第180页。。另一方面,资本在循环的不同形式中得以自我持存。虽然资本在循环的不同阶段中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商品资本形式显现自身,但其表现出的每一种既定形式始终表现为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向自身的返回,也就是“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正如阿瑟指出,资本的“发展不是朝向它之外的某物,而只是返回自身”(30)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8页。。这无疑与“外化”为别物又在别物中不断回首自身的绝对精神异曲同工。如果说,绝对精神以目的论的“无主体过程”获得自我实现,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理论视野,即以“无主体的过程”考察资本的辩证运动。
“无主体”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同自然历史一样呈现为“无规律的盲目运动”,而是体现出一种“无主体的主体性”。正如齐泽克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式的辩证过程,其实是最激进的‘无主体的过程’”,而这里的“无主体”的含义是缺少传统意义上居于社会历史背后的“能动者”,“无论这能动者是上帝、人,还是作为集体性主体的阶级”(31)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客观精神外化的世界精神“高于一切的权利”(32)《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3页。,而这一精神认识和实现自由的不断进步过程就是主体本身。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世界历史个人”只是作为“理性的婢女”实现“剧作者”的意志。与此相似,面对资本的无限循环时,马克思亦指认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第359页,第10页。。在资本的自动增殖运动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历史性分析揭示了个人主体性消解的社会现实。在“劳动过程一般”中,劳动者在有目的的劳动过程中使用生产资料,以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现实的个人则在资本的“自动增殖”过程中充当了类似于物的要素。因此,资本具有了自主性和主体性。一方面,尽管资本的运动从表面上看表现为产业资本家的个人活动,但这也仅仅是因为资本家以人格化资本的形式促成资本自身的循环增殖,“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只作为价值增殖过程中活劳动的化身,这不仅意味着工人只有被吸纳入价值增殖过程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更意味着一旦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就“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做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第359页,第10页。。可见,资本通过将一切社会关系吸收进自身之中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正因此,马克思才以“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来类比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取得的支配地位。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把握,马克思不仅描绘了一幅“资本决定”的“无主体”的图景,而且识别了启蒙哲学构建的“主体幻象”。在启蒙学者看来,市民社会是“蜜蜂的寓言”的现实显现,所有人出于特殊利益而结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维持着社会普遍利益的微妙平衡。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交换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双重结构。马克思指出,如果仅停留在简单商品交换领域,市民社会确实表现为“天赋人权”的伊甸园。这一方面体现于主体的“劳动幻象”,即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来源,在人对物的占有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得以确证;另一方面体现于主体的“平等幻象”,即主体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交换关系。在商品交换中,作为人的主体性确证的劳动产品得到社会性的承认与实现。而一旦走出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就得以显现出来。原本以自由、平等与所有权为表征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带来主体性的普遍解放,反而带来了“货币占有者”与“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主体对立。可见,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揭示了“资本的狡计”之下主体性消解的客观境况。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不能止步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主谓颠倒”的“过早宣判”,对现代社会“拜物”特性的互补批判构成了两者对话的真正领域。(36)Robert Fine,An Unfinished Project: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Karl Marx and Contemporary Phliosoph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p.115.
然而,马克思是否在《资本论》中仅仅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第359页,第10页。,进而使资本分析中的主体解放成为其在《资本论》中遗留下的“未竟的主题”?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将解放的“实际可能性”赋予无产阶级尚且是一种价值立场,那么,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为这一价值立场寻求现实前提。这一价值立场的现实前提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称为“生产的自然规律”(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其中的“自然”有着特殊意蕴:一是作为特设的逻辑规定的“非主体”状态;二是作为内含价值意义的“天然”又“合乎人性”的属性。前者是马克思以类比的方式指称人类历史的“史前时代”经济规律呈现出的“无主体”运动过程;后者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维度,即证伪启蒙学者和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构造的“主体神话”。 马克思这种“自然规律”的类比,与其说是为了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业已呈现为客观样态的经济力量,不如说其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超越维度,即超越由商品交换关系营造的“主体假象”,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主体解放的可能性路径。
三、解放何以可能:主体行动与历史规律之矛盾的解决
“主体危机”因历史情境的转移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主体危机”体现为自由、平等的启蒙承诺对主体被剥削与被压迫之生存境况的遮蔽。马克思的理论任务就在于,从资本运行的客观维度揭示主体消解的历史事实。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这一“资本决定”的特殊规律简化为“经济决定”的一般规律,这不仅忽视了经济事实本身的“历史性质”,而且造成了以“总体性”力量存在的客观规律与历史主体行动之间的割裂。因而,新历史条件下革命主体的缺位(39)SlavojŽiž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New York:Verso,2009,p.88.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主体危机”。面对无产阶级何以把自身建构为解放主体的时代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两种理论路向。一种是卢卡奇站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将无产阶级重新确证为能够窥透物化结构的解放主体。类比于黑格尔精神生产意义上“同一的主体—客体”,无产阶级是这种“同一”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实现,是“行动的主体与创世的我们”(4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6页。。另一种是阿尔都塞站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对主体“退场”的指认。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不是作为抽象的类本质抑或具体的个人,而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的辩证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带来的对无产阶级的“同化”与阶级的“退场”,当代激进左翼面临的“主体危机”则表征为“被压迫者”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消解。因此,当代激进左翼开启了另一种重塑解放主体的理论尝试,即不再将解放的希望诉诸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无产阶级,而是诉诸被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被排斥者”或是“边缘群体”身上,寻求资本主义的“象征秩序”断裂的可能。可见,主体危机的不同形态反映出解放政治始终关注的核心主题,即在“自然”“客观”的资本运行规律之下,彰显主体超越性的政治行动何以发生?
马克思与解放主体的当代建构者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解放主体之经验存在的流变,而既是基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分析对无产阶级超越性维度的科学指认(而非价值判断),又是对解放政治(甚至是萦绕于主体形而上学传统的)致力于破解的主体行动与作为对象物存在的社会规律的历史解答。
(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中赋予主体以解放使命
不论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寻求象征秩序“断裂”的革命契机,抑或从“绝对精神”之外的非理性因素中确定革命主体,无疑都偏离了马克思界定解放主体的核心思路,即揭示被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规律掩盖的阶级对立。如果说,青年马克思遵循价值悬设的“丧失—复归”逻辑,将无产阶级称为“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14-15页。,与当代激进左翼在“失无所失”中寻求革命希望的思想路向存在某种相似,那么,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则证实了这种“例外”并不意味着被排斥于生产关系之外,而是一种构成生产关系又证明其自我矛盾的“构成性排除”。这一“例外”并非存在于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想象中能够打开“真理政治的空间”,并象征着“社会整体和真实的普遍”的难民、流浪汉与移民(42)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类比于黑格尔辩证法中以否定性助推精神自我实现的中介性因素,作为理性边界的“非理性剩余”也只能作为主体理性的镜像,而根本无法摆脱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直观形态及其固有困境。可见,当代激进左翼不论是将解放主体视为“剩余之人”抑或“被排斥者”,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均是“谁是无产阶级”。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则在于“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马克思主体理论的变革,不仅体现在从思辨范式到生产范式带来的对主体内涵的重释,更体现在对“无主体”运行表象之下的解放使命的确证。
其一,只有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存在,才能成为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主体因素。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将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同义词使用,但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有关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简单范畴,‘无产阶级’则是有关真理 (truth)的范畴,指名副其实的革命主体(revolutionary subject) 本身”(44)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93页。。齐泽克的这一指责并不说明马克思忽视了“在生产关系中有着客观位置的阶级”与“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能动性主体”之间的界限。马克思不仅指认了仅具有共同利益但没有在生产关系中结成普遍联系的阶级无法走向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而且在现实的经济情势下指出了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历史必然。前者体现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阶级地位的分析:“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7页。;后者体现于《资本论》中对于无产阶级联合必要性的强调:正因为“孤立的工人”在追逐无限增殖的资本生产面前只能“无抵抗地屈服”(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第349页。,“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第349页。。可见,在马克思的界定中,并非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排斥与被压迫地位的社会阶级都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体现为两大阶级主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当代激进左翼重塑解放主体的思想路向是以“词句”的批判代替生产关系中的矛盾,这无意间为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形象的退隐提供了空间。在齐泽克那里,构成阶级对立的两极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与象征阶级(symbolic class)(48)象征阶级是齐泽克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中提出的概念。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矛盾形式,即“被纳入者”和“被排除者”之间的分裂。所谓“被纳入者”就是“象征阶级”,他们是在象征的虚拟世界中工作的人,包括银行家、学者、记者和律师等。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其二,只有以自身经验存在证实现存生产体系解体“症候”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承担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任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存在论奏响了探究“现存世界”解体秘密的序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最终以商品交换规律中价值形式的矛盾指认了无产阶级作为解放主体的历史必然。无产阶级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普遍化的标志。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绝不是因为在“购买契约”中先定的剩余价值生产,而是因为这一交换行为本身使货币关系发生了变革。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又从内部否定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原则的“平等交换规律”。无产阶级自身的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构成性例外”。所谓“构成性例外”即在证明意识形态普遍性的同时又颠覆自身的“症候”性存在。(49)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从形式上看,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行为具有公平的形式,但劳动力商品特殊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与工资的交换,使商品交换形式掩盖着剥削的实质。因此,无产阶级具有解放主体的地位,并非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与商品平等交换的资本主义时代原则相冲突,或是与永恒的道德律令相背离,而是因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特殊地位,“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二)解放的情势根源于资本循环运动中的危机与中断
如果说,马克思以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似自然性的特设规定,从“观念形态”上击穿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而又合乎人性的假象,为主体的解放找寻到了第一个历史前提,那么,主体的解放的第二个历史前提就是在资本循环运动的“现实形态”中对解放时机的科学判断。这体现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根本超越,即对资本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物化形式”的历史分析。
面对传统解释框架中的主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通过对马克思资本分析的辩证方法的当代阐释,在以“自动运行”为表征的资本“物神”背后找寻解放的希望。面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虽然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解读走向了对解放趋势的不同判断,但两者都陷入了同一个理论症结,即没有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相似背后的本质差异。卢卡奇将黑格尔辩证法中作为“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替换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阶级主体,却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特殊表现形式。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自我批评的那样,这种替换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中”(5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阿尔都塞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不再是阶级或现实的个人,却将资本运动的现实逻辑完全类比于绝对精神的思辨逻辑,从而将资本运行过程的内在矛盾与绝对精神中作为“中介”的否定性因素一样,视作了资本主义永恒发展的动力。面对自行运动的资本逻辑,晚年的阿尔都塞将打破“神话般纯粹的客观性”的政治可能性空间诉诸“能力” (virtu)与“幸运” (fortuna)的“相遇” (recontre)而造就的匿名主体(52)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第470页。。但在两者的偶然吻合中,主角的名字却留下了“彻底的空白”(53)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第470页。。这一理论趋向也影响了激进左翼对解放主体的形塑。齐泽克不仅立足于“象征秩序”之外的空白——贫民窟——之中确定解放主体,而且还将解放行动的发生看作无法预料的意外。可见,这种将资本的循环运动完全类比于绝对精神的自我演进的观点,只能站在“断裂”的视角下,使现实中解放行动的可能消解在必然与无法预见、确定与不确定的“错位”中。
但问题在于,如果马克思视野中的人类历史进程真的是一个无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的自然过程,那么,这与黑格尔绝对理念发展的客观逻辑体系又有何本质区别呢?难道在资本运动的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危机也能够通过绝对精神的不断“回首”得到消解吗?显然不是。黑格尔正是缺少了对“抽象成为现实”的历史前提的追问,才使其以绝对精神自我实现构成的客观逻辑体系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无意识表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指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所在,即黑格尔辩证法混淆了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与思维过程,从而“陷入幻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借助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把握了资本运动的逻辑,同时又强调了自己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截然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第127页。的思维反映。一方面,不同于精神自我演进中所内蕴的必然性,资本的循环运动过程具有偶然与中断的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交换价值的实现代替了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主导目标。当价值实现的过程只与“支付的需求”有关,而与“需求的实际情况”无关,就会产生过剩的危机。因此,马克思才将“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的过程看作一个“惊险的跳跃”(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第127页。。另一方面,不同于绝对精神演进遵循着走向和解的“同一性逻辑”,资本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G—W…P…W—G′)中,以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交换行为具有特定的历史前提,即“活劳动”与物的条件相分离。这也就是说,资本的生产本身就蕴含着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可能性,并非像“近黑格尔主义”者阐释揭示的那样,只能在资本的铁笼统治之下“犬儒地搁置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的程序”(56)包大为:《身份政治:反噬的政治及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9期。,而是共同蕴含于资本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对抗与流通过程中的“中断”与危机中。
可见,资本分析中的“主体解放”并非马克思主体理论中的“缺失维度”,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始终是双重维度的统一。在客体维度上,不同于围绕追问“我是谁”而展开的解释主体的启蒙传统,马克思在以“现实的个人”确定主体存在的物质根基之后,其理论任务转向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被奴役、被压迫以至于“退场”的历史事实。在解放维度上,不同于绝对精神以不断回归自身而实现的“无限”自我运动,马克思继承又超越黑格尔辩证方法的理论质点在于,他不仅以商品—货币—资本范畴的运动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的现实生产机制,而且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分析识别了资本“抽象外观”背后的主体性否定因素。这也就是说,资本实现自身的运动不能在理念的思辨中完成,而要在其自身对立面“活劳动”的价值创造中寻找其自我实现的物质基础。因而,马克思实现主体理论变革的非凡意义在于对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与解放命运的关切。
总之,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代激进左翼学者重塑主体的尝试是否成功,他们的理论意图都既显现了马克思主体解放宗旨的当代延展,也说明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下主体解放必然趋势判断的科学性,即不论作为解放主体的经验存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要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居于资本内部的否定性主体力量就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