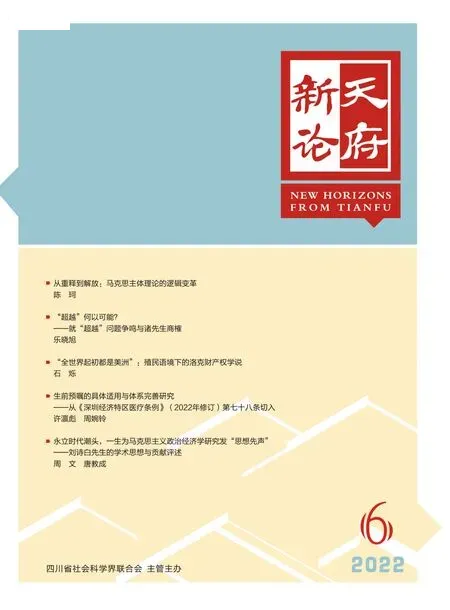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辉格解释的理论批判
张仕洋
辉格史学是以亲辉格党人为主的英国自由主义史学派别,其萌芽于18世纪晚期,繁荣于19世纪,长期居于英国史学界的主流位置。辉格史家的底层历史哲学是为辉格解释。20世纪初,受社会变化与学术转向的影响,辉格史学逐渐式微,广受质疑。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率先将这种质疑理论化、思辨化,提升为对辉格解释的系统批判,推动了当时史学思想的革新。
自1926年获剑桥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并转任教职后,巴特菲尔德终其一生在剑桥任教治学,1959年当选剑桥大学执行校长(vice-chancellor),1968年受封爵士并于同年宣告退休。巴特菲尔德作为英国20世纪最著名的史家之一,其重要地位在英美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退休前曾有多种学术荣誉加身。1955年至1958年其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1965年入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1967年与1968年分别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荣誉外籍院士和美国历史学会外籍会员。美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史杂志》创刊者菲利普·P. 维纳在纪念巴特菲尔德的讣文中评价道: “其对历史进程本质的思考之深刻,可谓前无古人。”(1)Philip P. Wiener, “Obituary: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1, No. 1, 1980.
与西方学界相比,巴特菲尔德在中文学界所获关注难以与其重要性相当。目前中文史学界虽已有学术成果关注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批判,但基本属于思想表征的浅显罗列,未能洞察其思想与英国学术环境、自身其他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深度有所欠缺。(2)大陆学界与台湾学界对巴特菲尔德的研究均有成果。大陆地区对巴特菲尔德的关注起始于科学史的辉格写作,随后在国际关系史方向稍有扩展。参见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张明雯:《科学史的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1期;周桂银:《基督教、历史与国际政治——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任东波:《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相比大陆,台湾地区对巴特菲尔德的关注起步较早,以中兴大学教授周樑楷为主要代表。1985年,周樑楷将其赴美求学于著名史学史家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其中两篇文章以巴特菲尔德为主题。在周樑楷之后也有少数学者对巴特菲尔德予以关注,但未能超越周氏之研究。参见周樑楷:《卡耳及巴特菲尔德史学理论之比较》《史学与宗教——评介巴特菲尔德的两本遗作》,载周樑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华世出版社,1985年,第55-107页;张妙娟:《一个基督徒的历史观——巴特菲尔德及其〈基督教与历史〉》,《史耘》1999年第5期;方志强:《时代中的史家——巴特菲尔德与英国历史的解释》,《思与言》2004年第4期。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具体批判思想完成三个层次的学术观察。首先,在彼时英国的现实与思想语境中探明巴特菲尔德关注辉格问题的学术成长路径,同时辨析“辉格史学”与“辉格解释”两个学术概念。其次,亦即主体部分,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构建巴特菲尔德批判辉格解释的思想体系,尤其突出其对传统思想的革新之效。最后,扼要点明巴特菲尔德辉格批判的核心不足及其永久性史学价值。
一、辉格概念与巴特菲尔德的辉格关注
虽然在当下的史学史话语体系中“辉格史学”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但其含义的固定有着明显的渐进过程。由于历史学科对于史学史的关注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有起色,对特定史学流派的归纳总结则相对更晚,所以“辉格史学”这一概念的出现远远晚于辉格史学家的出现。
1913年,G. P. 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模糊地认识到:19世纪的英国史学界可能存在一个持有“辉格党历史哲学”的史家群体,哈兰是这一群体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而麦考莱是最著名而雄辩的解释者。(3)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81页。但古奇并没有将其定义为“辉格史学”,更没有明晰辉格的史学特征。直至1928年,H. A. L. 费舍在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拉赖历史讲座上做了题为《辉格派历史学家》的演讲,批判性地评析了麦金托什、哈兰、麦考莱、G. O. 屈威廉等辉格史家,由此正式将“辉格”由一个政治用词转化为一个史学用词,以一党之名的“辉格”代指进步自由的历史观。(4)H. A. L. Fisher, “The Whig Historian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14, 1928. 讲座中提及的“屈威廉”是乔治·奥托·屈威廉(George Otto Trevelyan, 1838—1928),更为人熟知的历史学家是其第三子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后文所称“屈威廉”均为后者。辉格派史学家的目光主要聚焦于政治领域,试图将英国历史解释为19世纪英国式自由胜利的过程。他们强调“传统上的宪政连续性”,该连续性“起源于萨克森时期,经由《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一直延续至汉诺威王朝”。哈兰、麦考莱、肯布尔、斯塔布斯和弗里曼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5)Michael Bentley, “Shape and Pattern in British Historical Writing, 1815-1945,” in Daniel Woolf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4: 1800-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08-209.
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整体的歌舞升平中,取材历史以证明当前繁荣合理且必然的辉格史学颇占主流地位。正如E. H. 卡尔所言:19世纪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将历史视为进步的范例。(6)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1-132页。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格史学开始走入史学内部与社会外部的双重困境。
内部困境来自史学专业化的冲击。从19世纪末开始,以阿克顿勋爵为代表的部分英国史家接受德国史学观念,开始提倡科学倾向的专业化史学。20世纪初,同在剑桥大学任职的J. B. 伯里与屈威廉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伯里承接兰克学派观点认为历史学以科学性为首要,屈威廉却认为史学是同情想象的艺术。这场争论以屈威廉离开剑桥而结束,而其正被称为“最后一位辉格传统的自由主义史家”(7)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7页。巴特菲尔德接受这一观点,曾亲口认可屈威廉为“最后一位辉格史家”。参见Ved 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1, p.258.。辉格史学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社会外部。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停滞和政治纠葛,在战争之中的伤亡破坏与战争之后的迷茫无路,都从根本上挑战了辉格史学的乐观进步主义。对此,米歇尔·本特利形象地说道:“一个一直鼓励迈向进步之未来的学说,在面对着走向死亡的未来时,其无话可说。”(8)Michael Bentley, Modernizing England’s Past: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e of Modernism, 1870-19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辉格史学深陷困境的时刻正与巴特菲尔德的学术成长时刻相遇。巴特菲尔德在剑桥读书的1919年至1926年间,适逢“一战”结束不久,史学界对乐观进步的反思加剧,伯里与屈威廉的争论也余温尚在,这推动了其对辉格史学进行思考。晋升教职后,巴特菲尔德的这种思考仍在持续。C. T. 麦克英泰尔转述其与巴特菲尔德的谈话中对此有明确表达。1930年至1931年间,在进行关于“通史”的讲座和与阿克顿、伯里、屈威廉思想互动的过程中,巴特菲尔德不断思索辉格史学问题,并将这些思索记录为或长或短的文字。随后将这些文字融合为一篇论文,邀请良师益友、历史学家P. C. 维拉科特阅读讨论。在维拉科特的建议下,巴特菲尔德最终决定将这篇论文修正扩充为一册书交付出版。(9)C. T. McIntire,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6.此书即为《历史的辉格解释》(1931)。
此后,巴特菲尔德的反辉格思考并未止息,而是发散至多个方向。1938年,巴特菲尔德受邀至德国多所大学演讲时得知,很多读者读罢《历史的辉格解释》后,非常好奇辉格解释的形成史。这一问题引导了巴特菲尔德关注史学史领域。(10)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xii.随后分别出版的《英国人与其史学》(1944)和《人类回顾自己的过去:历史学术史研究》(1955)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纯粹的理论批判以外,巴特菲尔德也尝试撰写实证作品践行其反辉格思想。这种尝试首先应用于其熟悉的英国史领域,《乔治三世、诺斯勋爵与人民》(1949)即为代表。1948年的春季和秋季学期,巴特菲尔德分别受剑桥大学科学史委员会和神学系之邀,做了关于科学史和基督教的系列讲座。讲座成果均于次年出版,即《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和《基督教与历史》(1949)。巴特菲尔德借由前者将反辉格实践扩展至科学史领域,借由后者在基督教视角下解读了其反辉格思想的合理性。正如其学生莫里斯·考林所评价的,《基督教与历史》就是《历史的辉格解释》的另一种版本。(11)Maurice Cowling,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65, 1981.
由上可见,在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与学术氛围之中,巴特菲尔德形成了批判辉格的学术成长路径。这种批判萌芽于学生时代,以《历史的辉格解释》为标志性起点,随后延伸至不同史学分支进行不断的建构、调整与扩展,始终贯穿巴特菲尔德的治学生涯。G. R. 埃尔顿对此有相似看法:《历史的辉格解释》中的史学观念在巴特菲尔德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复现,其所有对史学方法的论述都是为了整固早前的标准。从始至终,他都是希望建立历史研究的正确功能与必要界限。(12)G. R. Elto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17, No.3, 1984.因此,若仅以表面内容观之,巴特菲尔德所关注的领域颇为繁杂,涉及史学史、英国史、科学史、基督教思想史等。但正如以上所述,繁杂之下,对辉格解释的反思始终是把握其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正是通过以上的连续思考,巴特菲尔德第一次定义了作为史学名词的“辉格解释”。《历史的辉格解释》开篇就言:“本书讨论的是很多史学家的一种倾向——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赞扬已然成功的革命,强调出现于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故事来美化至少是确认当下。”(13)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v, p.v, pp.19-21.巴特菲尔德所言的“史学家”会被当然地认为是辉格史家。但其紧接着说道:“这种倾向是与特定的史学结构与推论方式相关,所有的史学都易于犯下如此谬误。”(14)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v, p.v, pp.19-21.在《英国人与其史学》中,巴特菲尔德更明确指出:辉格解释与政党无关,托利派也不能逃脱辉格解释的窠臼。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就是“英国解释”,就是英国人将数百年前的历史加以利用的方法。(15)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2-3.所以,巴特菲尔德所言的“辉格解释”并不局限于辉格史学,其所批判的是一种当下主义的史学态度。只因辉格史学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因此命以“辉格”之名。
由此可见,“辉格史学”与“辉格解释”二者并非同一事物。前者是指一个史家群体和史学流派,而后者是指一种历史观念和史学方法。虽然二者相辅相成,辉格史学以辉格解释为内在哲学,辉格解释以辉格史学为典型表现,但本质并不相同。巴特菲尔德的重要性也并非在于首次认识到辉格史学的存在,而在于第一次定义并系统批判了辉格解释。而这种定义和批判已经成为学界无法回避之论。正如有学者所言:“巴特菲尔德的权威性恰恰表现在史学界对其术语的广泛接受……大多数这一主题的文章通常在开篇便需征引其论。”(16)Oscar Moro Abadía, “Beyond the Whig History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essons on ‘Presentism’ from Hélène Metzge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9, No. 2, 2008.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反思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即历史观、史学观与方法观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亦即对应本文以下三个部分。
二、历史进程:自然论视角与反道德判断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历史观的反思主要表现为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辉格解释看待历史进程的态度有着一种鲜明的以今溯古倾向,其将当下现实视为必然存在的终点,立足终点反溯过去。辉格宪政史开山者哈兰在《英国宪政史》中言道:“英国的自由是时间推移的缓慢成果,它在等待着完美成熟的更佳时节……而本书正是意在追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原因所在。”(17)Henry Hallam,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 to the Death of George II (Volume I), London: John Murry, Albemarle-street, 1827, p.2.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英国今日的自由原则在历史中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条件的变化更加完美,而“追溯”这种前进和变化正是哈兰撰史的目的。由此可见,辉格解释非常明显地以现状为标准衡量过去,将历史进程看做某种历史目的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有学者将辉格历史观概括为“目的论” (teleology)。(18)巴特菲尔德并没有使用“目的论”这一术语来形容辉格解释的历史观,但其他一些史家的确使用了这一词汇,参见Richard A. Cosgrove, “Reflections on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Vol.4, No.2, 2000; P. B. M. Blaas, Continuity and Anachronis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p.15.
与辉格解释的目的论相对应,巴特菲尔德提倡的是一种历史自然论,即历史上的一切都是无目的地自然发生的,都是不同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自然论的视角下,巴特菲尔德反对辉格解释的线性历史结构,而坚信历史的复杂性与不可知性。其直接表明:看似顺理成章的历史进程实际上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过程,是过去所有的复杂运动、争议纠葛和错综互动,共同产生了这个依然复杂的当下。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历史中任何已知行为和选择的最终结果都无法被预测。(19)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v, p.v, pp.19-21.既然历史千变万化不可预知,那么辉格解释的“历史目的”也就不复存在。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历史进程的争论没有止步于宏观,它还延伸到了一个更普遍、更微观的层面——是否要对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辉格解释认为历史有一个以现实为目的的前进方向,且这一方向必然成功,因为现实已然存在。因此就可将这一方向视为道德判断的准绳,凡是促进历史朝这一方向前进的事件和人物都是正面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反之则是负面的、阻碍历史发展的。这便是辉格史家一向推崇的道德判断。正因此,巴特菲尔德将其比喻为“复仇者”或“法官”——“站在过去的种种纷争之间,让失败者不至于一无是处,让成功者不至于傲气凌人。通过其文字上的无情揭露和公正裁决、笔调上的冷嘲热讽和义愤填膺,使不义者得以严惩、受害者得以复仇、无辜者得以平反”。(20)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1.这便是历史学家进行道德判断的具体表现。
巴特菲尔德对道德判断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其对阿克顿勋爵部分主张的激烈反对上。阿克顿本身并不属于辉格史家群体,至多只能说其部分思想带有辉格色彩。但在当时,阿克顿是对道德判断最具影响力的提倡者,因此也成为巴特菲尔德攻击的主要靶向。阿克顿认为人类社会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化中形成了一套绝对道德,“这套道德原则被镌刻在永恒的丰碑之上,不因观点立场的转换而动摇,不因风俗习惯的改变而消失,也不因教义信条的沉浮而更替”(21)Lord Acto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Gertrude Himmelfarb ed.,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p.28, p.25.。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捍卫这种道德准则,通过赞扬历史上的道德楷模从而成为道德传播者和最诚实之人。(22)Lord Acton, “Acton-Creighton Correspondence,” in Gertrude Himmelfarb ed.,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p.365.阿克顿告诫历史学家永远不要降低道德的要求或公正的标准,因为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逃脱永恒的审判,而史学家正拥有对错误施加审判的权力。(23)Lord Acto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Gertrude Himmelfarb ed.,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p.28, p.25.
针对阿克顿鲜明的道德判断倾向,巴特菲尔德提出了质疑: “任何道德之事都与专业史家无关”(24)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51, p.103, pp.105-116, pp.104-108.。这种无关的首要原因就来自于自然论视角下历史的复杂性与未知性。历史无目的地自然发展,是“多线缠绕的复杂问题”,而非简单的正邪斗争,即使是正直之人也会参与正邪双方,令人无法施加道德判断。(25)Herbert Butterfield, “The Conflict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History,” in C. T. McIntire ed., Herbert Butterfield: 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7.同时,过去的历史参与者并不知未来的结局,亦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将对历史造成何种影响。作为后来人的历史学家也“无力知晓过去之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只能以己度人地按照“人性的一般情况”加以衡量。这种判断别无他用,只会破坏史家的客观性,令所谓的道德标准沦为彼此攻讦的“战术武器”。因此,巴特菲尔德总结道:必须抵制那些宣称史学家是道德裁决者之人,尤其是那些将道德关注转移到对过去的还原之中的人。(26)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51, p.103, pp.105-116, pp.104-108.
在道德判断的问题上,基督教宗教观念对巴特菲尔德的影响十分明显。主要有两点基督教思想深刻影响了巴特菲尔德反道德判断的历史观:其一是人性本恶论,其二是天命有常说。
依据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假设世间充满了睿智正直之人,而应假设人皆罪人。(27)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0, p.42, pp.95-96.众生皆有罪,这种罪恶与生俱来,无法在本性上比较罪恶的高低,历史学家的原罪绝不例外于芸芸众生。与此同时,除了上帝施行的末日审判以外,道德的真理不可能被查明,历史学家的头脑绝不先知于末日审判。(28)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51, p.103, pp.105-116, pp.104-108.因此,当身负原罪的史学家面对着同样负罪的历史人物而自己并不掌握终极道德之时,他们无法对任何人给出有效的道德判断。
天命有常则更为直观。巴特菲尔德相信有一种来自上帝的天命(Providence)左右着世界的运行和人类的命运。(29)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0, p.42, pp.95-96.但是,巴特菲尔德的所谓“天命观”并非一种纯粹的宗教天命观,而是一种接近于历史主义的天命观。这就是说,巴特菲尔德不会以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解释原因,不会利用历史证明天命对人间的干预。其明确表明:我不能告诉人们如果他们读完了两千年欧洲史就会变成基督徒,也不可能指着一段历史对人们说这就是天命的杰作。如果人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上帝的存在,那么即使他们知晓了民族和帝国的浮沉起落、民主和科学的演变进步,他们也不会发现上帝存在于历史之中。(30)Herbert Butterfield, “God in History,” in C. T. McIntire ed., Herbert Butterfield: 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p.11-12.
实际上,巴特菲尔德是以天命的捉摸不定强化历史的不可推测性。如其所言,天命的运行是神秘的,决断是古怪的,天命为了达到其本来的目的会使历史表现出反复无常和自相矛盾。(31)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23.所以,作为凡人的我们不可能预知天命之下历史的走向,更无法判断历史时刻中某一行为的作用,因此也就无法判断该行为的道德优劣。所以,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只是以今人立场对天命的无知推断,是毫无根据也徒劳无用的。这才是巴特菲尔德天命观的最终落脚点。
固然,巴特菲尔德一生皆为虔诚的卫斯理宗基督徒。在论证反辉格的历史观时,其也的确从基督教思想中汲取营养。但是,这完全不等同于说巴特菲尔德的历史观与中世纪的教会史家如出一辙。实际上,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巴特菲尔德是利用“人性本恶”和“天命有常”的宗教思想来巩固历史的复杂性与未知性,进而佐证其历史进程的自然论视角及对道德判断的反对。巴特菲尔德引用基督教思想,“并非是重返迷信,而是要扫除一切对普遍性因果解释的盲从”(32)周樑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华世出版社,1985年,第76页。。这种“普遍性因果解释”的代表就是辉格解释的目的论及对道德判断的提倡。
正是通过对目的论和道德判断的反驳,巴特菲尔德构建了一种与辉格解释完全不同的历史观。辉格解释将历史视为通往当今的桥梁,当今则是历史的必然归宿,借古证今。而巴特菲尔德则认为当今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历史毫无目的也不可推测,每个时代不同因素间的合力将历史推向了如此的现实。而目的论和自然论投射在细节历史中的,则是对道德判断的不同态度。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辉格解释要求史学家用文字惩恶扬善,事实上是在守护当今时代的正义良知;而巴特菲尔德则要求史学家回到过去,去跟随历史走向不同善恶的变迁,只有带着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回到当下审视现实,才会最大程度避免现实由善转恶。
三、史学定位:还原过去与差异性探寻
如前所述,辉格解释的历史观有着浓厚的目的论色彩,其以当下为历史发展之目的,试图建立起一套由古必然至今的叙事结构。与此相应,辉格解释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回溯当下在过去之中的征兆与痕迹以揭示历史目的的必然性。而史学的关注内容则是历史与现实的相同性,因为只有相同性才能证明古今联系的存在,证明目的必然性的成立,以此体现历史发展目的始终延续、从未更改。
以辉格史学最突出的宪政主义特点为例,辉格史家在进行中世纪史研究时会“竭力回溯到中古西欧社会的所谓旧日耳曼传统中,去探寻宪政国家的历史源头”,“放大残留在中古社会中的日耳曼原始民主制的观念和习俗,结合国王的有限权力和封建离心倾向……将封建制与国家、国王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权力对立起来”,以证明当下代议制宪政民主制的合法性。(33)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对此,作为最为著名的辉格史学家之一的麦考莱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光荣革命时期的议会机制和政府原则从13世纪起就存在于古老高贵的条文中,比如无议会不立法、不征税等。(34)托马斯·麦考莱:《英国史》第二卷,周旭、刘学谦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449-450页。
由此可见,目的论下的辉格解释对史学的定位是在历史进程中回溯现实,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共通之处。据此,在翻开史料之前,辉格史家心中就已经以当下为蓝图刻好模板;翻开史料后,将史料按照模板安排位置,多余的则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在如此的作品中,整个历史便有了一条清晰的抽象主线,冥冥之中仿佛有着永恒的规则统治着历史进程并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与此相对,巴特菲尔德提出了两点与辉格解释截然不同的史学观。
第一,还原过去。巴特菲尔德强烈批判了辉格解释注重发掘历史现实价值的取向——“在研究过去时一只眼睛始终盯着当下,史学中所有的罪恶与诡辩皆根植于此”——并进一步提出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还原过去具体生活时的学术丰富性”,亦即“为过去而研究过去”。(35)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p.31-68, pp.10-12.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因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可以被发掘出来,也不是因为过去蕴含着现代道德;仅仅是因为过去是一片陌生之地,过去就是过去,是永不会再重演的过去”(36)Herbert Butterfield, The Historical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12-13.。 因此,任何如辉格解释般的总体目的与理论预设都与历史学家的任务无关,历史学家唯一的任务就是还原过去的事实。巴特菲尔德赋予了“还原过去”极高的史学重要性:正是还原过去才使历史编纂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才能保证史学的人文性特征。当所有处理历史材料的方法变得支离破碎各自为营的时候,只有还原过去才能被证明是“终极的史学”,是“永恒的遗产”。(37)Herbert Butterfield, “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Spade-work behind It,” History, Vol. 53, No. 178, 1968.
第二,探寻不同时代间的差异性。巴特菲尔德对时代差异性的关注实际上与其对还原历史的要求相辅相成。过去之所以需要被还原,正是因为过去与当今有太多的差异之处。这些差异的存在致使今人无法充分合理地理解过去,也就无法理解由古至今的变化。所以历史学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考察历史差异性调和古今,使古人的行为观念得到合理解读。否则,历史的特性和可信性都会被摧毁。(38)C. T. McIntire,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63.关于史学定位,辉格史家威廉·斯塔布斯曾出言不讳:整部英国宪政史仅仅是《大宪章》的评注。(39)William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olume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75, p.532.这句名言的意思是:英国宪政由古至今的发展是以《大宪章》为起点,在其基础上成长扩充而来的。这极大地强化了英国当代宪政与《大宪章》的因果联系,强化了二者本质相同的观念。巴特菲尔德对此回应道:许多专业研究证实了《大宪章》只是封建时代具有封建气息的文件而已,与辉格史家理解的含义截然不同。辉格史家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当今世界的“根源”或“预兆”,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看到的表面相似,而这种相似会引人误解。如果想要纠正这种辉格式的谬误,就必须要求历史学关注历史差异性而非相同性,要求史学家阐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之处,而强调和放大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同之处则与其无关。(40)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p.31-68, pp.10-12.
尽管有着对关注差异性和还原过去的强烈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巴特菲尔德提倡的史学是埋头书斋毫无现实关怀的。相反,其认识到史学研究的就是今人与历史的关系,是古今联结的方式以及这种联结的遗产。(41)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vi.这一点与辉格解释并无不同。但巴特菲尔德反对的是以现今立场回溯历史,将古今联结逆向解释为今日的事物在过去已有相同的存在。反之,他所认为的古今联结是过去经历了无数不被今人理解的转变和过渡发展为当今的现实。而史学的工作就是如实呈现出这些转变和过渡并使其可以被理解。
因此深入来说,还原过去与追溯现实之争实际上是历史学的主要价值之争;而历史相同性与历史差异性之争则是历史学的着眼点与落脚点之争。辉格解释必须通过回溯历史与现实的共同点才能证明当下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而巴特菲尔德却认为必须还原客观差异才能理解由古至今的转变。可以说,巴特菲尔德通过“还原过去”与“注重差异性”两点史学观,对史学定位进行了完全不同于辉格解释的界定。历史学不再研究现存事物的起源,而是研究过去难被理解的真实差异。正如其所总结的那般:历史学的首要兴趣是了解我们先人的生活,保持记忆片段的鲜活,如图像和故事般重温过去。(42)Herbert Butterfield,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in C. T. McIntire ed., Herbert Butterfield: 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7.只有如此,史学才能尽可能减少辉格解释的气息,史学研究所呈现出的才是真实的历史发展路径。
四、史家技艺:责任与意义的平衡
在完成了对历史和史学的观念性思考后,巴特菲尔德将其目光投向历史学家的具体写作实践,开始对辉格解释的方法观进行反思。他将历史学家进行写作的核心问题概括为“节略”或称“概说” (abridgement)。“历史学家的技艺正是节略的技艺,历史学的难题正是节略的难题。”(43)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102,p.22, pp.5-7,pp.102-103.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在对历史进行节略的同时,不得改变历史的意义和其所传达的特定信息。(44)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102,p.22, pp.5-7,pp.102-103.然而在巴特菲尔德的眼中,辉格解释的历史概说并没有承担起这份责任,而是辜负了这份责任。辉格式的历史编纂并不是“节略”而是“筛选”——基于“以当下为准”的原则进行的筛选。在如此的筛选中,历史的复杂性被大大简化。巴特菲尔德形象地说道:“辉格解释视历史为数学,将历史简化至几何图形一般,在多条线段中留着清晰的空白。”(45)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138.为了规避辉格式的错误,巴特菲尔德提出了两点纠正措施。
第一,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应尽量描述细节。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叙述越节略,就会成比例地变得越辉格。在此基础上,其分析了两种补救措施的不可行性。其一,不能用与辉格解释相反的节略作品,主要是托利派史学,来纠正辉格式错误。因为“偏见与相反的偏见”只能更加偏颇,而非平衡。其二,不能用小范围专门史的细节研究尝试渐进修补。虽然巴特菲尔德承认辉格错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因诸多专门史研究成果而有所纠正”,但他认为这种努力远不足够:一则是因为这些成果对历史整体轮廓的重建仍显缓慢;二则是因为这是一种把新研究补缀在旧体系中的倾向,所以注定无法彻底解决历史写作中的辉格谬误。(46)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102,p.22, pp.5-7,pp.102-103.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尽量避免节略。而与节略出的宏观进程相对的则是描述出的微观细节。巴特菲尔德希望史学家不必关注因果解释,只需通过讲述细节向读者传递全部的故事、揭示全部的复杂性。历史学家的最终成就就是呈现出一篇细节详尽的研究。(47)C. T. McIntire,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65.
然而巴特菲尔德对节略的批判和对细节描述的提倡过于纸上谈兵,恐怕所有的历史写作者都必须承认:没有任何史学家可以写出未经节略的作品,没有任何历史研究可以标榜其仅仅在展现历史细节。如果将历史细节不经行文构思仅仅全部描述出来的话,这部作品也会凌乱无序而难以卒读。一旦作者对细节进行了整理安排,则必然有所选择节略,必然有史学家的主观参与。
考虑到这一点,巴特菲尔德又提出了第二点措施——有原则地节略。这种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在不得不进行节略时,不得事先在头脑中建立一个模型或预设一个理论,而是通过节略向受众更客观真实地展现历史的复杂性。也就是说,这个原则将一个“保留什么丢弃什么”的机械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何既缩减细节又能保留主旨意义”的有机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的概说都是一种印象主义,所有的史学作品本质上都传达了作者对历史的印象,但关键在于这种印象是史学家预先想象的还是其通过“捕捉细节、探察关系,进而领悟到的”(48)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102,p.22, pp.5-7,pp.102-103.。
然而遗憾的是,巴特菲尔德的思考止步于此了,他并没有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型节略提出更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何使历史叙述既能不加节略地描述细节又能条理清晰,历史细节保留和省略的判断标准为何,是否允许史学家持有指导写作的历史主题或主旨,这些问题巴特菲尔德都没能给出答案。除了有关节略的要求过于模糊外,巴特菲尔德的方法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剥夺了历史学家的个体意义。如前所述,巴特菲尔德在历史观上要求史学家将历史看作完全自然的进程,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道德判断;在史学观上认为历史学的价值在于还原过去,“为过去而研究过去”;在写作实践上则要求史学家尽可能展现历史细节,至少是有原则的节略。如果完全按此要求进行历史研究,那么史学家极有可能沦为一个单纯的工具,在成山的故纸堆中复原注定无法完全复原的历史世界。
为了在历史学家完成责任的同时最大程度平衡其意义所在,巴特菲尔德引入了“历史想象”这一概念。伊格尔斯认为历史想象是指史学家利用思维的虚构,将经验认定的事实编排于一个完整的故事中,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必然有之。(49)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6页。巴特菲尔德也对此认可道:“即使是声称与确凿史料紧密相连的史学家也不可能不经同情的想象就能完成其作品。”(50)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36.
巴特菲尔德要求史学家利用历史想象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填补史料的空白。仅仅依赖史料研究历史颇有局限——太多的史料已然丢失,太多的历史未被记录,太多的历史无法记录。(51)C. T. McIntire ed., Herbert Butterfield: 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xlvii.这阻碍了历史学家捕捉过去,复原完整的过去生活,阻碍了其将历史写成一个完整的叙事。(52)Herbert Butterfield, The Historical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22-24, p.50, pp.102-103.历史想象恰恰能在史料沉默之处发声,给予历史连贯性和完整性。第二,建立古今理解的桥梁。因为时代环境的不同,在面对过去的时代时,普通人常常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困惑。而历史想象,通过历史学家的专业思维,将人们传送回过去,弥合了古今鸿沟,甚至消灭了时间。(53)Herbert Butterfield, The Historical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22-24, p.50, pp.102-103.正是经由历史想象,我们才了解了中世纪人们的生存条件,学会了如何获得对事物的不同感觉,领悟了我们与其他时代的关系。(54)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5, p.91.
然而,历史想象的存在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条件:尽管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各不相同,但人性必须始终如一。只不过这种相同的人性覆盖在不同的伪装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55)Herbert Butterfield, The Historical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22-24, p.50, pp.102-103.如果没有这种人性的相通性,那么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中的合理想象便成为不可能。可是,这种人性一致论恰恰也是辉格解释以古溯今、道德判断等诸观念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当巴特菲尔德提出历史想象之时,他就与辉格解释在人性一致论上达成了共识。既然人性本质不变,那么人类社会就可以存在一个总体不变的发展目的,就可以存在一个永恒道德;既然都是为了达成同一目的和存续同一道德,不同时期的人类社会当然会有可资当今借鉴的共同点。因此,人性一致的共识必然会削弱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前述反对。
对此问题,巴特菲尔德无法批评辉格解释不应使用历史同情的想象,于是转而攻击辉格解释仅针对特定历史进行同情想象:辉格史家的同情可被察觉则并无害处,但其错在会对某些历史事物中止同情,错在不能以相同热忱对其他历史部分进行同情理解。(56)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71;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51, p.121.然而,很难说这是足够令人信服的辩驳,以至于卡尔·贝克尔认为巴特菲尔德的历史想象在本质上与辉格史家们运用的方法并无不同。(57)Carl Becker, “Book Review of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 No. 2, 1932.
事实上,巴特菲尔德对历史学家具体技艺的看法体现了一种平衡。他一方面试图利用细节描述和有原则的节略保证史学家完成还原过去这一责任;另一方面利用历史想象保留史学家个体价值,纠正节略原则的偏激。历史学家的自主性在忠于历史整体性的节略要求下被极大地束缚,又在历史想象的名义下获得一定释放。然而,保证责任与意义互不侵犯的界限却十分模糊,实践中也难以应用。历史想象不仅没能解决史家意义的问题,反而将巴特菲尔德导向了与辉格解释相同的理论平台。所以巴特菲尔德对史家技艺的理解是平衡,更是矛盾。
五、结 语
通过以上思考,巴特菲尔德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反辉格体系:由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历史观),延伸到对史学定位的看法(史学观),进而以两重观念为基准对史学写作实践中的史家技艺提出要求(方法观)。与辉格解释相对,巴特菲尔德将历史的中心由当下推回过去,一次次重申必须“为过去研究过去”。他将整个历史看作无法预测的互动网络,没有目的也没有规律,不被任何人察觉地自然演化至今。所以以今判古的道德判断是对历史的苛责,以古证今的追根溯源是对历史的亵渎。只有努力还原逝去的过去,才是历史学宝贵的价值。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以展现真实为责任,以想象同情为意义,最终形成与辉格解释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
然而,尽管巴特菲尔德有着高度空前的思考,但其对辉格解释的反思并非无懈可击。其核心问题在于过于低估了当下主义取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巴特菲尔德努力将当下排除于历史研究之外,不允许过去成为当下的先导,更不允许史学家预设当下与历史的联系。基斯·C. 斯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巴特菲尔德在要求其他人不要进行理论预设之时,其自己早已预设了新的理论,且这种预设的坚定性并不亚于辉格史学。”(58)Keith C. Sewell,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3.这一预设就是:史学研究必须摒弃一切当下主义。可是无可否认,史学家的历史兴趣与知识方法必然来源于当下的个人经历。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历史研究中的当下主义不可能完全避免,因为恰当的研究选题就来自当代目光的审视。”(59)Stephen G. Brush, “Scientists as Historians,” Osiris, Vol.10, No.1, 1995.正因此,巴特菲尔德在具体的史学写作实践中也无法坚持自己提出的原则,其科学史、英国史等实证性作品都饱受亦有辉格谬误的争议。但是,巴特菲尔德的重要性本就不在于创作了天衣无缝的历史作品,而在于他改变了人们仅以辉格解释思考历史的方式。
在时代变迁和以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理论批判下,辉格史学于20世纪初便销声匿迹、风光不再。英国史学也早已完成专业化,不可能再落入党派史学的窠臼。但不断回顾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反思却仍有意义,原因在于辉格解释这种历史思维和史学观念会始终留存不灭。费舍在开篇提及的讲座中说道:“曾经是争议则永远是争议。只要人性不改,总会有人倾向权威,有人倾向自由;有人在意传统的保留,有人在意革新的尝试。”(60)H. A. L. Fisher, “The Whig Historian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14, 1928.后者是辉格,而前者是辉格的反对者。二者以这种永恒持续的争论平衡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好奇。史学家当然明白过去之事不因反复思索而更改,因此对辉格解释的思考不可能局限在史学内部,必然回应着社会中的辉格争论。所以,只要社会中的辉格态度没有消失,则史学中的辉格解释也会永存。
正缘于此,史学中的“辉格”一词非但没有随着辉格史学的落寞而消散,反而扩展到了包括科学史、法律思想史、宗教改革史在内的诸多史学研究领域。(61)Richard A. Cosgrove, “Reflections on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Vol. 4, No. 2, 2000.亦缘于此,2012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克罗农发表评论称:巴特菲尔德之所以影响深远,正因其阐述了某些史学家持续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62)William Cronon, “Two Cheers for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Perspectives on History, Vol.50, Iss.6, 2012,https://www.historians. 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september-2012/two-cheers-for-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 2021-11-04.这种困境就是对始终存在的辉格解释的取舍。而每当史学家取舍不决之时,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反思都是不可回避的史学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