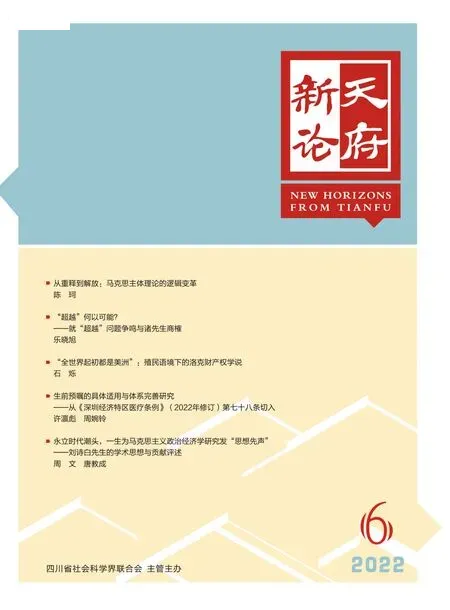“超越”何以可能?
——就“超越”问题争鸣与诸先生商榷
乐晓旭
“超越” (transcendence)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宗教与哲学领域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学界对“超越”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学者们大都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基于中西比较哲学视角,阐明儒家“超越”概念的真实意涵,探寻儒家现代化转型的路径。(1)参见黄玉顺、任剑涛:《儒学反思:儒家·权力·超越》,《当代儒学》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常会营:《“中西会通视域下的儒家超越性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儒学》第19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本文从当前“超越”问题的争鸣入手,在对“超越”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打破传统学界对“超越”概念的存在者化理解,转换思想视域,从本源层级寻求“超越”何以可能的存在论根基。
一、引言: “超越”概念及其汉译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超越”作为一种外来词汇自海外传入中国大陆以来,对“超越”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概念的翻译与诠释问题。“超越”概念出现于西方中世纪,源自拉丁语的transcandere,本意为“跨过”“超过”(2)Oxford Latin Dictiona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161.。动词性“超越” (transcend)指超出某种界限或范围,涉及“超越主体”以及“被超越对象”,这就决定了存在者层级上的“超越”概念总是在主客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名词性“超越” (transcendence)一般包含两方面,“广义上指从其他事物中上升或高于其他事物的性质;在哲学中,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更高层次的存在的性质。”(3)英文原文:“Transcendence, broadly, the property of rising out of or above other things (virtually always understood figuratively); in philosophy, the property of being, in some way, of a higher order.”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925.在哲学中, “超越”是指某种主体所具有的一种优越品质、能力或状态,即超出某种通常的界限;而在宗教学中,“超越”指“上帝”,即最高的神圣存在者。
而与以上两种词性有所不同,形容词性“超越”有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两种译法。最早对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进行区分的是康德(4)“(先验)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的),然而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说的。如果这些概念超出经验的范围,它们的使用就叫做超越的使用,要把这种使用同内在的使用,即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的使用,区别开来。”参见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2页。。Transcendent指超出可能经验的限度之内,其反面是“内在的” (immanent)(5)“我们要把其应用完全限定在可能经验的限度之内的原理称为内在的原理(der immanenteGrundsatz),而把宣称超越这些界限的原理称为超验的原理(der transzendenteGrundsazt)。”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康德认为,意志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ill)、灵魂不死(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和上帝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这三个命题在任何时候对于思辨理性来说都依然是超越的,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亦即对于经验的对象来说允许的、从而对我们来说以某些方式有用的应用”(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2页,第436页,第45页。。因此,康德将它们仅仅视为实践理性的公设,“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推论到这个确定的条件由以出发的有条件者,本身被先天地认识为绝对必然的”(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2页,第436页,第45页。。Transcendental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2页,第436页,第45页。,它是先天的(a priori),但又完全限定在可能的经验限度之内,与经验相关但在经验之上,是独立于心灵的先天构造。(9)“惟有使我们认识到某些表象(直观或者概念)仅仅先天地被应用或者仅仅先天地可能以及何以如此的知识,才必须被称为先验的(即知识的先天可能性或者知识的先天应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9页。康德认为,transcendental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相关,是对纯粹理性本身的来源及其界限进行批判性考察,如作为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空间以及作为知性层面的知性范畴。因此,在康德哲学中,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都是基于主客对立基础上的存在者化理解,并且在本质上归属于主体人自身,即一个归属于人的实践理性,一个归属于人的心灵。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现代话语体系下,尽管对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的翻译仍存在争议(10)在中国大陆学界,主流康德研究者倾向于将“transcendental”译为“先验的”,将“transcendent”译为“超验的”,如蓝公武、韦卓民、邓晓芒、李秋零等。而在中国台湾学界,牟宗三将“transcendental”译为“超越的”,而将“transcendent”译为“超绝的”;劳思光则将“transcendental”译为“超验的”,而将“transcendent”译为“超离的”。本文对于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的翻译均采用黄玉顺的译法,即将transcendent译为“超凡的”,将transcendental译为“超验的”。参见王庆节:《“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三重定义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康德批判——兼谈“transzendental”的汉语译名之争》,《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倪梁康:《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但是对其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共识,即transcendent关涉神圣至上神,而transcendental关涉人自身。黄玉顺将其总结为,transcendent(他将其译为“超凡”)的“超越主体”是作为神圣外在超越的至上神——“上帝” (God)或“天”(Tian), “被超越对象”则是我们生活的“凡俗世界” (secular world);transcendental(他将其译为“超验”)的“超越主体”是人本身, “被超越对象”则是凡俗世界中人的感性经验,所谓的“超验”就是超越经验。(11)参见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因此,通过对“超越”概念及其汉译问题的梳理,可以看出,不管是transcend、transcendent还是transcendental,它们都是基于主客架构下的存在者化的思想视域,在这种思想视域中,存在者乃是先于“超越”概念存在的,是“超越”得以可能的前提。受此影响,中国哲学界对“超越”问题的讨论亦局限于存在者领域。
二、关于“超越”问题的争鸣
在中国学界,有关“超越”问题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新儒家。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际学界宗教对话的深入开展,为与西方宗教学中作为神圣“外在超越”(external transcendence)的“上帝” (God)相对应,现代新儒家提出“内在超越” (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概念,以在中西文化对峙的前提下凸显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在港台新儒家中,牟宗三最早对“内在超越”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讲道: “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 。因此,我们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Immanent与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 。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页。他将作为神圣外在超越者的“天”内化为人本身,以便从人自身寻求形上根基。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中,将“内在超越”改为“内向超越” (inward transcendence)(13)张汝伦认为:“(余英时)郑重其事提出能避免‘内在超越’概念可能引起的误会与混乱的‘内向超越’,也不是他的‘孤明先发’,而是史华兹的发明。史华慈在《古代中国的超越性》(1975年)中就已提出‘向内超越’(transcendence inward)的概念。”参见张汝伦:《论“内在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认为“中国轴心突破的最后归宿于‘内向超越’”(14)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21页,第221页。。而他之所以使用“内向”一词,是“以其他文明的‘超越’形态为参照系而概括出来的……西方文明可以代表‘外向超越’的典型;在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的超越才显出其‘内向’的特色”(15)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221页,第221页。。随后,汤一介在《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一书中指出: “如果相比较地说,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是以外在超越为特征。”(16)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主张“内在超越”。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亦在其《中国古代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inAncientChina)一文中明确指出,“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最古老的中国世界观,而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导倾向之一。然而,这是一种包含了‘超验’(transcendental)元素的关于世界的看法。”(17)Benjamin I, “Schwartz: Transcendence in Ancient China,”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 Vol.104, No.2.因此,中国哲学中确实存在“超越”的成分,它表现为transcendental意义上的“超越”。由此可见,现代新儒家提出“内在超越”说的目的就在于“提升中国文化,对抗西方文化”(18)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学术界》2020年第2期。,而这种将“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视为中西哲学差异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且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固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下儒学思想转型的重要理论发展,是基于当时生活情景下的理论必然,应当加以同情地理解。但是,近年来,随着当下生活情境的转变以及对“超越”问题理解的深入,这种基于中西对立前提下对“超越”问题的理解却饱受争议,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理论层面质疑“内在超越”概念本身的合理性。李泽厚提出,“内在超越”的“内在”与“超越”乃是相互矛盾的,“严格说来,中国只有‘超脱’,并无‘超越’”(19)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3页。。蒙培元认为,“内在超越”容易产生逻辑问题(20)蒙培元:《蒙培元全集》(第八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4页。。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超越和内在的对立本身,是出于西方哲学的传统”(21)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因此,“‘transcendence’这一概念则含有独立性,似乎并不适合诠释儒家思想”(22)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张汝伦则认为“内在超越”论实际上暴露出了以西释中的根本缺陷与问题,“不但根本误用了‘超越’这个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本身也讲不通”(23)张汝伦:《论“内在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二是在现实层面反思“内在超越”观念所带来的影响。蒙培元指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更加注重道德实践而忽视了认知理性,阻碍了理性精神的发展。(24)参见蒙培元:《薛瑄哲学与理性主义》,《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增刊第1期。黄玉顺将“内在超越”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作为神圣界代言人的儒家丧失了独立的生命形态而沦为世俗权力的奴仆;在信仰层面, “超越”价值的丧失最终导致了神圣敬畏感的丧失。(25)参见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学术界》2020年第2期。任剑涛认为,儒家“内在超越”阻断了神人相通和物我互动,最终导致了两种悲剧性结果:“一是在人之上缺乏更高位的存在,人的行为之诉诸道德性修为的危险陡增;二是在人心之外不存在独立的物理,因此难以镜式的认识自然。于是权力屈从与科学缺席便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短板。”(26)任剑涛:《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三是打破对“超越”观念进行内外划分的固有传统,对中国哲学的“超越”观念做出新的创建。张世英提出,中西哲学均具备“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的传统,“纵向超越”是从现实具体事物到永恒抽象的本体世界的超越,“横向超越”是从现实具体事物到现实具体事物的超越。(27)张世英:《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蒙培元的“情感儒学” (Emotional Confucianism)(28)参见黄玉顺等主编:《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感超越” (Emotional Transcendence)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更多地是讲情感的超越”(29)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超越”本身就是情感性的,“情感超越”并非实体论意义上的超越,而是境界论意义上的超越。赵法生提出“中道超越” (Transcendence of the Middle Way)(30)参见赵法生:《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齐鲁学刊》2018年第2期;《论孔子的中道超越》,《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的概念,认为“中道超越是以体悟客观存有的天命和天道为前提,以主客观兼顾贯通为原则,以身心合一和仁礼双彰的人伦日用实践工夫为路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的超越形态”(31)赵法生:《论孔子的中道超越》,《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吴先伍也提出了“横向超越”(32)参见吴先伍:《横向超越:儒家哲学的形上之维》,《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自我超越”抑或“超越自我”?——儒家形上超越的他者之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造塔”与“织网”——中西哲学的形上超越之路》,《云梦学刊》2020年第6期。的概念,但与张世英不同,他认为儒家所追求的“横向超越”,“第一,重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第二,强调自我对于他者的责任。第三,关注世界的时间性。”(33)吴先伍:《横向超越:儒家哲学的形上之维》,《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蔡祥元从“感通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寻求“内在超越”何以可能的理论根源,“感通或仁,才是人心的根本,是人的真实生命所在,也是其内在超越的最终依据”(34)蔡祥元:《从内在超越到感通——从牟宗三“内在超越”说起》,《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是对“内在超越”的深化或拓展。郭萍从“自由儒学” (Liberal Confucianism)角度出发,提出自由问题是与作为哲学、宗教根本问题的“超越”问题相契合的,“自由即主体性超越。其中,相对主体性超越,是以绝对主体性为终极目标的超越;绝对主体性超越则是绝对主体性的时代性转变”(35)参见郭萍:《自由:主体性超越——儒家自由的超越论省思》,《学术界》2021年第3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学界关于“超越”问题的争鸣打破了现代新儒家以来对中国哲学“超越”问题研究的传统思维定式,但是,这其中也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超越”概念的理解总是局限于某种存在者化的思想视域。一方面,对“内在超越”合法性的质疑实际上并未走出中西哲学对立的传统主客思维模式,他们仍是站在西方哲学的视角上来否定中国哲学所具备的“超越”观念;另一方面,对“内在超越”所做的反思仅仅局限于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现实层面,这就意味着以上两种质疑和反思始终限于主客对立的经验论立场之下。除此之外,当今学界对于“超越”问题的新创见实际上也并未摆脱存在者化的思想视域。尽管张世英将“纵向超越”与“横向超越”视为中西哲学的共有特征,但是其“超越”概念仍局限于现象界;蒙培元的“情感超越”本质上是主体哲学视角下的“心灵超越”,因此“超越”概念实则是在主体心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赵法生的“中道超越”将中国的轴心突破归结为周公的道德化突破和孔子的内向化突破两方面(36)参见赵法生:《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而这两者实际均归属“内在超越”,因为他所强调的“德”是主体性的“人德”;吴先伍的“横向超越”将“超越”限定在形下存在者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从而彻底消解了“超越”概念的形上层面;蔡祥元尽管持现象学的立场,却将外部超越性问题的解决落脚到深化认识论的方式上(37)蔡祥元:《从内在超越到感通——从牟宗三“内在超越”说起》,《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意味着他又重返康德认识论路径,从人的自身出发,基于认识论的视角来建构“外在超越”;郭萍将自由视为一种主体性的超越,实际上悬搁了对于前主体性、前存在者化的对“超越”的理解。
由此可见,当今学界对“超越”问题的质疑、反思和建构实际上总是某种存在者化的思想视域。所谓的“存在者化的思想视域”是将存在者视为“超越”得以可能的前提和根基,而这种思想视域必然面临着“存在论困境”,即存在者是否以及如何能够确证其自身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 “超越”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存在者的存在,而是有其“超越的本源” (the source of transcendence)。所谓的“超越的本源”并不以存在者为前提,正好相反,存在者只有以“超越的本源”为源泉和前提才是可能的,而这个“超越的本源”正是生活,即生活本身就是超越。现代新儒家所讲的“内在超越”“外在超越”是将“超越的本源”即生活对象化后的结果,而“超越的本源”则并不涉及“超越主体”和“被超越对象”。
三、关于“超越的本源”探寻
实际上,但凡讲“A何以可能”,即已经意味着A是一个存在者;即便本来是说的存在活动、生活,也已经将其存在者化,A成为一个被陈述者。因此,“超越何以可能”这个表达,其实已经将“超越”视为存在者,或者已经存在者化。这也是“超越”问题争鸣中的“超越”观念普遍存在者化的一个原因。同理,严格说来,“超越的本源”这个表达也是存在者化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超越的本源”之“本源” (the source)与西方哲学中作为终极奠基性的原初存在者(如上帝)有所不同,儒学所说的“本源”“则是更进一步‘溯源’,找到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本身,这种存在就是生活及其情感显现……而作为终极存在者的本体,不过是渊源于存在及其情感显现的东西。”(38)黄玉顺:《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东岳论丛》2007年第6期。
在哲学史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对“超越”问题的存在者化的理解方式实则不断受到质疑,并且出现了试图探索“超越的本源”的倾向。自康德首次对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进行区分,并将其划入人类自身的范畴,开启对“超越”概念理解的主体化进程以来,海德格尔便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试图打破传统知识论和宗教神学对“超越”概念的理解,将“超越”归于此在范畴;黄玉顺则在“变易本体论”概念之上,试图解构传统本体论,建构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Transcendence Ontology)。
(一)此在现象学的“超越”观念
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超越”观念是在胡塞尔基础上的发挥。胡塞尔一方面持悬置“超凡存在物” (the Transcendent)的态度,将超出意识以外的东西放入“括号”,存而不论,“其结果却是使这些存在都成为了‘内在的’,即由意识本身的结构得到解释因而不再与(人的)意识相外在、相对立、相异化的”(39)邓晓芒:《胡塞尔现象学导引》,《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这就意味着“超凡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内在超越性”;另一方面,他认为transcendental“就是一个动机、一个去刨根问底,追问所有认知之形成活动的最后源泉,追问认知者对自己本身以及对其认知着的生命的自我思考之最后源泉的动机”(40)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6页。。胡塞尔哲学中的transcendental不再像康德哲学中那样与经验世界相关,而是与意识方式或存在方式相关,“一切其他形式的存在都是相对于及依存于先验意识的绝对存在”(41)德尔默·莫兰、约瑟夫·科恩:《胡塞尔词典》,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因此,胡塞尔所谓的“超验哲学”“要‘追溯’一切知识的根源,并且这个根源只能在自我(ego)中找到”(42)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1页。。这就意味着,胡塞尔的“超越”观念包含在纯粹先验意识的“意向活动” (Noesis)之中,“意向性把一切变为意识之内的东西,把外在超越变成内在超越,实际上是取消了超越本身”(43)张汝伦:《超越与虚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而这种“意向活动”实际上是主体人的活动,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观念仍是存在者化的主体性超越。
对此,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这种transcendens的一切展开都是超越的认识,现象学的真理(存在的展开状态)乃是veritas transcendentalis ‘超越的真理’”(4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5页,第412页。。他在对知识理论层面和神学层面的“超越”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强调: “超越既不是内在领域与外在领域之间的某种关系,以至于在其中要被逾越的,是一种从属于主体的界限,它把主体从外在领域分隔开。超越同样不首先是某个主体与某个客体的认识着的关系,作为其主体性的附加物,为主体所特有。超越尤其不简单地是充盈的东西,或有限认识不可通达的东西的头衔。”(45)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2页。因此,海德格尔的“超越”实际上意味着“此在必须超越被专题化了的存在者。超越并不是客观化,而是客观化以超越为前提”(46)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5页,第412页。。他将“超越”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之主体性的原始状况。主体作为主体超越着,如果它不超越着,也就不是主体。生存活动就意味着原始的逾越,此在本身就是逾越。2. “超越”的意思并不是逾越将主体首先封闭在某个内在空间的界限,而是说,被逾越的是可能对主体公开的存在者本身,更确切地说,恰恰在其超越的基础之上。3.作为主体的主体超越“之所向”是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4.此在之超越的基本现象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47)参见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主体并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他所谓的“此在”概念,“此在”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而这个存在方式就是“超越”。因此,海德格尔的“超越”实则包含两方面,“一是存在之为存在的超越意义,一是此在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的‘能在’的超越”(48)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一方面,作为此在的本质,“超越是在—世界—之中—存在”(49)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 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根据,“关于生存之超越的陈述,是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陈述”(50)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在这里,海德格尔反对将“超越”进行存在者化的理解,而将其视为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即“超越”并不仅仅是一种存在者意义上的超过、超出,而是“人之此在所特有的东西,是作为先于一切行为而发生的这个存在者的基本机制”(51)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5页。。它先于主体而存在,“标志着主体的本质,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52)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5页。。并且作为此在的本质, “超越” “取决于人们如何规定主体之主体性,也就是说,此在之基本状况”(53)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超越的此在,给予每一个实际存在的存在者进入世界的机会,“这种从此在方面的机会之给予,无非就存在于超越活动中”(54)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另一方面,“超越”指超出作为存在者的自身而回归此在之为之故,“超越就是超越自己的存在,超越作为与他人共在的存在者,超越自然或用具意义上的存在者。”(55)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因此,海德格尔的“超越”是“使具体存在者(beings)‘去蔽’的一种境界”(56)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即摆脱被抛的沉沦境遇,真正达到此在的本己性的建构,而“此在之本质的存在者,必然作为自由而彰显”(57)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因此,只有通过“超越”活动才能重新获得自由,“自由本身就是超越的,对于存在者的超出通过自由发生且向来已经发生,而我们始终以这样的方式遭遇这种自在存在着的存在者,即我们通过自由而返回到这里,从源头出发而在源头之中”(58)马丁·海德格尔:《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赵卫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第238页,第227页,第272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4页。。
通过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中“超越”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矛盾。尽管在他看来,所谓的“超越难题”是一种存在论问题, “超越”乃是先于存在者而存在的,但是“超越”实则被限于此在的范畴之下,“被把握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超越,是人之此在所具有的。”(59)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2页,第162页,第165页。而此在在本质上仍归属于主体人自身,此在“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60)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页。它仍作为一种存在者而存在,这就意味着海德格尔的“超越”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存在者化的思考,并没有跳出存在者化的思想视域,他的超越论实则是此在现象学的“超越”观念。但是,这种对于“超越”问题的存在论理解却为我们敞开了一种思考“超越”问题的新思路。
(二)生活儒学的“超越本体论”
近年来学界在反思现代新儒家“内在超越” “外在超越”概念的基础上, 针对中国哲学中的“超越”问题提出了许多富含创造性的见解。其中,黄玉顺从对政治哲学的关切出发,尝试跳出传统学界对“超越”问题的理解,建构基于现代生活方式下的“超越本体论” (Transcendence Ontology),为重思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超越”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
自2020年开始,黄玉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超越”问题的相关文章。(61)实际上,自2019年开始,黄玉顺就开始思考“超越”问题,只是到了2020年才有相关文章发表。参见黄玉顺、任剑涛:《儒学反思:儒家·权力·超越》,《当代儒学》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他在反思当下“超越”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具体论述周公(62)参见黄玉顺:《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尚书·金縢〉的政治哲学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孔子(63)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孟子(64)参见黄玉顺:《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墨子(65)参见黄玉顺:《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董仲舒(66)参见黄玉顺:《董仲舒思想系统的结构性还原——〈天人三策〉的政治哲学解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等哲学理论中的“超越”观念,对中国哲学的“超越”观念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入的研究。黄玉顺十分注重本体论(ontology)的建构,面对后现代哲学影响下产生的“解构本体论”的哲学思潮,他指出“哲学的核心恰恰是本体论”(67)黄玉顺:《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本体论或是说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它为诸多的形而下者提供了“本体论承诺” (ontological commitment)(68)“对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之存在、甚至对任何个别存在者之存在的承诺,都已蕴涵着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用唯一绝对的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存在者何以可能;而任何一个陈述,最终都指向了形而上学。”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他强调“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69)黄玉顺:《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因此,他提出了“超越本体论”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生活儒学” (Life Confucianism)的“内在转向” (an internal turn),即由“变易本体论” (Change Ontology)转为“超越本体论”。在他看来,“变易本体论”是普遍性的概念,它是以“变易”为一切存在者的本体,此时“变易”这个本体不是存在者,而是一切存在者的根源,即“存在”,一旦我们将其视为某种“形而上者”的时候,它就被存在者化从而变成观念系统中的最高范畴,此时“超越本体论”便应运而生。(70)黄玉顺:《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超越本体论”的提出试图解构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在超越”的独有论和优越论,还原到中国前轴心期的神圣外在超越,最终建构顺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神圣的外在超越者。(71)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因此,“超越本体论”归属“观念奠基”(72)关于“观念奠基”和“观念生成”的相关论述,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 (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的序列之中,它仍是对形而上存在者层级上的“超越”概念的理解。
实际上,黄玉顺的“超越本体论”在某种意义上蕴含着建构前存在者层级上的“超越”概念的倾向。一方面, “超越本体论”的建构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超越本体论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性;这就是说,超越本体论是在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内、特别针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本体论建构”(73)黄玉顺:《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因此,形上“超越本体论”的建构是基于现代生活方式之下的,这意味着现代生活方式乃是先于“超越本体论”而存在的,“按照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这种建构并非照搬古代的那个外在神圣超越……而是一种‘重建’,因为今天的生活方式已非昔日的宗法社会或家族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74)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可以说,这里所谓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前存在者化的、本源层级的生活展现,这与其“生活儒学”的理论密切相关,“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一切存在者皆由存在给出,即皆由生活生成,亦即一切皆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75)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另一方面,“超越本体论”的建构与作为本源“生活情感”的敬畏情感密切相关。他认为,形上超凡存在者的生成与生活情感密切相关。生活情感是无物的,是先行于任何物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被这种生活情感给出的。生活情感是有多种显现样式的,敬畏情感便是显现样式之一。敬畏情感的最本真含义并不是指向某种具体对象,它作为一种情感体验是先于敬畏对象以存在其自身,“换言之,作为敬畏对象的‘神圣超越者’乃是敬畏情感对象化之结果”(76)黄玉顺:《“情感超越”对“内在超越”的超越——论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哲学动态》2020年第10期。。这就意味着,在“生活儒学”的视野下,这种本源意义的敬畏情感生成了神圣超凡存在者。当然,若仅就“超越”概念自身而言,他实际上并未正面展开本源性的阐明,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超凡者的建构上;但其“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实际上已经蕴含着这种本源性的揭示。
四、关于“超越何以可能”问题的思考
基于以上对于“超越”概念的探讨,笔者认为,或许能够在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之“超越”观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超越”概念本身进行前存在者化的、本源层级的思考。因此,本文尝试沿着黄玉顺“超越本体论”的思路,围绕其尚未展开的“生活—存在”的本源层级的“超越”观念,探索“超越何以可能”的根源,寻求“超越的本源”,以对中国哲学的“超越”观念做进一步的阐发与说明。
(一)作为“超越本源”的“超越活动”
正如前文所述,作为西方外来词汇的“超越”概念,其本身便是一种存在者层级上的对主客关系的思考,现象学对超越论的建构试图摆脱对“超越”概念的经验性理解,强调“存在始终被某种并非它自身的东西所规定,被超越所规定”(77)让·华尔:《存在哲学》,翁绍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5页。。胡塞尔将其归结为纯粹的意识现象,海德格尔将其归结为此在的本质以及此在回归本真、获得自由的过程。显然,尽管两者都试图摆脱对“超越”概念的经验论的诠释,但是他们的超越论却都是基于主客二分之下的主体人的建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是某种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了对“超越”概念的诸多误解。
在笔者看来, “超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超越”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存在意义上的“超越”,而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笔者称之为“超越活动” (transcending)。 “超越活动”本身并不是一种存在者,而是一种倾向和势头,即Transcendence is not any being,but is going to be。“超越活动”作为前存在者的、本源层级的范畴,摆脱了传统超越论主客二分的经验论传统。“超越活动”与对象化的超凡存在者和超验存在者的“超越”有所不同,它是“超越的本源”,“形上的超越跟形下的超越一样,都渊源于本源的超越。”(78)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第271页,第266页,第5页。因此,作为本源层级的范畴,“超越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
一方面,“超越活动”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在本源上,超越之为超越,乃是生活本身的事情”(79)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第271页,第266页,第5页。。因此,生活就是“超越”。这就意味着,“超越活动”并非主体性存在者的“超越”,而是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超越”,因为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人也是在“超越活动”中生成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本源层级的“超越活动”并不意味着在“超越活动”之前没有主体、没有存在者,而是说,正是因为“超越活动”使得一个存在者变为另一个存在者,一个主体变为另一个主体,从而获得了新的主体性。对于新的存在者、新的主体性来讲,“超越活动”并不是物,而是活动和过程。在这种活动或过程中,主体性存在者才得以生成,因此,对于新的主体性来说,这种“超越活动”便是前存在者层级上的。
另一方面,作为“超越活动”的生活本身表现为生活感悟,即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过程,“本源的超越就是生活情境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80)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第271页,第266页,第5页。。“在生活”是指生活生成主体性存在者,即所谓“被抛”;“去生活”是指主体改变自己的生活,即所谓“自由”。此即生活的本源结构。(81)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第271页,第266页,第5页。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超越活动”中,生成了基于当下生活情境之上的超凡存在者和超验存在者。这就意味着,不论是超凡存在者还是超验存在者,其存在与生成实际上都是“超越活动”——生活对象化的结果。因此,“超越活动”是先于“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但是其又包含着“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倾向。自轴心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确实经历了至上超凡存在者“天”的地位不断下降,而超验存在者人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甚至到了宋明理学,“理”和“心”直接代替了超凡存在者而发挥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是互相矛盾、无法共存的概念。一方面,“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概念本身所涉及的“超越主体”和“被超越对象”便存在差异,“内在超越”的主体是人,而“外在超越”的主体是“天”,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将“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视为中西文化和哲学之间根本性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都不过是“超越活动”的一种存在者化的显现方式而已。因此,两者实际上同时存在于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并且同样展现为超凡存在者地位不断降低、超验存在者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也是“人本主义” (humanism)的必然结果。
通过对“超越何以可能”问题的追问可以看出,“超越活动”是“超越”的本源,它作为本源的生活,生成了作为“内在超越”的超验存在者和作为“外在超越”的超凡存在者。那么,超验存在者和超凡存在者的“超越”又是何以可能的?其具体的内在生成机制又是如何?
(二)人的“超越”何以可能
“内在超越”的“超越主体”是人,而“被超越对象”是凡俗世界之中人的感性经验。因此,“内在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人何以成为超验者” “人何以能够是超验的”。此时“超越活动”本身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超越活动”使人成为一个超验者,即达到超验状态。而在这个阶段,作为“超越活动”的生活通过本源层级的“爱” (love)与“思” (think)表现出来。(82)“儒家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视为大本大源,将生活情感尤其是‘仁’即‘爱’的情感的显现视为源头活水;在这种本源上,通过‘思’,去‘成己’‘成物’,而给出存在者,从而建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一方面,作为“超越活动”的生活本身,首先显示为“爱”的情感。作为本源层级的生活情感, “爱”的情感不是主体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并不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先行于主体的。人因为“爱”而成为“爱的存在者”,此时,作为情感本身的“爱”是先于存在者的生活情感。只有当我们对这种“爱”进行存在者化的打量(“去生活”)的时候,理性情感和感性情感才得以生成,这就是所谓的“情感超越” (Emotional Transcendence),即感性情感→理性情感→生活情感(仁爱情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情感超越”与蒙先生的“情感超越”有所区别,蒙先生的“情感超越”实际上是境界论意义上的“超越”,强调主体通过自我的心灵超越获得新的主体性以达到境界的提升,因此,始终未超出作为主体性的心灵范畴。而这里所谓的“情感超越”则在传统的性情架构之上,又找到一种前存在者层级的、本源的生活情感,而这种生活情感首先表现为“仁爱”情感。
另一方面,在本源层级的生活情感对象化的过程中,“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生活儒学”的理论视野下,曾被归属于理性范畴的“思”不仅仅是存在者的“思”,更多的是本源层级的“思”,它是先行于主体性的事情,人因为“思”而成为“思的存在者”。只有当我们在“去生活”的进程中,本源之思才对象化为形下之思和形上之思,此时“思”便不再具有本源层级的意义。形下之思的主体和对象都是形而下的存在者,而形上之思的对象则是形而上的存在者,这就是所谓的“理性超越” (Rational Transcendence),即形下之思→形上之思→本源之思。需要注意的是,先行于存在者的、本源层级的“思”包括领悟之思和情感之思两种,这两者都是先行于存在者的、本源性的“思”,“但是,这两种思还是不同的;思首先是情感之思,然后才是领悟之思。”(83)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第113页。因此,“理性超越”实际上仍然是情感型的,因为“儒家所讲的‘思’,或者中国人所讲的‘思’,首先是生活情感的事情,是爱之思”(8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第113页。。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十分重视情感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的“性情”架构之中,“情感超越”乃主体人的“超越”,即从感性情感到理性情感的“超越”。孟子讲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他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道德情感作为其道德性根源,也正是因为这四种经验心理层次的情感的存在才形成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性,即“四端”升华而形成“四性”,这是道德情感的超越层次。“孟子的道德理性是建立在情感之上,是情感的‘扩充’,即普遍化、理性化,离了情感,便没有理性。”(85)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页。生活儒学认为,在传统宋明儒学“性→情”的架构之前又有一种“情”,生活儒学将其称为“生活情感”。与前两种存在者意义上的情感有所不同,生活情感是无物的,是先行于任何物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被这种生活情感给出的。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感性情感最终都是由“不忍人之心”所生发出来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正是因为“不忍人”这种“爱”的情感的存在,才会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感性情感和仁、义、礼、智等理性情感的生成,此“不忍人之心”乃是某种本源性的情感,正是这种本源性的情感促成了具备新主体性的存在者的生成。因此,作为“超越活动”的情感显现为“爱”的情感,“爱”的情感与“超越活动”相伴而行。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超越活动”生成超验存在者的过程中,情感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超越活动”不仅仅是本源层级的生活本身,而且其始终与生活情感密切相关,是“作为存在的生活、生活情感——仁爱情感”(86)黄玉顺:《生活儒学关键词语指诠释与翻译》,《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因为生活本身首先展现为生活情感,故笔者将其称为“情感超越论” (Emotional Transcendence Theory)。
(三)天的“超越”何以可能
在中国哲学中,“外在超越”的“超越主体”是超凡存在者“天”,而“被超越对象”则是凡俗世界,“对古代中国人而言,天的确可以称为‘超越界’或‘超越者’(the transcendent)”(87)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中华书局,2010年,第37页。。早在周公那里,“天”就被视为神圣的外在超越者,可以赏善罚恶,甚至为政权的存在提供超越层面的合理性证明,“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 (《尚书·大诰》), “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 (《尚书·多士》), “天降丧于殷” (《尚书·君奭》)。周公之后,尽管孔子认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治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神圣超越存在者的“天”就此消失,“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天”仍然具有某些人格神的特质,如“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雍也》)“天丧予!天丧予!” (《论语·先进》) “天”具有赏善罚恶的作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侑》),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渊》)。但是,其人格神的特质已不像春秋之前那样明显。孟子继承了周、孔以来对神圣超越者“天”的重视,他肯定了“天”的创生性,“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孟子·滕文公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孟子·万章上》)并且“天”仍为政权及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论证,“‘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孟子·万章上》)“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孟子·万章上》)“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 《孟子·万章上》)“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孟子·梁惠王下》)“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离娄上》)因此,“外在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天何以成为超凡者”“天何以能够是超凡的”的问题。
实际上,从传统观念看,或者从“观念的奠基”的维度看,“外在超越何以可能”或者说“天的超越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是不合法的,因为“天”或“上帝”本来就是超凡的,他作为“自身所与者”或“终极奠基者”,不是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事情使之如此。唯有从“观念生成”的维度看,即从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才能成立,但问题的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即变成了:天何以能够在观念中呈现为一个超凡者?实质上是:人何以能够将天视为超凡者?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回答:一方面,天之所以能够在观念中呈现为一个超凡者,与人的敬畏情感密切相关。殷周时期的《诗经》中便有多处敬天、畏天的描述,《毛诗正义》曰:“天之变怒,所以须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谓之明,常与汝出入往来,游溢相从,终常相随,见人善恶。……反道违天如此者,则上天罚之,故戒王使敬天也。”(88)《毛诗正义》,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3页。先秦时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心服曰畏……‘畏天命’者,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顺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89)《论语注疏》,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因为天能降灾赐福,所以君子敬畏它,“不畏敬天,其殃来至闇。”(90)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第1489页。孟子曰: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孟子·梁惠王下》)“圣人乐行天道,如无不盖也……智者量时畏天,故保其国。”(91)《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哲学早期,敬畏情感始终与超凡存在者相伴相生。另一方面,天之所以能够在观念中呈现为一个超凡者,与人的形上追求相关。“超越活动”作为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的生活感悟,在生成了形下的超验存在者之后,具备主体性的人努力寻求形下存在者背后的终极根据,寻求万物背后的终极支撑,此时形而上的存在者便生成了,“主体性的绝对化,形成了形而上存在者的观念,诸如本体、上帝之类的观念”(92)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综上所述,人通过作为“超越活动”的本源层级的“爱”与“思”而成为超验的存在者,而“天”的生成与人的敬畏情感与形上追求相关。因此,“超越”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超越性”问题。而近年来,对于“超越”问题的讨论如此热烈,与人本主义背景下“人的超越性”密切相关。
五、余论: “超越”问题的本质及其时代性
当今的前沿科技,如“克隆技术” (Clone)(93)参见姚大志:《人类有权利克隆自己吗?》,《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基因编辑” (Gene Editing)(94)参见卢俊南、褚鑫、潘燕平等:《基因编辑技术:进展与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11期。、“人工器官” (Artificial Organs)(95)参见张志会、李振良、张新庆:《机体哲学视角下的医学人工物》,《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14期。和“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96)参见许万增、王行刚等:《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科学出版社,1996年;段伟文:《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生理感官或心理智能方面造人的目的。这些新兴技术颠覆了传统“人”的定义,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既有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97)参见黄玉顺:《重建外向超越的神圣之域——科技价值危机引起的儒家反省》, 《当代儒学》第1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黄玉顺将“那些关乎人的存在与本质,从而导致人伦忧患的技术”称为“攸关技术” (the technologies concerning humanity, TCH)(98)黄玉顺:《人是什么?——孔子面对“攸关技术”的回答》,《孔子研究》2021年第4期。,而“攸关技术”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人本主义”指导下生活方式的当下呈现。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本主义”确实带来了人的启蒙和解放,但是“人本主义”本身及其当下发展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99)参见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学术界》2020年第2期。,表现为人类理性的僭妄和神圣超越者的失落。一方面,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高举“知识就是力量”的大旗,认为理性无所不能,人类自身更是至善全能。而理性的僭妄的背后是权力和资本的支撑,即权力或资本通过理性的外衣掌控人类的生活,从而限制人类自由的实现,最终导致了权力的肆虐、资本的傲慢,使得“占有技术资源的人拥有压倒一切的必胜技术”(100)赵汀阳:《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另一方面,作为神圣外在超越者“天”或“上帝”的地位不断下降,人的地位甚至逐渐取代了神圣外在超越者的地位,而伴随着神圣超越存在的缺席和斥退,人类精神生活失去了价值根源,“在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世界里,伦理学问题很可能会消失,至少边缘化”(101)赵汀阳:《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何乏笔(Fabian Heubel)曾指出,“在现代科学/科技、经济或美学的发展中,这类的‘内在超越性’经常以‘越界’的方式显现”(102)何乏笔:《儒学气论与内在性哲学:从德语之张载研究谈起》,《国际汉学》2009年第2期。。因此,在笔者看来,一方面,现代性需要一个神圣超凡存在者以为众多形而下者提供基于“本体论承诺”之上的价值承诺,这意味着人作为超验存在者不能取代超凡存在者,不能替代超凡存在者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超越何以可能”问题的追问表明,超凡存在者和超验存在者作为“超越”活动对象化的产物,并不是非此即彼、矛盾对立的存在,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发挥着彼此不同的效用。
——围绕《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若干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