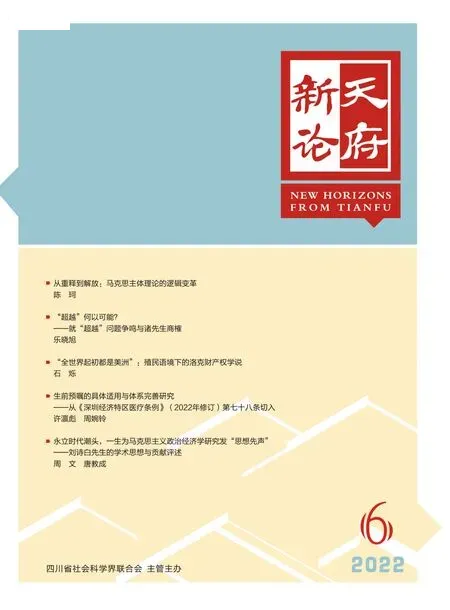“全世界起初都是美洲”:殖民语境下的洛克财产权学说
石 烁
1801年,时任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的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写出了一本关于本州土地权利的历史论著。沙利文在这本书中宣称,当马萨诸塞的土地上活动的还是印第安人时,“没有农耕的痕迹”。印第安人会种植玉米和南瓜,但那只是“漫不经心地耕作”,“不能作为他们拥有排他性永久权利的证据”。为了论证他的说法,沙利文援引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财产权来源于“区分”而非“占有”,并且附着人的劳动。鹿在深林,鱼在汪洋,人人都可以去捕猎;但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捕捉到的猎物才为你所有,而并非深林和汪洋本身。并且,当把捕捉到的鹿放回深林,把鱼放回海洋,这些动物就不再是你的财产,你也就不享有对它们的所有权。沙利文引导读者相信,印第安人之于土地的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只是不稳定且短暂地占有一块土地”,之后便迁移到别处,这就相当于把抓到手里的鱼重新抛还给供人共享的自然。如此一来,印第安人被认为不再对其土地享有财产权。(1)James Sullivan, The History of Land Titles in Massachusetts,Boston, 1801, pp.21-24.
沙利文对洛克的引用是一例直接的证据,它证明了在印第安人逐渐丧失掉北美土地的历史进程中,洛克的财产权学说曾有意无意地为白人占领土地提供了正当性论证。但是,思想学说在历史中的呈现往往是复杂的,它的接受史不仅不以首创者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还可能出现互相矛盾的挪用情况。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检讨,作为一套融贯的学说,洛克的财产权学说是否本身就支持一种殖民解读的可能性?换言之,洛克有关财产权的论述,是否在理论上为殖民者征占美洲原住民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部分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文本内的,它考察的是思想学说的内在逻辑。
本文另一部分的工作是文本外的,希望结合具体的殖民语境,揭示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在历史现实中折射出的复杂性。洛克本人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一位有着丰富殖民经验的实干家。洛克的私人藏书馆中有关海外旅行的书有195本之多,以至于他能够在其著作中信手拈来地引用“新世界”的事例。(2)John Harrison, Peter Laslett, The library of John Lock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他在1669—1675年间曾担任英属卡罗来纳殖民地的业主秘书,负责殖民地日常事务的管理,并参与起草了“卡罗来纳基本法”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他还出任过贸易与殖民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的秘书(1673—1674),以及贸易局(Board of Trade)的委员(1696—1700),并在后一任职期间主导过维吉尼亚殖民地政府结构的改革。此外,洛克还投资过一些殖民贸易公司;甚至新大陆的一个小岛,即今天的埃迪斯托岛,还曾经以洛克的名字命名(Locke Island)。这些历史事实促使我们思考,在洛克的殖民实践乃至英格兰早期殖民活动中,他的财产权学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殖民地的经验与洛克的学说之间是否存在张力?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答构成了本文的第二项工作。
一、洛克财产权学说的殖民读法
洛克的《政府论》出版于1689年。直到19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成书于光荣革命之后,是对革命的辩护。1960年,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一传统看法,他认为洛克是在1679年到1680年冬季的排除派危机(Exclusion Crisis)中写作《政府论》下篇的。(3)彼得·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导论》,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在拉斯莱特研究的基础上,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为洛克的《政府论》引入殖民语境。他的文章成功证明在1675—1696年这看似与殖民事务无关的21年中,洛克并没有放下他挂念的卡罗来纳。洛克很可能在1682年参与修订“卡罗来纳基本法”第四版的同时,创作《政府论》下篇中著名的“论财产”一章。(4)David Armi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Theory, Vol.32, No.5, 2004.本文试图说明,在洛克的财产权学说与殖民事务之间,不仅存在着阿米蒂奇暗示的共时性,也存在着更具实质性的内在关联。具体来说,有关美洲的经验与信息是洛克论述其财产权学说的重要参考,也是这种学说得以成立的知识前提。洛克的理论内在支持一种殖民解读的可能,并且从逻辑上支撑了欧洲人对原住民土地的征占。
洛克财产权论述的出发点体现了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所概括的“制造物模式” (workmanship model)(5)詹姆斯·塔利: 《论财产权:洛克和他的对手》,王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页。——“上帝把世界给予亚当及其后人共有” (2.25)(6)后文中对《政府论》的引用,不再单独用脚注标明,而是遵循学界通则,用1和2表示《政府论》的“上篇”和“下篇”,再结合节的序号完成对引文的定位。比如“2.25”即表示“《政府论》(下篇)第25节”。所采用的原文见:Peter Laslett 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Student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译本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如未做特殊说明,以中译本为准。。但这就带来一个困难: “怎能使任何人对任何东西享有财产权呢” (2.25),因为 “必然要通过某种私占(appropriate)的方式,才能对某人有用,或对某一个人有好处” (2.26),这是自然理性(自然法)赋予人类的生存权利(right to preservation)。此处的矛盾在于,本质上,上帝恩赐的土地从不是专属而是共享,但人又必须以私占的方式利用土地,才能享用这上帝的恩赐。(7)约尔顿(John Yolton)精当地将这一困难概括为:“公有的特殊化(particularisation)如何得以可能”的问题。见John W. Yolton, Locke and the Compas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 Selective Commentary on the“essa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87.因为上帝这么做毕竟是为了人好(洛克喜欢用的词是“便利”),而人如此行为是为了实实在在接受上帝的好,因此,“就不能假设上帝的意图是要使世界永远归公共所有而不加以耕植” (2.34)。(8)有学者认为,洛克所谓“自然法的执行权”实际上是自然法传统“松动”的表现。因为在洛克看来,自然法需要“强力” (force)才能够“有效” (2.7)。这种观点由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最早提出,李猛在《自然社会》中进一步阐发。 (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26-231页;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74-381页。)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不仅仅是自然法,而且“自然”本身在洛克学说中都必须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行之有效。其表现就在于自然本身虽然是丰裕的、公有的,但如果不加以人力的改造(劳动),则不足以维持生活,也就是说,是没有用的。自然物作为神的恩赐,其价值竟然取决于人自身。参见下面几处:“自然和土地只提供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资料” (2.43),“我们甚至把完全听其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符其实地叫做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是等于零” (2.42),“我们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之于劳动” (2.40)。在解释这一问题上,洛克提出了他本章的第一个例证,一个关于印第安人的例证:
野蛮的印第安人既不懂得圈用土地,还是公有土地的佃户,就必须把养活他的鹿肉或果实变为己有,即变为他的一部分,而别人不能再对它享有任何权利,才能对维持他的生命有任何的好处(2.26)。
在这一例证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读出洛克的用意:即便是不懂得圈地,生活于公共土地之上的印第安人,依然需要让鹿肉或果实变为“己有” (排他性的),才能从中受益以维持生活。前半句是让步式的口吻,因为“野蛮的印第安人”更接近上帝恩赐之初的“包容性权利” (inclusive rights)状态;后半句则强调,即便这样,印第安人也要通过私占才能获益。尤其需要注意,这里印第安人的私占对象是“鹿肉或果实”,皆非土地。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洛克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众所周知的:“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公有状态,确定了我对它们的财产权。”按照洛克的理论,人首先对其人身享有所有权(2.27),正是这种所有权,使得通过人身(body)的劳动本身是属己的。通过人身的工作,自然物与属己的劳动混合,如洛克所说,使自然物加上了一些东西(2.27),从而使前者脱离自然状态,即脱离自然的公有状态而带有排他性, “因而就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所以,洛克认为,是劳动使自然物脱离上帝恩赐之初的公有状态:“他的劳动把它从自然手里取了出来,从而把它私自占有,而当它还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是同等地属于所有的人的。” (2.29)(9)在洛克之前,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都将财产看成是约习性的(conventional)。洛克否定了这种财产起源的契约论,代之以劳动论。但是在占领美洲的问题上,三者看法更为复杂。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和芭芭拉·阿内尔(Barbara Arneil)都认为,在将美洲确认为“荒地”,进而暗含着欧洲人享有占领权利这一立场上,洛克非常接近格劳秀斯,而拒绝了普芬道夫。参见Barbara Arneil, John Locke and America: The Defence of English Colon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43-64; 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罗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92-198页。为了解释上文的观点,洛克紧接着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同样也是一个关于印第安人的例证:“这一理性的法则使印第安人所杀死的鹿归他所有;尽管原来是人人所共同享有权利的东西,在有人对它施加劳动以后,就变成他的财物了。” (2.30)可以看出,这依然是讲印第安人与鹿或者野果的事情。在32节之前,论述劳动使自然物属己的全部例证,要么关于捕猎(鹿、兔子、鱼),要么关于采集(野果、橡树果、水、龙涎香)。通过提及印第安人的这两处,洛克把这些行为与野蛮人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32节之后,被混合进人的劳动的自然物从橡树果或者兔子变成了土地。我们来看关键性的32节的第一句话:“但是,尽管财产的主要对象现在不是土地所生产的果实和依靠土地而生存的野兽,而是包括和带有其余一切东西的土地本身,我认为很明显,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和前者一样取得的。”被施与劳动的自然物发生了改变,劳动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耕耘、播种、改良、栽培” (tills, plants, improves, cultivates)代替了简单的摘取或者捕获。两者相比,创造出来的价值完全不能匹配。对此,洛克问道:“在听其自然从未加以任何改变、栽培或耕种的美洲森林和未开垦的荒地上,一千英亩土地对于贫穷困苦的居民所提供的生活所需能否和德文郡的同样肥沃而栽培得很好的十英亩土地所出产的同样多呢?” (2.37)很显然,这种产值的巨大差异是两种生产方式间的差异,也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上一处引文并非第五章唯一一处将英国的情况与美洲对比,我们可以再举两处:
关于这一点,没有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这些部落土地富足而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自然对他们也同对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充分提供了丰富的物资——那就是能生产丰富的供衣食享用之需的东西的肥沃土地——但是由于不用劳动去进行改进,他们没有我们所享受的需用品的百分之一。在那里,一个拥有广大肥沃土地的统治者,在衣食住方面还不如英国的一个粗工。 (2.41)
然而人类从这块土地上一年所得的好处为五英镑,而从那块土地上,加入一个印第安人所得的一切利益在这里估价出售的话,可能一文不值;至少,我可以真诚地说,不到千分之一。 (2.43)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提醒我们:“对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批判几乎是早期殖民者作品中近乎恒久性的内容,在这样的批评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殖民者们相信土地必须要利用的观念。”(10)威廉·克罗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鲁奇、赵欣华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6页。洛克关于英国与美洲的对比,恰好体现了克罗农笔下“早期殖民者”的一般观察。另外,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洛克对于“改良” (improvement)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不完全等同于农垦,也同样指向“圈地行为” (enclosure)。在2.37节的美洲与德文郡比较之前,洛克同样比较了十英亩圈地和一百英亩共有土地产值上的巨大差异。而在上文提及的2.26节,洛克论及印第安人“不懂得圈用土地”。在他生活的17世纪,圈用土地带来的好处几乎成为共识。稍晚于洛克的贵格派宗教改革家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有着和洛克相似的看法。在他看来,作为“闲散和粗野之温床”的森林和大量的公地“让依赖它们生存的穷人太像印第安人了”。(11)John Bellers, An Essay Toward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k, London, 1714, p.40.
让我们将以上2.32节之前对劳动使自然物成为财产的论述与32节之后具体关于土地开垦的论述相比较,或者更具体来说,将32节之前对美洲印第安人例子的用法和32节之后的用法相比较,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1.印第安人并非没有财产权,但他们仅对自己捕获的猎物或者采摘的果实享有所有权。而对于他们生活的土地,由于他们没有通过农耕对其进行改进,更没有对其进行圈占,因此也就没有把自己的劳动掺入其中。所以,他们不享有对土地的排他性的所有权。
2.同样是通过劳动对自然物赋予价值,渔猎采集和农业耕种完全无法比较。前者带来的仅仅满足低限度的存活,而后者则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洛克的这种对比并非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更带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意味。首先,垦殖土地并非仅仅是更加优越的“经济行为”,而且在洛克看来,是一件更加合于上帝意志的行为。对于耕种土地的行为,洛克认为是“上帝与人的理性指示他开垦土地” (2.32),“他(上帝)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 (2.34)。其次,洛克认为对荒地的圈占与开垦是一件于全人类都有益的事情,因为这“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 (2.37)。也就是说,改善土地不仅仅是对某个人好,而且对于人类整体来说都是利好的。最后,正因为耕种土地所带来的巨大价值,洛克认为对这一行为的考虑应该被纳入政治范畴,作为洛克所谓的“施政的伟大艺术” (great art of government):“一个君主,如能贤明如神,用既定的自由的法律来保护和鼓励人类的正当勤劳,反对权力的压制和党派的偏私,那很快就会使他的邻国感到压力。” (2.42)如此一来,按照以上三点对开垦土地附带的说明,我们可以认定,这一行为是信仰上敬神的、德性上勤劳的、政治上明智的和功利上有利于全体利益的。可以想象,与之相反的印第安人便是不虔敬的(没有利用神赐予的理性能力)、懒惰的、政治低级的以及无益于人类福祉的。可见,至少在改良土地这一点上,洛克对印第安人带有明显的鄙夷情绪。通过将印第安人利用土地的方式与英国人加以对比,洛克阐明了“正确”或“合理”地开发土地的方式,应该是建立在土地圈占基础上的垦殖行为。
洛克的通过劳动使自然物变得属己的财产学说并非没有限制。在《政府论》下篇第五章中,洛克给出了两条限定条件,有时候仅称第一条为“洛克但书” (Lockean proviso)(罗伯特·诺奇克的说法),有时候两条都称作“洛克但书”。第一条限制即私占土地的同时要留给其他人足够的土地以供利用——你不能 “种自己的地,让别人无地可种”。第二条限制是说,通过劳动特殊化共有的自然物必须以享用(to enjoy)为尺度。简单来说,你不能够采摘很多果子,却吃不完,任其烂掉;你也不能圈围一大块土地,而耕种不及,任其荒芜。我们接下来要表明,在对这两条限制条件的解释中,美洲事例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但书。洛克一方面认为要给他人留下足够的土地,但他又极力强调“事实上并不因为一个人圈用土地而使剩给别人的土地就有所减少” (2.33)。类似暗示土地不会因为他人私占而减少的表述,又如:
没有任何人的劳动能够开拓一切土地或把一切土地划归私用;他的享用也顶多只能消耗一小部分;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种方式下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为自己取得一宗财产而损害他的邻人,因为他的邻人(在旁人已取出他的一份之后)仍然剩有同划归私用以前一样好和一样多的财产。(2.36)
洛克认为,“在世界初期”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world),这种随意私占却不侵害他人的情况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时物资丰富、人口稀少,并且人的活动范围有限。但是,到了洛克生活的年代,虽然“似乎有人满之患” (as full as the world seems),但“同样的限度仍可被采用而不损及任何人” (2.36)。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洛克之所以相信即便是在“人满为患”的状况下,通过劳动对自然物的私有化占有仍不会损害别人,是因为合理的利用方式本身会在原始丰饶的基础上创造出额外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会以货币为载体弥补贫困者因占有不足而减损的福利。显然,这是一种洛克版本的“涓滴理论”。斯蒂芬·巴克勒(Stephen Buckle)很好地表述了这种看法:“随着货币经济的出现,虽然产生了不平等但这也是正当的,因为新经济形势下的生产力甚至能为生存条件最差者带来利益。”(12)斯蒂芬·巴克勒:《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从格劳秀斯到休谟》,周清林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47-148页。
毫无疑问,这种解释确实是洛克自己的观点。(13)见2.36、2.37的相关表述。但是,在2.36节的最后,洛克展现了一种让步的姿态:
但这还不是我想强调的。我敢于大胆地断言,相同的私有权法则,即每个人能够利用多少,就拥有多少,将继续在世界上行之有效,并且不会让他人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世界上的土地能够满足成倍的居民,即便这些居民尚没有发明货币,通过默示同意赋予它一种价值,从而通过同意引入更大的财产,并对其享有权利。 (2.36)(14)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在这一段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翻译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重译。
这种让步表明,上述解释虽然是正确的,但还不必诉之于此。这种解释是世界全部被占满后对这一问题的终极解释,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土地能够满足成倍的居民”。奇怪的是,洛克的祖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700年时,不算威尔士,英格兰本土人口就已达到500万以上。(15)John Marshall, Esq., Statistic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838, p.22.为什么洛克如此乐观地相信世界上的土地足够充裕呢?我们发现,当洛克想说明“同样的限度仍可被采取而不损及任何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美洲,虽然是仅仅作为例证的美洲:
试设想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在亚当或诺亚的子孙们起初在世界上居住时的情况:让他在美洲内地的空旷地方进行种植,我们将看到他在我们所定的限度内划分自己私用的土地不会很大,甚至在今天,也不致损及其余的人类……(2.36)
由此,我们不妨如此猜想:当洛克认为世界还足够宽敞,能够让人自由地圈占土地而不至于危及他人时,他很可能想到的是被他认定为有着“空旷地方” (vacant places)的美洲,而绝不可能是拥挤的英格兰。洛克思想的变化佐证了这一猜想。在早期作品《论自然法》(EssaysontheLawofNature, 1664)中,洛克对自然丰饶的看法远没有后来那么乐观。自然能够提供给人的物资是一个常数,“无论何时人类的欲望或对所有物的需求总在增加,但有限的世界却不会立即得以扩充”。如此一来,对自然物的私有化将注定是个零和游戏:“当任何人尽其所能去攫取时,他便从其他人那里夺走了他们意欲占为己有的那些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排除以其他人为代价来增加自己的财富。”(16)洛克:《自然法论文集》,李季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8-69页。在这段叙述中,我们找不到劳动创造额外价值的论述。1660年代末,洛克开始逐步涉足海外事务,参与到卡罗来纳殖民地的管理中。这些来自“新世界”的信息或许促成了他对早年观点的修正。
环境史家沃斯特(Donald Woster)认为,新大陆的“发现”对于“旧世界”的人来说,其实是发现了“第二地球” (Second Earth); “第二地球”上丰富的资源和土地为原本已经陷入停滞的旧文明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他写道:“第二地球的发现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丰裕时代,最终以新的自然资源和这些资源所支撑的自由洗刷了陈旧的文明。”(17)Donald Worster, Shrinking the Ear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n Abund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3.洛克对于新大陆的援引印证了沃斯特的说法。他在“论财产”一章中向读者声明,这个世界的资源和土地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他做出这一声明时,他想到的绝非旧欧洲:虽然这里创造了高于美洲无数倍的产值,却显得十分拥挤。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洛克的世界图景中,世界似乎被一分为二,分别对应着他在2.36节提到的两种状况:人满为患的现代世界和丰裕富饶的原初世界。这两个世界竟然存在着共时性,在17世纪并存不悖。2.49节再次以不同的措辞提到了“世界之初”,但这次对应关系呈现得更加直白:“全世界起初都是美洲” (in the beginning all the world was America)。原初世界的状态和美洲的状态(尤其是美洲之前的状态)即便不能说完全等同,也在很大程度上近似。洛克发现了美洲这颗“第二地球”。这里物资丰富,人烟稀少,土地广阔而未加开垦。在这片土地之上生活的印第安人只对他们所采的果子、所捕的野兽具有所有权,而对其所居住的土地不享有所有权,因为这些土地在洛克看来是未加垦殖的荒地。无论出于道德还是功利,开垦美洲的荒地对殖民者来说都是利好的,甚至是义不容辞的。在此我们看到,正是借助“第二地球”的引入,洛克完成了对第一条但书的突破,同时暗示了欧洲人利用美洲广袤土地的前景。
第二条但书讲的是对自然物的私有化必须以及时享用为尺度。这一点明显地带有清教徒精神对浪费恶习的拒斥。但是,同上一条一样,这一条但书实际上也缺乏约束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2.37节和2.46节的表述存在表面上的分歧:
但是如果它们在他手里未经适当利用即告毁坏;在他未能消费以前果子腐烂或者鹿肉败坏,他就违反了自然的共同法则,就会受到处罚;他侵犯了他的邻人的应享部分,因为当这些东西超过他的必要用途和可能提供给他的生活需要的限度时,他就不再享有权利。 (2.37)
这些结实耐久的东西,他喜欢积聚多少都可以。超过他的正当财产的范围与否,不在于他占有多少,而在于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他手里一无用处地毁坏掉。(2.46)
但实际上,这种分歧是不存在的。因为洛克的真正看法是,占有本身并不是罪过,即便这种占用远远超出了享用。占有的对象如果是自然物本身,那么大部分自然物由于易朽的特点不便贮存。这些自然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使用价值,这对于上帝赐予人类公共享用的礼物来说是一种破坏,因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掠夺他人”。但是,如果改换占有的形式,将短暂的自然物变为耐久的金银,那么对后者的囤积就是正当的,因为金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价值。这样一来,洛克就引入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货币。虽然财产权的来源不是同意,但在洛克看来,同意正是货币的基础。由于出现了货币,自然物容易损坏的问题得到了回避,因为人们依然可以通过挣取更多货币的方式实质上私有化更多的自然物。简言之,囤积果子导致其烂掉是不可饶恕的,但是攒钱却不关乎原则问题。在此处,我们近乎得到了一种类似于韦伯“新教伦理”意义上的表述。
货币使用最大的后果,就是刺激人去占有更多的土地,这一点在2.36节已经表明。如果没有货币,“人们就不见得会扩大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尽管土地是那样肥沃,他们又可以那样自由地取得土地” (2.48)。货币的出现促使“第一地球”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因而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第二地球”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让我们回到“全世界起初都是美洲”的2.49节:
全世界起初都是美洲,而且是以前的美洲,因为那时候任何地方都不知道有货币这种东西。只要一个人在他邻人中间发现可以用作货币和具有货币价值的某种东西,你将看到这同一个人立即开始扩大他的地产。
因此,由于没有货币的发明,美洲印第安人没有扩大土地的需求。这让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英国的一个“粗工”。在对第二条但书的突破上再次出现了英国与美洲的对比。懂得使用货币的英国人比完全不知货币为何物的印第安人更有动力去占用土地,后者没有这样的需求,并且受困于第二但书的限制,只能够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利用自然物。
至此,我们业已展示了一种对《政府论》“论财产”一章的殖民读法。这种解读指出了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带有美洲烙印,他对财产的思考必须借助美洲的经验和信息,在美洲与英国的对比参照之下才得以成型。并且,这种学说预设了欧洲人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在道义和功利上都具有优越性,同时暗示美洲土地缺乏开垦,从而不属于印第安人的财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在理论上为欧洲人占领美洲土地提供了便利。然而,我们还不能就此止步。进一步考察英格兰早期殖民实践的历史现实以及洛克的殖民事务管理经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张力。
二、土地:购买还是直接占用?
詹姆斯·塔利在讨论洛克学说的殖民影响时,采纳了以威廉·克罗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看法。(18)James Tully, “Rediscovering America: the Two Treatises and Aboriginal Rights,” 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Locke in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37-176.这种看法认为,英国殖民者是通过对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的否定来为自己占领美洲土地的行为辩护的。具体来说,殖民者将印第安人认定为狩猎者和采集者,从而对他们的生产方式大加批判。克罗农写道:“在欧洲人看来,印第安人似乎在滥用那些对欧洲人有用的资源。印第安人的贫困是印第安人的浪费造成的:对土地利用不足,对自然的丰富性利用不足,对劳动的利用不足。”(19)威廉·克罗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鲁奇、赵欣华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6页。因此,印第安人由于缺乏在农耕意义上对土地进行改良的能力,所以他们不具备对自己脚下土地的所有权。克罗农认为,殖民者正是在这套说辞下,完成了对印第安“荒地”的直接占有(而如果遇到反抗,那么占有将变成征服)。塔利将这种为占领美洲辩护的观点称为“农垦说” (agricultural argument),并认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正属于此。他将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和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在1630年代关于占领美洲的争论看成是洛克版本的“农垦说”的知识语境。温斯洛普是洛克的先声,正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一系列小册子,让洛克的观点显得像是“老生常谈” (commonplace)。(20)James Tully, “Rediscovering America: the Two Treatises and Aboriginal Rights,” 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Locke in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2.和克罗农一样,塔利认为洛克的学说就像温斯洛普的一样,直接被用于为占领美洲土地辩护;理论和现实之间不存在距离。阿米蒂奇更进一步,他认为洛克的理论主张与其殖民实践是一贯的。他以“卡罗来纳基本法”第112条为例,这条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从土著人或其他人那里通过购买、赠予或其他方式持有卡罗来纳的任何土地或声称对卡罗来纳任何土地享有权利,而仅能从业主手中获得。否则将承受没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和无限期的流放作为惩罚。”(21)John Locke and Mark Goldie, Lock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60-181.阿米蒂奇认为,禁止购买土著人土地的规定意味着洛克对土著人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并且这正好与他在《政府论》中的财产权论述相符合。(22)David Armi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Theory, Vol.32, No.5, 2004.
克罗农的观点虽然影响巨大,却遭到了一些新近研究的挑战。有学者认为,虽然诉诸否定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的殖民辩护一直存在,并且在19世纪初逐渐成为共识,但这种声音在英格兰早期殖民史上并不占主流。在观念层面,不仅大部分殖民者相信印第安人是他们土地的主人,甚至作为殖民当局的英格兰王室同样以法令的方式不断强调这一点。(23)Lindsay G. Robertson, Conquest by Law: How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Dispossessed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ir La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在实践层面,早期殖民阶段印第安人土地的易主并不主要依靠占有/征服,而是购买/交换。(24)Stu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 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8, pp.35-37, pp.39-42.早期殖民者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并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其土地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虽然由于瘟疫的蔓延,印第安人口在殖民者初来乍到时就已经大有消减,但是两方的直接遭遇是早期殖民史的重要特点。如此一来,殖民者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的印第安邻居的确有耕种自己的土地。另外,虽然学界倾向于强调英国人将农耕与土地所有权关联的思维否定了印第安人的权利,但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英国人有着这样的惯性思维,他们才会认定作为农民的印第安人对其土地享有权利。(25)Stu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 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8, pp.35-37, pp.39-42.更重要的是,在早期殖民史上,土著人的力量远远大于英国移民,同时他们又乐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交换土地。对于殖民者来说,这笔成本低而收益高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26)Stu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 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8, pp.35-37, pp.39-42.以克罗农和塔克笔下的“农垦说”代表人物罗伯特·库什曼(Robert Cushman)为例,虽然他确实认为殖民者有权合法地占用无人利用的土地,但是当他谈到现实中殖民地的来源时,却承认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由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酋长马萨索伊特(Massasoit)将土地赠予殖民者斯坦迪什船长(Captain Standish)的。(27)Henry Wyles Cushmans, A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Genealogy of the Cushmans, Boston, 1855, p.34.
至此,我们一方面说明了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在理论上有利于殖民者占领美洲土地,因为按照该学说,美洲的广袤土地没有被合理、充分地加以开垦利用,从而不属于印第安人的地产;而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这种诉诸否定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手段在英格兰早期殖民史上并不占主流。在殖民实践层面,殖民者更喜欢用购买的手段换取原住民的土地。对于殖民者来说,这既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也是基于他们对印第安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遍确信。如此一来,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的张力将我们带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前所述,洛克本人虽然从未到过美洲大陆,却深刻卷入了殖民事务,尤其是参与了英属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日常管理。他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一位殖民实干家。那么,作为英格兰早期殖民亲历者的洛克,又如何看待印第安人的土地权与美洲土地的易主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回到洛克的卡罗来纳语境。
三、洛克的卡罗来纳语境
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从来都是以复数的形式存在的;并非每一种殖民主义都内含着殖民者对土地的追求。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活动一开始并不是以土地为核心的。(28)Nancy Shoemaker, “A Typology of Colonialism,”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Vol.53, No.7, 2015. 作者在文中列数了12种殖民主义,其中采掘型殖民主义、贸易型殖民主义、运输型殖民主义等都不强调大面积占据殖民地土地。众所周知,北美第一个存续至今的殖民地弗吉尼亚的建立与烟草种植业的兴起密不可分。但是,在17世纪初,詹姆斯敦探险活动的资助者们最期待的回报并不是农产品,而是矿藏。寻找各类英国本土缺乏的原材料才是殖民者们的初衷。(29)John Darwin,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012, p.111.可是在殖民实践中,殖民者却发现北美的资源并没有他们想象的丰富。更糟糕的是,自然环境的残酷让这些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客时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经过一段不堪回首的“饥馑时期”后,殖民领袖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反思道:“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挨饿,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计划,没有努力劳作,也没有良好的政府。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大部分人认为的土地贫瘠。”(30)Edward Arber, ed., Travels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Edinburgh, 1910, p.499.就这样,经济利益和生存问题共同把殖民者留在了土地上。不同于习惯了迁徙的印第安人,移民们只有像在母国那样, 依赖于土地, 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 进而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谋求殖民利益。
到了卡罗来纳殖民地的草创时期,垦殖(plantation)与定居(settlement)已经成为殖民者的共识。如果找不到金银财宝,不如就地利用肥沃的土地获取农产。在早期殖民地的计划性文件“授权与协议” (ConcessionsandAgreements, 1665)中,业主们构想了一套类似后来西进运动时期的土地授予政策。最先到达土地的移民将会被授予最高150英亩土地。(31)Mattie Erma Edwards Parker ed., North Carolina Charters and Constitutions, 1578-1698, North Carolina, 1963, pp.109-127.后来问世的“基本法”经常提到开垦(planting, planted, plantation),比如1669年版的第5条“以便居民定居和开垦土地”,第10条“直到整个卡罗来纳领地按照这份基本法的比例规划全部占用并垦殖”,以及1682年新增的第101条“随着殖民地被充分地开垦,被分开成适当的部分”。上文提及,“基本法”第112条宣称:
任何人不得从土著人或其他人那里通过购买、赠予或其他方式持有卡罗来纳的任何土地或声称对卡罗来纳任何土地享有权利,而仅能从业主手中获得。否则将承受没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和无限期的流放作为惩罚。
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卡罗来纳殖民者的土地并不是从印第安人那里购得的,但这并不符合史实,因为这条法规并没有被真正贯彻过。事实上,洛克的恩主(patron)沙夫茨伯里就是这条法规的反对者,也正是从他开启了卡罗来纳殖民者在1670年代后大规模购买印第安土地的风潮。1675年3月,他签署了卡罗来纳第一份有记录的土地转让契约,允许安德鲁·帕西瓦尔(Andrew Percival)以“一块贵重的布匹、斧头、珠子和其他物品与手工制品”换取印第安人一块名为“大小卡索” (Great and Lesser Casor)的土地。在1682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印第安部落参与到了与卡罗来纳移民以物换地的买卖中来。
沙夫茨伯里的这一举措历来受到史家的好评。里弗斯(William James Rivers)认为沙夫茨伯里灵活地拒斥“基本法”第112条,体现了他在卡罗来纳殖民实践中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并称赞这是“如此简单而公平的措施……将会减轻急躁好战的土著人的敌意,并确保定居者的和平和繁荣”(32)William James Rivers,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To the Close of the Proprietary Government, Charleston, 1856, p.124.。麦克拉蒂虽然认为“诉诸欺诈并不比诉诸武力好多少”,但他仍然赞同里弗斯对沙夫茨伯里的评价,并认为正是在洛克影响下沙夫茨伯里才放弃坚持禁止买地的法令。(33)Edward McCrady, The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Under the Proprietary Government, 1670-1719, Macmillan Company, 1897, pp.178-180.
我们不清楚洛克在沙夫茨伯里放弃坚持“基本法”第112条中发挥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沙夫茨伯里的心腹和秘书,洛克非常清楚伯爵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洛克应该清楚卡罗来纳的土地扩张并不是通过荒地占领,更不是通过征服,而是主要通过购买或以物易地的方式从印第安人手中换来的。一些材料能够佐证我们的推测。在《沙夫茨伯里文献》的“洛克卡罗来纳备忘录” (“Locke’s Carolina Memoranda”)中,我们发现在对沙夫茨伯里的信件进行摘要时,洛克提及“用商品与印第安人贸易并购买他们的土地的愿望”(34)The Shaftesbury Papers,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2010, p.388.。这能够说明洛克了解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土地买卖。另外,沙夫茨伯里在写给殖民地总督的一封信中,告诫殖民地的管理者不要去侵扰“印第安邻居”的财产,因为殖民事业志在垦殖和贸易,而非掠夺和劫掠。(35)The Shaftesbury Papers,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2010,pp.327-328.洛克作为这封信的代笔者,和他的恩主一样承认印第安人的财产权。
更进一步,对于印第安人开垦自己土地的事实,洛克同样不可能不知道。在班纳看来,这一结论在洛克出生之前就已经是殖民者们的共识,而如此熟悉殖民事务的他不会不了解。(36)Stu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 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7.洛克当然知道。在他写于1695年末的《关于提升货币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中,有这样的表述:
当一蒲式耳的玉米将卖出换回或兑换更多磅的烟草时,它就会在弗吉尼亚的英国人中涨价,这时在印第安人中,它能够被卖出挣回更多的“沃蓬皮” (wampompeak),这是印第安人的货币;而在那里的英国人中,它将能够换回比之前多得多的银子。(37)John Locke, Further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696, pp.26-27, p.21.
既然印第安人能够卖出他们的玉米,他们怎么可能不是农民呢?这段引文还说明了另一件事:洛克不仅清楚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的土地买卖,清楚印第安人也是农民的事实,甚至还清楚印第安人使用货币。“沃蓬皮”就是印第安人货币,洛克对此亲口承认。在这段引文之前,洛克对此亦有提及:
因此,在任何国家里,仅有一种金属能够成为算账和合同的货币,并且是商业的尺度。在所有的金属中,最合适这种用途的是银。原因很多,在此无需提及。全世界已经一致认可它,并且让它成为共同货币,就像印第安人正确地称其为“尺度” (measure),这就足够了。(38)John Locke, Further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696, pp.26-27, p.21.
在洛克看来,印第安人对货币的使用和欧洲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和欧洲人一样明晓货币作为商业之尺度的意义。(39)1696年,友人莫利纽(Molyneux)在致洛克的信中提到了印第安货币“沃蓬皮”。莫利纽直言:“我们对它们(指货币)的了解并不比印第安人对他们的贝壳了解得多。”参见John Locke,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11th ed, Vol.9, London, 1812, p.380.
在分别考察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和殖民实践之后,两者之间的张力也最终浮出水面。一方面,作为殖民管理者的洛克清楚地知道,在卡罗来纳殖民地,殖民者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一行为本身已经隐含了对印第安人土地权的肯定。同时,他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关心海外拓殖的人一样,承认印第安人是耕地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农产品,甚至拥有自己的货币。然而另一方面,在《政府论》中,洛克将印第安人描绘为不事农事的采集者,他们并没有恰当地开垦自己脚下的土地,并且因为不懂得使用货币而不具有扩大土地的需求。这些都暗示了印第安人在洛克界定的财产权意义上并不对美洲土地享有权利。在构建自己的财产权理论时,洛克参照了大量来自美洲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不仅不符合美洲原住民的生存现实,甚至有违于他自己在殖民实践中获取的信息。这一点令人匪夷所思。
对这一矛盾的解释并非本文的任务。一些试图对洛克进行殖民批判的学者,或许会将这一张力解释为洛克为了炮制他有利于殖民扩张的财产权理论,有意歪曲了他本该知道的美洲经验。(40)这些学者往往把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与他的正义战争理论并举,用以说明洛克的思想如何为征服美洲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参见石砾: 《洛克的正义战争学说与奴隶制问题》,载孔元编: 《帝国与地缘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72-101页。而一些更关注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土地利用方式之差异的学者,可能会进一步追问:北美广袤无垠,当一块土地肥力不足时,印第安人有条件迁徙到别处种植他们的玉米和南瓜;这相当于对原来那块土地进行休耕。这种迁徙式的农作方式是否符合洛克对改良土地的认定呢?留作休耕的土地又是否算作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呢?总之,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应当是开放式的,它有待于更多学者在相关问题上花费精力,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对这种张力的揭示而非解释有着自身的价值。它提醒我们注意近代早期欧洲知识生产背后的殖民语境,关注欧洲思想家如何在与“新世界”进行知识交换的过程中搭建自己的理论,并且对他们的理论与殖民实践之间的距离与差异有着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