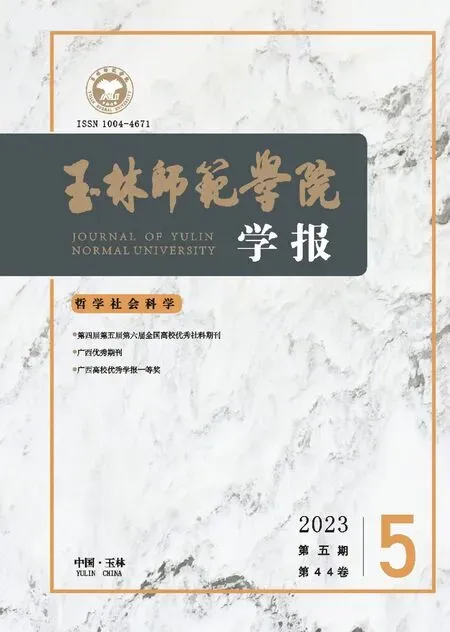京剧水路班历史剧特色研究
王 珏,单 雯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222;南京艺术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京剧水路班,指主要活跃于清同光年间至20世纪中叶,以船只为交通工具,以江南水乡为主要演出区域,以京剧演出为主的戏曲班社。①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历史剧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背景的剧目,是京剧水路班演出较多的剧目。历史剧在京剧水路班流行,其中原因是复杂的。京剧水路班所演历史剧无论在情节上还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都颇具特色,值得关注。
一、地域色彩明显
京剧水路班演出的历史剧往往有极为明显的地域色彩,能表现江南地区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首先,京剧水路班的历史剧里,有大量在江南地区评价颇高的民族英雄为主人公的剧目。这些民族英雄都曾在江南有所建树,深受江南百姓爱戴。为纪念和歌颂他们,京剧水路班演出了许多以这类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剧目。
岳飞就是江南一带群众十分敬佩的大英雄,京剧水路班演出的关于岳飞的剧目有很多,如《挑滑车》《镇潭州》《潞安州》《朱仙镇》等,这些都是京剧水路班常演的“岳飞戏”。
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卞家班”演员小八斤便深谙其中道理,《风波亭》《九更天》都是他的“看家戏”,都和岳飞有关。为更好地塑造岳飞心怀家国、情系百姓的英雄形象,小八斤在这两出戏里就人物的唱念进行了改编,且以其所演《风波亭·送百姓》一段为例:
老伯(白):啊呀元帅呀,想当年金兵犯中原,那时候可怜哪可怜!可怜我们朱仙镇的老百姓,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死得不明不白。幸亏岳元帅带领万兵来到朱仙镇,杀得金兵望风而逃,我们百姓重返家园,才得安居乐业。元帅这样忠心报国,爱民如子,受尽千辛万苦、使人恭敬。如今岳元帅要回京而去,我们老百姓如何舍得?元帅一走,金兵又要杀奔前来。可怜我们朱仙镇老百姓,又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老的老,少的少,男男女女,又要受金兵的刀头之苦哇。元帅你——不要走吧。
群众(拭泪,悲泣):元帅你——不要走吧。
岳飞(拭泪,唱西皮二落):听罢父老一番讲,心酸两泪挂胸膛。国土常思量,乡亲的安慰我常挂在心上。人马扎在朱仙镇,金兵不敢来逞强。卫国保家理应当,怎敢私自离疆场。十二道金牌三道圣旨吊我回朝纲,圣命二字难违抗,吉凶二字不知详。望求列公道路让,列公快快回家乡。
这段《风波亭·送百姓》片段经小八斤改编后,人物对话通俗易懂,很受当地观众喜爱。小八斤在演到老伯向岳飞表白时,情动于衷,热泪滚滚。
根据小八斤后人的记载可知,小八斤的《风波亭》岳飞“送百姓”一段的说白是其在小达子版《风波亭》基础上增加而来的,与之前京剧演出完全不一样,是小八斤迎合江南一带群众对岳飞这位抗金英雄的赞赏与崇拜心理,根据剧情发挥出来的。①卞韵良、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粉墨江湖》,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现在《风波亭》已基本绝迹于京剧舞台,只有新编京剧《满江红》有与《风波亭》类似的情节。
与之相似,有些剧目如《方腊造反》就不能在京剧水路班演出,因为方腊是浙江淳安人,在浙江建安、淳安一带方姓人群很多,此剧目在不少祠庙中是不允许演出的。
其次,对于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京剧水路班的历史剧里往往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与评价。从《岳飞传》可以看出,江南人对金兀术的态度与其他地区不同。剧中没有将金兀术塑造成一个扁平的反派形象,而是把他视为一个同样优秀的统帅。金兀术在戏中也没有骂过岳飞一句,平时称岳飞为“岳王爷”“岳元帅”,就是情急之下也不过是一句“岳南蛮”。江南人认为,金兀术是一名儒将,曾对江南地区有过屠城行为的是蒙古和后金统治者,江南地区没有与金廷直接对抗过,所以,江南百姓认为岳飞的悲剧并非来自金廷,而是把一腔愤恨都抛给了秦桧,因而京剧水路班历史剧对金兀术的评价相对客观。
第三,京剧水路班所演历史剧很多是以江南为故事的发生地。《甘露寺》是京剧水路班的保留剧目,更是京剧水路班的看家戏,上世纪30年代后期,活跃在江南一带的各京剧水路班几乎都会演《甘露寺》,这出戏也成了江南地区观众常看的戏目。因为《甘露寺》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江南,江南百姓热爱自己的家乡,喜欢看与江南有关的历史剧。与此类似的剧目还有《除三害》《马前泼水》等。《马前泼水》在浙江建德地区很受欢迎,因为“这是一本‘建德戏’。建德城西35 里有个朱池村,相传就是朱买臣的家。朱池住有不少姓朱的村民,还有朱买臣的祠堂”②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7),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60页。。
正如蒋桕连先生所说,地域性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渗透性很强,它不仅哺育自己的地域文化,同时也对外来文化进行地域性渗透和融合。京剧水路班因地制宜,根据地域文化需要创造各具特色的、互有异同的不同样式的京剧,京剧水路班为适应时代发展而变,为求自身之完善而变,说到底,是因地制宜而变。③蒋桕连:《京剧水路班的生存形态和当代启示》,《艺术百家》1990年第3期,第38页。京剧水路班所演历史剧及剧中人物很多都是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们所熟悉的,即便如此,水路班还是会根据观众的喜好对演出剧目进行取舍和改编。
二、世俗气息浓厚
京剧水路班演出剧目除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外,还具有明显的世俗性。京剧水路班演出的历史剧充满现实的精神,弥漫世俗的情调、庶民的趣味及乡土的气息。
我们仍以《甘露寺》为例,感受京剧水路班历史剧的世俗性。在通行本《甘露寺》中,乔国老上场后先念:“丹心正国,辅君王,社稷安康。”之后再念定场诗:“天子渊源重老臣,为子孝亲臣奉君。皇图永固民安乐,但愿我主万万春。”然后自报家门,最后才与乔喜展开对话。真正开唱要等到《奏本》这场才开始。
在京剧水路班的版本里,乔国老一上场先唱两句【散板】:“与张昭下完棋回府门,街市上悬灯所为何情?”紧接着与乔喜开始对话,特别像一个在江南乡间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家的老大爷,和老朋友下下棋,慵懒地打发一下午时光。人物一出场就非常市井化、生活化、世俗化。且看《相亲》一段:
乔国老:啊皇叔!
刘备:太尉,哈哈……
乔国老:越发的貌美了,进去多磕头少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刘备:是、是。
乔国老:这就是刘皇叔,皇叔这就是太后,快快见过。
刘备:参见国太。
这里的“越发的貌美”“多磕头少说话”都是非常鲜活的生活中的语言,剧中人物说着这样的话,仿佛从生活里走出来。又如水路班剧目里还有这样的唱词:
孙权:无奈何,忙施礼,国老你真真的讨厌。
乔国老:两国和好礼要当先。
通行版《甘露寺·相亲》里的情形是这样的:
乔国老(白):啊,太后,可知皇叔的根基?
吴国太(白):我不知呀。
乔国老(白):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陛下之玄孙,荆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献帝之皇叔。喏喏喏,国太请看,生得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真乃是帝王的根本呐。哈哈……
孙权(白):噢?他乃帝王的根本?
乔国老(白):帝王的根本。
孙权(白):与你何干?
乔国老(白):说说也无妨紧要呀!
孙权(白):多口!
乔国老(白):嘿嘿!反道我多口。
刘备(唱):弟兄结义在桃园结拜二弟关美髯。
乔国老(白):啊,太后,关美髯可晓得?
吴国太(白):我也不晓得呀。
乔国老(白):乃皇叔结拜的二弟,此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解良人氏。弟兄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暂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十名俱一不受,闻得皇叔么,有了下落,立时挂印封金,在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这位将军,他的义气不小哇!
孙权(白):哦?他的义气不小?
乔国老(白):义气不小。
孙权(白):你可曾亲眼得见?
乔国老(白):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哎,是哪一个不晓哇?
孙权(白):真正的唠叨!
乔国老(白):这也不算我唠叨啊!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京剧水路班的《甘露寺》与通行版《甘露寺》在《相亲》这一场中,无论是念白还是唱段差别都较大,京剧水路班的《相亲》在内容上更简洁,文辞上也更通俗。像“国老你真真的好讨厌”“两国和好礼仪要当先”明显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近于口语。京剧水路班剧目里的人物是从生活中经提炼后抽象化的,更贴近生活,因此深受观众喜爱。
京剧水路班的历史剧不仅在语言上有世俗化倾向,剧情设置上也偏向世俗化。“田记舞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排过一出新编历史故事大戏《越王献西施》,轰动一时,为京剧水路班编演新戏开创了先例。①《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浙江戏曲志资料汇编》(3),《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1985年编,第112—113页。西施故事发生在江南,家喻户晓,西施、范蠡、夫差、勾践、伍子胥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明人梁辰鱼所著《浣纱记》传奇写的正是“吴越争霸”的故事。京剧里有《长亭会》《武昭关》《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刺王僚》等以吴越争霸为背景的剧目。梁辰鱼创作《浣纱记》是歌颂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范蠡和西施,对荒淫骄奢的吴王和卑鄙卖国的伯嚭给予无情贬斥,同时赞许为报仇雪耻而忍辱负重的越王勾践,作品表达了对国家兴衰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之后的《长亭会》《文昭关》等剧目则是以伍子胥为核心人物创作的。
在传统京剧中,将政治从故事中抽离出来,重点渲染,便出现了《长亭会》《武昭关》《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刺王僚》等作品,如《长亭会》讲伍子胥战樊城后,中途与申包胥相逢,戏中需要两位老生,这就符合京剧重老生戏的传统。
京剧水路班“田记舞台”创作的《越王献西施》和传统京剧路子不一样,这部戏将“吴越争霸”里的政治淡化,重点突出感情戏。这部戏的剧本已失传,但据京剧水路班传人孙国良介绍说,这出戏删除了大部分与吴国有关的情节,伍子胥等角色被弱化,剧目的重点放在越王献西施的起因、越王劝说范蠡、范蠡劝说西施及越王进献西施的过程上。《越王献西施》将一部讲述民族大义的戏改编成了一部儿女私情的戏,甚至在这部戏里加入了越王与西施的感情戏,“轻大义而重小情”,将“吴越争霸”的格局弄小了。不过这出戏在当时很受欢迎,因为这出戏的剧情相比之前的“吴越争霸”戏更世俗化。这出戏突出了浣纱女的戏份,浣纱女由正旦扮演,正旦一般不会翻筋斗,但在京剧水路班,正旦到浣纱女从码头投入江中时,会做出类似“吊毛”的动作,跑圆场时,还会用水袖做出随波逐流的起伏动作,表现富春江上的风光,到了下场门口,还要做一个亮相才会下场。这和别的地方所演的浣纱女有很大差别。越王不再只是一个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工于心计的君王形象,西施和范蠡也不再是深明大义、为了成就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爱情的人,他们沉迷于对名与利的追逐,陶醉在感情的游戏中。就算演《文昭关》,京剧水路班通常在演完之后会带上演《浣纱女》和《芦中人》,唱词也自然粗野一些,并且东皋公和浣纱女、芦中人的戏,与伍子胥的戏同样重要,这和别的版本里一味突出伍子胥的戏份是很不同的。
京剧水路班的剧目除了剧情,“在表演处理上,多接近于民间生活,如《打鼓骂曹》一剧中祢衡击鼓一节戏,演员是赤膊擂鼓的;《芦花荡》一剧中张飞的扮饰是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翻跟斗出台疾步亮相的”②《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浙江戏曲志资料汇编》(3),《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1985 年编,第121页。。
京剧水路班剧目为何会走向“世俗化”,有一个记载似可说明问题——“特别是林家的姑婆(她能看懂《聊斋》《列国》——笔者注),更是喋喋不休。她经常‘考你一下’,要我回答殷纣王是谁的子孙,《六国封相》是哪六国以及要我讲述蒋干如何盗书之类,有时弄得我很窘”③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以京剧水路班观众的见识和生活经历,其实绝大多数人是看不懂历史戏的,所以有一个婆婆能看懂《六国封相》《三国》,反而显得十分难得。为迎合绝大多数看不明白剧情的观众,京剧水路班所演剧目必须走向“世俗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更多市场。
京剧水路班历史剧里的人物贴近生活,这与京剧水路班剧目的语言世俗化是相辅相成的。语言和人物塑造的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实则是京剧在水路班的演出里地域化的表现,京剧水路班历史剧的世俗化说到底还是为了适应演出市场的实际需要。
三、感官上的欢愉
在江南乡间,群众受生产活动限制,除一些如红白喜事等突发性事件带来的社会交往外,其他社会交往与娱乐活动并不频繁,并且这些社会交往与娱乐活动常常发生在农闲时。戏曲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观看戏曲不仅是群众的娱乐活动,还是群众的一种社交活动。对于平时难得看戏的农民来说,看戏除了能一饱眼福,尽情畅游,还是一种自由寻欢、苦中取乐的过程,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极大快慰,因此显得兴高采烈。对于绝大多数京剧水路班的观众而言,一年之中看戏的机会并不多,看戏给他们带来的体验也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观剧过程中,观众得到了感官上的观愉。
京剧水路班著名小生杨小卿曾经说过,京剧水路班里“有很多历史故事,像杨家将、岳传、三国戏、列国戏、包公戏等,歌颂了忠臣良将、英雄主义,谴责了一些人类不齿的卖国求荣、贪财好色的奸佞恶棍。许多人是在当亡国奴的痛苦心情中怀着寻求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慰藉来看戏的”①何荣穆:《启航杭嘉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在书塾这类正规知识传播机构里,要获取知识,需要来自个人的内在努力。与书塾不同,戏曲也是传播历史和社会知识的重要途径,从传播信息的角度看,戏曲的休闲性更明显,易于被人们接触与接受。
因为是抱着“图热闹”的心态去看历史剧,加之京剧水路班的观众文化知识比较浅薄、审美趣味简单,他们喜欢看的戏要有很强的娱乐性,所以京剧水路班的演出会追求热闹。如要营造出热闹的演出场面,就要将锣鼓敲打得更响亮一些,演员穿的服装和脸上化妆的色彩要更为艳丽,武打动作也要更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演唱时声音更高亢一些。京剧水路班的许多历史剧和其他版本比起来,很少在剧情上争胜。水路班所演历史剧,故事情节是当地观众了如指掌的,剧中人物性格也不复杂——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人物立场黑白分明,不存在争议;剧情也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悬念设计,观众看戏不费脑子。由此,京剧水路班演出历史剧在表演上下足了功夫。
如水路班在苏州吴县平台山庙台演戏时,多数以《长坂坡》这一剧目“压台”,演戏时周边伴随着吵闹声,观众看戏时感到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兴奋不已,这样就达到了理想的演出效果。京剧水路班演出时,还有一场叫“大操”的戏,据卞韵良回忆,这类戏“有十六个人扮演长枪手、盾牌手、撩刀手、短刀手等,伴奏吹将军令,在台上四人一组,表演舞蹈、翻筋斗,以显示戏班武戏的实力。‘大操’演来热烈、火爆,也是很好看的。杭嘉湖的观众,尤其是农民兄弟最爱看”②卞韵良、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粉墨江湖》,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那时,“农民、渔夫看戏就是为了娱乐。‘技与戏合’,为武戏表演之上乘,然以此项标准要求水路京班,便勉为其难了。在戏与观众之间,他们务必首先迎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和爱好。杭嘉湖水路京班的一些武戏表演,真似‘百戏’的回归,可是这一复古的现象,却受到观众的青睐;或者说,这一复古现象,原就是戏班为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要求而出现的”③于质彬:《南北皮黄戏史述》,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21页。。于质彬曾记下京剧水路班演员的表演,他说,京剧水路班“庆升堂”擅长演武戏,他们在表演《四杰村》里的余千时,有上栏杆表演“张飞卖肉”的绝艺,而且每次表演手法还不完全一样,追求的就是惊险和刺激。④于质彬:《南北皮黄戏史述》,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15页。
卞韵良曾记载他父亲小八斤当年和小达子在杭嘉湖地区演《风波亭》时,“缺少武功绝技,在杭嘉湖唱戏没有武功绝技,就是像小达子这样的红角也吃不开。父亲决定把小达子的《风波亭》变一变花头,唱词、武打动作都变一变”⑤卞韵良、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粉墨江湖》,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小八斤演《送百姓》一场,表演岳飞受刑时,臀部要垫上一寸厚的牛皮,然后八十军棍敲上去发出“啪啪”的响声,产生像是真的挨打的效果。此外,在这出戏里还要用到“吊毛”和“一口印”的功夫。演《九更天》时,检场会在演员胸脯上喷洒洋红水,然后演员双手抱着一个二尺长、一尺五寸宽的钉满棺材扒头钉的钉板,在台上左右翻滚三次,共计六个转身,然后一蹿,趴在钉板上,演员这时要双腿颤抖着站立起来,之后再扑在钉板上,假装精疲力竭不能动弹,这时四个校尉连人带钉板抬走,演岳飞的演员左右晃荡,展示“岳飞”的胸膛是一片鲜血淋漓。①卞韵良、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粉墨江湖》,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5页。为迎合观众的看戏心理,京剧水路班演出时都会对剧本做一些改编,以此来适应演出市场需求。
为给观众带来欢娱,除了演出开打精彩火爆的剧目外,在唱词上,京剧水路班也会有所改编。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逍遥津》,即使是著名演员,一般也只连唱13个“欺寡人”。“龙凤舞台”是京剧水路班里以老生见长的戏班,班主孙柏龄是麒派老生,在表演《逍遥津》时能连唱36个“欺寡人”。②于质彬:《南北皮黄戏史述》,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17页。
如同当时一篇对观众的采访里所说:“借着这一机会可以让终年辛劳的朋友上街来游玩一次,让蛰居乡间的人民来增点见闻,让闺房的小姐们来展展愁肠,让年青的伙伴来凑凑热闹,让城里的老板们多赚几个利钱……无怪乎要如斯热闹了。”③艾芊:《东平会日杂笔》,《临安武肃报》1946年10月21日。在这里,观众大多数时候看戏不需要深度,他们更需要在忙碌劳作之后通过看戏带来的短暂欢愉。能够看到那些让他们精神放松下来、大笑一场、大声喝彩的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达到看戏目的。如《萧何月下追韩信》是京剧水路班常演的一出历史剧,是“龙凤舞台”班主孙柏龄的拿手好戏。孙柏龄在演这出戏时,噱头既不在扣人心弦的表演上,也不在响彻云霄的唱腔上,而是让萧何每次出场就换一次戏袍,一本戏演下来,能换上六七件之多,这就是所谓“翻行头”。为了给“翻行头”的演员换衣服的时间,以及给他们有充分展示戏服的机会,水路京剧班的编剧便对这出戏进行重新创编,短短一出戏,为了让萧何多换几次服装,用了十多场,进进出出,忙个不停,达到让观众目不暇接的效果。
四、结语
京剧水路班所演历史剧有着较为鲜明的特点,它们或具有明显的江南区域历史文化背景,或带着世俗性,又或充满欢愉性。说到底,这些特点都是为迎合京剧水路班的观众群体。历史剧只是京剧水路班所演浩瀚剧目中的一类,对这些历史剧进行研究,能让今人窥见京剧水路班演出剧目之一角,也能引起业界对当下中国京剧如何地域化和多样化发展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