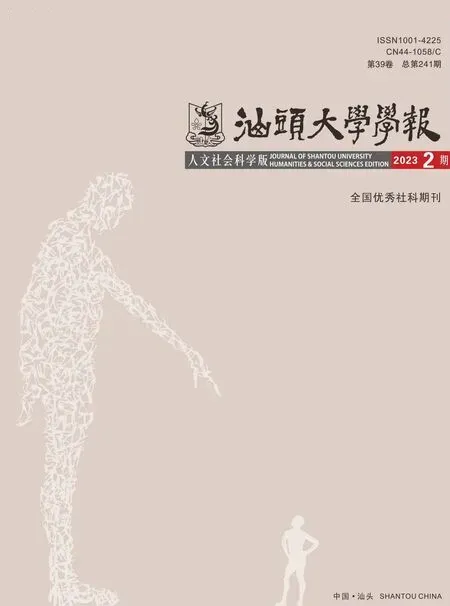论憨山德清“唯心识观”解庄
李志明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引言
憨山德清(1546-1623),安徽全椒人,俗姓蔡,字澄印,谥号弘觉禅师。他一生致力于融通三教,主张禅教合一、禅净双修,为晚明佛教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与云栖祩宏、紫柏真可、藕益智旭并称为“晚明四大高僧”。憨山德清一生著述颇丰,除佛门著述以外,又有《观老庄影响论》《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篇注》《中庸直指》《大学纲目决疑》等传世。其中《观老庄影响论》按其自述,“创意于十年之前,而克成于十年之后”[1]174;《老子道德经解》按其序文则花十五年之久;《庄子内篇注》虽未明确说明创作时间,但《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云:“四十八年庚申(1620),予年七十五。春课余。侍者广益,请重述《起信》,《圆觉》直解,《庄子内七篇注》。”[2]584《庄子内篇注》序言又云:“其学问源头,《影响论》发明已透。”[3]1则《庄子内篇注》一书从起念写作到最终完成耗费心血将近三十年。①《庄子内篇注》的具体成书过程及时间考索,可参看师瑞《憨山〈庄子内篇注〉成书时间辩疑》(五台山研究,2014 年第4 期)。由此可见,对于老庄的研究在憨山德清后半生的丛林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学术界围绕憨山德清《庄子内篇注》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代表性成果如李曦《释德清〈庄子内篇注〉研究》认为德清基本解开了庄子哲学“有待”—“无己”—“无待”的哲学结构,并对其注庄方法与失误之处进行了说明;王红蕾《憨山德清注〈庄〉动机与年代考》则对德清注解《庄子》的思想动机和注庄年代进行了考辨;韩焕忠《高僧能解南华意——憨山德清的〈庄子内篇注〉》则将憨山德清对《庄子》内七篇思想要旨的解读一一进行了评述;李大华《论憨山德清的庄子学》围绕“逍遥与玄冥”“方内与方外”“真知与真人”等问题对德清在注解中展现的庄佛互契及相异之处进行了分析;尚建飞《以佛法验证“老庄之大言”——释德清诠释老庄思想的进路及其特点》认为德清将“德性论”作为老庄思想的核心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不过德清的“误读”却进一步验证了老庄思想的价值。
这些成果对于憨山德清思想和庄子学的研究无疑都是富有建设性的,但是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一是“唯心识观”是憨山德清注解老庄的根本立场,目前学界对其思想内涵缺少更深入的揭示;二是憨山德清注解《庄子》遵循着一定的思想脉络,目前学界缺少更为清晰的梳理,对其背后贯彻的佛禅思想还有进一步剖析的必要。综合以上,论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一是憨山德清“唯心识观”的思想渊源、具体内涵及其对于老庄思想的整体判摄,二是憨山德清依据“唯心识观”解庄的具体思想路径,三是憨山德清以“唯心识观”融通三教的具体途径及其在《庄子内篇注》中的体现。
一、憨山德清“唯心识观”对老庄思想的判摄
憨山德清认为非佛法不足以尽老庄之意,《观老庄影响论·论宗趣》云:“吾意老庄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证,向之信乎游戏之谈,虽老师宿学,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识观,皆不出乎影响矣。”[1]173这里的“唯心识观”即指“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憨山德清在《化生仪轨》中说:“唯吾佛出世说法四十九年,所集诸经,有一大藏,始终只说了八个字,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2]372可见“唯心识观”既是憨山德清佛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注解老庄的出发点。
憨山德清的唯识学思想与法相唯识学有所不同,故此处有必要进行辨析。从法相唯识学角度看,人之心识是造作万物之因,为一切杂染生灭的根本,又被称为阿赖耶识,人的前七识如眼、耳、鼻、舌、身、意、末那皆依此识建立,阿赖耶识由如来藏因一念无明转变而来,如来藏不增不减、无染无着,又被称妙圆真心、众生本有之佛性。而正是在对阿赖耶识的界定及其与如来藏的关系上,憨山德清与法相唯识学存在较大分歧。按《瑜伽师地论》所述:“云何建立阿赖耶识杂染还灭相?谓略说阿赖耶识是一切杂染根本。所以者何?由此识是有情世间生起根本……复次,此杂染根本阿赖耶识,修善法故方得转灭。”[4]581法相宗认为阿赖耶识作为一切杂染之根本,属生灭法,是需要被转灭、否定的对象,唯有修持善法,将八识转为四智,才能证得佛果。憨山德清的观点与此不同,他在《大乘起信论直解》中说:
“经云‘如来藏转三十二相入一切众生身中’,是则迷如来藏而为识藏,乃众生心也。以此心乃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而成,名阿赖耶识。而此识体原是真如,亦名本觉,本无生灭。今因无明动彼净心而有生灭,故为业识。”[5]118
又在《〈楞严通义〉补遗》中说:“由此藏性迷为阿赖耶识,变起见、相二分;藏性在识名自证分;由本性不染,名‘白净识’,为证自证分。按论真如、生灭二门:此证自证分即是真如,其自证分即迷中本觉。”[2]288在憨山德清看来,阿赖耶识(众生心)固然由如来藏因一念无明转变而来,但因其本体仍是如来藏,因此并不失其不生不灭的本来觉性。憨山德清对阿赖耶识的看法继承自《大乘起信论》中的“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梨耶识。”[5]124他说:
“《楞伽》云:如来藏为生死因,若生若灭。故今在生灭门中要显此心为迷悟依。故云依如来藏有生灭心,譬如波涛依海水而有也。若据此一心真如,则了绝圣凡,故云三界唯心,则心外无一法可得。今显圣凡迷悟因果皆生灭门收,所谓不了一法界义故,不觉动念而有无明,迷此真心变为藏识,故经云识藏如来藏;故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5]125
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如水与波的关系。水无形无相,不属生灭;波有形相,故有生灭。水与波性质不同,故而“非一”;波本身即水,故而“非异”。阿赖耶识即同此波,是受无明扰动下的如来藏,阿赖耶识虽有生灭、能生万法,但其根本仍为不生不灭的如来藏。这样一来,无论是阿赖耶识还是前七识,皆可视为真如与生灭的和合,因此证悟佛境的过程就并非如法相宗一样需要转灭八识,而是发掘出八识受无明覆盖的原本清净圆满的如来藏性,一旦悟此如来藏性,则“一切法悉皆真如”,一切生灭亦可视为如来藏的随缘显现。
憨山德清的唯识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他对老庄思想的整体判摄至关重要。憨山德清认为“《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1]6,他对老庄思想的判摄是这样的:
“至若老氏以虚无为妙道,则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寿,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绝圣弃智,忘形去欲为行,以无为为宗极,斯比孔则又进。观生机深脉,破前六识分别之执,伏前七识生灭之机,而认八识精明之体。即楞严所谓罔象虚无,微细精想者,以为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以此识乃全体无明,观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此识体,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故曰,玄之又玄,而称之曰妙道,以天地万物,皆从此中变现,故曰,天地之根,众妙之门。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庄称自然。”[1]171
在憨山德清看来,老庄体认的道以“绝圣弃智”“忘形去欲”“无为”为特征,按佛家的修证层级看,是已“破前六识分别之执,伏前七识生灭之机”,而指向“八识精明之体”。“八识精明之体”即为阿赖耶识,按《楞严经》的描述,阿赖耶识具有“罔象虚无、微细精想”,“全体无明、观之不透”,“受不思议之熏变而生成世间万法”的特点,与老庄之道所具有的“惚兮恍兮、杳杳冥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蕴生万物”等特点一一对应,因此憨山德清认为:“老氏所宗,以虚无自然为妙道,此即《榜严》所谓‘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者是己,此正所云八而识空昧之体也。以其此识,最极幽深,微妙难测,非佛不足以尽之,转此则为大圆镜智矣。”[1]5由于老庄的妙道以阿赖耶识为最终归依,未能上溯到阿赖耶识背后的“无始涅盘元清净体”,因此在憨山德清看来道家思想仍不究竟,是“未打破生死窠窟”。但同时,憨山德清又运用“如来藏与阿赖耶识非一非异”的思想,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他认为老子与佛陀一样,皆为悟道之人,其所言说的“道”,同样是从“妙悟心”中流出的,只是因圣人的施教对象不同,故言教之深浅有所不同,“盖古之圣人无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从妙悟心中流出,应机而示浅深者也”[1]161。因此,尽管老庄所谓的妙道落脚点在“八识空昧之体”,是属生灭,但因为它同样是圣人“妙明一心”的体现,故不失其“真如常性”。因此对于道家弟子而言,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圣人所言说的“道”,而悟圣人之心(如来藏),如能悟圣人之心,则道家的一切言教均为清净法,与佛法无异,如憨山德清所说:“若以平等法界而观,不独三圣本来一体,无有一人一物,不是毗卢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现。故曰:不坏相而缘起,染净恒殊;不舍缘而即真,圣凡平等。但所施设有圆融行布、人法权实之异耳。”[1]164
二、憨山德清“唯心识观”解庄的思想路径
憨山德清对《庄子》极为推崇,他说:“间尝私谓中国去圣人,即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唯庄一人而己;载道之言,广大自在,除佛经,即诸子百氏究天人之学者,唯庄一书而己。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之下不知有妙论。”[1]163并认为佛法有益阐明庄子之旨。
借助佛家思想阐发庄子意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鲜见,相比较于前人注解《庄子》时缺乏固定的视角,憨山德清则明确的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立场出发,运用唯识思想“印决”《庄子》。憨山德清认为《庄子》内七篇的排列顺序遵循着一定的思想脉络。他认为《逍遥游》“乃明全体之圣人”,为“一书之宗本,立言之主意”;《齐物论》言世人“未明大道之源”“妄执我见以为是”,意在令人见其真宰、识其本性;《养生主》劝诫世人若能养其生之主,则“天真可复,道体可全”;《人间世》为“涉世之学问”,以明圣人“忘己虚心以游世”,彰显“圣人之大用”;《德充符》则明圣人“忘形释智,体用两全”;《大宗师》则言圣人“道全得备,浑然大化”,可为“万世所宗之师”;《应帝王》则以终内篇之意[3]101-102。概括地说,憨山德清对《庄子》的注解主要是沿着“心性论——功夫论——体用论”这条思想脉络展开的,下文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从“心性论”立场出发注解《庄子》是憨山德清解庄的核心。庄子所言的“道”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顺承老子对于“道”的界定,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成因,有难以被描述,无形无相却又客观存在的性质,如《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6]252另一方面也指一种逍遥无待,与天地并生、万物为一的圣人境界。围绕如何达到“道”的境界,庄子给出了“遗形去智”“泯灭是非”“心斋”“坐忘”等一系列方法。在此过程中,庄子也旁涉心性的问题,如他认为人的是非知见、机心智巧皆与圣人的境界相违背,是需要被否定的对象。但庄子并没有对于人性的结构以及人性何以如此作进一步具体说明,憨山德清则运用“唯心识观”对此做了深入的阐发,他在《大宗师》的注文中说:
“此明大宗师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天地、万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禀此大道而有生,处此形骸之中,为生之主者,所谓天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真,故称之曰“真宰”。而人悟此大道,彻见性真,则能外形骸,直于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为一体,而为世间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师”者,此也。”[3]113-114
憨山德清的这段注解仍是基于他的唯识学思想,在论述策略上是这样的:阿赖耶识能生万法,故“人人皆禀此而生”;阿赖耶识是生灭与不生灭的和合,人之形骸属生灭,故而“形假”,人之“天然之性”属不生灭,故而“性真”。若能悟此“性真”,则一切生灭与不生灭,法法皆真,故能“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为一体”。憨山德清将大道解释为人人本有之“天然之性”,把“所宗者,大道也”解读为“所宗者,人之天然之性也”,这样就把庄子所构想的圣人境界归入到人的心性中来,将庄子体悟大道的过程转变为“彻见性真”的过程,于是庄子的“境界论”就变成了“心性论”。例如《齐物论》开篇提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长嘘”,弟子颜成子游问“形故可如槁木,而心故可如死灰乎?”南郭子綦答到:“今者吾丧我。”[6]48按庄子之意,“吾丧我”指南郭子綦已“外其形骸”,泯灭知见之我,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合于道境。憨山德清则将“吾”解释为“真我”,将“丧我”之“我”解释为血肉之躯的“假我”,这种对“二我”的划分明显基于对阿赖耶识“真如与生灭和合”的体认;再如《齐物论》云:“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悉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按庄子之意,此“成心”当为“师心自用”之心,是一己知见之心①《庄子》内七篇中提到“心”时,常常对其采取警惕关照的态度,因为人之“心”常与智巧、思虑等意识活动紧密关联,而这与道的境界是相违背的。另外《人间世》云“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与《齐物论》之“师心”两相对照,犹可见庄子对于“师心”的否定态度。而后人如郭象、成玄英、林希逸、陆西星等均认为庄子此处是肯定“师心”,故在此作一辨析。,憨山德清则将此心解读为“现成本有之真心”,并认为“人人具有此心,人皆可自求而师之”[3]28。
其次,用佛家“破我执”的思想解读庄子的功夫论是憨山德清注庄的显著特点。庄子的功夫论主要表现为通过泯灭知见、摈弃机心、心斋坐忘等,达到遗形去骸、与物同一的圣人境界。憨山德清则以“破我执”统摄庄子的功夫论。他在《老子道德经解·发题》中说:
“然虽三教止观浅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执为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尽以“我”之一字为病根。……老子亦曰‘贵大患若身’。”[1]7
“我执”是佛教的根本问题,憨山德清曾说:“至若吾佛说法,虽浩瀚广大,要之不出破众生粗细我、法二执而己。二执既破,便登佛地。”[1]8佛家的两种“破我执”一者针对人自身(人我执),一者针对现象世界(法我执),在这一视角下,庄子的功夫论也可大致分为两种,当他主张“心斋坐忘”“外其心知”时,则属破除“人我执”;当他主张“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时,则属破除“法我执”。在“破我执”的具体方法上,憨山德清主张“止观”,他说:“以孔子专于经世,老子专于忘世,佛专于出世。然究竟虽不同,其实最初一步,皆以破我执为主,工夫皆由止观而入。”[1]8“止观”是天台宗证入涅盘的主要途径,智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云:
“若夫泥洹之法,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7]452
“止”为停止心妄,降服烦恼;观即观察妄惑,达到觉悟。“止观”又可称为“定慧”,唯“止”能“观”,唯“观”能“止”,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憨山德清借鉴了天台宗的止观思想,并以之为庄子功夫论的主要内容,如他认为《齐物论》所示的体道功夫关键就在于“观”:
“虽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观音声如响,则言语相空,如此则言自忘矣。言虽忘而未能忘我,则观自己如影外之影,观血肉之躯如蛇跗蜩翼,此则顿忘我相,不必似前分析也。盖前百骸九窍,一一而观,乃初心观法,如内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观;今即观身如影之不实,如蛇蚶之假借,乃即色明空,更不假费工夫也。虽观假我而未能忘物,故如蝶梦之喻,则物我两忘,物我忘,则是非泯。此圣人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结之。如此识其主意,摄归观心,则不被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归趣,此齐物之总持也。观者应知。”[3]58
憨山德清认为《齐物论》是按“止观”的深浅层次来结构全文的:先观人言的虚妄性,以明“言语相空”;继而观人身的虚妄性,以“顿忘我相”“即色明空”;最后观万物的虚妄性,从而“物我两忘”合于道境。再如《应帝王》中讲述了一个神巫季咸为壶子算命的故事,壶子先示之以“地文”,次示之以“天壤”,后示之以“太冲莫胜”,而神巫季咸三次测算皆出现失误,庄子通过这个故事揭示道心莫测、随缘任用之旨。而对于壶子的三次展示,憨山德清则解释为:
“此下三见,壶子示之安心不测之境,此即佛门之止观,乃安心之法也。”[3]135
他认为“地文”即“安心于至静之地,此止也”;“天壤”谓“高明昭旷之地,此即观也”,并认为从“地文”到“天壤”,是“言自从至深静之地,而发起照用,如所云即止之观也”;而对于“太冲莫胜”他解释到:“言动静不二也。初偏于静,次偏于动。今则安心于极虚,动静不二。犹言止观双运,不二之境也。”[3]136而前人如成玄英则认为“地文”为“妙本虚凝,寂而不动”,“天壤”为“垂迹应感,动而不寂”,“太冲莫胜”为“本迹相即,动寂一时”[6]306。这里憨山德清的解释虽出于佛家视角,但与前人的解释亦并不矛盾。
最后,体用论也是憨山德清解庄的重要视角。憨山德清重视体用,一方面与佛门弟子“知体不知用”有关,他在《示段幻然给谏请教》中说:“及宋而元,知识虽多,学人邪见不少,不堕生灭则落空见,有体无用。”[2]69另一方面则为了应对自古以来儒家学者对佛道二家不能“涉世利生”的指责。憨山德清在《老子道德经解·发题》中说:“或曰:三教圣人教人,俱要先破我执,是则无我之体同矣,奈何其用,有经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体用皆同,但有浅深小大之不同耳。”[1]8在他看来,三教皆以“破我执”为旨归,故而“体同”,同时三教亦皆有“利生之用”,故而“用同”,而对于三教“体用皆同,但有深浅大小之不同”,憨山德清解释道:
“若孔子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则诚,体也;诚则形,用也;心正意诚,体也;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用也。老子无名,体也;无为而为,用也;……老子则曰:常善教人,故无弃人。无弃人,则人皆可以为尧舜。是由无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书所言,为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语。皆以无为为经世之大用,又何尝忘世哉?至若佛则体包虚空,用周沙界,随类现身。乃曰:我于一切众生身中,成等正觉。又曰:度尽众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众生发菩提心,宁使我身受地狱苦,亦不疲厌。然所化众生,岂不在世间耶?既涉世度生,非经世而何?”[1]8
儒家以“匡持世道”为己任,故以“心正意诚”为体,以“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为用;道家因见“人心浇薄”,故要人“离欲清净”,以“无名”为“体”,“无为而为”为用;佛家为救世人脱离苦海、“成等正觉”,故以“真如常心”为体,以“度尽众生”为用。这样看来,佛道二家就绝非要人摒弃世事,正是要人走向世间、涉世利生,而憨山德清的这种观点是有其唯识思想作为依据的。正如《大乘起信论》云:“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5]118憨山德清则说:
“故云是心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故。今依此心显示大乘义者,以法界一心具有体、相、用三大义故。今依此一心开真如、生灭二门:若约真如门,则离一切相,名言双绝,但显其体,不显相、用,故云即示摩诃衍体;若于生灭门,则妄因真起,即显相用。故于生灭门中,具显体相用三大之义,是故名大。”[5]118
真如门揭示佛性的超言绝相、不可言说性,故而能显其体,不显相用;生灭门剖析世间万象,一切“有为”均属生灭。虽然生灭是“妄因真起”,但若从“悟”的角度看,则一切生灭均是真如的随缘显现,真如必依生灭门才能显示相用,即佛法必须在“有为”中揭示自身的体用,而永明延寿在《宗镜录·序》中也曾说:
“……不知性相二门,是自心之体用。若具用而失恒常之体,如无水有波。若得体而阙妙用之门,似无波有水。且未有无波之水,曾无不湿之波。以波彻水源、水穷波末,如性穷相表,相达性源。须知体用相成,性相互显。”[8]
因此重视“有为”是憨山德清唯识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太和庵真如庵记》中曾对修道弟子摒弃“有为”的行为进行严厉批判:“未悟空宗之体,而弃有为之行,讵非枵腹以待王膳,望济其饥乎?所谓有为虽伪,弃之则功行不成;无为虽真,拟之则圣果难克。苟能达性空而建万行,可谓理事双修,真妄一契者也。”[2]464正因此,体用论成为憨山德清注解庄子的重要视角,《大宗师》一文中描述古之真人: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6]239
一般来说,庄子是视“刑”“礼”“德”“知”为体道的阻碍的,而这里的说法却完全相反,因此有学者认为该段属衍文。对于这种矛盾,憨山德清是这样解释的,他将“以刑为体”解释为“刑者,不留其私,谓中心一私不留,以为其体”,将“以礼为翼”解释为“虽忘礼法,犹假礼以辅翼,可行于世”,因此上面的整段文字便可被理解为“言既游世,不可出于礼法之外”,而只要“中心一私不留”,摈弃“我执”,“无心而游”,则一切礼法均不会成为束缚,因此也就“虽行而不劳也”[3]107-108,这与他“悟其性真,法法皆真”的唯识思想是相一致的。再例如《应帝王》云:
“泰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6]293憨山德清则解释道:
“此言泰氏超越有虞,虚怀以游世,心闲而自得,且物我兼忘。……至其德用甚真,不以人伪。即已超凡情,安于大道非人之境,而不堕于虚无。且能和光同尘,而未始拘拘自隘。此泰氏之妙也。盖已得大宗师之体,而应用世间,特推绪余以度世。故云‘未始人于非人’。”[3]131
在憨山德清看来,泰氏并未因已悟其“性真”,便摒弃凡尘,恰恰相反,泰氏之所以超越有虞氏,正在于他已超越凡尘却又能“和光同尘”,此时属生灭的世俗生活已不再被视为遮蔽真理的存在,而是法法皆真、事事顺理。如此便是有体有用,既能“安于大道非人之境”,又能走向世间,悟其真如而不碍生灭。
三、憨山德清“唯心识观”解庄与融通三教
憨山德清对三教的统摄同样是从“心性论”“功夫论”“体用论”三个层面展开的。具体表现为首先通过“唯心识观”从心性本体层面说明三教本质的相通,继而用佛家修证层次说明三教在功夫论和体用论层面又各有区别,最后说明三教本质为一,应当“相须为用”。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憨山德清融通三教的理论基础。《观老庄影响论·论教源》云:“盖古之圣人无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从妙悟心中流出,应机而示浅深者也,故曰‘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1]161憨山德清认为三教皆依此“妙心”建立,以此“妙心”为旨归,他说:“三教之学皆防学者之心,缘浅以及深,由近以至远。”[1]166所谓“皆防学者之心”,即防止人本有之清净之心因无明妄念而败坏。在他看来,孔子为“防学者之心”,故“以仁义礼智授之,姑使舍恶以从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赏罚之权,作《春秋》以明治乱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伦之节。”[1]166老子为“防学者之心”,故主张“绝圣弃智”“剖斗折衡”“离欲清净,以静定持心,不事于物,澹泊无为”[1]166。这样一来,儒、道虽主张不同,却皆有济世利生之心,因此憨山德清称孔子“观其济世之心,岂非据菩萨乘,而说治世之法者耶?”[1]166,亦称老庄“观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归,有无双照,又似菩萨”[1]168,所以他认为三教之心皆同佛心,孔、老二圣为“吾佛密遣二人,而为佛法前导者”[1]166。
宋代高僧契嵩在《广原教》曾云:
“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夫教也者圣人之迹也,为之者圣人之心也,见其心则天下无有不是,循其迹则天下无有不非,是故贤者贵知夫圣人之心。”[9]
憨山德清延续了契嵩对“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迹”的划分,他说:“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1]10他认为圣人之心无不相同,圣人之迹(三教的思想言教)则有差异,若“以迹求心”,将具体之言教当作圣人之心,则三教之间就会轩轾难通,是“以蠡测海”、拘拘自隘;而若能“以心融迹”,则如芥子虽小却能容纳无边虚空,三教亦皆可融于一心之内。三教之所以“迹异”,则是因为“良由众生根器大小不同,故圣人设教浅深不一”[1]165。这里憨山德清借助佛家的修证法门,对儒、道二家的功夫论和体用论进行了评判。佛教的修证法门从低到高共有五种,分别为“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又分别对应着五界众生。憨山德清认为,孔子之教法是“欲人不为虎狼禽兽之行”,故“设仁义礼智教化为堤防,使思无邪,姑舍恶而从善”,“定名分,正上下”,使人“由物而入人”,但因“未离分别”,“其所言静定功夫,以唯识证之,乃断前六识分别邪王之思,而以七识为旨归之地”[1]171,故而其修证法门属于最浅的“人乘”。对于道家,“其静定工夫,举皆释形去智,离欲清净。所谓厌下苦粗障,欣上净妙离,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舍欲界生,而生初禅者,故曰‘宇泰定者,发乎天光’”[1]168,因此属“天乘”。而佛法最为究竟,“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1]165。
憨山德清认为三教虽有修证层次的不同,但却同等重要,《观老庄影响论·论行本》云:“究论修进阶差,实自人乘而立,是知人为凡圣之本也。……由是观之,舍人道无以立佛法,非佛法无以尽一心。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镃基,人道以佛法为究竟。”[1]169在他看来,“孔助于戒,以其严于治身;老助于定,以其精于忘我”,正因有儒、道二家,佛法才更易于被接受。总体而言,他认为儒、道二家需与佛“相须为用”,因为“执孔者,涉因缘;执老者,堕自然”,而只有佛法达到了“究竟一心”的境界,因此儒道要以佛法为最终旨归;而佛家虽能“究竟一心”,但却必须依托人天才能设教,故而佛家不能离开儒道。同时,憨山德清又指出,若能悟此“一心”,则“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1]165。在他看来,儒、道、释三教皆依“真如常心”设教,尽管三教之迹属生灭,但若能悟其“如来藏”,则一切教法均为如来藏的随缘显现,“一切诸法,但是一心,染净融通,无障无碍”[1]164。
憨山德清融通三教的思想在《庄子内篇注》中亦有鲜明体现,那就是他不仅“以佛解庄”,同时也“以儒解庄”。例如《德充符》中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德不形”,孔子答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6]220按庄子之意,“水停”之喻旨在说明圣人的德行湛渊澄净,可以取法为准,“成和之修”指圣人依乎天理,与天地万物混融,合于“道境”;“德不形”指圣人合于“道境”但不显露自身,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意;同时,圣人合道,无为而治,因此“物不能离”,此正如“道”虽不以具体形象出现,但是万物运作均不能离“道”。憨山德清则将“德者,成和之修也”断句为“德之成,和之修也”,并认为此句乃发明《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之意,并评价到:“观孔子对哀公之言……何等正大精确。”[3]97再如《人间世》中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向孔子请教如何避祸,孔子答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6]161憨山德清对于庄子引述孔子的话,是这样解释的:“庄子诽仁义,独于人之事君,以义为主,又以死忠为不善。今言人臣之事君,无往而非君,乃忠之盛也。此老何曾越世故耶?”[3]76同时他又评价《人间世》一篇云:“《庄子》全书,皆以忠孝为要名誉、丧失天真之不可尚者,独《人间世》一篇,则极尽其忠孝之实,一字不可易者。谁言其人不达世故,而恣肆其志耶?且借重孔子之言者,曷尝侮圣人哉?”[3]77在他看来,庄子并非有心要否定孔子的仁义忠孝,只是因世人以“仁义忠孝”为沽名钓誉之具,“有丧天真”,故而才否定孔子。
这样憨山德清“以儒解庄”,实际上也折射了他“儒道相通”的理念,再如庄子对于孔子的矛盾态度自古以来即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憨山德清则认为:“因人之固执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于诽尧舜,薄汤武,非大言也,绝圣弃智之谓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谈也,甚言有为之害也。诋訾孔子,非诋孔子,诋学孔子之迹者也。”[1]166他认为庄子“非诋孔子”,因为孔子之心为济世利生之心,亦是人道之根基,所以庄子时常借重孔子的话;另一方面,他认为庄子真正要否定的,实为“学孔子之迹者”,即“执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坚固我执,肆贪欲而为生累,至操仁义而为盗贼之资,启攻斗之祸者”[1]166。这样在憨山德清看来,庄子主出世而不弃孔子之言教,虽批判仁义忠孝但实已悟孔子之心,因此庄子的做法正是“以心融迹”、不拘泥一家之言的表现,也是佛家所谓悟其一心、法法不碍思想的体现,因此憨山德清称庄子谓“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应当说,憨山德清的解释,对于揭示庄子思想的深刻性,丰富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以及更好地理解三教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