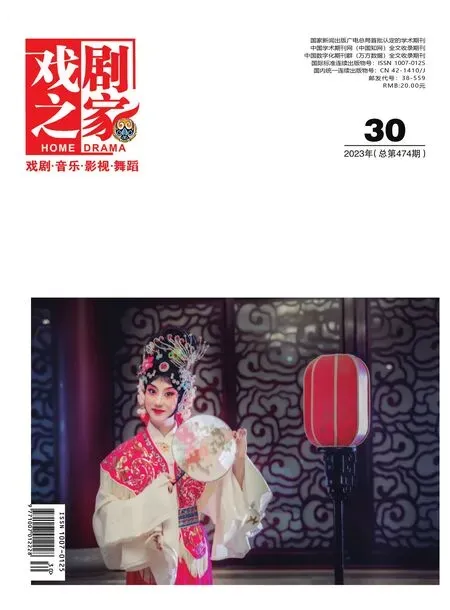叙事结构与和声策略
——储望华钢琴改编曲《茉莉花幻想曲》作品分析
范佳铭
(华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上海 200241)
一、“茉莉花”曲调的延续
民歌“茉莉花”又称“鲜花调”,产生于明代末年,兴盛于清代,最早在江淮地区流行。最早记录茉莉花歌词和曲调的文献史料被认为是由英国学者约翰·巴罗(John Barrow)于1804 年编写的《中国游记》一书,原题是“Moo—lee—wha”。中国人自己最早关于《茉莉花》的记谱晚于西方,是1837 年明清俗曲作品集《小慧集·小调谱》中以工尺谱形式记写的《鲜花调》。无论中西方关于茉莉花曲调的记谱,学界均无法考究某一部乐谱、某一种记谱法对于本源曲调的还原程度,但是可以确定这一曲调确实是当时传唱最为广泛的民间音乐。
茉莉花旋律不但中国大众耳熟能详,在国外也为人们所熟知,作为较早传到欧洲的中国民歌,最受西方人青睐的音乐实践当属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普契尼使用茉莉花旋律的契机是在一位曾驻中国的记者朋友法兰西公爵家中听到了来自中国的音乐盒中的三段旋律,第一段旋律就是茉莉花,这段旋律被用作剧中图兰朵公主的主导动机。
《茉莉花幻想曲》是华裔作曲家储望华在2003 年于家中与钢琴家陈巍岭约定的选题。先前钢琴家在墨尔本演出的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储望华作曲)深深吸引了在场的作曲家本人,两人一见如故并很快达成了合作这部作品的共识。《茉莉花幻想曲》同年首演于悉尼音乐学院,2004 年后分别跟随演奏家、作曲家的巡演来到了中国内地。在《茉莉花幻想曲》中,作曲家采用东方的创作思维,即线性的叙事逻辑,结合西方严谨的曲式结构,成就了这一部经典的中国钢琴曲作品。
二、“幻想曲”的叙事结构
(一)“逻辑化”的曲式
“幻想曲”体裁(意大利语fantasia,法语fantaisie)是一种很不注重形式的作品,此类作品通常采取对位的写法,被认为是变奏曲的前身①。从16世纪至19 世纪幻想曲的创作传统一直被认为保留着作曲家的主观想法,因为这种体裁在本质上是作曲家所获取灵感的自由运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作曲家即兴地运用变奏手段发挥已有的主题材料。在《茉莉花幻想曲》的结构布局上,作曲家亲言:“在布局上……有一个始由、初呈、延续、进展、转折、高潮、回落、再现、回味等。”②图示是笔者结合作曲家的结构意图划分的曲式结构。(见图1、图2)

图1:
全曲是采用原样再现、对比主题的单三部曲式,《茉莉花》主题旋律在呈示部和对比中部分别是使用江苏《茉莉花》的变体旋律A 和原样旋律B③。因为民歌主题是集中的、贯穿全曲的,弥散在逻辑化的曲式结构之上,与西方艺术表现形式相交融,笔者愿称之为“弥散在西方庭院的东方花香”。调式框架建立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A 宫系统和C 宫系统的徵调式构建,各乐段具有明确的边界,多数乐段内部调性稳定,而在“延续(24—32)”和“转折(46—56)”两个连接性段落有复杂的离调。
(二)“单线”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本是一个文学概念,在小说中叙事结构是构成形象体系和总体轮廓的方式,是作家的审美观照在叙述过程中的一种现实展开,音乐也具有叙事结构。在叙事学角度将音乐作品看作产生意义的文本符号的编码方式,即文本话语的组织结构。作品分析时,乐思及其逻辑化的展开成为音乐叙事最重要的展现方式,一方面的原因是:“叙事结构”一词借用文学中的“情节”因素展现作品的“音乐呈现”(musical procedure),即都具有典型结构——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其次,作曲家在不经意间已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义的空间,艺术形象的创作是需要依靠欣赏者在审美活动中的联想生发的,个人审美的经验十分开放。
单线性叙事结构遵循的是一种戏剧性的音乐叙述方式,强调音乐主题的密切“因果”联系,前段是因,后段有果,环环相扣、首尾呼应,呈现出情绪上的自然起伏和画面塑造的自然美感。音乐文本《茉莉花》是一首情歌,刻画的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细腻爱慕的情态,茉莉花的情态象征和赞誉美好的爱情是全曲情感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地,改编曲仍旧是想要诉说一个发生在东方庭院下的爱情故事,并表现出茉莉花香飘满园的场面。
引子部分(1—8):在钢琴的高音区表现出“茉莉花旋律A”,预示着将要出现的主题材料,7—8 小节出现的5 连音点状织体同样预示着呈示部的织体形态。
呈示部(9—23):三乐句非完整的乐段结构,主题旋律在左手部分第一次呈示。有趣的是,主题旋律出现在左手的中音声部,表现出平稳、温柔的性情,而上方弥漫着的六连音、五连音、三连音音型仿佛是传统的“花香”,赋予东方的气质。调性构建在A 宫系统,三个乐句的调式主音分别是“E 徵—A 宫—E徵”,调性稳定,属于收拢性乐段。
连接1(24—32):在作品经过主题呈示后,呈示部出现过的三连音音型开始成为对位的主体,速度加快,三音对二音的演奏方式使得连接部稍有幻想的气质,一种拟声性、情绪化的释放在连接部迸发了出来。调性的转换是复杂的,28—29 小节属于严格的离调模进,每小节内部变换一次调性,“#F 宫系统—bA 宫系统”“C 宫系统—A 宫系统”,30—31 小节有一次调性的变换,“E 宫系统—bD 宫系统”。(见谱例1)

谱例1:
中部(33—83):中部属于合成性的中部,主体结构包含展开性乐段R(33—45),连接部(46—56),对比性乐段C(57—73),另包含一个单乐句规模的变化再现f1(76—85),起到再现主题材料前的连接和情绪的回落与铺垫作用。
展开性乐段R(33—45)相当于主题材料的第一次变奏,采用展开性的乐思陈述方式,速度恢复呈示部速度“Tempo I”,调性建立在A 宫系统上,织体继承了三连音的基本模式并得到复杂化发展,主旋律移到右手高声部进行,以陈述性为主,旋律的线条逐渐明朗。第二个连接部(46—56)包含2 小节“Ad lib”即兴演奏和11 小节的“Cadenza”华彩乐段,充分地展现了“幻想”这一意义,速度和力度得以较大幅度的变化,为高潮处情感迸发积累了情绪。对比性乐段C(57—73)可以看作主题素材的第二次变奏,具体而言,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与主题素材相对的对比性乐段,材料上运用另一段“茉莉花旋律B”,调式建立在C 宫系统上,调性开放,采用厚重的八度织体形式。上述因素较呈示部有更大程度地渲染东方传统的色彩。“回落(74—83)”乐段在81—83 小节使用了呈示部的A 主题旋律,暗示着再现部的到来。
再现部(9—23)属于原样再现,尾声乐段(84—99)中两段“茉莉花旋律”分别在“a3”“f2”乐句陈述,茉莉花曲调得到交融。a3 乐句舒缓道出深情,而情绪在f2 倾泻而出,充斥着悲情色彩。
储望华亲言:“因为这首歌太好了,太知名了,所以我用它写成钢琴独奏曲时不敢掉以轻心,审慎为之。”④作曲家在构建逻辑化的结构布局,使得全曲具有严谨曲式结构的同时,在创作中极力保持茉莉花旋律的完整性以确保音乐情节发展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作曲家延续使用了中国传统音乐“起—承—转—合”的结构原则,使得核心材料呈线状展衍变化,从始至终,所有乐段环环相扣,整个情节的线性局面已经得到确立。因此,可以认为《茉莉花幻想曲》的结构布局是单线的叙事结构。
《茉莉花幻想曲》的音区十分宽广,力度范围达到“ppp—ff”,如“转折”乐段的音强从“ppp”到“f”在第47 小节便达成,情绪的增长是雄起的;速度呈现出明显的分界,有四个明显的节拍器标记和两个相对模糊的速度术语“poco più mosso(稍快)”“Meno mosso(稍慢)”。通过整合全曲主要的力度、速度标记,进行全曲情绪逻辑化表达的梳理。(见图3)

图3
在到达“转折”和“高潮”前,力度大部分时间处于“ppp—pp”的范围,速度因素主导了这一时段内情绪的升温。“转折”乐段情绪陡然提升,跟速度和力度因素的大幅度变化直接相关,并且,这个“转折”被安排在全曲长度前1/3 处(或0.382 的黄金分割点)附近,即华彩段的位置(第48—56 小节),赋予这个高潮不可抗拒的心理强度,借此契机再次绽放出了东方的象征之花——茉莉花。“回落—再现”呈现出与“初呈—转折”的镜像对称,这一西方对称性的逻辑结构和东方的情韵在情绪表达上的巧合,更像是符合东方审美的有意味的伏笔,具有东方艺术写意的美感。从情绪的整体走向看,曲子十分契合拱形的发展结构,“高潮”乐段情绪达到极值,而在“回味”乐段后半部,力度速度在经历陡然的增势过后急转直下,“茉莉花旋律”在花瓣片片凋零中消散,充满着悲情的演绎。
三、和声渲染的东方意蕴
由于《茉莉花幻想曲》的音乐文本选材于传统民歌,中国传统民歌的写作属于内涵文法⑤,即通过意象横向的组织表达情感和幻想,发挥意象本身的表现潜力,表现为乐思的写作和发展追求感性。作曲家显然是遵循这一传统——有意保留完整的民歌旋律并使用单线的叙事结构。在改编的过程中,为充分发挥原有旋律优势,钢琴的表现策略在和声语汇上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下文的论述重点是:东方的单线思维和西方逻辑化思维是如何恰当地利用和声策略得以交融。
和声语汇是这首中等篇幅作品中核心的主导因素,作品通过使用大量的二度音程叠置、四度叠置和弦和高叠和弦的分解,在描摹和诠释东方庭院下茉莉花盛开的场景。
呈示部(9—23)大量的二音叠置模仿古筝的三种基本音色(泛音、散音、按音),增加了和声的色彩性。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之“论琴”中载:“泛聲應徽取音,不假按抑,得自然之聲,法天之音,音之清者也。”古琴泛音的奏法为左手轻触弦,右手取单音,音色朦胧空灵,富有幻想色彩。如谱例2 所示,从乐曲第9 小节开始高声部连续的二度音叠置采用“断奏”的方式,即点状的织体形态,通过调节触键的效果造成明亮的音色,突出古琴的发声特点。二度音程选用高音位烘托出主旋律的平稳流畅,仿佛清晨时分雾气氤氲、花香清净淡雅的场景。(见谱例2)

连接部(24—32)使用四度和弦的叠置是模仿传统乐器笙、琵琶的音响,在增加浓郁的民族风格的同时,使用复节奏模式,即截然不同的节奏同时使用于织体的不同声部中,密集的织体以经典的西方对位(2对3)为载体呈现出动力化的进程,暗示茉莉花瓣片片飘零的场面。(见谱例3)

高叠和弦是指由五个不同音,按三度排列起来的九和弦、十一和弦、十三和弦。谱例3 展现了一个三度叠置的和弦结构和五声性调式旋律结合使用的范例,在小七和弦的基础上,附加一个纯四度,这种方式使得每一个高叠和弦内部自成一个五声音列,从而实现软化调式偏音的效果,再依托线状织体的音阶级进、跳进相结合造成乐曲旋律的流畅。并且,这一策略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和弦解决这一步骤,在艺术效果上极其不和谐的音响效果也不断推动着曲风向高远的意境延伸。(见谱例4)
全曲多处使用“una corda”(左踏板),钢琴点、线状织体产生朦胧效果起到了辅助音色描摹的作用。综上,《茉莉花幻想曲》显性的和声策略是通过五声性和弦结构打破完全三度叠置的西方模式,采用多样的和弦结构加以描摹中国传统音色,追求的是和声色彩对音乐形象的塑造;深层次上,和声策略是在叙事结构的多义性原则下以更加内敛的方式暗示、隐喻作曲家的审美情趣,表达追求东方审美意境的愿望。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茉莉花幻想曲》的叙事结构与和声策略的分析,旨在探讨作曲家储望华采用西方写作技法诠释东方传统音乐这一经典案例,赋予茉莉花旋律新的诠释和内涵。储望华先生代表着海内外无私奉献、顽强奋斗的中国作曲家,他们结合民族音乐传统,发扬中华优秀传统的音乐实践,创作出新时代的中国钢琴音乐。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严谨的曲式分析也将启迪我们理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技法,在音乐创作和分析中寻找融贯中西的恰当节点。
注释:
①参见迈克尔·肯尼迪,乔伊斯·布尔恩:《牛津简明音乐词典:第4 版》人民音乐出版社,第376 页。
②④参见储望华:《谈钢琴独奏曲〈茉莉花〉的改编》,《钢琴艺术》2005 年第10 期,第36 页。
③原样旋律参见袁静芳,褚历执:《中国传统音乐简明教程谱例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第22 页。
⑤参见林华:《音乐符号的内涵文法与外延文法》,《音乐艺术》2011 年第2 期,第53—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