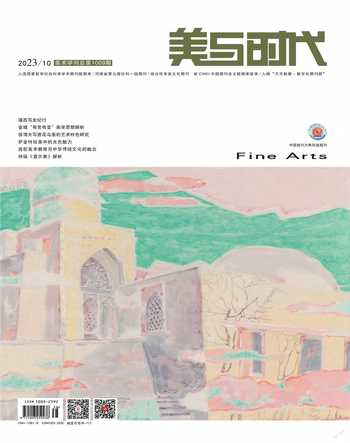八大山人绘画艺术中的自由美学思想探析
摘 要:八大山人在绘画领域成就极高,花鸟走兽都被其赋予了独特的艺术思考,但我们在关注其猎奇画面的同时,需要对其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思考,这样才可以真正领悟八大山人绘画作品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八大山人一生以明代遗民自居,被时代抛弃的孤寂之感在他内心膨胀。八大山人通过入佛修道来躲避政治诡谲之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催生出独特的自由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有关。正是青灯古佛、悟道观花的日子,给了创作者与宇宙人生连接的机会,使其基于对道家思想的充分思考形成了浓重的自由意识,在道家自然观的浸润中滋生出“逸”的绘画品格。此外,禅宗的艺术特质也完整了八大山人的艺术构造,使其作品从神品向逸品转移,最终孕育出自由美学的一片笔墨天地。
关键词:自由美学思想;八大山人;佛道文化
八大山人(亦作“八大”)作为明末清初的画坛“四僧”之一,其画作中“白眼”“冷眼”的标志性符号将其绘画艺术成就推向新的高度,这种“以丑为美”的极端审美也催生了现代绘画艺术创作的初芽。出生于皇室贵族、从小受到父辈艺术陶冶的他,年幼时便能画青山绿水。由于近师董其昌,所以深受其影响。“逸”的意识强调个体,关注人与自然,超绝、放纵、释放的审美背景将其观照视角聚焦于荒寒萧疏之景中。经历过“三月十九日”之后,留恋旧山河之情弥补了他精神世界的空白,也使得他情绪化的创作手法与艺术特征凸显,以恣意任性的笔墨挥洒下一只只怪鸟、一群群怪鱼,留给世人的是无尽的争议。现代绘画艺术性的构成需要情感和自我抒发,尤其是对创作者生命意识的考察和价值追求的关注。八大山人一生以明代遗民自居,被时代抛弃的孤寂之感在他内心膨胀,通过入佛修道来躲避政治诡谲的同时,其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由美学气质。
一、物我两忘的自由之风
如果要考察八大山人的画作思想,就必须从其特殊的王孙、明遗民、僧人、明道者等几重身份去理解。八大山人二十三岁削发为僧,而后辗转徘徊于佛、道之间,“谈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离禅”。宗教的传情作用能对人的精神进行一定的温养,但当我们欣赏八大山人的画作时,会感受到其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极度抒发,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压抑、窒息的不安情绪。即便有飞蛾扑火的勇气也无法改变惨痛的历史现状,当个体和时代发生巨大交锋时,压抑、冲击会震碎一个孤傲的画家,其在漫长的余生里不断捡拾生命碎片,拼凑出自由的美学思想。
要想探讨八大山人的自由意识,就要先从“八大山人”四个字入手。他在六十岁时启用此署名作画,“八大山人”四字连起来仿佛“哭之、笑之”,啼笑皆非的字样表露出其对清王朝的痛恨及对自我身世流亡的无可奈何,这是对社会身份不自由的排斥。好友澹雪性格与其相似,是一般倔强,故友病死狱中后,八大山人外出云游,此时期创作密集。于常理而言,家国俱损,亲友皆故,前途黯淡无光,本应该对世间毫无留恋,但其“死生存亡,实为一体也”的生死观在艺术创作维度拓展了自由美学的范畴。道家思想中充满了对于人生的思索,将个人的精神寄托于宇宙广阔天地之间,自然质朴的回归观本质上要求人产生对尘世的超脱感。对艺术创作者来说,需要将个人的审美剥离个体,将艺术创造与感性想象结合起来,艺术性地创造出纯艺术品,如庄子的绝美艺术想象,在天地间寄托精神,留给后人丰富的美学瑰宝。而将天地与自我进行有效连接的途径必然是“忘我”,这种消亡自我的方式是目的与过程的统一,恢复到纯粹的自我,进而获得自由的价值。
八大山人在接触道教朋友、汲取与思辨道家思想的同时,在内心形成了独特的生死观念,寻仇觅恨无处发之时也试图梦回老庄,将个体在时间的刻度上消弭,于是将自我短暂地从现实流变中抽离出来,企图用艺术创作去重塑精神世界。但其又自幼受儒家文化礼浸,被迫成为隐士后又矛盾地向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这种矛盾心理让我们在仔细梳理八大的花鸟意象时,不难发现多有兰菊灵芝、仙鹤椿鹿,但此类奇花异兽的神情多似人,虽是寄托于天地间,已化成草木走兽,但依旧有着对人世的眷恋、鄙夷、麻木、期盼的神色。如《荷花》一图,画面构图锋利,点墨堆出藕塘之上竖立着的一朵孤傲的菡萏,欲开却未开的姿态彰显着对生死的淡忘。独立于天地之间的自由精神成了艺术创作的核心,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视作其自由美学的本质映射。又如《鱼》一图,有人说这是太极的图案。圆融的笔法、极致简约的线条勾勒出鱼的外形,轻重快慢的运笔节奏、强弱虚实的晕染技巧,寥寥数笔就概括出一条鱼的全部。画面墨点无多,两点墨滴点出鱼的眼神,表现鱼的神态。这种神态是绝望,是麻木,是圆融,也是淡然。超脱个体的精神构建,反映出八大对于人生的思索。鱼本象征自由,此中扭曲顺滑的笔画却能见到极力挣扎的样貌,看着圆滑的身形却是极其不自然的。微微裂开的鱼唇似语非语,如创作者本人一般。根据史料记载,八大唯有饮酒后陷入癫狂状态才会与人多交流,才能在创作的时候挥墨画百篇,所以大概是由于极端的压抑,画中的鱼才被迫咧开了嘴。
我们不过多评价八大山人绘画背后是否含有对道教的推崇,但其画作中蕴含的丰富的道家思想是我们可以论证的。自由美学表现在对“逸”的绘画艺术追求上,道家自唐宋之际开始对绘画艺术产生写意导向作用,入仕失败后遁世归隐的情怀形成了画坛对“逸”的追求和推崇。刘勰提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主张将个人的抒情与客观理路结合,要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自由永恒化,达到“逸”的美感。
二、逃禅涉佛的入净之感
除了道家的自然观对八大山人自由美学的影响外,出家逃禅也在其自由美学思想的池子中栽培了一朵金莲。八大师从曹洞宗禅师颖学弘敏,在礼佛期间将佛理融入艺术创作中,如《水仙》犹如佛教中佛祖拈花时所持之花,四片花叶呈四散状,花蕊低垂,如世尊传法。《五灯元会》中有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葉。”这是一种向内看的智慧,是感悟与思考的集合。
曹洞宗推崇“无情”,主张将凡尘之物看作自足之态下对大千说法的表达,这一点契合艺术创作中的“模仿”。自古以来,艺术创作要求追求事物的本来面貌,区别于西方美术的“形似”,但中国美术的“神似”也在意艺术与客观世界的相似问题。“无情”是对“神”的高度集中概括,创作之初要将自我消弭,丧失自我之后再去观照客观物体的形态,以自由无阻的神思去体悟世界。神品之作要求完美无瑕,从顾恺之的“点睛”发展到明清两代之间的“至善至美”,过度社会政教化的艺术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一个断功名、剃人发的遗民僧人,故其逐渐将“逸”的特征作为创作中的美学指导。出家逃禅,追求清冷,青灯古佛的起居中以“逸”为反抗的突破点,在画面中多灌入清寒凄凉之景,对自由的无限遐想也就成了“逸品”的高尚表达。画菊要画低垂开败的,画鸟要画收羽侧目的,寂灭自我的同时寻求自由的本质,不限于时空的拘束,在对“自由”的哀歌中升华。这份自由的美学气质是长期战战兢兢下的自保,是向死而生的勇气,亦是看淡生死后对世界的反抗。因此八大在创作花鸟图卷时,超脱基于物象的“神品”,而在“逸品”的塑造中灌入了自我的思考,这种思考就是自由美学的体现。将自由和永恒视为一体,死是生的开始,生是死的延续,将生命看作一个整体的轮回。佛教认为世间存在轮回,所以他汲取了佛教思想,以自由为创作核心。个体肉体的消亡并不会阻断精神价值的持续产出,他将情绪凝聚在笔墨之中,建构起多个“白眼”走兽。
吴昌硕曾说:“雪个,清湘皆禅之上乘,参悟不难也。”当然,八大山人很少对禅理进行谈论,仅有少部分能从其诗画中解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佛理不解,正如其所言,“禅分南北宗,画者东西影。说禅我弗解,学画那得省”。禅宗认为万物无相,世界的本质为空。八大在绘画艺术中以大笔墨铺陈主题,将与主体无关的他物留白,留给看客独立自由思考的空间。八大笔下的鸟不只是鸟,前文提到鸟具有了人的神思。目前大多数人论及八大的画作,都会称其是对自我的表达,但仔细琢磨,画中之物又何尝不是观画者呢?如寒鸦,其在冷眼看的是画外的客体,但是画外之人也就在观画的同时映照进寒鸦的眼睛里。八大特别爱给鸟兽塑造眼睛,或许是因为受“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思想的影响,一切感受都在于心,于是鸟兽有了心,有了自由,用感受万物的眼睛去洞察宇宙的真理。存在在纸面上的事物由此达到了永恒,是对自由的忘却,也是对生命的尊重。美与善在看似诡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无论是八大山人对时代的怨恨,还是对身份的悲叹,又或是对人生变迁的感慨,都在这一幅幅画作中获得新生。
三、孤独焦虑的精神之塔
如果八大山人的自我情绪成了求生的本能,那么孤独与焦虑的精神特质则从时间与空间上为其塑造出了一座自由的高塔。友人吴氏曾评价其“数年对人不作一语”。追求极致的静谧,基于孤独的本质凝练出高度集中的思想境界,以致观八大之作,如入画观花,在其“静”的审美创作中感受到永恒的情感抒发。可这种孤独之感又伴随着焦虑的恐慌。从史实角度来看,明遗民的身份造就了他对自身社会身份的不认同,独行天地间的悠然悲怆之感必然会使内心终日焦虑不安。然而这种焦虑是有别于惶恐的,惶恐来自对现实需要的迫切渴望,焦虑则是个体与时代这一宏大命题下对自我认知的迷茫。
孤独和焦虑是表征,自由才是其内在的核心追求。八大山人在地域上终日混迹于宗教场所,在时间上感受到无穷无尽的煎熬,历史无法扭转,自我身份不被社会认同,强烈的情绪造就了其对于自由本质的审美追求。孤独作为一种强烈的精神特质,在审美艺术创作中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八大山人的花鸟山石都是其孤独精神的具体表征。传统绘画艺术讲求“妙得”,其游鱼之妙,则在于后人考察其为阴阳鱼图像,又在于给予了这条造型曲滑的鱼以人的神态,诡谲的弯曲角度隐藏在淡雅的画面中,鱼的眉目则成了视觉焦点。游鱼的怪不单单体现于面目特征上,更多体现在了鱼自身所处的环境之中,就如同八大一般,身处于不匹配自己身份的时代,被社会压迫到心理扭曲,但人们只关注面目上的忧愁,无法深入理解他与时代脱节的孤独感。游鱼画面极简雅致,略微波澜起伏,这片天地里鱼无疑是自由的。又如孤鸟之妙,在春意盎然的礁石上冷眼示人,斜目而观则是焦虑的心理特征,单足而立成了八大精神的无言呼告。八大运笔极简,“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虚实之法以线条形式形成空间排布变化,在若喜似悲的情感变化中展现独属于创作者的自由美学。
孤独与焦虑的特质来自现实生活,同时也是长期进行宗教性思考的产物。八大的写意作品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于其以自然为本位进行艺术性思考与创作。禅宗追求顿悟,排除外界干扰,以孤独之眼观察自然的本质规律,进行加工提炼,以求简中见繁、返璞归真。在艺术创作中,则表现为从宏观视角对艺术语言进行高度概括,将所悟具象化于纸面中。而焦虑又赋予抽象化规律以动的美感,以综合的感性表达创造自由的美学情趣。八大山人将宗教哲学融入文艺创作中,形成独特的艺术特性,这种对特性进行凝练的过程也是其对自我价值观进行选择的过程。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在于抒情,有感而发的艺术手段为艺术创作者找到情感表达的窗口,抒发内心所感能极大缓解孤独与焦虑情绪。八大山人的艺术创作为其塑造了一座自由的高塔,由于地域上的限制及精神上的打压,无家可归的寂寥之感促使其投身于宗教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中,向往自由是其形成自我认同的必要途径。现实生活中的形式自由无法满足艺术创作者,使得其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鸿沟中徘徊,最终以绘画艺术创作为支点,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片天地无疑是孤独和焦虑的,但也无疑是自由的,只有孤独能够凝聚艺术家内在的生命活力。八大山人《个山小像》的题跋是对自我孤独的认同,亦是价值论上给予自由的尊重。
参考文献:
[1]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全集[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
[2]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3]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4]張馨之.八大山人山水画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5]范曾.神会:范曾与八大山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萧鸿鸣.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7]朱良志.八大山人绘画的“怪诞”问题[J].文艺研究,2008(8):101-109.
[8]范曾.八大山人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30-138.
[9]宗维新.艺术情感的表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101-104,109.
[10]朱若蓓,唐明丽.孤独感对艺术的造就:以八大山人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3(2):16-18.
[11]史宏云.古代花鸟画题画诗的意象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1.
[12]杜觉民.隐逸与超越[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7.
作者简介:
吴超,中国计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评朱良志先生《八大山人研究》(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