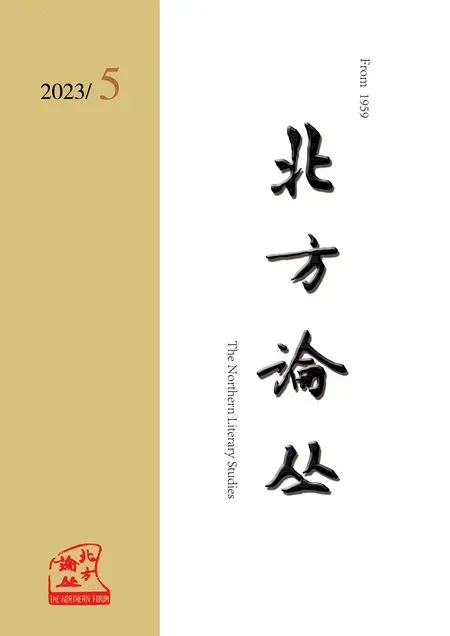松柏种植与苏轼的“松柏世界”
贺同赏
本文所谓的“松柏”,是以松树、柏树为主,包括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松柏纲所包含的松、柏、杉、桧、栝、枞等相近树种;将这些树种归为一个大类,除了它们皆为外形接近的乔木以外,另一重要因素是它们的叶子都常绿不凋。认识到这些树种外形相似、枝叶常绿的近似特征并将其归为一个大类,并不自现代始:“更冬不凋者,多有之矣。松、柏、栝、桧、杉……未尝改柯易叶。”[1]399
一、松柏的自然面貌、人文品节与中唐至北宋士人的种植诗作
(一)古人对松柏之属的生物学考察与人文体认
我国古人对于上述松柏一类树种,在生物学上早有观察与认知。“食松叶令人不老……松脂沦入地,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璧,烧之,皆有松气。(《本草》)……松柏为百木丈(《史记》)……丁固梦松树生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后十八年,为公,遂如梦。(《吴录》)”[2]1105-1106“百木之长,犹公,故字从公。磥砢多节,盘根樛枝。皮粗厚,望之如龙鳞。四时常青,不改柯叶。三针者为栝子松,七针者为果松……又有赤松、白松、鹿尾松,秉性尤异。”[3]206“柏,椈也。(《尔雅》)……四时常保其青青(《庄子》)。”[2]1139“柏,性坚致,有脂而香……柏视松也,犹伯视公。伯用诎,所执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执桓圭者以此。桧,柏叶松身,则叶与身皆曲;枞,松叶柏身,则叶与身皆直。枞以直而从之,桧以曲而会之。世云柏之指西,犹磁之指南也。”[4]138“柏,一名椈树。耸直,皮薄、肌腻。三月开细琐花,结实成球,状如小铃,多瓣。九月熟,霜后瓣裂,中有子,大如麦,芬香可爱。柏,阴木也。木皆属阳,而柏向阴指西,盖木之有贞德者。故字从白,白西方正色。处处有之,古以生泰山者为良,今陕州、宜州、密州皆佳,而乾陵者尤异。木之纹理大者,都为菩萨、云气、人物、鸟兽,状态分明。径尺,一株可值万钱。川柏亦细腻,以为几案,光滑悦目。”[3]207“柏叶松身,曰栝。”[5]149“栝,桧也。”[6]469由上可见,古人不但对松、柏、桧(栝)、枞等树种各自的生活习性、外形特征、材质用途等认识全面,而且对它们之间外形上的相似性也有细致考察。
在观察认识松、柏等树种的生物学面貌的同时,我国古人基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维方式,对于松柏等树身上所隐含的与人类相通的某些高贵的人文品格,也有了深沉的感悟与体认。儒家经典有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松柏之有心也……松柏凌寒而郁茂,由其心贞和故也”(《礼记·礼器》)。中古时期的诗人们亦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三首》其二);“巫山小摇落,碧色见松林”(杜甫《西阁二首》其一)等等,不一而足。综合来看,人们认为松柏身上的所具有精神意蕴,主要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青碧之颜色、坚贞不渝之品节以及英才之被埋没。
(二)唐代到北宋士人松柏种植诗作述要
笔者据《中国基本古籍库》《全唐诗》《全宋诗》三检索系统统计,士人种植松柏类树木之诗作的数量,初唐之前未见;盛唐1首,中、晚唐11首;北宋34首。再对作者做一简略分析。唐五代有岑参、白居易、柳宗元、刘得仁、施肩吾、陆龟蒙、皮日休、齐己、文丙9人;其中,白居易作品最多,3首。北宋时期有释智圆(士人化僧人)、舒雄、韩琦、韩维、王安石、郑獬、强至、程颢、苏轼、苏辙、范祖禹、陈师道、晁补之、李复、谢薖15人,其中,苏轼作品最多,7首。
唐代士人种植松柏诗作之精神意蕴,绝大多数不出赞美松柏青碧之颜色和坚贞不渝之品节以及感叹英才之被埋没三个方面。比如,岑参(715?—770)五律《使院中新栽柏树子呈李十五栖筠》“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白居易(772—846)五古《栽松二首》其一“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其二“知君死则已,不死会凌云”;施肩吾(780—861)七绝《玩手植松》“青翠才将众草分……看看气色欲凌云”等,主要是赞美松柏的翠色与高节。又如,白居易五古《栽杉》“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不见郁郁松,委质山上苗”;柳宗元(773—819)五古《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二首》其一“青松遗涧底,擢莳兹庭中……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风”,则主要以赞美松树、杉树等树之高节、表达嘉树(同时比况人才)少人赏识的悲慨。此外,从白居易诗中还透露出将杉树与松树混同看待的社会风俗。
相较于唐人种植松柏之作品,北宋士人的同类作品的精神意蕴则显得更加多样化。首先,赞美松柏之碧色与高节,仍是其最大主题。释智圆(976—1022)七律《新栽小松》云:“冷碧岂容尘染污,贞心宁共草凋衰。”韩维(1017—1098)七律《种柏寄苏子美》云:“人皆种花我种柏,为此劲性寒不易。三春虽怜少姿媚,岁暮方看霭颜色。南堂之南可数到,列树六本翠磔磔……”;陈师道(1053—1102)《次韵德麟植桧》云:“植桧三尺强,已有凌云气……缅怀万仞颠,千丈蔚苍翠。”李复(1052—?)《种松》云:“渐有干云势,轩昂出楸梧……想当千载后,黛色凌天衢。”上述均描写出松柏之青色,赞美了松柏高拔之节。其次,亦偶有感叹松柏落寞、英才不遇的作品。郑獬《乌龙老栽松既以诗三首》其一云:“高标不畏雪霜侵,枉斸孤根出旧林。但恐长安无地种,人家桃李自成阴。”这便是赞松柏之高节,叹世俗之不赏。惟北宋大部分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士人不如意者较少,故假借松柏无人赏识来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诗作,也就寥寥。再次,一些为前代咏松、种松之作罕有涉及的主题,也在北宋士人松柏种植诗作中,有所表现。舒雄《太守王公植松因赋》“种是万株松树在,至今民唤作甘棠”,歌颂了植松泽民之仁政慈心。韩维《和景纯栽松二首》,其一,“芳根出涧底,秀木依墙东。莫顾一时好,当观三世空。”其二,“论坚莫如松,言脆莫如葱。坚脆卒同尽,无尽无如翁”,隐含了较为浓重的佛家色空思想。王安石《蒋山手种松》“青青石上岁寒枝,一寸岩前手自移。闻道近来高数尺,此身蒲柳故应衰”,则以青松之长生,来衬托自己年老体衰、人生苦短之惆怅。韩维《丞相城上植柏》“有心解报公封植,不学群芳艳易凋”,则以被植幼柏自况,曲折表达了自修才干、自砺品节以报答前辈栽培之恩情的深意。郑獬《乌龙老栽松既以诗三首》其三,“栽松初不为茯苓,自要禅关门径深。禅老一朝飞锡去,不妨留下海潮音”,则从种植者为僧人的特点,由其栽松之举抉发出不妄求食苓长生、惟留下海潮松涛永恒的佛理禅意。
上述唐代到北宋士人松柏种植诗作之精神意蕴,大致呈现出稳中有变、由简单到多样的趋势,并建构起一个颇有意味的士人“松柏世界”。
此外,与一般以松柏为主的咏物诗不同,唐宋士人在被种植松柏身上,在其松柏种植诗作所建构的“松柏世界”中,投射了更多心力和情感,这就使得种植者与被种植者之间更多了一层生命之交感与相生。岑参“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白居易“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柳宗元“青松遗涧底,擢莳兹庭中”,韩维“人皆种花我种柏,为此劲性寒不易”,李复“移松自南山,昔种十三株……对立耸奇姿,秀发动吾庐……清风为我来,飘爽洒我裾”,等等,皆为夫子自道,同时都为这个“松柏世界”注入了更为充沛、亲切的生命色彩与感情因子。
当然,上述这个“松柏世界”中最有风采和韵味的一部分,是属于苏轼的;换言之,苏轼以其深情高才,通过其系列松柏种植诗作,营建出一个独具魅力的“松柏世界”。
二、苏轼“松柏世界”的丰富意蕴
苏轼“性好种植”[7]2578,且不论名品凡类,皆好种植、观赏。这从他植红梅(《谢关景仁送红梅栽二首》)[8]1650、栽不具名之花(《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诗次韵》)[8]1494、求种来自寺院之茶栽(《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8]1089等行止,便可略窥一二。此外,他还喜欢做一些探索性、高难度的园艺试验,如嫁接果树等:“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胶合其罅。予少时颇能之。尝与子由用苦楝木接李。既食,不可向口,无复李味。”[7]2363然而,他最喜种植且常加吟咏的,还是首推松柏一类。苏轼“松柏世界”的丰富意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苏轼亲手种松并对种松要领、松树功用做出总结,将传统意义上的“小人之事”转化为“君子之事”
苏轼(及其弟苏辙)自幼在乡间广种松树,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戏作种松》诗云:“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8]990他又在另一首诗的题目中说:“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8]1807成年后,游宦四方,他依然喜植松柏之类,并将早年积累下的种松之成功经验,形成文字。
十月以后,冬至以前,松实结熟而未落,折取,并蕚收竹器中,悬之风道。未熟则不生,过熟则随风飞去。至春初,敲取其实,用大铁锤入荒茅中数寸,置数粒其中,得春雨自生。自采实至种,皆以不犯手气为佳。松性至坚悍,然始生至脆弱,畏日与牛羊。故须荒茅地,以茅阴障日。若白地,则杂大麦数十粒种之,赖麦阴乃活。须护以棘,日使人行视,三五年乃成。五年之后,乃可洗下枝使高。七年之后,乃可去其细密者使大。大略如此。[7]2361
这段文字将收取松实的时间、分寸,种松之时间、环境,种植以后的养护等事项完整细致地记录下来,具有一定的园艺学价值。出于北魏贾思勰之手、在北宋时期仍然称雄农学著作之林的《齐民要术》[9]205-307对种植各种树木的注意事项早有载录:“凡种树讫,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触突。《战国策》云:‘夫柳,纵横颠倒树之则生,使千人树之,一人摇之,则无生柳矣。’凡栽树,正月为上时。谚曰:‘正月可栽大树。’言得时则易生也。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10]256-257但这些对松柏在内多种树木的种植方法、原则的概述,与上引苏轼种松文字比较起来,则显然粗疏多了。
除种树经验以外,苏轼晚年在海南还对松树的总体功用,有详明论述。
东坡在海外,于元符二年春且尽,因试潘道人墨,取纸一幅书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愈风痹强腰。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酽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上藓,为艾纳,聚诸香烟。其材,产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坚韧冠百木。略数其用于世,凡十有一。不是闲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11]154
据东坡所记,松可养生、照明、制墨、为艾纳、做栋梁等,不一而足,确是“有利于世者甚博”。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宋以前的文化传统来看,种植之事,乃是“鄙事”,是小人之事,是士人、君子羞于做、不屑做、更不肯研究的事情。北宋唐庚的说法很具代表性:“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变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农之判盖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当为。而从学之徒一言及此,则深诋而力排之。”(《策题》其十八《耕读》)[12]10-11于此,笔者论之已详。[13]姑再举几个例子。北魏贾思勰称自己写作《齐民要术》的目的是:“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10]19晚唐五代的韩鄂在其《四十纂要》自序中说:“编成五卷,虽惭老农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9]266二人对写作、传播农艺学著作所表现出的羞怯,依稀可感。但在苏轼看来,种植松树、研究松树,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非但亲手种植,他还将其独到的种松之法,磊落堂皇地传授给别人,并被士林引为君子风雅之事,事见其本人作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离扬州知州任返京拜兵部尚书途中所作的诗作《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见杜舆秀才,求学其法,戏赠二首》以及晁补之诗《东坡公以种松法授都梁杜子师,并为作诗,子师求余同赋三首》。晁诗其二云:“长锥散子岩岩遍,短竹扶条岁岁添。待得烹茶有松叶,不应更课木奴缣。”此诗前两句写细心的种松过程,后两句预想松树长大后就可以享受其泽惠了。诗风轻快典雅,从而赋予种松的“鄙事”以士林风流的气息。由于苏轼自身对于种松之事的亲近,与士林中人对此的认同、吟咏,在一定意义上,“鄙事”就转化为“雅事”了。
要之,种松能活,明松功用,化鄙事为雅事,便是苏轼与松树的第一层关系,亦是苏轼“松柏世界”的第一个方面的精神意蕴。
(二)苏轼知赏松柏之品节,引松柏为心灵上可堪终生依倚的故交
神宗元丰元年(1078)秋冬,苏轼在知徐州任上所作《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云:“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阴。我独种松柏,守此一片心……”[8]855其中一“独”字,可见苏轼为人之秉持高节,不肯随俗俯仰;而种植松柏并与之相守,以此修身进德,更可见他把松柏直接当成了品格高尚的良友。苏轼还说:“青松种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余,气压千亩槐。”(《种松得徕字》)[8]885一棵松对千亩槐,作者爱松远槐,在抑扬之间,那棵松树之高拔伟岸气压凡木的气骨,历历如在目前。
元丰二年下半年,苏轼以“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在狱中,他处境孤危、心情黯淡,以至于写下了类似绝命诗的《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8]975。诗中写到了牢狱之森严冷寂与自己的凄苦无助:“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其二)甚至自度难免一死而与胞弟苏辙诀别:“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其一)在这样孤危悲苦的境遇中,能够给苏轼带来慰藉的,除了少数亲友为之奔走呼告以外,恐怕就是那牢房之外的几棵榆、槐、竹、柏之类的大树了。而在这些树中,苏轼最喜爱且引为挚友的,就是那一棵柏树了。
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幽囚无与乐,百日看不已。时来拾流胶,未忍践落子。当年谁所种,少长与我齿。仰视苍苍干,所阅固多矣。应见李将军,胆落温御史。(《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其四)[8]969
此诗最堪瞩目者有四句。“幽囚无与乐,百日看不已”是明写作者与那棵柏树之间互为知己、相看不厌的深厚关系,而以柏树对作者的温情抚慰为主。“应见李将军,胆落温御史”两句,则以曲笔反映出作者孤苦畏怯的心灵悸动,与对那棵柏树的仰赖依倚之情态。
苏轼不仅在危难之时对松柏之属怀有依倚之深情,在寻常时节亦以之为排遣寂寥之老友、甚至困苦生活中温暖光明的使者。苏轼喜欢桧树,曾在一首诗里对友人赞美汝州桧树的英姿香气。“汝阴多老桧,处处屯苍云……体备松柏姿,气含芝朮熏。”(《和赵景贶栽桧》)[8]1720不惟如此,在苏轼自己到汝州以后,举目无亲亦无友,便直接把此地的高桧老柏,认作了抚慰心灵的知己。“予来汝南,地平无山。清颍之外,无娱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桧柏。自拱把而上,辄有樛枝细纹。治事堂前二柏,与荐福两桧,尤为殊绝。孰谓使予安此寂寞而忘归者,非此君欤也!”[7]2364以文质“殊绝”的“二柏”、“两桧”,为“安此寂寞而忘归”的故人,其间洋溢的人树相亲、风采交映之高情大美,跃然可见。又,哲宗绍圣四年(1097)冬,苏轼及其幼子苏过,谪居海南,暮寒难堪,于是便燃松明以取暖照明:“岁暮风雨交,客舍凄薄寒。夜烧松明火,照室红龙鸾。”(《夜烧松明火》)[8]2184此时的松树,便化作了带给苏轼及其家人温暖与光明的慈心天使了。
概言之,高节相砥,寻常相慰,苦难相依,化异类为故交,就是苏轼与松树的第二层关系,亦是苏轼“松柏世界”的第二个方面的精神意蕴。
(三)苏轼欣赏松柏之属身上所洋溢的生命力和自由意志,并用以涵养自己的心胸
哲宗元祐七、八年间,苏轼任礼部尚书,可谓位高名大;同时,他也深受党争之困扰,对于人生之自由颇多向往。在这一时期,他作有《王仲至侍郎见惠稚栝,种之礼曹北垣下,今百余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诗》一诗。诗云:
翠栝东南美,近生神岳阴……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樊笼中,摧我鸾鹤襟。谁知积雨后,寒芒晓森森。恨我迫归老,不见汝十寻。苍皮护玉骨,旦暮视古今。何人风雨夜,卧听饥龙吟。[8]1871
作者从所种幼栝的“蔚然有生意”,联想到其长大后“寒芒晓森森”的凛然生气,又进一步联想到人生常陷“樊笼”之不自由,曲折反映出作者对于生命自由的希冀及人生苦短的怅惘。苏轼好友范祖禹(1041—1098)在其和诗中说:“苏公沧洲趣,日夕怀山阴。公堂植珍木,寄梦天姥岑。……苍生望安石,出处本无心”(《和子瞻尚书仪曹北轩种栝》),正可为年近花甲的苏轼阅尽世间沧桑、洞悉名利缰锁、返归生命本真的洒落心态,做一条亲切生动的注脚。
还有一个特异却为人忽略之处需要指出,即在苏轼以及其他一些唐宋士人的心中和笔下,松树与柏树、桧(栝)树等同中有异。具备坚贞之风骨是其同,野性则为松树所独具。自先秦到北宋,虽然历代圣贤英杰对松树、柏树、桧(栝)树等都有所称扬,但是相对而言,柏树、桧(栝)树的贵族格调、精英气质要更突出一些;而松树的乡野气息则更浓一些。先看柏树。圣贤、宰相等与柏树、桧(栝)树的文化关联很是密切。人们在成都武侯祠内外多植柏树,杜甫即有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北宋某位宰相也喜植柏树,如前引韩维诗《丞相城上植柏》。再看桧(栝)树。孔夫子曾手植桧树,此桧千古长青,为世代瞻仰,并逐渐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孔门后裔北宋人孔舜亮《手植桧》,对此有生动描述:“圣人嘉异种,移对诵弦堂。双本无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顺,左纽象干纲。影覆诗书府,根盘礼义乡……”韩琦在其《得太清小桧植馆中》一诗中,也称所种桧树为“仙桧”,且“得地最宜儒馆种”。又,在上引苏轼《王仲至侍郎见惠稚栝……》诗中,作者同样凸显了桧(栝)树超凡脱俗的气质:“翠栝东南美,近生神岳阴。”再看松树。虽如前述,松为“百木之长”,然其所宜种植之地,则多为山崖乡野。上引苏轼《种松法》已指出,松树生长最适合在“荒茅地”,且还须“以茅阴障日”。故而,如前所引,王安石是种松于蒋山(即钟山)之野,强至是“野园移植小松”;少年苏轼则“种松满东冈”。既然松树多被种植于荒野之地,也就不免蕴涵了为柏树、桧(栝)树等所少有的“野性”,亦即疏放不羁的自由品质。恰如苏辙所说:“城郭人家岁寒木,桧柏森森映华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尘土辱……”(《种松》)[14]1173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之山野种松,并深研其种法,赞美其功用、品节,便增加了一层对“野性”与其背后之寻常生命及生命自由的深度认同与称扬。同时,这也是对中古以来,人们以松生山野之中来隐喻、感叹英才之被埋没一种反拨,从而体现出一种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唐以降士人思想平民化的时代新变。
简言之,认同松柏之“野性”,称扬寻常之生命,崇尚生命之自由,便成为苏轼与松树的第三层关系,亦是苏轼“松柏世界”的第三个方面的精神意蕴。
三、苏轼“松柏世界”之因缘
上述苏轼所亲近并深情建构的“松柏世界”意蕴丰富,高逸多姿;然则,是何种因缘促其形成并辉光内充呢?下面,从苏轼的童年经验与人格特点两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苏轼童年经验之投射
苏轼生长于北宋成都府眉山县(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一个耕读相济且兼营商铺的小康之家。其父苏洵自云:“昔者倦奔走,闲门事耕田。蚕谷聊自给,如此已十年。”(《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15]461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自然会经常接触到一些种植耕稼的活计。苏轼在其作品中曾经多次自报家门并提及自己的稼圃经历。在知徐州任上下乡劝农时,他曾对村民说“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五)[16]237又如他曾赞美其叔丈说:“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人……》)[8]1580按:此处“识字耕田夫”,本指王庆源,但苏、王两家为姻亲,门户差似,故亦可视为作者自称。又,其弟苏辙《泉城田舍》亦自云:“家世本来耕且养,诸孙不用耻锄耘。”[14]949凡此,都说明苏轼(包括苏辙)是以自己的农家出身自甘的。
在所有稼圃劳作之中,早年的苏轼及苏辙最为喜欢做的,就是种植树木,特别是松树,而且是大规模的种松。诸多诗例已见上述,此不赘。这样一来,苏轼成年后的种植松柏之行为以及其对松柏之观赏,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一种心灵上的归依,用以慰藉、安顿其在宦海浮沉中时常生起的愁苦无助。如其《戏作种松》云:
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朅来齐安野,夹路须髯苍。会开龟蛇窟,不惜斤斧疮。纵未得茯苓,且当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飞霜。槁死三彭仇,澡换五谷肠。青骨凝绿髓,丹田发幽光。白发何足道,要使双瞳方。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8]990
此诗作于苏轼甫出牢狱初到黄州,心有余悸、人无所安之时期。此诗在结构上体现出一个大回环:少年家居种松——离乡宦游想松——贬谪黄州多松——却老延年赖松——最终回乡看松。而这个回环的中心就是家乡,家乡的符号就是松树。在现实条件不允许回乡的情形下,身边的松柏之类,便暂时化作了可以慰藉心灵的微型精神家园。又,在前面提到的《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其四《柏》中的“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幽囚无与乐,百日看不已”四句,也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在“我”家乡,翠柏多有,不以为意;而今我身陷文字狱,孤危无助,对望眼前之柏树,犹如暂时回到了熙熙而乐的家乡,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换言之,在苏轼的“松柏世界”中,投射了他可爱家乡与少年生活的多彩影像。
由上可见,苏轼是以出身乡野、幼事稼圃自甘的;他成年离乡以后回忆中的家乡世界与少年生活(包括种松),化作了他毕生珍藏心底的精神故园;在这个精神故园中,“松柏世界”无疑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这种家世与童年经验,在苏轼心底种下了“野性”的种子。
(二)苏轼人格境界之折光
由前所论可以推知,苏轼“松柏世界”中隐含的人文品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坚贞,二是自由。坚贞者,则是秉持素志,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自由者,由自也,一切行动都由自己的心灵来决定。前者重在始终不渝,表现为一种刚正的气概;后者重在随心变化,表现为一种疏放的襟怀。综观苏轼的一生行止,坚贞与自由兼有,刚正气概与疏放襟怀并存。对此,自宋迄今,论之已详[17];兹稍作撮述,聊为文章推演之津梁。
先看苏轼的坚贞品节与刚正气概。这主要表现在苏轼的政治品格,即“立朝大节”方面。早在少年时期,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14]1117。迨其步入政坛后,多以社稷苍生为念,为官地方,恪尽职守。他曾灭蝗于密州,抗洪于徐州,浚湖修堤于杭州,赈灾荒于浙西,即使在晚年南迁的途路中,还帮助所经地方改良农具和引水方法。不惟如此,他在朝堂之上,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修正,更是很少考虑自己仕途之得失,每每秉公直言。在神宗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18]10802;稍后,更陷“乌台诗案”,几至于死;经多方救济,才被宽大处理贬谪黄州。但到哲宗元祐年间返京任职以后,他又因部分新法之存废问题,与宰相司马光发生激烈争论,惹得“光忿然”[18]10802。后来,由于在政治上坚持己见,而与当权者不合,乃有白发南荒之贬。职是之故,无论当时后世,赞之敬之者颇多。其弟苏辙评价他:“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南宋陆游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19]177现代文化巨匠林语堂称苏轼“是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20]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与苏轼同时代的政治异见者,也赞扬其立朝大节,如司马光弟子、朔党人物刘安世即是一例:
刘元城先生云: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温公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惟己之是,信是他浩然。[21]532
然则,这般立朝大节所从何来?如何养成?苏轼自己的回答是:“轼受性刚简。”即“我”天生就是一副刚正不阿的脾气,想改也改不了的。试想,这与松柏之属自然而然的凌寒不凋的坚贞气质,何其相似乃尔!
再看苏轼的自由意志与疏放襟怀。 苏轼之自由意志与疏放襟怀,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对自然的亲近与对人为束缚的冲决,这是一种元气淋漓的生命力的表征。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野性”和“狂”[22]19-25。“野性”一词,两见于苏轼诗文。其《游卢山次韵章传道》诗云:“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出入岩峦千仞表,较量筋力十年初。”[8]590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都下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7]1809前者中的“野性”,偏于行为举止的疏放不羁;后者中的“野性”,则重在对强调对山野生活的缅怀与向往。有研究者指出:苏轼的“野性”,是一种“生于泥而不染,超脱社会的束缚与礼法的拘忌之人生态度,以超脱环境来超越自我而完成精神上的自由和心灵上的解脱”[22]20。不为无见。但是,没有看到“超脱”、“解脱”等表象下,激荡着的充沛生命力。苏轼还经常在笔下标举自己的“狂”:“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登云龙山》)[8]852“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密州出猎》)[16]146“且趁陈闲身未老,且放我,些子疏狂。”(《满庭芳·蜗角虚名》)[16]458文同《往年寄子平》一诗对苏轼壮年时的狂放情态有生动描写:
往年记得归在京,日日访子来西城。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喧呶歌诗嘂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更呼老卒立台下,使抱短箫吹月明……[23]5429
按:“诗中子平,即子瞻也。”(文同《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四首·月岩斋》所附家诚之注[23]5371)苏轼此字用得极少,也很少被人称呼。[24]5盖仅在早年用过一时,惟当时亲友(如表兄文同)知闻。又,“嘂”,古同“叫”,高声大呼。文同与苏轼是表兄弟关系,少年乡居时即常在一处游玩。两人异乡聚首,自然任情谈笑,仿佛回到四川老家一般;尤其苏轼,掀画壁、脱帽子、高声吟诗诵文、寂静夜月偏吹箫,真是狂放之极,一时竟然有点像后世小说中回到花果山的孙猴子。可见,苏轼所说“狂”,与前述“野性”,其实是同一个意思。而苏轼的这般“野性”,与前述他家乡山野中所种的千万棵松树之“野性”,又何其相似乃尔!
通观上述,苏轼出身乡野、喜种松柏尤其是松树的童年经验,与其坚贞品节与疏落襟怀等个性因素融于一处,使他平生对松柏之属亲近有加,并通过自己的诗笔建构起一个意蕴丰富、高逸多姿的“松柏世界”,并使之成为一个慰藉、安顿自己灵魂的精神故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松柏世界”并未因苏轼本人的辞世而消失,它在仰慕、承继苏轼深情逸气的后代人心中生生不已。谢薖(1074—1116)《种松》:“胡不种杞柳,但种青青松。念汝受命独,劲气凌三冬……唯当护以棘,养视如婴童。此法岂浪传,闻诸玉局公”;刘克庄(1187—1269)《寄题惠州嘉祐寺坡公手植枞树》说:“谁道炎州无劲植,君看韩木与苏枞。”孙蕡(1337—1393)《灵洲》:“坡老留题空断碣,德云种柏满幽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