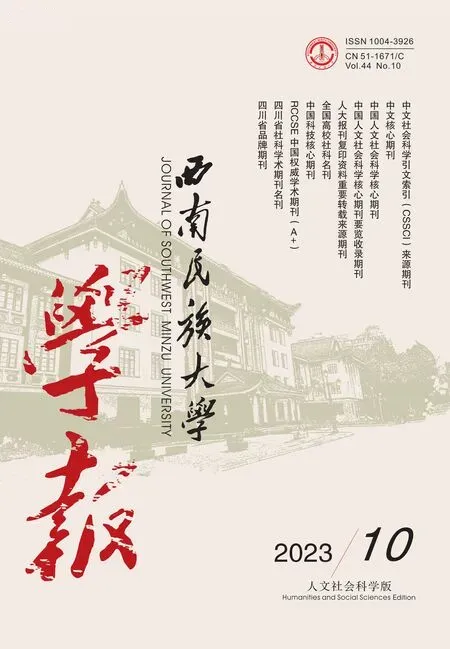跨学科融合:风景研究的历史逻辑与当代路径
颜水生
[提要]20世纪后期以来,风景研究突破艺术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等传统学术范型,成为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关键性概念。风景概念呈现四种解释模式,即风景分别作为艺术类型、存在方式、空间形式和观看方式。风景的叙事分析和美学阐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和差异,风景并非只是一种现代性叙事,风景审美意识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密切相关。风景研究十分重视风景的批判作用、认同价值和影响因素,以及风景的文化生产作用、文化政治价值和文化阐释功能。跨学科融合是风景研究的最重要特征,风景的概念界定、叙事分歧和研究路径不仅展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美学阐释和知识生产的多样化,也促进了人类对自我、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20世纪后期以来,风景研究突破了艺术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等传统学术范型,风景被纳入到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进行探索,风景研究也向着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靠拢,围绕“风景”而展开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谱系,繁荣的学术态势凸显了全球环境危机并影响了当代世界的社会认识和文化认同。国外学者米切尔、萨义德、达比、沙玛等发表了一系列著述,他们注意到风景研究不是单一学科范畴,而是一个涉及多种内涵的跨学科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风景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下国内学术创新的重要增长点。风景的概念界定、叙事分歧和研究路径不仅展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美学阐释和知识生产的多样化,也促进了人类对自我、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一、概念界定与思维模式
“风景(Landscape)”是一个舶来的学术概念,它与中国文化中的“风景”概念大相径庭。“风景”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辞源》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经典寻找“风景”一词的起源,认为“风景”一词有两种意思:“风光,景物。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候(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犹言风采。晋书刘毅传石鑒等举毅奏:‘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1](P.3408)从《辞源》引用的例证可以看出,“风景”是指自然的“风光,景物”,也可以指人的“风采”。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风景”一词是指“供观赏的自然风光、景物”[2](P.382)。从这些词典的解释来看,“风景”一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大都是指自然的风光与景物,可供观赏性(即客观存在性)是其必要属性。实际上,“风景”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概念,来源于英语landscape的翻译。“风景”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被译为英语Landscape,而Landscape在《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中被解释为“natural or imaginary scenery ,as seen in a broad view”[3](P.1138), Landscape在广义角度上被认为是自然性或想象性的风景,即包含“自然性”和“想象性”两种属性,这也说明了“风景”与Landscape在内涵与外延上并不完全等同。即使如此,国内学者也大都把Landscape译为“风景”,比如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就把LandscapeandPower、LandscapeandIdentity和LandscapeandMemory等外文著作中的Landscape都译为“风景”,这些翻译意味着“风景”的学术内涵大多来源于Landscape。风景一直都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风景”引发的学术思考不仅涉及艺术,而且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阐释。风景作为学术概念在历史上大致有四种界定方式,分别体现了四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知识体系。
首先,风景是一种艺术类型。风景作为学术概念最早是在关于风景画的分析中产生,里尔克在《艺术家画像》中就认为风景画是风景的起源,他还强调“风景的发现恰恰是更重要的发现”[4](P.274-275)。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杰克逊也提到了这种情况,他在DiscoveringtheVernacularLandscape中分析风景的起源时指出:“这个词首次(或再次)被引入英语时,它并非指风景本身,而是指风景画——艺术家对风景的诠释。”[5](P.3)英国学者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从词源上考察风景在英语、荷兰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中的最初内涵,除了德语没有明确指向风景画,荷兰语和意大利语都明确指向了风景画,而英语Landscape本是由荷兰语转化而来,因此英语Landscape的内涵与风景画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个方面来说,风景画是风景概念的起源,风景画是西方学术对风景的最早诠释。《美国大百科全书》详细概括了风景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征,其中对词条Landscape的解释是:
“风景,是艺术中的一种形象,其主题是自然世界观,这种自然世界观依据空间、大气或植被来描述特征。它可能是一个广阔的全景或自然的一个小角落。它可以直接依据自然或记忆来描绘,有时也可以借助于现场的草图。风景可以描绘一个记录了极端客观的或由理想主义转化而来的真实地点。风景也可以是一个由不同场景组合的情境,或者是一个与特定学校或艺术家有关的程式。艺术家自己的经历对他选择的主题有很大影响。因为都市景观和风景都关注门外,所以人类形象可能会被看作是次要因素或戏剧性焦点”[6](P.707)
这段话也可以说是风景画的概念。《美国大百科全书》概括了风景画的形式、内容和历史。从形式方面来说,艺术家运用技术创造风景画,以表现世界上的视觉和物理现实。从内容方面来说,风景画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及其对工作、娱乐和生存的影响。从历史方面来说,在古代世界和近代西方,风景画主要为英雄或宗教场景提供背景。20世纪,抽象派和表现主义绘画比风景画吸引了更多关注,与西方风景画的世俗性和大众化不同,中国风景画通常表现了对自然的深刻崇拜,并不断享受了“崇高的自尊”[6](P.707-708)。《美国大百科全书》概括了风景画的概念、艺术特征和发展历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风景概念的解释,从这个意义来说,风景概念可以看作是一个艺术问题或美学问题。从艺术角度或美学角度来研究风景或解释风景概念在西方历史悠久,英国学者恩斯特·贡布里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的兴起》中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分析风景的艺术历史和美学内涵,英国学者安德鲁斯曾经上溯到18世纪分析风景的美学起源,他认为西方风景艺术中存在一种如画美范式,安德鲁斯在《风景与西方艺术》中探讨了风景概念的形成方式,着重分析了风景概念的艺术历史及美学内涵。由此看来,风景作为艺术问题或美学问题是西方风景研究中最重要的传统。
其次,风景是一种存在方式。众所周知,风景画是一种古代遗产,但风景概念并没有与之同时产生。《美国大百科全书》就明确指出风景画在古代世界就已出现,而风景概念的出现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法国学者卡特琳·古特在《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中考察了风景在欧洲语言中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演变,并明确指出风景概念的出现是在15世纪,从语言角度来说,风景起源于欧洲语系中的土地(Land)或地方(pays),表明风景与土地的密切关系,而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是人类和所有文化最原始的元素”[7](P.2),因此,风景是人类文化的表现,也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表现。风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画中扮演的角色是由风景在当时思想中的地位所决定,安德鲁斯认为“这个时期的风景按照传统仅仅扮演着一个辅助性的角色”[8](P.37)。在现代时期,人类的生存方式大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对风景概念的阐释也产生了重要差异,古特甚至认为现代时期的风景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根本不同。风景关系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每处风景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每处风景(艺术的或自然的)都体现了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每处风景也都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古特认为“风景也表达了我们和世界、和他人,甚至是和我们自己的关系。”[7](P.2)古特探索了一条思考风景的独特思路,他重视风景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他强调“风景就是存在于世界的方式和状态”[7](P.158)。古特对风景定义的分析是风景概念史上的重要变革,他把风景从艺术问题(美学问题)中解放出来,把风景看作是一种存在方式,强调了风景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最终使风景概念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学问,成为一种关于存在的学问,从这个意义来说,风景概念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哲学问题。
再次,风景是一种空间形式。风景概念由艺术到哲学的变革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发展,但是哲学并非风景概念发展的唯一途径。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成为人类知识生产的重要潮流,空间理论为风景成为空间问题创造了条件,杰克逊和米切尔在这个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尤其是沙玛认为杰克逊“对风景进行了革命性阐释”[9](P.759)。杰克逊在DiscoveringtheVernacularLandscape中对Landscape作了一个独创性的定义,他认为Landscape“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杰克逊强调Landscape“意味着人类承担起时间的角色,创造人类历史。”[5](P.11)杰克逊把Landscape看作是一种空间形式,而不是艺术类型,他认为Landscape是一种主观性空间,它由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服务,并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杰克逊把Landscape界定为一种具有独特地理和文化特征的永恒空间,体现了空间转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虽然Landscape有时候被译为“景观”,杰克逊也强调了Landscape与Scenery的区别,但杰克逊对Landscape的定义仍然对风景概念的阐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正是在杰克逊观点的启发下,美国学者米切尔提出了一个崭新看法,他指出:“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地方的景色”[10](P.2),他把空间、地方和风景看成是一个辩证的三位一体的概念结构。米切尔批评戴维·哈维、加斯东·巴什拉和马丁·海德格尔对风景的忽视,他从德·塞图的二元分析和列斐伏尔的三元概念结构中发展出辩证的三位一体的概念结构,强调风景“总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10](P.2)。杰克逊和米切尔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概念,他们把风景看作一种空间形式,从而使风景概念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空间理论问题。
最后,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无论风景是作为艺术类型,还是作为存在方式和空间形式,风景都被看作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对象。然而,在风景概念的历史长河中还存在一条主观思路。安德鲁斯在《风景与西方艺术》中特别强调了英国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关于风景是一种由特殊历史和文化力量决定的“观看的方式”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上溯到1938年勒内·马格里特在《人类境况》的讲座中宣称“这就是我们看世界的方式”[9](P.11)。所谓“观看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认识方式,那么风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而且还是一种主观形式。在风景作为主观形式的概念演变过程中,从伯明翰《风景与意识形态:英国乡村传统,1740-1860》到希拉里《风景:想象世界的方式》再到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都提出了相似观点,伯明翰认为风景是一种话语的意识形态,希拉里认为风景是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达比则认为风景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11](P.12)。
风景概念从艺术类型到存在方式再到空间形式的演变,从客观思路到主观思路的探索,不仅体现了风景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也体现了人类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在历史上,风景概念多种多样,正如杰克逊所说:“这个词本身很简单,我们似乎都能理解,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涵义又不尽相同。”[5](P.3)人类生存方式不断演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风景概念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
二、叙事分歧与美学阐释
学术界不仅对风景概念有着多种阐释方式,对风景叙事及其起源也存在几乎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科立场使风景的叙事和审美认识存在明显分歧和差异。在欧洲文学史上,风景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从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到贺拉斯再到托马斯·哈代和华兹华斯,一直存在着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书写,阿卡狄亚甚至被认为是欧洲文学的重要母题。然而,齐美尔在《风景的哲学》中认为“古代和中世纪时对风景没有感觉”[12](P.106),这种观点在中国也存在,从胡适到陈平原等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缺乏独立的风景审美意识,强调风景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以萧驰和曹文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有独立的风景审美意识,萧驰的专著《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就明确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存在独立的风景审美意识,强调自然风景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表达。正如《美国大百科全书》在追溯风景画的起源时特别强调了中国因素,曹文轩在《小说门》中发掘风景的起源时也强调了中国传统,他试图从中国古代小说寻找“风景之发现”的起源。实际上,中国古代不仅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风景的作用,也有大量作品精细描摹风景,全面展现了风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
自然是一切风景的源泉,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决定了艺术作品中风景描摹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周易》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开创了中国传统的“观看之道”。《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周易·咸卦》提出的“物感”也强调了观看的重要作用,“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3](P.182)《周易》中的“物”包蕴天地万物,“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然;“感”既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交感,又是人对天地万物的感应,由“物感”和“感物”而见天地万物之情和宇宙自然之理,而“物感”与“感物”的条件或途径就是观看/观察,“物感”与“感物”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观看之道。“物感”说对中国文学写景产生了深刻影响,刘勰把“物感”融入了《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4](P.56)这不仅强调了自然是感物的必要条件,而且指出“吟志”是感物的目的。刘勰以“物感”说为基础创作了《物色》,集中讨论了诗歌中景物描写的方法:“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4](P.415)刘勰进一步总结了《诗经》《楚辞》《离骚》中的写景方法,认为文学创作应该“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14](P.417)。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认为文学写景要“真力弥满”,陆机《文赋》提出“瞻万物而思纷”的观点,这也就是说情感源于物感,物感源于自然。“物感”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物感”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描写风景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不仅对文学风景理论有过深入探讨,文学创作中也存在大量的风景描写。风景叙事在中国文学中历史悠久,《诗经》《楚辞》《山海经》可谓典型代表。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如果说《红楼梦》“为后世中国小说在风景描写方面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经验”[4](P.276),那么《诗经》在美学方面的贡献更加具有开创性,《诗经》可以看作是中国风景叙事和风景美学的起源,无论是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是展子虔的《游春图》,都与《诗经》渊源极深。《诗经》中的风景大都可以说是“元风景”,《诗经》开创了中国风景叙事的重要源头,奠定了中国文学乡土风景的美学传统。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在中国文化中,风景都与土地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土地是风景的基础或起源。杰克逊在考察“landscape”的词义时,着重分析了音节“land”的涵义,“它被引入英格兰时,表示土地、土壤或地表的一部分。但是一个较早的哥特式意义指‘犁过的地’(plowed field)。《简氏德语大字典》指出,‘land’最初指田野中每年轮作的一小块土地。”[5](P.7)杰克逊引用了“land”的古老定义,突出土地在“landscape”中的地位,强调“landscape”是“土地的集合体”[5](P.9)。托马斯·布朗特在《词汇注释表》中也把风景看作“是一种对土地的表述”[8](P.39)。作为农业文明国家,土地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是“占着最高地位的神”[15](P.10),乡土性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和美学的发展,也决定了风景叙事的起源与发展。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15](P.136),土地条件决定了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审美方式。中国农民离不开土地,“‘土’是他们的命根”[15](P.10),他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诗经》把乡土风景诗意化、浪漫化。一方面,《诗经》中的风景叙事体现的是一种根植于土地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诗经》中的风景叙事促进了先秦时期中国农民的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发展,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审美意识和想象能力,使他们能够看见自然的面容,能够想象自己的家园,能够憧憬更加美好的世界。从文学史角度来说,《诗经》培养了中国文人的乡土审美意识,中国古代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兴盛就是这种乡土审美意识的重要表现。自《诗经》以后,风景叙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山川、江河、森林、草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风景叙事的重要对象,比如《楚辞》对江河风景的描写,《山海经》对山川风景的描写。《春江花月夜》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诗词风景描写的经典,诗歌中展现的独立的风景意识,即使是现代诗歌也都望尘莫及。如果说《诗经》描绘的乡土风景,体现了风景的审美内涵,那么《东京梦华录》中的城市风景,集中体现了风景的社会内涵。《东京梦华录》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城市社会文学作品的开创之作”[16](P.2)。《东京梦华录》描绘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开创了中国文学通过城市风景展示权力意识形态的先河。皮雷纳认为12世纪的城市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集体法人”[17](P.133),《东京梦华录》同样展现了12世纪中国的城市风景,但东京并非“集体法人”的象征,而是天子皇权的象征。一般来说,城市风景往往表现了社会分工与阶级对立,比如皮雷纳就明确指出,“在城市中两种并存而不融合的居民之间,暴露出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立”[17](P.107)。虽然《东京梦华录》通过街巷坊市、店铺酒楼等的描绘,表现了12世纪中国的社会关系,甚至表现了市民百姓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但是在古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远没有欧洲那么明显,比如同样产生于12世纪的《清明上河图》更是表现了东京城市与周围乡村的和谐统一。乡村与城市是人类的居住空间,它们展示的风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在整个宇宙中,有很多客观的自然世界是人类无法接触和实践的,人类只有通过思维去想象和思考。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墨客面临江河大海,却对日月星辰进行想象和思考,以此表达他们对自然宇宙的看法。乐府诗《长歌行》和曹操《观沧海》揭示宇宙永恒而青春易逝的自然哲理。谢灵运的风景哲理诗描绘极美图景,想象山河日月,揭示自然规律。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表达他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思考,并感慨个体生命短暂渺小,揭示宇宙神奇永恒的自然哲理。人类无法到达和实践的空间才能称之为纯粹自然,但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类似乎越来越难以发现、找到纯粹自然。从理论上说,客观自然成为风景之后,它就已经不再是客观的自然风景,因为风景已经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作品中的江河湖海都是一种主观风景,蕴含了作家的审美追求,借以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思考和对宇宙的探索,这意味着“风景,作为自然的物质形态的肖像,也可以行使将抽象概念实体化的功能。”[8](P.18)
中国古代文学的风景叙事并非缺乏明确的风景意识,也并非没有把风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风景的起源”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正如曹文轩所说,《红楼梦》可以看作是小说中风景描写的经典,即使是现代小说也大都从中吸取经验。因此,如果把“风景之发现”看作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分水岭”,“把‘风景描写’看作一种‘现代叙事’”[18](P.18),那么“风景之发现”就完全被现代性叙事所遮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文轩从《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寻找“风景之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使现代性的断裂叙事暴露了历史性危机。古代中国对“风景之发现”的认识也证明了“风景”并非只是一种现代性叙事,历史上最早提出“赋比兴”的《周礼》就涉及到了风景与叙述的关系,后人对“比兴”的阐释也大都涉及到了风景对叙事的作用。《文心雕龙》也多次谈到了风景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4](P.250),强调了风景与主观情感的融合,突出了风景与文学想象的密切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分析了意境与写景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9](P.26);他把写景看作是构成境界的必要条件之一,认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19](P.38)。王国维揭示了文学作品中风景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关系,强调了风景作为独立审美对象而具有的审美内涵和艺术价值。
无论是从“风景之发现”的文学叙事来看,还是从“风景之发现”的美学阐释来看,风景并非只是一种现代性叙事,风景也并非可以看作是“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学与风景之间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即使纵观整个中国文学,风景大都可以看作是独立的审美对象。风景由来已久,但又常常被遮蔽了,现代性叙事为了突出自我的现代性,有意遮蔽了“风景之发现”的传统元素和审美起源。
三、研究路径与知识生产
风景概念的多样界定、风景叙事及美学阐释的分歧,表明风景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问题,当代风景研究也呈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当代风景研究以文学风景作为主要对象,同时涉及到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多种学科,风景研究充分挖掘了风景的文化生产作用、文化政治价值和文化阐释功能。风景研究也是人类知识生产过程,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对自我、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首先,从文学发展变迁中透视风景书写的特征与价值一直是风景研究的主要对象。一,文学风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用是文学风景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雷蒙·威廉斯在欧洲文学中透视了风景书写的意识形态价值,威廉斯的专著《乡村与城市》研究16至20世纪英国文学中的风景,把文学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密切结合,把乡村与城市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揭示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从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二,安德鲁斯和安东尼·阿韦尼更多的是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中的风景书写,揭示风景与西方文学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安德鲁斯的专著《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从维吉尔、贺拉斯的牧歌传统中揭示风景之发现在英国诗歌中的特征与价值,认为乡村的隐居和牧歌情调反映了对伊甸园、黄金时代生活方式的向往。安东尼·阿韦尼的专著Creationstories:landscapesandthehumanimagination讨论风景在人类讲故事中的作用,他认为风景不仅是人类环顾四周时看到的东西,也是土地、天空和人类的复合体,风景与故事可以共同作为政治、历史、社会关系和生活观念的一种解释方式。三,柄谷行人和托尼·芬查姆主要分析风景与人类心理之间的关系,柄谷行人的专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从心理角度阐释风景写作在日本文学中的特征与价值,强调了风景与人类心理和社会认识之间的密切关系。托尼·芬查姆的专著Hard`slandscaperevisited:ThomasHard`sWessexinthetwenty-firstcentury认为哈代作品中的风景提供了关于存在的可变性和短暂性的默契,哈代作品中的风景是一种心灵的风景。四,文学风景的认同作用也得到了深入研究,比如阿尔弗雷德·卡津的专著Awriter`sAmerica:Landscapeinliterature从浪漫特征、地方色彩、权力表现等方面讨论霍桑、爱默生、惠特曼、福克纳、梭罗等作家作品中的风景,他认为自然不仅是美国的梦想,也是美国文学的中心形象,文学作品中的美国形象使没有任何共同点、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内部形成了一种团结一致的东西。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著作Spiritofplace:ThemakingAmericaliterarylandscape讨论美国文学风景的书写历史,认为风景在文化认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风景在艺术中的作用是让人们在情感上参与到生活中来,从而获得情感认同。斯文德-埃里克·拉森的论文landscape,identityandwar认为文学中的风景总是集体身份的一种象征。罗格·爱伯斯坦的著作《想象的英格兰:民族、风景与文学》也对风景的认同功能提出了看法,认为文学风景是想象英格兰的重要方式。这些研究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学风景书写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作用。五,文学风景的影响因素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马修·约翰逊的专著Ideasoflandscape是一部风景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认为英国风景传统的思想基础源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当前的风景研究与当代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约翰·诺特的专著ImaginingtheForest:NarrativesofMichiganandtheUpperMidwest讨论了美国文学中的森林风景,认为森林作为咆哮的荒野和森林作为神圣的天堂在19世纪经历了蜕变,与森林相关的美学价值观也随着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发生蜕变。罗伯特·E·艾布拉姆斯的专著LandscapeandIdeologyinAmericanRenaissanceLiterature讨论美国文学中的风景和空间感,认为美国作家的风景想象受到美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约翰·苏塞兰德的专著LiteratureLandscapes:ChartingtheWorldsofClassicLiterature考察19世纪至今的世界各国的文学风景,认为任何“风景”都与人类的存在、目的和特质密不可分,任何风景都是地方和人的综合,风景的创造不仅依赖于地理上的物理细节,还依赖于共同的习惯、习俗和价值观等一系列社会行为。关于中国文学风景话语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深入讨论了文学风景的批判作用、认同价值和影响因素。从中国文学变迁中考察风景书写的特征与价值,并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风景描写与古代文学的风景描写之间的重大差异,强调风景话语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发展,是中国文学风景研究的重要特征。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具有重要影响,不仅有日本藤田梨那、中里见敬和韩国朴昶昱、薛熹祯等学者借鉴柄谷行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而且有程光炜、吴晓东、李建军、朱羽、傅元峰、郭晓平等中国学者借鉴了柄谷行人的理论与方法,比如张夏放的专著《旗帜上的风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从柄谷行人的观点出发揭示中国现代小说风景话语的隐喻、象征以及意识形态功能。风景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风景研究有助于揭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功能,也有助于揭示作家作品的内在心理机制和意识形态价值。
其次,风景研究不仅在文学领域得到重视,也渗透到了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一,在文化地理学领域,迈克·克朗和段义孚等学者揭示了风景的环境因素和地理价值,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认为地理风景不仅具有个体特征,也反映了社会的信仰、实践和技术;地理风景不仅反映人类的宇宙观,也体现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秩序。段义孚的Romanticgeography:insearchofthesublimelandscape讨论了浪漫主义与地理学的关系,认为风景不仅构成了浪漫地理学的核心,而且影响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感觉和判断,还影响人类想象和体验巨大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二,在文化人类学领域,西蒙·沙玛和段义孚等学者深入揭示了风景的情感价值,西蒙·沙玛在专著《风景与记忆》中勾画风景隐喻的悠久历史,认为风景神话具有惊人的持久力和强大的影响力。段义孚在《风景断想》中认为风景是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认为恋地情结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情感,人类在地方风景中不仅获得审美愉悦,而且建立了难以磨灭的恋地情感。三,艺术学领域的学者重视风景的文化阐释功能,如马乔里·万贝林赫姆的论文LandscapeasReflectioninBritishContemporaryArt从山水画角度考察风景在英国当代艺术中的位置和功能,认为风景是当代英国艺术家发展新思想的工具、手段和反思场所。安·伯明翰的LandscapeandIdeology:TheEnglishRusticTradition(1740-1860)考察从1740年到1860 年英国山水画黄金时代的风景画,他认为艺术的历史是思想的阐释过程,风景画的阶级观点体现了一套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嵌入被表征的对象中,而且嵌入社会代码或表征体系。四,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重视风景的文化生产作用,比如詹姆斯·邓肯的论文Landscapetasteasasymbolofgroupidentity:westchestercountyvillage认为风景品味是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的群体认同的重要指标,社会群体的网络边界与风景品味的边界密切相关。又如达比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认为风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仅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的宝库,也是文学和艺术的根源,风景深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论文集《风景与权力》的主编米切尔认为风景可以被译解为各种文本系统,风景不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也是文化权力的工具;风景作为文化中介具有双重作用:风景把文化和社会建构自然化,把人为的世界再现成必然的结果,风景是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交换的媒介。五,政治学领域的学者重视风景的文化政治价值,马丁·沃恩克的专著PoliticalLandscape:Thearthistoryofnature认为政治风景不仅不会损害人类对风景的欣赏和感知,反而增强人类对风景的欣赏和感知,风景是人类的避难所,人类可以在风景中体验到经济、社会或私人世界中被忽视、被压制或被遗忘的东西。在风景的文化政治价值中,风景作为民族国家的想象方式无疑是讨论最多的话题,如卡特琳·古特在《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中认为风景可以唤起国家意识,风景代表某一个地区或国家象征性的影像。孔莉莉和杨永强合著的《新加坡的风景政治:国家的建构》认为风景在新加坡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风景在“国家”和“民族”的构建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学者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也都对风景的国家想象功能发表了看法。风景的文化生产、文化阐释和文化政治功能在中国学术研究中也得到了重视,张箭飞、蔡翔、沈杏培、黄继刚、郭晓平、杨辉等学者把风景看作是一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强调风景具有丰富的文化生产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如厉梅的专著《塞下秋来风景异: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认为风景描写带有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风景的文化阐释关涉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身份意识。
最后,从理论上探讨风景的丰富内涵与意义,从而建构风景的诗学体系也是当代风景研究的重要思路。风景诗学建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从哲学美学角度讨论风景的理论内涵,比如齐美尔在《风景的哲学》中认为风景是在人类宇宙观最终形成的基础上产生,为风景的哲学建构提供了概念基础。美国学者史蒂文·布拉萨的专著Theaestheticsoflandscape从审美对象、审美经验、审美规范等方面讨论了风景美学的理论体系,为风景诗学的体系建构积累了重要经验。约翰·威利的专著Landscape考察了风景研究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方法。二,从关系角度讨论风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如卡尔·贝内迪克松和安娜·隆德编著的ConversationwithLandscape创造性地提出将人与风景视为一种对话关系,他们不仅把风景从浪漫和静态的地方联系起来,而且提出了视觉的重要性,将风景视作为人类感官接触的一部分,他们从现象学哲学、人类学、美学、视觉艺术角度探讨人类与风景的关系,为风景研究拓宽了思路。保罗·谢帕德的专著Maninthelandscape:ahistoricviewoftheestheticsofnature揭示了风景与人类的关系,讨论了自然美对人类的重要性。克里斯·菲特的著作Poetry,Space,Landscape:Towardanewtheory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和历史理论解释“风景”概念的兴衰,强调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决定了对自然、现实的不同理解。莱恩·比格斯的论文Recoveringlandscape:anartbetweenseeingandhearing认为风景是一个复杂的包括视觉、听觉和嗅觉的感官编织方式,风景可以触摸到社会组织和人类经验。马克·罗斯基尔的著作Thelanguagesoflandscape认为风景是人类在世界上的具体物理经验和从这些经验中产生的对事物的理解,风景构成了社会意识的一个根本方面,风景唤起了人类冲动、情绪和调节或控制意识的模式,这些模式与人类使用的各种语言和视觉表达形式相关联。三,从历史角度讨论风景理论的发展过程,如英国学者莫尼卡·雅洛夫斯基和蒂姆·英戈尔德编著的Imagininglandscapes:Past,PresentandFuture讨论了风景想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风景的诗学建构奠定了历史基础。杰夫·马尔帕斯编著的Theplaceoflandscape:concepts,contexts,studies和詹姆斯·科纳和艾莉森·比克·赫希编著的Thelandscapeimagination:collectedessaysofJamescorner1990-2010以及西蒙·斯瓦菲尔德编著的Theoryinlandscapearchitecture:areader等论文集讨论了风景理论的起源、本质、内容和研究方法。此外,霍华德的《风景导论》《风景研究指南》等著述也对风景研究的多样内涵与形式进行了探讨。程虹、张箭飞、黄继刚、代迅等国内学者对风景的诗学建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丁帆在著作《人间风景》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记载了对风景的观察和思考,从哲思、人性和审美三个方面构建了一种学者型的“风景诗学”[20]。正是这些不同学科的风景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风景的认识,为风景诗学建构奠定了研究基础,也促进了人类对自我、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结 语
作为人类思维和想象力的产物,风景不仅能够唤起自然并参与自然建构,而且能够促进人类的文化建构。风景阐释模式、叙事分析和研究路径的差异性与多样化,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目的。作为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风景研究不仅要突破单一学科的阈限,而且要超越欧美现代性资源的理论阈限,还要重视风景的传统性、历史性以及风景研究的方法论,才能建构系统的风景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