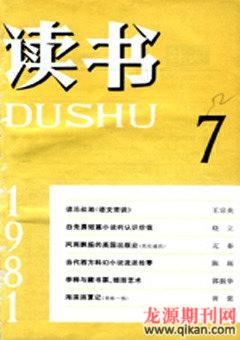读吕叔湘《语文常谈》
王宗炎
吕叔湘先生的这本近著,看体积是一本小书,看内容却不下于一本大书。把汉语语言学的主要问题用六万多字概括起来,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晓畅,这需要长期的酝酿、深入的发掘和艰苦的锤炼工夫。
依我看,这书是有明显的目标的。它提倡文字改革;它说明应当采用拼音文字;它给推广普通话扫除了一些障碍;它明确地提出,既要重文(文字),也要重语(语言)。作者似乎觉得,这些事情要做,就好象应该戒烟,应该从事体育锻炼一样——可是有不少人就是照样抽烟,又不肯去跑步或打太极拳。
但是这书也不是单纯宣传文字改革的。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语言,又谈文学;既谈现代汉语,又谈古代汉语。作者掌握了大量生动有趣的事例和材料,有的是读书心得,有的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娓娓而谈,津津有味。即使你并不关心文字改革,读了这书也会增加许多有用的知识,对中国语言文字能进一步地理解和欣赏。
对于搞普通语言学或外国语的人,这书又别有其吸引力。作者没有引经据典,可是深入浅出,论证详明,给我们指点出语言研究的一些窍门。他撇开枝节,抓住重点;不从理论出发,而从事实出发。他通过对比中外语言,力图摸出汉语的真正特点。有些议论,看似平淡无奇,因为作者是那么安详平静,不动声色,可是细想一下,其实是挑战性的。
一
没有语言是否就没有意义?意义依赖语言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思维是否必须通过语言?有人说,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可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
作者当然研究过斯大林的语言理论,可是对于科学家,观察事实重于背诵经典,或者说客观事实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作者的意见是:“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的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又比如人们点点头,招招手,也都可以传达一定的意义,可见不是离开语言就没有‘意义。”(62页)这些话十分使人信服,分明讲到了体语(bodylanguage),即思维有时可以离开语言,不用语言来表达,不过不使用语言学术用语,不引用外国学者的话为自己张目而已。
第四章谈汉语语法特点,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作者指出,次序不同,意义也就不同。“‘一会儿再谈是现在不谈,‘再谈一会儿是现在谈得不够。”(47页)这讲得很好,头一个“再”是然后的意思,第二个“再”是继续的意思。“‘三天总得下一场雨,雨也许是多了一点儿,‘一场雨总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47页)这也讲得好,前面那个“三天”是“每三天”,后面那个“三天”是“三天之久”。我由此想到,次序不同,词义、句义也就不同,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如此复杂的关系,Chomsky能否用什么公式表示出来?
在谈汉语语法时,作者“下决心不搬出主语、谓语、宾语”等等,我赞成。说实在的,我猜(当然不能肯定)对于中国学生,多讲这些东西未必有用,提一下就可以了。讲英语语法不能不讲主、谓、宾,因为英语谓语动词要跟主语的人称和数取得一致,人称代词充当宾语要用宾格,动词充当宾语又只能用-ing形式。汉语语法是否要大讲而特讲这些玩意儿呢?我有点怀疑。
如果学生只读一本语法书,老师还好当;要是多看了几本,老师就麻烦。最近出版的一本谈现代汉语的书是这样分析句子的:
(a)去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去年”是主语。)
(b)去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去年”是全句的修饰语。)
(c)津浦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津浦路上”是全句的修饰语。)①
这种分析法未必能得到读者举手一致通过。有人会说,a是无主语句,a、b两句的“去年”跟c句的“津浦路上”半斤对八两,都是全句的修饰语或状语。又有人会说,a、b两句的“去年”都是主语,只不过前者后头有动词谓语,后者后头有主谓谓语。这种争论闹了许多年,双方各执一辞,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问题是,我们该纠缠在这些名称术语上头吗?也许不应该,而应该注意别的东西。
总之,我赞同作者的意见:汉语语法未必简易,只是有人习焉不察,以为“中国话就是没有什么文法”罢了。
作者说,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都不大,如果把虚词算在词汇一边的话。”(86页)一般说来,这话是对的。但是我感觉到,对于研究方言或推广普通话的人,各方言之间的语法分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比方广州话某些词语的安排次序,有的是普通话所不容许的:
广州话普通话
你行先。你先走。
奇怪啊,又。可又奇怪啦。
俾
关于词与非词的区分,这两种话也不完全一样。有个广州记者这样写:
他就在这又窄又嘈的环境中潜心翻译,刻苦攻读。
在广州话,“窄、嘈”都是词;在普通话,“窄”是词,“嘈”只是语素,跟“狭、伟、宏”一样,不是词。
作者拿汉语和英语比较,认为“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可是他补上一句,“经济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的体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61页)两面都看到,这就避免了偏见。有时候英语确是显得絮烦,例如:
跑警报runforshelterduringanairraid
等门situpforsomebodytocomeback
谢幕respondtoacurtaincall
偷嘴takefoodonthesly
但是有时候英语比汉语能少用一个宾语:
Hedrovetothestation.他开汽车到车站。
Heactedwell.他演戏演得好。
Hetelephonedtome.他打电话给我。
HeflewtoNanjing.他坐飞机到南京。
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文字(汉字)和语言是并列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作者说这是不正确的理解。他指出,“一个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5页)。他听过人说,“汉字最美,‘玫瑰二字能让你立刻看见那娇嫩的颜色,闻到那芬芳的香味,一写成méiguì就啥也没了。”这种看法他觉得是认识不清,我也是这样看。
但是天下事情总有个根由,认为文字与语言平行,这种误解的根由何在呢?
我以为,第一,这是由于只看见文字的超时间和超空间性,而没有看到它对语言的依附性。例如唐诗“莫向临邛去”,现代普通话念mòxiàngLínchòngqù,可是唐代据说是念makxǐaηclǐ
唐代语音—→汉字←—现代语音汉字在这里仍然是附着于语言,标志着语音的,不过它是不同时代的语言之间的桥梁,能把唐代语音所表示的意思保持下来而已。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汉字确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因为它的部首偏旁往往能表意。有人说“玫瑰”二字很美,大概是从玉旁得到颜色的联想(芳香的联想不能由此得来)。要是说作为文字,“玫瑰”与meíuì完全一样,或者与英文rose,德文Rose,意大利文rosa作用完全相同,人家未必信服。不懂英语的中国人,看见tungsten,fluorine,loon,lynx是根本什么也猜不出的,可是看见“钨”知道是金属,看见“氟”知道是气体,看见“
“有人拿阿拉伯数字和科学上各种符号作为文字可以超脱语言的例子”,这诚如作者所说,是只看见表面现象,拟于不伦。(6页)2×2=4,说汉语的人懂,说英语的人也懂,这些符号是不附着于任何语言的。可是“二乘二等于四”这句话,说英语的人(除非学过汉语)就不懂,因为那是èrchéngèrdèngyúsì的符号或标志,离开了汉语,它就没有意义了。
二
现在谈谈采用拼音文字的问题。我觉得,简化汉字是小改革,采用拼音文字是大革命,二者大不一样。简化汉字我们已取得了经验和成绩,但是前几年考虑不周,跑得太快,还是不得不后退一步,重新研究应该如何前进。采用拼音文字事关重大,它的利害得失如何,实用性、可行性如何,更得认真地盘算、讨论和实验——最重要的是实验。
我想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汉字难学,拼音文字似乎易学,可是后者到底比前者好多少,特别是在正字法没有确定之前?
在我所看到的外国书里,只有一个人以为,对某些语言来说,拼音文字未必比汉字好。这不能成为权威性意见,可是仍然不妨参考一下。
在第八届世界语言学家会议上,DonGrahamStuart叙述了下面这个事实。他那六岁半的小孩能说日本语、荷兰语和英语,父母教给他的主要是拉丁字母,小孩自己看日本假名书本(其中有许多汉字)只有一年多,可是这小孩阅读英文书最困难(因为拼写法不规则),荷兰文次之(那是半音位文字),而阅读日文书则进步最快。Stuart相信,日本小孩开始阅读书籍,进步一般比欧洲小孩快。
本书作者说,汉字容易写错别字(这当然是事实),拼音文字比较不容易写错别字。可是在正字法还没有确立和形成牢固习惯之前,分写连写也会成为混乱的来源的。不信,请看看我们那些出口商品的商标和说明。在一个口服蜂乳的盒子上,一边写Koufufengru,一边却写Koufufengru。又如“紫花杜鹃糖衣片”是一种药,该写zihuadujuantangyipian呢,还是zihuadujuantangyipian呢?
标调是另一个问题。汉语拼音方案是标出声调的,可是现在许多拼音名称都不标调。《人民日报》是RenminRibao,《光明日报》是GuangmingRibao。可是如果不标调,看见ShanxiRibao我们怎么知道是《陕西日报》还是《山西日报》?十年前广州的公共汽车上写着GongGongQiChe,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公公汽车”,婆婆坐不得。
第二,确定了正字法之后,是否就能够和应该采用拼音文字呢?这个问题很大,我也许是无知或保守,不过不妨谈谈个人意见,向读者请教。我觉得,遥远的未来难以预测,可是在2000年以前,换一种文字似乎可能性不大,也没有可见的利益。采用拼音文字,只对一种人方便——能说普通话,又不认得汉字的。不会说普通话的人,要正确地书写拼音文字是困难的。至于要认得汉字的人改用拼音文字,那就好比要用惯右手的人改为左撇子,既费劲,又费时间。恐怕不能说不热烈赞成拼音文字的人都是愚昧和懒惰,因为文字一改变,就要大大减低阅读速度(甚至减低书写速度),耽误许多工作,而浪费精力和时间是四个现代化所不允许的。
汉字笔画多,可是占空间少。李方桂先生举过一个例子:“东京驿”三字写在墙上只占一点地方,DongjingYi可是一长串。长一点的名称更是如此,试比较“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和ZhongguoRenminYinhangSichuanShengFenhang。如何才能节省纸张和印刷费,这在我们这个穷国家是不能不考虑的。
本书说:“不错,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张字母表和几条拼写规则,还要有课本,有词典,可以让不太熟习普通话的人有个学习的工具。”(109页)问题是,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里,要印多少课本和词典才够呢?凑合着使用汉字,把编写、印刷、运输、销售几千万本讲拼音文字的课本、词典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别的更急需的东西,岂非上算一些?
人们不赞成采用拼音文字,还与关心传统文化有关。有人说,文字一改,人们就不能读古书,不能继承文化遗产了。作者承认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读古书是比较少数人的事情,古书的精华总是要翻译成现代话的。”(109—110页)事实上,读文言古书现在虽是少数人的事情,读白话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等却是小学生都会了。改了文字,就剥夺了他们看孙悟空、鲁智深的故事的权利。至于翻译古书的精华,谈何容易!有几个人能把周秦诸子译成现代话?又有谁能把骄文、律诗、宋词、元曲译成可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通话?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还不是古书和古代文化,而是近百年来,尤其是解放以来的近代、现代书和现代文化。试想文字一改,我们的档案、条约、地图、史料、鲁迅的《呐喊》、老舍的《茶馆》、各大中小学的教材、各研究机关的文献资料、各社队厂矿积累下来的文件和纪录,样样都要译成拼音文字,不然未来的中国人就看不懂,用不上,我们哪里有这么多的人手、时间、纸张油墨、印刷机器?这是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大事情,是不是?
我当然承认,汉字识字难,写字难,打字难,排字难,利用穿孔卡片分类、排顺序、做统计难,利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搞翻译难。文字工作效率不高,这是大家都感到头疼的事情。但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有利弊,文字一改,全盘皆翻,非但影响语文教育,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将来真的采用拼音文字,也要考虑到时机、条件、可能性、易接受性等等问题,急躁不得。
三
本书写得浅显明白,但是个别地方还有些小问题,如需要加注或改动一下词句等等。这里抄下若干条供作者考虑。
12页说,“嗫嚅”是双声。但是现在的读法是nièrú。古音怎么念,最好用音标注出。
18页说,“上古诗歌以元音和谐为主,似乎声调不同也可以押韵。”这在一般读者难以了解,可否举例说明?
19页说,“儿尔汝”双声,“恩怨”双声,这与现代语音不同,也应该把古音注出。
22页说,“郭冠军家”双声,“凡婢”双声,这也需要注音,理由同上。
27页说,“苹果”是音译词。不知是否以为“苹果”即是梵语“频婆”?据新《辞海》说,“中国苹果”原产于我国,而广东话“频婆”指的是凤眼果,不是苹果。作者根据什么书,希望告诉读者。
31页说,“大宛”古代读dà-yuān,“龟兹”古代读qiū-cī,“单于”古代读chán-yū,“冒顿”古代读mò-dū。这是无疑的。可是古代译者为什么要采用这些古里古怪的音译,而不把“大宛”译为“大元”,“龟兹”译为“秋雌”?最好说明一下。再说,作者主张废除破读,例如“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说第二个“王”字不必读wàng。(32页)那么“大宛”今天该读dà-yuān呢,还是dà-wǎn呢?读者会想知道作者的意见。
57页说,“黑色金属=铁。”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可是《现代汉语词典》说黑色金属是“工业上对铁、锰、铬的统称”。
(《语文常谈》,吕叔湘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年九月第一版,0.29元)
①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312,319页。
②据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