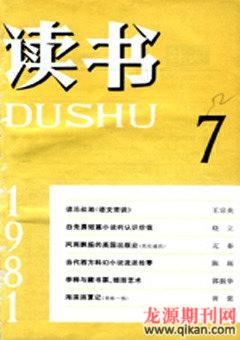《围城》引起的回忆
沈鹏年
岁月如流,《围城》问世忽忽三十五年。作为一个在四十年代嗜读和偏爱它的青年读者,曾经从中认识了行将崩溃的旧中国面貌,看到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困境,坚定了要求前进、追求革命的信心,因此长期来总像思念故友似的,一直萦绕于怀。新印本出版了,展卷重读,它的光泽依旧、魅力如昔,更令人爱不忍释。
当《围城》英译本出版,被推崇为“一部近代中国经典”时,使我想起了有关《围城》问世初期的一些往事、几个对《围城》倾倒备至的战友——他们在十年动乱中先后去世了。“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我不能不感到绵绵的惆怅。
一
《围城》的寓意,乃法国成语“fortesseassiegée”就是“被围困的城堡”的意思。解放前夕,当出版界不景气而唯有《围城》在短短一年半中重版三次,风行畅销之际,正是“百万雄师下江南”、上海成为“围城”之时。正像《围城》中描写方鸿渐在峨嵋春川菜馆的筵席上,听苏文纨、褚慎明谈论“金漆的鸟笼”和“被围困的城堡”,所谓“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后来也说:“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围城之感。”《围城》象征着人生领域的一场战役。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熙熙攘攘,没有了局。举凡爱情的纠葛、家庭的风波、人事的倾轧、生活的煎熬、阶级的对抗、社会的矛盾、国族的战乱、尘世的纷争……,都和《围城》的情况相仿佛。《围城》中描绘了一些留学生从海外到国内、都市到乡镇、学校到家庭,出现各个阶层大小人物六十余名;而主人公方鸿渐转辗奔波、到处碰壁;冲进逃出、谋生乏术……小说中写他的困境是:“鸿渐郁勃得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见一九四七年初版第407页、一九八○年重印本第305页)《围城》既是启示人生之路的象征;又是揭露命运之谜的妙喻。
这部杰作“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使彼世相,如现目前。”从一滴水窥沧海,《围城》反映了整个时代。人们不会忘记,在解放以前的人生长途上,出现过许多似曾相识的方鸿渐的面影;他是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4页)方鸿渐尽管“百无一用”、“书生气十足”、身上有许多毛病,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并不是“先进分子”;但他具备了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一个“精神条件”:即“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他留欧四年、“游学”三国,对“帝国主义文化”却表示了鄙视,认为“西洋文明”传来中国的,只不过是“鸦片和梅毒”。方鸿渐能够保持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当他服务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了,便毅然向报馆辞职;他在身无分文、饿着肚子时,也不肯“做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最为可贵的,他“不愿意跟国民党走”。国民党反动官僚苏鸿业的“千金”小姐“女博士”自愿委身相许,方鸿渐决不领情、不肯“攀龙附凤”。他见了国民党“政客王尔恺”的字,就“撇嘴”冷嘲、百般挖苦,还说“不向他谋差使”。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也是耻与为伍,不肯随波逐流。最后,为保存了一本“时髦书《共产主义论》”,竟被校方视为“思想有问题”而“解聘”。他和赵辛楣一样,认为“要靠了裙带得意,那人算没有骨气了”。总的看来,这是一个“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正开始“站起来”的“有骨气的中国人”。(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4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时代里,方鸿渐的“典型性格”正和俄国革命前夜的《罗亭》一样,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意义。《围城》在四十年代后期之所以一纸风传、万人争诵,其源盖出于此。
一九四八年,我参加了一个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成员有信孚印染厂的陆君、立丰布厂的顾君、新华银行的石君……,都是当时的“《围城》迷”。有时在生活中接触到某些人物,议论中常与《围城》中的人物相类比。我们当时在沪西番禺路上的石君家中集合,主要在私地里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围城》中的某些情节,帮助我们从感性上加深了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某些章节的认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革除”的那种“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大家在讨论中各抒己见,争论得不可开交时,石君随手拿出《围城》,翻开小说第二章,其中描写方鸿渐留学归来,在家乡的省立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读道:“方鸿渐强作笑容说:……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见《围城》初版本第48页)大家在笑声中都认为方鸿渐不伦不类的“演讲”,却说出了简单明白的道理。人们记忆犹新,帝国主义用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华帝国大门,畸形的卖淫制度便和“五口通商”的租界同时发展起来。在旧上海,“会乐里”的高等书寓、“青莲阁”的“红倌人”、“四马路上的妓院”、大大小小的“燕子窝”(大烟铺)……,同帝国主义统治机构“工部局”和“巡捕房”,都是设立在同一条马路上的。“鸦片和梅毒”,是对“帝国主义文化”绝妙的讽刺和概括。《围城》通过对方鸿渐等留学生精神世界陷于困境的精湛描写,展现了一幅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在中国失败和破产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意义上,《围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二
最难忘怀的,《围城》在解放初期,曾配合对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重要文章,接着便围绕讨论白皮书、认清“民主个人主义”本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围城》由于对帝国主义吹嘘的“历史上曾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脊骨”的上层知识分子,别开生面地作了深刻的揭露、解剖、讽刺和批判,正好为大家认清“民主个人主义拥护者”的面目,提供了一份生动的形象材料。
《围城》在塑造主人公方鸿渐的同时,还刻划了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是与方鸿渐由“情敌变为同情兄”的赵辛楣,表面上象“正派”的“留学生”;使方鸿渐认为“像尊人物,不胜倾倒”的董斜川,虽然“英年洋派”而“口气活象遗少”;后来当了方鸿渐的姑父的陆总工程师,“好谈论时事”,却对帝国主义“存着幻想”……,都是一些典型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属于人民群众中的中间派。此外,有“靠着三、四十封”西方学者“回信吓人”的“哲学家”褚慎明、向反动统治阶级卖身投靠的曹元朗、冒牌博士韩学愈、伪君子汪处厚、假道学李梅亭、趋炎附势的顾学谦、卑鄙无耻的陆子潇,以及“花旗洋行买办”张吉民等等。他们有的是政治上近视、思想上糊涂;有的头脑中充满着许多反动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是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这一群形形色色有时代气息、富于社会共性和鲜明个性的人物和情节,有机地构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典型环境”。在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条道路进行决战的历史关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赖以支柱的,就是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当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的伟大胜利后,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鼓励他们“终于会再显身手”的所谓“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的代表(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5页),也就是这样一些人物。为了用善意去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是很必要的。上海沪西区委为此吸收各工厂企业的高级职员,举办了“职员学习班”。开始时,大家对怎样认识“民主个人主义者”并与“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划清界线等问题感到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学习班”负责人之一的陆君,便和我谈起了《围城》。他说:“如果让大家读读《围城》,对于‘民主个人主义者本质的认识,可能有所帮助”。经过区委领导的同意,《围城》便列为学员们的辅助参考读物。
我当时是“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不但有机会看到学员们的《思想小结》;协助陆君一同整理了《运用<围城>等文艺作品进行思想教育的几点体会》;还在上海总工会办的“工会干部学校”中介绍《怎样做好职员的思想工作》第二部分,引用了《围城》的例证。学员们在《思想小结》中联系《围城》谈体会,主要有这样四点:
其一、通过《围城》,认识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不能救中国。
大家普遍认为:“读了《围城》,进一步加深了对《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件的感性认识”;“从方鸿渐的遭遇,更看清了‘民主个人主义在中国失败和破产的必然性”。他们说:“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原来是留学生当作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从欧洲带回的。正象《围城》所描写:‘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见《围城》第2页)但这一套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不少学员还以方鸿渐为鉴,照了一下镜子,回忆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都认为“方鸿渐为人比较正直、有爱国心,能保持‘中国人的骨气;结果到处碰壁,没有出路。可见‘民主个人主义救不了方鸿渐;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也同样不能救中国。”
其二、通过《围城》,看到了“民主个人主义”的反动实质。他们说:“从《围城》中赵辛楣、曹元朗的经历和演变,进一步看清了‘民主个人主义的反动实质。例如:赵辛楣从美国留学归来,自鸣清高,不屑当‘外交公署处长,而在‘华美新闻社当政治编辑;当他在‘三闾大学出丑后溜到重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了国防委员会颇为得意,‘一步一步高上去,终于‘步入了反对人民的行列。曹元朗原来是‘留学英国,在剑桥念文学,是位新诗人,回国后自鸣风雅,做些莫名其妙的诗;但与国民党反动官僚的女儿结婚后,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官,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终于加入了反对革命的阵营……。他们的经历,就是从‘民主个人主义演变为反对人民、反对革命。‘民主个人主义的实质,也就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
其三、通过《围城》批判了“保守中立”的“清高”思想的错误。
他们原来以为:“过去能够‘不左不右、保守中立,思想上很清高”。“从《围城》中陆总工程师的形象和抗战期间‘约翰牛、‘山姆大叔、‘法兰西雄鸡的描绘,认识到‘政治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中立的,自己的‘清高思想是错误的”。他们都认为:“《围城》中写道:‘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见《围城》初版本第432页)这是对一切标榜‘中立的中间派思想本质,富于幽默的艺术概括。”
其四、通过《围城》划清了与“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界线。
他们说:“《围城》用艺术形象把‘民主个人主义者作了一次集中展览,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有的说:“本来还以为‘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皆有之,无伤大雅;认为这种思想即使不好,也无非像一块‘臭豆腐干,外臭内香……。现在通过《围城》中的褚慎明、韩学愈、李梅亭、汪处厚等人身上,暴露了这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面目是如此丑恶、灵魂是如此龌龊……,看到他们,人皆厌恶。谁还愿意去步他们的后尘呢?”——从而便自然地与“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划清了界线。
《围城》作者站在四十年代“历史的前线”,写出了“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画廊中的艺术典型,又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定生活环境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诗人是预言者”,小说《围城》为新华社社论批判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预示了一份生动的形象材料。《围城》的形象思维终于能为新华社社论的逻辑思维服务,这就证明:凡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总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而具有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三
《围城》问世以来,有人誉扬;有人诋毁;有人把它当作一面“自我教育”的镜子;更有人不求闻达、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埋头从事研究。
国外的学者和记者认为:“《围城》在海外盛行而在本国绝少人提起。”一一其实,这是不确的。
《围城》一发表,曾经纸贵洛阳、在国内文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九四八年四月,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写道:
“《围城》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rite(最爱好)了。我的儿子、内侄、姨女、内嫂以及我自己都争夺般地抢着看,……”。
同年七月,一位署名“无咎”的老作家在《读<围城>》中承认:
“朋友聚谈时,要我来谈一谈《围城》,说几句话;且说,这是位和平后出现的作家,颇有些读者的”。
但是,“秀出于林,风必摧之”。《围城》也同时招致了一场激烈的责难和围攻。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横眉社出版的《横眉小辑》第一期,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论香粉铺之类》,指责《围城》道:“这部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象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
同年四月二十日 ,同代人社出版的《文艺丛刊》第一期,发表了一篇《从<围城>看钱钟书》,竟然胡诌什么:“《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
同年七月一日,香港出版的《小说月刊》创刊号,也发表了一篇《读<围城>》,说这部小说只是:“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
由此可见,围绕《围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非“在本国绝少人提起”。尽管“提起”时有褒有贬,却都是重视《围城》的表现。
有人说:在一九四八年,领导和指挥这场围攻《围城》事件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过调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解放以前,地下党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刘长胜、马纯古等同志。解放初期,刘长胜同志任市委第三书记兼上海总工会主席;马纯古同志任市委常委兼劳动局局长。当时他们大力支持沪西区委举办“职员学习班”,都亲自来讲课。在学习班确定把《围城》作为辅助参考读物之前,沪西区委副书记安中坚同志指定陆君和我,一起向刘长胜、马纯古等同志进行走访,了解一九四八年由上海首先发难的围攻《围城》事件。
刘长胜同志说:“这件事”,他“一点也不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市委领导,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要批判《围城》的指示和意见。什么蚂蚁社、横眉社批《围城》,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同我们党的市委领导没有关系。”
马纯古同志说:“对文坛上的情况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去年(即一九四八年)的打击《围城》,与我们党的领导毫无关系。因为在当时,我们主要是贯彻执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有关指示。毛主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公开打击《围城》和它的作者,是违反‘扩大文艺统一战线的精神;因此,批《围城》决不是党的意见……”。
我们还请教了邵荃麟同志。他说他“是反对抹煞《围城》的那种过左倾向的。”在他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我们必须避免重复左联时代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轻视或放弃对于一切可以合作前进的人的团结与争取,这种倾向……应该及时纠正。……反对抹煞一切的过左倾向,……帽子乱戴,……这将使新文艺运动的发展,遭受巨大的损失。”(见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香港出版《文艺的新方向》第15页)
事实证明:一九四八年围攻《围城》,并不是党的意图;一九四九年沪西区委把《围城》当作“思想教育”的参考材料,反映了我们党对《围城》的根本态度。
《围城》究竟为什么无辜受到打击?——完全是模仿了苏联“清算文艺”的一套作法所致。
当我国的讽刺艺术杰作《围城》出版时,苏联正在以倾国之势发动全民批判讽刺小说《猴子奇遇记》达到高潮。个别人不问国情、生搬硬套,便向《围城》开刀。影响所及,导致《围城》在上海未能及时重印。这是我国文艺界的一个损失。时代的讽刺:苏联去年出版了索洛金的《围城》俄文译本,“序”中批评“中国埋没了这部书”,令人啼笑皆非。
事实上,“左”倾思潮对《围城》的错误打击,反而激发人们对《围城》的认真研究。如果说:在国外研究《围城》是为了考博士、硕士等学位,“一举成名”,可以获致一生衣食不愁的“金饭碗”;那么,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几个共产党员不问对《围城》的褒贬、不论处境的顺逆、不计个人的荣辱,坚持为革命文化发展的需要而默默地研究《围城》及其作者的所有著作,苦心孤诣、锲而不舍,垂二十余年,这纯粹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善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的胸襟和气魄!
建国初期,陆君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归来,邀请石君和我,谈了他听艾思奇同志讲《历史唯物论》的体会和学习列宁《青年团的任务》的心得,相约继续研究《围城》等问题。他雄心勃勃,提出通过《围城》对钱氏著作进行系统研究,以十年为期,集体写作《钱钟书评传》。我自审水平很低,缺乏写《评传》的才识,便承担了搞资料的任务;陆君原来爱读“西洋文学”,便负责对钱氏全部创作的研究;石君是名教授严景耀先生的门生,负责《谈艺录》、《小说识小》等著作的研究。可惜后来情况起了变化:石君远去青海西宁;陆君调至郊县嘉定。千里外鱼雁相通,大都是交流读《谈艺录》的心得;难得从郊县回沪,见面时娓娓交谈,也无非是对钱氏创作的分析。陆君曾把《围城》同《阿Q正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罗亭》、《名利场》、《赣第德》、《堂吉诃德》等中外名著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看法。有一天,陆君急匆匆跑来,向我借《围城》。他说他的一本“被朋友借去弄丢了”。三个多月以后,原书还我时,给我看了一部恭楷缮写的手抄本《围城》。这是他用一百多个假日和晨昏,以每天抄写二千多字的进程的结果。一九六六年八月,我收到石君给我最后也是最短的一信,原文是:“已受审、勿来信。”后来获悉,他已经死于非命。陆君则在折磨后瘫痪失音、成为残废;在洞庭东山养病多年后,也不幸逝世了,骨灰安葬在太湖中的莫
“雪老霜新惯自支,岁寒粲粲见冰姿”。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芒照耀下,《围城》首次重印十三万册,不出百天,抢购一空;再次重印,拟出二十万册,读者已在翘首等候了。我好不容易在新华书店排队购到一册,于清明前夕带到陆君墓前焚化以表心意。片片纸灰、化作蝴蝶,随着春风吹面、翠柳拂首,在长空飞舞,我仿佛看到陆、石两君的英灵,正在百花丛中微笑。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病中草
(《围城》,钱钟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0.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