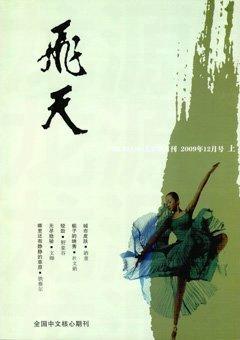《土豆的微笑》以及土豆的生活
尔 雅
《土豆的微笑》从一个角度来看,表达的是对于种植土豆的农民的礼赞。作品的背景是西北地区因贫困和干旱而著名的定西。那里的气候异常的干旱,土壤非常贫瘠,作为一个至今仍然保留了完整的农耕社会特征的地方,可以想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的艰辛。虽然少数地方已经向城市化迈进,但其功能实际上相当的不完善。比如被命名为定西市的这座城市,还不如说仍旧是一座小县城。吃水的问题困扰着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因为没有充足的水源可以满足城市里的生活需要。几乎所有的开支都要有赖于上一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幸亏还有一种植物可以使他们树立起坚强的也是唯一的信心。那就是土豆。这样的土壤和气候居然能够生长出最有味道的土豆。现在,定西的土豆差不多与定西的穷困一样出名。通过土豆的规模化种植,定西的相当数量的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少数人则成功地跻身于富人的行列。有些学者则乐观地估计说,假如定西的农民进一步扩大种植的规模,也许大部分人都会走上致富的道路,定西会变得和沿海的城市一样富裕繁荣。本书的作者阎强国也表达了类似的期望,虽然他是谨慎和有所保留的。书里面列举了大量的来自现实的例子,这些人物都是通过土豆的种植获得改变生活的契机的。在一定意义上,《土豆的微笑》书写的就是土豆对于艰难生活和恶劣天气的胜利。只要勤于耕作,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也仍然有脱离贫困的可能。
不过除了读者可以看到的内容,本书还表达了一个隐蔽起来的主题。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即在于其书写的丰富性。《土豆的微笑》一方面描述那些种植土豆的农民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描述了其获取利润和财富之前的那种艰辛岁月。这两者似乎不具备相应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还是愿意把后者当做是前者的一种动力。的确,越是贫困的人,就越是有改变生活的勇气。不过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部分的书写。这也是我认为最具文学意义的地方(个中缘由,我还会在后文提到)。在我看来,本书展现了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人的求生本能。人生中的大部分残酷的境况被完全裸露,比如难以想象的物质上的匮乏,生存环境的险恶,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不安和焦灼状态。贫困还带来了道德上的逼仄。他们一方面渴望改变,另一方面又对于试图改变的人施以精神上的压迫。这是贫困的乡村社会里一道鲜明的景观。由此造成了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过度的、甚至是过分的渴求。比如他们赤裸的祈求愿望和姿态——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故意地显示自己的穷困状况,对于自我的评判夸张其辞,目的是获取别人的同情和帮助。比如令人诟病的“等靠要”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此反常的状态来渴望拥有生活中的尊严,借此来获取安全感,减轻内心的慌乱和紧张。这是卑微人生里的抗争。这本书讲述的其实是关于距离土地最近的人是如何试图逃离土地的束缚,但事实上又无法逃脱,最终要依赖于土地的供养的历程。这其实是人类的共性。阎强国在书中的描述非常节制,看上去往往并不经意,但其实包藏了作家本人的深刻用意,否则的话,一本介绍农作物种植过程的书,就会很容易流于一本简单的农业生活的报告,恐怕这远非作家的本意。所以作家的写作是相当智慧的,他把宏大的话题变作具体细微的镜像,从而使得本书既是一份详实的报告,又是一部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作品。
定西谚语说: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说的其实是同一种作物。可见定西之穷,也可见土豆对于定西之金贵。土豆是把人和土地联系起来的一个强大的中介。土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土地、山川、河流、天空,以及在地面上行走的人。它从土地里面生长,能够迅速成长为块状果实,最终的果实也是被土壤包裹。它能够迅速满足人类的口腹之需。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一种植物有着土豆这样丰富的、缓解饥饿和供给体能的营养。而且土豆在越是恶劣的环境里就越是能够长出肥硕的果实。——定西的土豆与定西的乡村生民是何其相似。比较一下南方的土豆就可以知道,定西的土豆有多么好吃。因为雨水过多反而会损害土豆的养分和食用口感。现在,土豆已经成为某种贫困或者有过类似经验的标志,是某种被庄严地仪式化和戏剧化的乡村景观。《土豆的微笑》里写到一个叫小张的定西农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饱饱吃一顿洋芋”,然后他还梦想如果他考上大学,“就有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来供他”。他陷入这样一个怪圈里,竟然影响到他的学习,总也上不了大学,最后下决心种植土豆,他发现,只有土豆才可以帮助他。他果然以此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这节材料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书里面有很多。它滑稽、喜剧化,又庄严、深刻,在定西的乡村和小型的城市里经常上演,几乎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一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可能会有意识地抛弃土豆对于他的这种深刻的影响,因为土豆已经成为某种物质和精神上的穷困的标志,唯有摆脱才可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城市公民,但事实上能够吗?不能。即便他不再种植土豆,土豆的记忆也很难干干净净地抹杀。我当然说的是另一回事,是一种近似于文化上的烙印一类的东西。
是的。我们必须要正视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所显现的文化上的困顿。我曾经写过数篇关涉这片土地的作品。我的一个“乡村小说系列”,大部分素材都来自于定西的乡村,另外还有几篇散文作品,也都是关于定西生活的。因为我就出身于这块土地上。在一篇散文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对于定西和定西的土地,我怀有复杂的情绪。那里是我的故乡。我能最深刻地体味到那地方的气息。那地方的人没有见过大海,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洗过澡。那些笑容是憨厚朴实的,但眼角又藏了浓厚的警惕和狡黠。他们卑微地活着,也同样有着卑微的野心。他们经常不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他们以为人生就应当如他们自己一样附着于贫瘠的土地,缓慢而痛苦地爬行。他们就是土豆,是生物链和食物链最底端的部分。多少人一生都在渴望逃离,但又渴望依附在这块土地上。故乡的气味伤害过我,但同样,若干年之后,我必须承认,它又滋养了我。我身怀悲悯,包括对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我更希望故乡的人能够真正摆脱这多少显得残忍的命运。土豆的收益只能够修一座好一点的房子,给放牧或者耕种的儿子讨一房女人,但他们知道好生活是什么样吗?精神上的贫困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文化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他的眼界的。正好,《土豆的微笑》里写到的那些通过种植土豆致富的人,有几个还跟我认识。我们见过面,还讨论过一些关于时尚生活的话题。也就是说,他们(她们)其实也非常渴望精神层面的愉悦。不过我总是感觉,他们的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严重缺失的,比如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世界就是他们所开垦的土豆农场那么大,而时尚也无非是对于定西乡村里固有的审美标准的局部放大。一件昂贵的衣服可以使自己增加虚荣和品味,却又从来认识不到这件衣服其实根本不适合他(她)自己。但是当我们试图说服对方的时候,却发现这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他的固执如同某种牢固的自信,你是无从改变的。文化上的真相就是如此:有些东西与生俱来,即使老之将至也未必可以洞察真相。物质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脱贫。
从社会学的功能论和冲突论来看,消费链条的最低端仍旧是不能改变物质的匮乏的。在社会学上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耐克品牌在全球市场拥有超级的影响力和巨额的利润,但那些制造耐克服装的工人却永远处于廉价佣工的市场。从来没有一个佣工可以藉此来改善自己的穷困状况。土豆也一样。现在,据说在中国销售的肯德基快餐的薯条,大部分(或者说最好的)原料来自定西,但其价格却是定西的数百倍。定西其实也可以制作出肯德基一样的薯条,因为炸薯条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技术,但是它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城市里的快餐盒之中?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问题。消费链条中的配置永远是不平等的,但是你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肯德基的感召力要远远超出定西的土豆。因为定西仍然是贫困的另一个代名词。物质上的匮乏带来精神上的穷困,精神上的穷困反过来又巩固了消费链条里的弱势地位。所以,改善贫困的状况需要技术和加入全球化的消费链条之中。但更需要文化、教育和观念的改变。我迫切地希望故乡的人们能够在物质的丰富之后(假定如此,实际上还有相当的人口处于绝对的贫困),可以懂得真正的生活。
若是从文学层面来看,《土豆的微笑》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阅读的过程相当愉快。纪实类文学本身具有虚构类作品不能比拟的鲜活元素,这是很多当下的小说家需要汲取和学习的。因为很多虚构类的作家都陷入一种材料匮乏的状况之中。另一方面,纪实类作品又是非常考验作家功力的门类。它需要剔选凌乱材料里最为直接和朴实的部分,关涉作家对于事件和生活真相的理解与判断。写作上的熟语: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有一些章节写得非常美,比如写漳县风物,写定西回乡青年侯新民的故事,等等,单独抽取出来,都可看作是有相当水准的美文。阎的文字内敛节制,行文恰到好处,保持了某种可贵的悲悯情感。当下的许多作家书写人文情感时候过于铺张累赘,其实内心缺乏深刻的体验和真诚。非常做作。阎又是聪明的,本书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完备深刻的土豆传记,又有非常好的可读性和文学水准。我在此表达真诚的祝贺。
(作者简介:尔雅,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