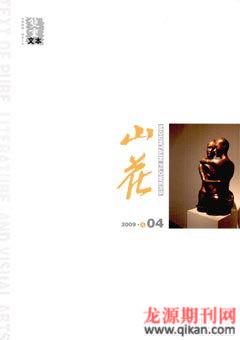酒窖
张 炜
1
经过不知多少代的开垦和经营,我们这里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之一。这片一望无际的绿园显然包含了一个地方的荣誉和尊严。我有时想,这么多的葡萄难道都酿成了酒?秋天,一辆辆马车汽车都载满了葡萄,驶向了榨汁厂。原野上,贮存葡萄汁的一个个大金属罐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巨人般耸立。
这一片大葡萄园,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当地那个葡萄酒酿造公司。这个公司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拥有全国最大的地下酒窖。我从得知了这个酒窖之后,就一直想亲眼看一看。有一天我甚至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很大的地下洞穴,洞穴里排满了一个个椭圆形的大柞木桶;头上滴着水珠,地下是坚硬的泥土,一个个盛了葡萄汁的柞木桶被枕木垫起来。我沿着洞穴走着,不知走了多远,随着灯光越来越黯淡,寒冷和潮湿也阵阵袭来……我知道这是一处地下酒窖,美酒就是在这儿悄悄地、隐秘地贮藏着,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甘甜的葡萄汁在这里贮藏上许多许多年之后,再变成那些诱人的酒浆,贴上精致的商标,被轮船或火车运向四面八方。那么大一片葡萄园就应该配有这样一处地下酒窖,它们地上地下互相呼应和衬托:一个在阳光的照射下生机盎然,一个在地下隐秘的角落里默默蕴酿……
那个梦境其实是有根据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样的酒窖。想着想着,终于记起是在东北的长白山下。那儿的一个小城也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那一次去长白山,途中好客的主人邀请我们参观当地名胜,其中一项就是地下酒窖。就是那样的一处地下洞穴,里面摆满了硕大的木桶;地下通道是旋转的、弯曲的,主人说如果拉直了算,有十公里长呢。葡萄汁都是野葡萄榨成的,长白山周围大大小小的丘岭和山坳都生满了野葡萄,是一个天然的葡萄园。
那一天主人还领我们参观了酿造车间。在一个接待室,我们品尝了各种酒。这些酒有的紫红,有的棕黄,有的是深黑色。我们每种都喝了很少一点,脸上开始发烧。我们还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题词——从元帅到总理,都留下了赞美的词句。这些墨迹都经主人精心装裱,装在玻璃框中,悬在醒目处。
那次参观留下了如此难忘的印象,它植入了梦中。
当年我们在山上行走,不时要撩开浓密的藤蔓,看到黑紫的葡萄。人们就是把这些散布在漫山遍野的颗粒采集起来,一点一点汇聚到巨大的木桶中,藏入地下酒窖。
我们这片茫茫的海滩平原既有无边的葡萄园,就该有更大的酒窖。这个酒窖的准确位置到底在哪儿,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曾发现过一些很小的、零散分布在民间的一些小酒窖……那一年我流浪到南山时,曾经遇到一个奇怪的老人,他就把几只木桶藏在红薯窖里,里面装的竟是甜甜的葡萄汁。他有自己独特的酿酒方法,据说那些葡萄汁有的甚至是他的老爷爷藏下的。这一家酿酒的历史也许值得好好追溯——他的老爷爷就在赫赫有名的那个酿酒公司做过职员,后来由于很不体面的一件事被赶出来了。他大概一回到家里就捣鼓起了那个事情。
山里老人用自酿的葡萄酒招待客人,毫不吝啬。我记得那种酒多少有点艾草味儿,而且十分强烈。它在当地十分有名。
类似的私人酒窖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酒窖,还是当年在长白山下的那个。
由于酒窖所在地之不同,它们装的葡萄汁也不同,酿出的酒也千差万别。长白山下那个小城的葡萄酒有一种药味。记得那次酒厂主人带着自豪的口吻,告诉我们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基地时,我心里曾响起一个反抗的声音,一句话差点脱口而出:最大的葡萄园、最大的葡萄酒基地,应该在我们的那片平原上……但我容忍了他的话并客气地、感激地喝了他的酒。
后来我才知道,我并没有把事情搞得更确切,他的本意,是指拥有全国最大的野葡萄酒基地。
那个小城的夜晚让我难忘。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上了街头。记得街巷上灯光很暗,我踉踉跄跄往前走,有些凉的初秋的风吹着胸脯。在一个路灯下,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心扑通跳了一下。我害怕地把脸转向一边。一会儿我侧过身子重新去看,一颗心才慢慢跳得平缓下来。
那不是她。只是那个侧影极其相似。
我松了一口气,可是额头已经渗出了一层汗珠。尽管这样,我却再也没有平静下来。
第二天还是参观。我极力压抑着心里的一点什么,可是很不成功。我的思绪再也不能收拢。那个下午我说话很少,同行的朋友交谈着什么,我也不太注意。好不容易把一个下午度过了。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小瓶很精致的酒。
很早以前,我在一片葡萄园里发现了她。我觉得她的额头、发辫和眼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葡萄的气味。当我看到她在那儿欢快地跳跃、跟周围的人讲话,总是不知怎样才好。我们的学校也在一片葡萄园里,我的确是在葡萄架下发现了她。上课的时候,无论有多少人,我总能感到她的存在。她的那双有点深陷的眼睛多么明亮,它也许要照耀我的一生。我那时想得多么简单,甚至认为这会是命中注定的一种结局,而且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这个结局。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和葡萄园,去了很远的一座城市。可是那双明亮的眼睛仍然在照耀着我。有一天乘市内公共汽车去郊区,在拥挤的乘客中一转脸,突然又发现了那双眼睛。我的心咚咚跳,双手颤抖,茫然若失地抓着车上的横梁,几次都抓空了。当我再一次回头看去的时候,发现她正若无其事地盯着车窗外。错了,不是她。
自那一天开始,一座偌大的城市化为了一片藤蔓,我需要不断地撩开一些披挂才能往前。
在长白山之夜,我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她。因为我完全被一路上的新奇所吸引,被崭新的事物唤起兴趣。可就在那个夜晚我蓦然回首——她又站在了路灯下……那个晚上我一个人走了很远,但没有迷路。
回到住处觉得有点头疼,并不知道那是一次感冒的前兆。第二天早晨开始发烧,我吃了一点药,坚持上路。半路上病得很厉害,有人听见我迷迷糊糊地说起了梦话,说了酒窖和葡萄园,还有一个陌生的名字
长白山下的小城之夜距今已经三十几年了,这期间经历了多少事情,既平平淡淡又惊心动魄。关于与她的那个“结局”,实在是非常遥远了。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误,类似的遗失可以属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当我想起这一点的时候,才多少有些原谅,原谅生活和命运。我不知道该责备什么,正像我不知道该感谢什么一样。我没法忘记的只是源于葡萄园中的那双眼睛,明亮的眸子。
我偶尔回到那片葡萄园,可是如何寻觅昨天的足迹?葡萄园中那条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还在,它还在。一次次归来,是因为梦中的酒窖对我产生了诱惑——与此同时,她也出现在梦中了。
我们好像一起走在葡萄园里。当我们俩很近地在一片薰风里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一言不发地往前的时候,当我们的手不得不紧紧地握在一起,依偎在那儿的时候,无法抗拒的辛酸也袭上心头。她的质地很厚的、做工特别讲究的暗黄色长裙挨在了我的身上。我在冰凉的葡萄架石桩上抵紧了后背,吻了她长长的
眼睫毛、她有些消瘦的面颊……谁也没有寻问共同的过去。我们带着过来人的宽宥和温厚互相抚摸着,平静而又热烈。我们都闭着眼睛,在黑夜里感受着那种奇怪的磁力,那种无所不在的引力和准确无误的抵达。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在永远左右着你我他?它能够测知我们到底走向哪里、我们最终的归宿?这种感觉。这种超乎理性和逻辑的陌生之物,环绕着我们,不愿离去。它似乎真的存在,在哪儿指引我们。她像一个很好的母亲那样微笑着,我像一个很好的父亲那样沉默着。我们在那个夜晚都恰好是五十周岁生日的前后。我们当时用自己成熟的步伐丈量了大片的葡萄园。最后,也许是不经意间,她问了一句:
“你参观过酒窖吗?”
“什么酒窖?”
“就是我们这儿的葡萄酒城,那个大公司的酒窖呀,还有什么酒窖?”
我摇摇头。
2
小时候在葡萄园里劳动,跟随母亲在绿色的世界里进进出出。当时的葡萄园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后来才连成了一大片一大片。葡萄园之外就是没有人工痕迹的荒原,我不敢一个人深入内部,总是走一会儿就折回。我常常拿着拣到的鸟蛋和蘑菇、一些奇奇怪怪的花朵归来。母亲在葡萄园里劳动,像别人一样熟练,做得又快又好,两只手慢慢磨出了老茧。葡萄园的人都同情她,因为在他们眼里,来自远城的母亲是不该做这种粗活的。
在我眼里没有比母亲更漂亮的人了,而且她永远年轻。
多少年之后,当我离开了母亲,不得不独自远行时,只靠藏在深处的怀念安慰自己。这样有十几年。
有一天我一个^徒步走回了那片荒原。那是一个傍晚,秋天的气息弥漫了大地。天气不太冷,狗的叫声在远处淡下去。我轻手轻脚往前,像怕惊动了母亲。这么多年了,这里的一切竟没有多少变化。我沿着小时候熟悉的路径往前。终于看到了我们的篱笆。推开了柴门,走向院子当心……母亲没有发现她的儿子。她坐在东间屋里,安详地坐在昏暗处,什么也没有做,两手合在一起。她比记忆中的要矮小和瘦削,头发差不多全白了。我站了足足有四五分钟,一声不吭。泪水在鼻子两侧流动。
“……”
母亲想站得直一些,但我看出她的两腿有些抖。我扶住了母亲。我把脸伏在她的肩上。
母亲没有问什么,需要询问的太多了。她一声不吭地把手按在我的后背上。
母亲原来这么瘦小。
从那时以后,我走得再远,也要频频回返,要站在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越来越衰老了。她的眼睛再也看不清书上的字了,却能够用平淡的口吻谈论周围的一切。她的话很少,然而总是让我难以忘记,给我永远的警策。她常常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告诉她:我像她一样不停地劳作和奔波,也不停地阅读。我能够在最绝望的日子里寻找下去。说过这些话之后,我的脸上一阵羞愧,轻轻地背过身去。我不敢迎视母亲的目光。
当我走出家门,重新开始了遥远的行程时,脑际又一次飘过葡萄园里那淡淡的清香,想起了第一次看见的那个姑娘、那片连同她一块儿毁掉了的废墟、我的惆怅和张望。在数不清的日子里,我从未忘记日落黄昏下那片破碎的砖石瓦砾。荒野上像幻景一样出现的那片青色屋顶,总是在遥远的天际闪动。我甚至想起了苦行的玄奘,想起了他向西的奔波以及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
不久之后,我来到了莱茵河畔的乌珀塔尔,在欧洲这片出现了众多思想巨人的土地上,竟然有人在这里做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那一天我们得到消息,乌珀塔尔将有一个有趣的仪式——个叫“自由思想者协会”的组织将要接纳一批新会员。于是我们一大清早就好奇地赶去了。尽管我们走得很早,到乌珀塔尔已经是当地时间上午九点了。我们走进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台上装饰了鲜花和旗帜,有人讲话,接着是乐队奏乐、给新会员献花。合唱队唱起了歌,并再次向新会员祝贺。祝贺者讲话的大意是:你们从现在起成了自由思想者了,成了独立的人,但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等等。
介绍者说,“自由思想者协会”现在已经发展到四万多人。“人会的条件是什么呢?”我问他们。对方告诉:加入这个协会的唯一条件,就是放弃任何信仰,年龄要在十四岁以上。协会成员以工人和职员为主,还有少量知识分子。
一位长者对新人会的会员——个小男孩说:“要理解父母,他们对你们的管束都是以爱为前提的,明白吗?”
那个漂亮的男孩严肃地倾听,庄严地点头。
从“自由思想者协会”人会仪式上出来,我们又到巴门参观恩格斯纪念馆。在他的家乡,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纪念馆是恩格斯祖父的旧居改成的。我在留名薄上签名时,一个欧洲人用手指着说:“东方人的字,就像一朵一朵的小花。”
纪念馆的人指引我们参观了一个地下酒窖。看来恩格斯的祖父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这个酒窖很大,当我踩着石头阶梯走下去的时候,一股湿气扑面而来。我想起了长白山下的小城,那个巨大的酒窖。这儿也有一些很大的柞木桶,当然离长白山下的酒窖规模要差很多,但的确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酒窖。通向酒窖的一个地下小厅是喝酒的场所,那儿摆着一个很长的木桌,挂了一排排的粗瓷酒杯。主人介绍说,当年很多朋友到这儿串门,恩格斯的祖父就和大家坐在这个桌旁喝酒的。
我们都觉得有趣,都坐在长条木桌旁。
从纪念馆出来不远,就是恩格斯的出生地,可惜那座建筑已经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原址上立了一块石牌,上面刻了这样一行字:
这里曾经诞生了这座城市的伟大儿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离开乌珀塔尔,我们驱车沿着莱茵河回到波恩。一路沉浸在回忆中,想像那座酒窖里谈笑风生的老人和他的后代、他们与东方的关系。想起长白山下的酒窖和那个当时还没有发现的地方——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窖之侧,那儿的一片大葡萄园。
列宁曾经用悲切的口吻谈到了恩格斯的去世,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接着列宁写道:“一八九五年新历八月五日(七月二十四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
列宁说自己和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另一个人出生在特利尔,这是卡尔-马克思。小心翼翼地踏上黄色橡木地板,从第一展室直看到第二十三展室。卡尔·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伦敦逝世。
特利尔的马克思故居经过一年多的翻修和整建。于一九八三年三月重新开放。接待室里是一些陈旧的家具。遗憾的是,马克思家的用具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些家具是从特利尔其他市民之家买来的。这儿有马克思的父亲从事律师职业时的办公室。不远处有一口水井,那儿有厨房。第十一展室是卡尔·马克思诞生的房
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展览部分就从这里开始。
第二十一展室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从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首次阐述,到一九一七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共产党宣言》,占据了展室的主要部分。我看到了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早期译文和其他重要版本。一个展室陈列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__一个玻璃柜里摆着《资本论》第一卷,十分珍贵的平装本。这里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赠给友人的书籍、他们的手稿和书信,马克思赠给父亲的一本诗集的手抄本、他搜集的一本民歌。
在莱茵河畔的日子,正是一个初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美丽的野栗子树,有血橡树。野栗子树开一串白花,血橡树叶子暗红如血。有的野栗子树开一串红花,那更美丽。
从莱茵河畔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看望母亲。母亲似乎已经等待了很久。当我远远看到了母亲的白发在风中拂动时,一颗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母亲接过我扑满尘土的黄色挎包,问:
“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他们。”
我跟母亲描述了很多,特别是那两个人。“我走到了他们的出生地,用手摸过他们房间的墙壁。”
母亲没有做声,默默地倾听。
“我还看到了一个酒窖。那是他爷爷的。”
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那么说,那个老人也是爱喝酒的人了?”
我点点头:“也是个好客的老人,他有一个很大的长条桌,客人一去。他就跟他们喝起酒来。”
母亲笑了。
在这个晚上,我一个人在西间屋里,听到母亲安歇了,就轻轻地开了灯。睡不着,翻找起母亲堆在一角的书。取了一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着他谴责斯大林的那些话……多少无辜的人被杀。赫鲁晓夫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开国元勋,声威显赫的将军,被列宁称为“党内最可爱的人”……都死在了斯大林时代。
合上了书,一阵窒息。做了一个又一个噩梦,不断从梦中惊醒。这个晚上我很想走到母亲身边,想让母亲像我小时候那样,让我依偎一会儿。我站在母亲门外,听着里面均匀的呼吸,站了一会儿又离开。
那个夜晚我回忆着过去的那个泥屋,回忆着泥屋四周一望无际的荒野,特别是,回忆起了父亲。他早已不在了,是他用一双大手养活了我们全家,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了,然后倒下,死去。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们迁离了那里,小泥屋没有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再也不愿呆在屋子里了,走出去,在灰暗的天色里踱步。四周还是一片沉睡,没有一点声音。我往前走,慢慢走到了郊外。郊外是一片葡萄园,我在葡萄园的石柱前驻足。葡萄已经全部收过了,架子上的葡萄叶被冰凉的风吹落,剩下的变得枯黄。很快就要脱落。似乎听到了芦青河的流水声,可这里离河毕竟远了一点。一些葡萄没有来得及被园子的主人摘下,这时就干结在架子上。这儿的葡萄太多了,葡萄榨汁厂也收不下这么多的葡萄,许多成熟的葡萄常常被遗忘。我取下一串干瘪的葡萄放在嘴里咀嚼,一丝甘甜和苦涩同时留在了舌尖上。我相信这些葡萄同样可以酿酒。
3
另一本书记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东方的一位胜者在建国初期到了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一见面就拉着对方的手,说:“伟大,你真伟大!”一个深夜,客人被斯大林安排在一个长条桌的两边,喝起了葡萄酒。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喝了红葡萄酒和自葡萄酒(掺在一块儿)。客人当时觉得奇怪,悄悄问一个翻译:“为什么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喝掺起来的酒?”翻译不明白,想问一下斯大林,客人把他制止了。那一天他们喝了很多葡萄酒。
我自然而然地注意了斯大林的著作,甚至粗粗地翻过了所有的译本。有一篇文章叫《不要忘记东方》,其中写道:“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作自己幸福的基础,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资源、自然幅员,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是在东方。”他接着写道:“但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幅员,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随和的、廉价的劳动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回他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文章这样结束:“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这是一个夜晚,我合上他的著作,久久寻思其中的含义,那个陌生的、冷峻的面容浮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怎么,站起来,蹑手蹑脚地从想象中的塑像走开,没有留下一点声音。他的目光看着东方,他的声音至今还让我感到惊讶。我记得在我生活过的这个城市里,在她的心脏部位,那里矗立了一个花岗岩石雕。我曾经怀着无比的敬仰走近了它——那是一个大学广场,冬青树墙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我急于找到通向那个雕塑的甬道,后来就费力地翻过冬青树墙。我小心地抚摸一下那坚硬的花岗岩,发觉像冰一样凉,铁一样硬。
那一夜我翻出所有的书,把它们摞满了床头。这么多的书怎么可以在一个夜晚读完呢。我只是拂去了书上的灰尘。我不止一次地搬动这些书了,只为了不让它们陌生。是的,它们毕竟是我们人类当中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写下来的,是他们的声音。我只需抚摸一下这些书页,手指触到这些坚硬的外壳,就能与之接通。它们的颜色,气味,都沾上了一方泥土的气息,磨擦也是枉然。
这一年春天,我应朋友之邀,来到了生活过多年的那个城市。我在那里读完了自己的大学。每逢走到这里,我就有一阵按捺不住的冲动。在这熟悉的建筑旁,在这一条条弯曲的马路上,我掷下了一段最好的年华。我觉得自己很可笑:明明不会饮酒也要豪饮,结果一次次沉醉不醒,戗害了身心,留下了笑柄。我记得一个脸色苍白、身材娇小的姑娘喝过酒。喘息着和我们一块儿讨论东方西方、一些至大的人物和问题,没有血色的嘴唇很快地闪动,被一些概念弄得惊惶失措。那时候我们大家一块儿讨论,那么认真,小伙子被她玩弄的那些概念给整得晕头转向,就没有一个想起去吻她一下。她喝了酒变得有些可爱了,两颊通红,也愿意笑了。
有人提出去参观“葡萄酒城”,那个最大的酿酒公司。我怀着一点神秘感在他人陪伴下走了进去。我来得太晚了,我在葡萄园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流下了那么多汗水,却是第一次走到这个葡萄的归宿之地。主人请我们先到一个接待室,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件了不起的复制品——那是很久以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题词——他喝过了葡萄酒,写下了四个大字:“品重醴泉”。
我们端起主人递来的葡萄酒,开始品尝。
“当年的孙中山也到过地下酒窖吗?”
“他肯定到过。”
我们开始看酒窖。迈下一些台阶,一下就闻到了浓重的葡萄汁的香气,它掺杂在湿气和腐木味道中间。这里果然是一个偌大的场面,明亮的灯光下,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橡木桶卧在面前。在这个地下的酒之长城里,我不知怎么走才好,只想兴奋地奔跑,像童年那样在一个个橡木桶间捉捉迷藏。有时我蹲下来,像寻找一种流水的声音,似乎期待着酒的河流在前面奔涌。头上,一滴水从水泥顶板的缝隙里渗下,衣服上落下了斑痕。长白山下、莱茵河畔,所有的酒窖——大地上这么多的葡萄园,这么多的酒。只要活着就要酿造,不再停止;只要活着就要饮用,不再停止。是的,不可避免地沉醉一次。那一片一片的葡萄园,无边无际,足以让人感到惊讶一当年我们驱车在莱茵河畔急驰的时候,有人曾指着高速公路两旁大片绿色的原野,问那是什么?我只稍稍瞥去一眼就答:“葡萄园。”车子往前急驰,又出现了大片绿野,有人又问那是什么?我仍然不假思索地回答:“葡萄园。”一个叫查理的先生笑了,说:“这次您可说错了,那是啤酒花。”
这一天,结束参观地下酒窖之后,主人用最好的酒款待了我们。他搬出了四五种在国际博览会上得过金奖的酒给我们喝。忍不住好酒的诱惑,我们开怀畅饮。由于没有节制,我们真的有些醉了。这些酒太让人愉快和兴奋。我们高声歌唱,一时像孩子一样乐不可支。我们走到了街上,在一片繁星下挥舞双手歌唱起来。我们互相叫着名字,互相取笑,有时还要热烈地辩论。总之这个夜晚过得愉快极了。我们之间有那么多话要说,好像永远不知疲倦,再沉重的话题在我们嘴里也没了份量。
这个夜晚我们一直狂欢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一早,我被人唤醒了。那时候我睡得很沉,因为我实在疲惫了。可是砰砰的敲门声不管不顾,一直把我们大家都吵醒了。
敲门的人是找我的。他把我引到一边,悄悄说出的是一个噩耗……
原来就在我们大家冲动地呼喊和狂欢的那个时刻,我的母亲却像往常那样,合上书,躺下……她再也没有醒来,就此结束了坎坷漫长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