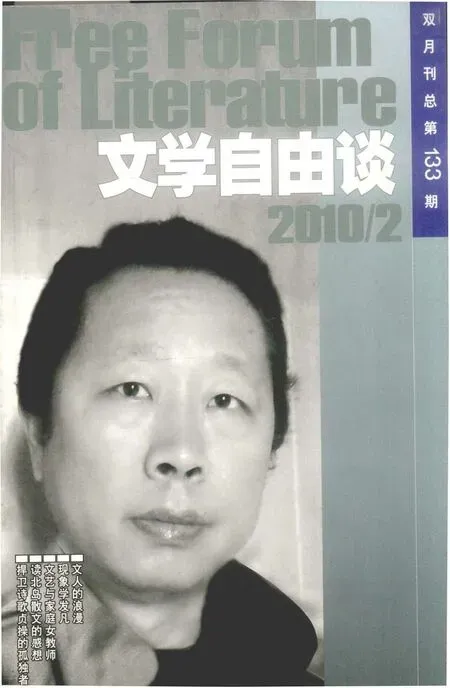作家最好懂点诗词格律
●文 钮宇大
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国人无人不知。当今传统文化回归,连幼儿园的孩子都能背诵一些传统诗词,全国更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诗词热,上自七八十岁的离退休老干部,下至十几岁的中学生,许多人都在习仿填写。发表的园地也多了,各级文联作协所办的文学刊物不必说了,就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大报也所见不鲜。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艺术,是由本国本土生民的血脉心性化育所生。传统中国诗的不幸,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刀斩断中华古典诗词的血脉,使中国诗一度几无传统可言。国诗既亡,国格无尊,国气不扬,国运何昌!但是,外在的刀斧只能乘一时之威,如掘土去根则难做到。事实是只要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天,其文化根脉就依然会衍生出自己的文学花朵。“五四”迄今已近百年,中国诗词不仅没有被根绝,方今反而更加繁荣。
却是,当今许多作家、诗人却很少涉笔诗词。原因或可归结为一是不屑,二是不敢。说“不屑”,是以为这样的“老古董”已登不得诗的大雅之堂,为它耗时费力,不如写写现代诗更为时尚。说“不敢”,是诗词有着严格的格律,弄懂不易,写好更难,与其生吞活剥,不如敬而远之。
中国的诗歌已发展了多少年?产生了多少名篇佳作?就我所知光是保留下来的全唐诗就达五万多首,宋词仅可以查及的词调就达一千几百个,可谓浩如烟海。有这么多的文学精华存在,“不屑”自然无从说起。主要的怕还是胆怯,望着古人的名篇大作而心生忧惧,以为与其出乖卖丑,不如拉倒。当然了,这种艺术形式“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也不大适宜于表现今天的社会生活。这都无可厚非。那么欣赏和借鉴呢?登上古人的肩头创建新的辉煌呢?事实是,许多作家、诗人虽不写作传统诗词,涉猎和借鉴却不少。中华诗词毕竟是一座蕴藏宏富的宝山,可欣赏、可感悟、可挖掘的东西太多了,谁又肯面对宝山而不踊跃呢?
中国诗从《诗经》起就和歌唱联姻:《国风》是民歌,《雅》是都人之歌,《颂》是祭祀之歌;楚辞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如《九辩》即“九遍”,一阕为一遍,“乱”和“少歌”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汉乐府的“乐府”,就是专门搜集整理民歌的机构,诗的歌唱性不言自明;至于唐诗从写作到吟诵都与歌唱相结合,以五、七言绝句和律诗配制的音乐多不胜数;发展到宋词,干脆成为流行歌曲的歌词,当时叫曲子词或长短句,因为填词者多是当时的文学大家,所以词的文学底蕴也就不失雅人深致。
中国诗之与歌结合不同于欧美的诗,概因中国字本身所特有的声韵所决定,并非哪个人的专利。正因此,从《诗经》到今天流行的酒桌段子,从发语到声腔皆一脉相承。中国的文人诗发展到唐代,诗人们充分运用了中国字的抑扬美,加强了诗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于是产生了格律。格律是中国诗歌发展上的一大进步。虽说掌握这种格律需要下一定工夫,但为了使诗歌艺术达到完美,显然是值得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这一联诗无人不知。
但这诗句到底好在何处呢?许多人会说好在词性相对:“两个”对“一行”,“黄鹂”对“白鹭”,“翠柳”对“青天”。很对,数量和色彩及所展示的画面,都足以悦人。那么声音呢?欣赏者如果不懂格律,就很难说清楚了。其实极简单:“个”是仄声,“行”是平声;“黄鹂”是平声,“白鹭”是仄声;“翠柳”是仄声,“青天”又是“平声”,就连“鸣”和“上”两个动词,也是平仄相对。如果再连上后面的一联,“窗含西岭千秋雪,门舶东吴万里船”,我们就知道这首诗的尾字押的是“言前”韵。因为有了这些声调上的讲究,读起来就有了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不仅朗朗上口,且好听好记,通篇充溢着一种和谐感。如果再深究一步,首句是由仄声起,二三两句都由平声起,尾句又回到仄声,那么二三句就是所谓的“粘对”,首、尾二句就是仄起仄落。五、七言律诗也不过如此。
在用韵上也有讲究。如表现明快的内容和主题多用平声韵,表现沉郁的内容和主题多用仄声韵。比较复杂点的是词,每一种调式的词格律均不同。这是因为词是为流传的歌曲所填制,声律失当,字便走音,唱出来难免让听者不知所云。在用韵上大致和诗相同,视思想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而定。最显著的例子如岳飞和毛主席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用的都是入声韵,亦即仄韵。这种韵都是将气流往口里吞,读起来就产生了一种激越沉郁的艺术效果,与词的内容与情感正好相合。如换成平韵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掌握和运用诗词格律需要一个过程,但运用和不运用却大不一样。这就是传统诗写作的规矩。你不懂,在阅读时就只能忽略掉,那么你的欣赏也就失却了声音部分,不能如甘如饴地嚼出诗的妙趣。中国诗歌历经了近千年才发展到这种字字讲究的高级阶段,也是诗歌进入唐代这一鼎盛期和成熟期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果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是不是愧对我们的祖先?
凡艺术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向前发展,诗歌由不讲究格律到讲究格律,是中国诗创作的一大进步。自然,我们今天写诗可以完全不管这些,但不管归不管,懂还是要懂的,否则连阅读都难尽其意。何况一旦我们掌握了这规律,自能感受到其中的佳妙,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二,也可以为诗作增光添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由于当今许多作家不谙诗律,出手虽可写出长篇巨著,但若写到一些有资历的知识分子唱和应对,则难尽其兴,最终不得不吊上几句古人的诗袋了事。倘若能让笔下的人物平仄谐和地唱和上一番,对于写活人物和深化主题又将是何种效果!有人研究过,曹雪芹著《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诗才。诗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不仅表现在塑造人物上(如以十二首诗概写十二钗),简直就是小说的眼睛和灵魂。试想,如果没有了第五回的“曲演红楼梦”,没有了大观园的“试才题对额”,没有了菊花诗和葬花诗等等,《红楼梦》的文化含量和艺术水准该会有怎样的落差!曹氏如此地倚重诗,把诗在小说中的作用扬厉到极致,除了他深厚的诗词功底和过人才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小说还不为社会上的多数人尤其是上层人士所看重。而诗就大不一样了,“诗礼传家”是中国的古训,历朝历代从帝王到高官显贵几乎无人不通无人不写,曹雪芹所在的乾隆朝,玄烨皇帝本人就是个诗迷,一生写诗近万首。而《红楼梦》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示封建社会生活的长篇巨制,又如何能缺失了诗。所以,当今的作家要想在文学上有大成就,谙晓传统的中国诗道当是一项不可少的基本功。
本人不才,上大学时虽讲过诗词格律,却并没有完全弄懂。2000年我在太原办了个书法个展,写出若干首自作诗,细审之,忽有不伦不类之感,这才悟醒到掌握格律的重要。我买下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以求弄懂,结果反是越读越糊涂。后来我干脆把一些耳熟能详的词作默写出来,按我的理解标上平仄韵脚,一首首地填写。总共也就填写了七八首,后来交给《山西文学》,竟全文照登。我害怕编辑们不通格律,专门找了几位善诗词的朋友斧正,结果除个别入声字欠妥外,悉然无误。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下力掌握入声字。山西是一个入声字岛,方言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入声字,所以并不难。我国许多省市如江、浙、闽、粤等情况亦然。至于立意谋篇、因形赋意等,是我的看家本领。因为我就是由写诗起步走上文学之路的。
有了这次成功的实践,我就决定下气力干个大活。我找到大学母校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师借来明代的《词谱》和清代的《词律》,开始遴选词调,约半年,共选出字数长短不一的词调309个,然后断开句,加上标点(两部大书均为竖排本无标点),添上词谱,又一一抄写在稿纸上,这就着手一调一调地填写。因为数量太大了,有的词调又不只填写一首,加之绝大多数词调是首次接触,读过多遍对其音韵声律才能稍微熟悉,因而进度很慢。但又不敢放下,害怕“冷”了。而有许多事又不能不办,比如到珠海、深圳举办书法个展。这样我就走到哪把一摞稿子背到哪,得暇就填。坚持了两年多,终于全部完成了。但我仍放心不下。书名叫《范词今填三百谱》,“范词”皆取自唐代至清代的名家,自不含糊,但“今填”如何,未经一位权威审定,也就不敢自以为是。我先将打印好的书稿呈送给我的山西大学恩师、教授、诗人马作楫过目。马老师说,他有一位中学同窗霍松林,原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精晓诗学,不妨送他教正。上大学时我曾购买过霍先生的《宋诗三百首评注》,知道他早年上中央大学时诗已名噪一时。经马老师和霍老通话说定,我就将我的书稿寄去求教。我万没想到,霍老不仅为我的拙著题写了书名,竟至不顾年高事冗为我写下一篇溢彩的序文。这我才放心地送到了出版社。后来这部专著居然博得许多诗词写作者的喜爱,至今登门求书者不断。
我之所以干这么个难度较大的活,主要是考虑到律诗的格律较简单,一通即百通,而词就不同了,一调一个样,填写者又不可能把每一调的格律都背下来,临时找寻往往又缺少蓝本,我这样做,至少可以为一些填词爱好者提供一部词谱,而我的实践也可以供他们参考借鉴,因此吃点苦还是值得的。
追述这一过程,我是想告诉作家和诗人朋友们,弄懂诗词格律并不难。关键,一是要敢于实践,就如同学习游泳,光站在水边比划各种姿势无用,只有跳入水中扑通来扑通去,才能一招一式慢慢学会。道理很简单,格律源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摸索掌握。自然必要的工具书也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韵新编》就给了我不少帮助。书中有韵律,又有单列的入声字,我在填制中偶有个别字吃不准,查对一下也便了然。再就是要下得辛苦,不惜字斟句酌地用心下力。诗词是一门艺术,遣词用字既要有形象,又要有文采,即便是用乡俗俚语写作,也要做到白而不俗,白中孕雅,即所谓的大俗大雅。这就需要工力。其实这也不难,思考斟酌得多了,自会谙习其中的奥妙。最忌讳的是政治口号入诗(词),将现下的一些领导讲话用语照搬到诗中,许多老干部写诗就常犯这个毛病。其三,就是一定要运用形象思维。直抒胸臆也可,但直抒不等于自白,不能把要表达的思想直说出来,而要用形象说事。使用形象无非比、兴之法,以一物彰显另一物,把思想隐于比喻中。实际上一切文学写作都如此,只不过诗更甚之罢了。
以我这等笨人能把诗词格律掌握了,诸多文学俊彦、文章妙手简直不在话下。问题只在于肯不肯小试身手,肯不肯“下水”探骊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