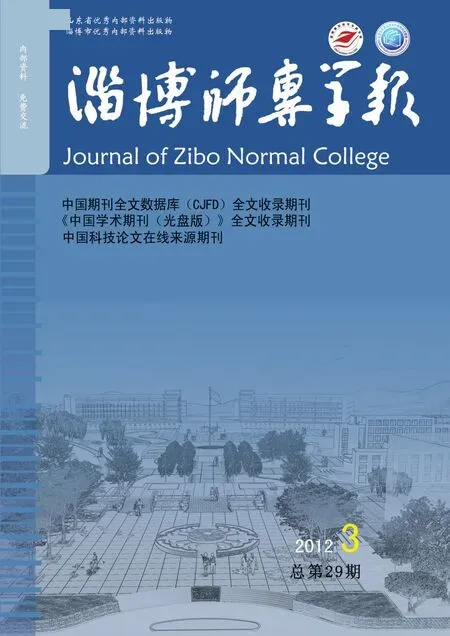传承古代书院文化精神加强当代大学文化建设
牛蒙刚(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淄博 255130)
书院,堪称我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玉海》称:“院者,周垣也”。其原意是指一圈矮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后发展成为“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聚徒讲学,重视读书自学,师生共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1](P8)书院自唐宋确立以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研究机构,是封建社会中后期不断缔造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独特的个性色彩对我国古代人才培养和学术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科举仕进、思想禁锢的社会环境中涵育了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我们认为,书院文化精神是指在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精神成果的总和。[2](P63)这种文化精神作为书院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基础,是书院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是书院教育家们一以贯之的深层追求,也是书院成其特色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确立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承传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书院制度的废止并不意味着书院文化精神的终结。故而,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教育的优秀典范,积极汲取和传承古代书院文化精神的重要经验,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精神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改造中国大学教育和加强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秉持以道德为核心的育人诉求
重视德行的修养,乃至把德行放在比学业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是自孔子以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的共同目标追求。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这种价值的方式方法,都体现在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上。儒家士人之“道”的追求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士人通过改造自身、完善自身人格,实现“修身、齐家”,即以“道”修身;在此基础上,儒家强调士人应该将“道”转化为统治秩序,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大同”的理想,即以“道”治世。
书院自始至终秉持以道德为核心的育人诉求。书院教育家们普遍把道德教育放在书院教育的首位,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3](P83)他在“揭示”中提出了比较完备的一系列学习、修身、待人、接物的准则和方法,以此保证书院的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此“揭示”设有“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其中,“五教之目”即“五伦”,是德性伦理,以人性为基础;“为学之要”是学习方法,归结到笃行;“修身之要”是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处事”与“接物”之要,则是儒学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短短五条学规,却阐明了古代书院根本精神之所在,即以培养教育人“理义养心”“成己成人”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求取功名利禄为目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办学的准则。正如明代王阳明所讲“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它们不但将书院的性质、宗旨、方针、目的、内容、方法讲得十分清楚,而且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整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教学思想,同时还包含着丰富的涵养道德人格的意义和思想。
二、崇尚自由探究的学术创新精神
崇尚自由探究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书院教育至为关键的优秀品格之一。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和清代的乾嘉汉学、实学。这些学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或者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或者以书院为传播基地。封建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各级各类学校往往依附于官府而存在,成为统治者笼络和控制人才的必要手段。学术的核心价值无从确立,当然更不可能产生自由的学术创新。而古代书院多由民间筹资创办,它以远离政治的山林姿态和相对的办学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的独立与学术的自由,形成了为官学所不具有的学术师承关系和学术自由传统。
书院讲会制度的确立则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外部保障。讲会只是书院讲学方式的一种,是指师生会集一起,共同讲辩、共同亲证讲学心得,是书院开展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最重要的活动方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提倡读书讲会制度,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师生之间相互观摩、切磋和启发。学术大师可以自由到各地书院讲学,这就从制度上打破了学术壁垒,破除了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推崇不同学派各抒己见、互相砥砺和取长补短,为各学派自由讲学、学术争鸣搭建了平台,充分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如著名的“鹅湖之会”“中和之辩”等。书院学生也能较为自由的流动,往往是择师而从、来去自由,使独立的学术追求更为便利与频繁。明代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听者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他认为讲学的目的就是“以道义相切磨”,共同“进到圣贤之域”,形成“四方学者不远万里寻师觅友,济济一堂,互相切磋,声应气求”的动人场景。[4](P82-83)
概言之,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重要机构,古代书院相对宽松的办学环境、自由探究的风气与开放的对话精神、自主的学术创新机制与环境,形成了学术大师云集、师生间相互质疑问难、不同观点相互激荡、学术创新成果与教学活动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这不但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基于此,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5](P64)
三、奉行谨严善教乐学的治学态度
书院谨严治学最突出的表现是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书院“学规”“学则”和讲会制度。这些“学规”“学则”不仅从宏观上规定了师生应当遵循的社会价值观和基本的道德修养方法,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更是从微观上对师生修学过程所应遵循的生活和学习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规定。这就从制度上有效地保证了书院教育的谨严治学态度。而讲会制度则将教学和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使书院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对社会的影响实现了整体统一,学生自然成为新思想传播的载体,突出了书院教学的革新精神和实践经验。
另一典型特色是在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框架下教学的自由自主性和民主革新意识。书院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主,提倡师生间平等的质疑问难和讨论争辩,形成了师生善教乐学的和谐局面。其一,书院向广大平民子弟开放,“草野之芥民”“总角之童子”都可以“环以听教”[6](P82-83),以满足士子们“道问学”的需要。书院继承了私学尊师爱生的传统,十分重视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朱熹在讲学时注重“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7](P206),“从游之士,选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8](P85)在平等轻松和谐的交流中取得互为启发、教学相长的效果,充分体现了书院师生之间深厚的情意和平等民主的教育精神。其二,书院教育家们往往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培养其自学能力的重要途径,重视质疑问难。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9](P209)他鼓励讨论争辩,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10](P84)据记载,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11](P73)其三,教育教学方法独特,寓教于乐。朱熹在白鹿洞期间,师生共同起居,与学生悠游山水,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师生间争辩诘难,寓讲说、启迪、点化于休息游乐之中。他还经常带领学生考察名山大川,遍交当世有识之士;或追寻名士遗踪古迹,使学生“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同时也不忘游历城乡,体察民情,多闻多见,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12](P48)正是由于古代书院充满自由、民主、人文气息,师生关系平等,书院学生才敢质疑教师的讲学,进而形成师生善教乐学的良好氛围。这正是教学民主风气的真实写照,也是古代书院充满人文气息的真实反映。
四、恪守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知行合一、躬行践履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要求,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决定了古代书院教育学用一致、知行合一的理念。这首先体现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古代书院以传授道德义理,培养圣贤人格,养成治国安邦的才能为根本宗旨。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实践理性,它需要受教育者通过道德实践去体现,使道德戒条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才能真正提高道德境界。因此,经世致用便成为书院教育的一种自觉的价值取向。《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含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以及接物之要。其一,它提出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其二,它要求学生按照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其三,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13](P122)这都旨在教导学生在学问思辨中理解五伦之道义,进而将这些道理践行于“修身”“处事”“接物”中。整篇“揭示”实际上涵盖了知的范畴和行的准绳,始终要求学生做到知行融合,为培养学生躬行实践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提供了借鉴。
书院教育恪守的实践精神还体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上。南宋书院教育家、理学家张栻认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14](P34-35),提倡把教育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联系起来。古代书院大都是以远离政治、遁居山林的隐逸姿态而存在,因此书院教育家们直接参与政治、实施儒家学说的机会很少,主要是通过言论和著述发表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当时的政治。朱熹也曾说:“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遇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也。”[15](P13)书院师生问答讨论之中,涉及到政治时局方面的内容也不少,有些是评论历史人物及政治得失,有些则是直接讨论现实问题,这都体现了书院师生们的现实关怀。古代书院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多少也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最突出的例子当属明末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制定的学规《东林会约》以“维道脉,系人心”之大任自负,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经济、政治和民生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色的理论观点,从而使东林书院成为当时一个进步思潮的社会舆论中心。有学者指出,“我们对东林书院和它所代表的实践精神这样的神往,这无非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独立理想。唯其独立而有尊严,唯其尊严而能赓续中国的人文传统。”[16](P109)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古代书院以其独特的思想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在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中显示了书院教育的特殊价值。
五、营造和谐清幽僻静的读书生活环境
自书院开始出现,就非常重视环境的选择,“依山林,即闲旷以讲学”,“择圣地立精舍”成为书院的理想选址。[17](P274)中国古代著名书院大都设在依山傍水之地:岳麓书院隐于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清溪茂林之间;白鹿洞书院建造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掩映密林瀑布之中;嵩阳书院位于河南嵩山南麓太室山下,背山面水;石鼓书院则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古代书院之所以多选址在山水胜景之处,幽遐寥阒之境,其主要目的就是营造出一种修读游憩、潜心学术、涵情养性和清幽僻静的环境氛围。这样的环境能令书院师生远离世俗的烦扰,安心读书和精心钻研,从而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追寻自然回归与天人合一。儒家学派还认为,自然山水具有某种与人的精神品质相类似的形态结构,具有德化的作用。这就继承和发扬了孔子“以美比德”的教育思想。后世历代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以自然山水陶冶弟子的情操,从而形成了重视学校环境自然美的传统。“创设如此幽深的学校环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想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净心情,使学生获超然世外之感,在万籁空寂之中悟道皈真。”[18](P386)书院为秀美的山水增添了文雅内蕴,而山水又令古朴的书院倍显静谧清幽。山以人重,人以文传,人文融进了自然,自然又变成了人文的一部分,充分体现出书院的文化生态意蕴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道德品性。
同时,书院建筑布局、设施陈设、风格展示等格调皆崇尚自然,取景于自然,不力求雕饰和华丽,一般都比较朴实无华。比如色彩清新淡雅,主色调多选用黑、白、灰和棕红等沉着稳重的中性色,或以灰白相间描边的山墙表现出自然朴素的文化韵味。书院内设有大量的楹联、箴碑、匾额等富含道德教育意义的器物,如岳麓书院的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白鹿洞书院文会堂朱熹祠联“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知仁独得之天”,东林书院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它们都承载着道德的内涵,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道德教化氛围,彰显了书院师生共同的道德旨趣和追求。
结语
古代书院秉持以道德为核心的育人诉求,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崇德笃学的价值观,是书院教育的生命之基;崇尚自由探究的学术创新精神和开放气度,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坚韧的学术追求和宽广的胸襟抱负,是书院教育最为突出的个性和至为关键的特色;奉行谨严善教乐学的治学态度,展示了书院教育的科学规范,是书院教育家们灵魂与思想的凝结;恪守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则凝聚着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是个人修业与奉献社会的完美结合;书院营造出和谐清幽僻静的读书生活环境,则作为一种潜隐的教育信息和观念的本体,潜移默化的对书院师生进行德育和美育。古代书院的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贯穿于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化为书院教育永恒的精神动力,并对当代大学文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和全面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思结合和知行统一,养成良好学风,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当代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服务社会、引领文化”的历史使命,大学文化建设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文化精神,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精神中“学以致用的文风、学术争鸣的学风、德育为先的思想精髓和重视环境陶冶作用”在内的优秀传统,要不断浓厚校园文化,提高校园文化品位,构筑富有活力的高尚环境,充分发挥大学的独立精神,培养一种超脱于急功近利的求学精神和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形成朝气蓬勃、浓厚、和谐的学术氛围,使当代大学文化更具活力和生机。
具体到我校大学文化建设而言,就是落实“文化固校”的发展战略,牢固树立以“立德树人”为校训,加强“求真创新和谐”的校风、“学聚问辩、宽居仁行”的学风、“严谨善教、敬业爱生”的教风建设,弘扬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培育良好的校园环境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学校师生文化修养的提高;完善管理规章制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不断凝练办学特色,形成富有浓厚师范特色的大学制度文化,为学校提升办学层次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 [11]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2] [5]李兵,朱汉民.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核心——书院精神探析[J].中国大学教学,2005,(11).
[3] 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6][7][8][9][10][18]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12]李广生.趣谈中国书院[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3]詹丽萍.论白鹿洞书院办学特色蕴含的教育思想[J].天中学刊,2011,(4).
[14]王观.岳麓书院[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15]蒙培元.略谈中国的书院文化[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1).
[16]盛敏.论古代书院对当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启示[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
[17]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