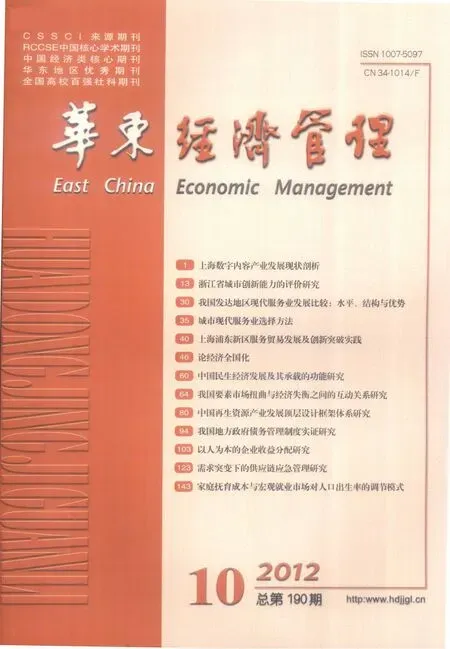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研究
王海兵
(重庆理工大学 财会研究与开发中心,重庆 400054)
一、企业收益分配模式述评
从各国的企业收益分配实践上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物质资本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人力资本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以及利益相关者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每种收益分配模式在实践中可以演化出许多变异形式。物质资本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也称为资本管理型企业(Capital-Managed Firm,CMF)收益分配模式,以英国、美国等国家为代表;人力资本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也称为劳动管理型企业(Labor-Managed Firm,LMF)收益分配模式,以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和西班牙蒙特拉供式的合作社制度为代表;利益相关者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也称为分享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CMF模式对于发展经济起到巨大作用,但近年来其弊端也日益凸显,这种收益分配模式加大了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并且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威胁,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LMF模式在实务中非常少见,相关理论基础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该分配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化、人本化程度以及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政治背景有关,在资本要素自然博弈条件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国家强制力的推行才能运转,现阶段我国企业推行该模式的可能性不大。从CMF模式到LMF模式,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企业的核心经济权力由物质资本出资者转移到人力资本出资者手中,都不能全面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因此,利益相关者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越来越受到青睐,该分配模式综合考虑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本权益,更具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达国家日趋流行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股票期权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等,极大地推动了利益相关者主导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式的应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CMF模式是主流的企业收益分配模式,但正在逐步添加人本因素。当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弱化和间接化时,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却在逐步地强化和直接化。针对这一现况,应赋予人力资本产权收益以法律地位,使人力资本“名正言顺”地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劳动者权益是作为人力资源的所有者而享有的权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人力资本,二是新产出价值中属于劳动者的部分[1]。我国已有承认人力资本价值并赋予相应资本产权权益的实际案例,体现了收益分配的以人为本。上海天娜药物研究所以高新技术成果控股51%,打破了《公司法》规定的技术参股不超过35%的比例。此外,我国曾有企业实行劳力股、人力资源权益股等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模式①。这些好的做法没有得到推广,一方面源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人力资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强大的物质资本集团的制度寻租阻碍了以人为本财务分配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也与普通人力资本供过于求、高级人力资本定价存在技术困难有关。在我国,物质资本的稀缺性下降,而知识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使得未来我国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不断上升。亟待建立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调整和完善包括《公司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从法律上保障其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当然,企业收益分配的“人本导向”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导向”。“人力资本导向”不仅重视经营者的利益诉求,还重视普通员工的利益诉求。而“人本导向”则进一步强调维护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益,这其中既包括经营者,也包括员工,同时还包括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物质资本所有者为了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效率,通过让渡部分企业剩余给经营者或员工以实施激励。实践中常用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方式包括奖金、年薪制、虚拟股票(俗称“干股”)或股票增值权、股票奖励、期股(业绩股份)、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ES⁃OP)、经理股票期权(Executive Stock Option,ESO)、利润分享等。以上收益分配模式虽然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作用,但赋予人力资本的剩余权益是不完整的,依然作为投资者提高经营者和员工工作效率、防范道德风险的激励手段。企业用于激励员工的薪酬分配模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制度规范,而且有可能使得人力资本的努力方向发生偏移甚至逆反,例如奖金可能导致被激励者的短期行为,股票期权制度则受到行权时间、股权数量等诸多限制,可能引发管理层寻租行为,损害投资人利益。在我国ESOP是否会遭遇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MBO)一样的结局,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但股票期权制度引发的管理层寻租现象日益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程仲鸣、王海兵、陈芳(2009)的研究表明,在外部投资者保护较弱与内部治理不健全的环境下,股票期权激励可能引发内部人的管理层寻租,增加代理成本[2]。这些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强权逻辑所引发的弊病,需要转换思路,创新机制,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取得平等地位,共同分享企业控制权及收益权,将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外部激励和中短期激励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自我激励和长期激励。
二、我国企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收益分配的必要性
世界经济理论由古典主义、制度主义向人本主义演进。传统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已经从开源节流、早收晚付滑向“揩”源“劫”流、多收少付甚至只收不付的危险境地。财务管理“物”是“人”非,财务核算“见物不见人”[3]。大股东“携资本以令诸侯”,以股东权利为轴心的传统收益分配模式缺乏公平性,它在促进物质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容易损害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导致偷逃国家税款、损害消费者权益、劳资矛盾激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从而降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企业公民”理念的普及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运动的兴起,宣告股东至上的收益分配模式日渐式微,并昭示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时代的到来。“经济”的本义是“经世济民”,企业收益分配以人为本,有利于促进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从国家宏观层面考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12年政府的九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企业收益分配改革是国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看,科学分配企业收益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大量研究表明,公平的企业收益分配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改进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以及促进投资和经济可持续增长(Alberto Alesina&Roberto Perotti,1996;Jie Zhang,2005;Russ Lopez,2004;Kwan S.Kim,1997;Douglas O.Walker,2007;Yang Jun,2011)。Alberto Alesina等(1996)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会增加政治的不稳定性,并与投资有效性及经济增长负相关[4]。Douglas O.Walker(2007)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一国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长期来看,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之间是不矛盾的[5]。Yang Jun等(2011)在对中国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指出中国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和环境质量显著负相关,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环境质量[6]。收益分配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社会收入分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时,有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以人为本的社会结构(孙显元,2004)。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我国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型”,比“金字塔型”还糟糕②。我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高于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Donald V.Coes(2008)运用随机占优方法探讨了中国和巴西两国的收入分配趋势问题,认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有大幅增长,但收入增长的不公平性问题尤其突出[7]。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透露,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9.8%,但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是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是7.1%,与经济增速不同步。目前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约占GDP的35%,企业利润约占45%,居民收入(即城镇劳动者收入和农民收入)约占20%③。除了收入分布不均衡外,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偏低。相关机构援引的一组数字显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与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相比,我国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尚有较大上升空间。
近年来,我国的投资增长每年都超过30%,而内需增长仅为约10%,内需不足的根本症结,在于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而投资产能过剩。消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0%,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超过85%。2008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8.6%(1979年为64.4%)④。据估算,目前我国直接投资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每增加1%,可拉动GDP上涨0.22%和0.87%,消费拉动是投资拉动的4倍⑤。国民收入水平偏低,不仅会阻碍物质资本投资,也会制约人力资本投资。日本1961—1970年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的黄金时代。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财富,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依然很低,贫富差距较大,资源和环境负荷超载。与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企业利润相比,我国经济多年来处于廉价劳动力时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使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显著减慢,企业依靠低工资、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不同于我国近年来实行的“限高扩中补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倍增计划不是单独实行的,而是和经济发展计划绑定实施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强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不仅赋予劳动者博弈的工具,即参与制定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且要求政府对企业实行一般的减税降息,为企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有条件地放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管制,压缩财政收入在GDP中过大的比重,还利于企、藏富于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2010年6月表示,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⑥。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和人力资本投资者,国家近年来提出改善民生、建立工资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让广大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于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重大,同时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把“蛋糕”做大固然重要,提高做“蛋糕”的人的劳动积极性也非常关键。所以,初次分配不仅要注重效率,同时也要改革企业收益分配机制,提高财务分配的公平性,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具有生产和分配两大功能,企业的生产功能是指企业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的功能,企业的分配功能是指向要素所有者分配收益的功能。企业收益分配决定了当期既得利益的占有格局,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态度,进而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和未来的收益情况。当前,对于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重视不够是企业收益分配议题中尤为突出的问题,劳资矛盾引发企业内部冲突,全面提升企业风险水平。从资本的性质上看,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具有可分离性,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具有不可分离性。从资本的功能上看,物质资本具有完全的担保功能和受限的经营功能,即物质资本的经营功能必须借助于人力资本的经营功能来实现;人力资本具有完全的经营功能和受限的担保功能⑦,即人力资本的担保功能必须借助于物质资本的担保功能来实现。所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发挥不同资本的协同效应,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理所当然都应该分享企业剩余价值,这里所说的企业剩余价值,是指企业收入在补偿物质资本损耗(材料费、折旧费等)、人力资本损耗(工资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支出(土地补偿、环境补偿等)后的增值部分。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有独特的作用,只是在不同行业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资本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存在差异。但笼统地讲劳动雇佣资本或资本雇佣劳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都不利于化解劳资矛盾。
人力资本是最富有价值创造力的资本,具有独特的内在可控性和外在难监测性特征[8],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残缺影响人力资本产能的发挥。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政策,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这里的“资本”是指货币、实物、土地等物质资本和环境资本,劳动、管理和技术则归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我国企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收益分配,有利于促进分配体制改革,改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下的“两权分离”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融合及利益共享提供了制度支持。资本和劳动是相互雇佣关系,“股东→经营者→员工”之间依次存在顺向的物质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物质资本委托者对代理人保留决策和监督权(用手投票),同时存在“员工→经营者→股东”之间的人力资本反向委托代理关系,人力资本委托者对代理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也受到一定限制,但可以通过“关闭”自身人力资本或在职消费等方式影响对方决策权和监督权的实现(用脚投票)⑧。物质资本所有者承担了企业亏损、倒闭等投资风险;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了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风险,以及降薪、裁员等投资风险。所以,基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双向委托代理关系、资本协作增值以及投资风险共担的原因,企业收益分配应在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三、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原则
“以人为本”是指以人为根本,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本文“以人为本”概念中的“人”,是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即能够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具体包括企业的“内部人”(经营者和员工——价值创造机制的主体)、“外部人”(投资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消费者、社区公众等——价值实现机制的主体)和“后代人”(价值可持续机制的主体),企业的“内部人”和“外部人”可统称为“当代人”。以人为本企业收益分配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收益分配的合理性,即人们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国家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防止财富的极端分布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二是收益分配的公平性,按照各利益相关者投入到企业的资源以及其对社会财富的贡献进行分配。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可以分为横向结构性公平和纵向时间性公平两个维度,横向结构性公平是指“权益结构”(相对于“资本结构”而言)合理,投入、产出与收益分配所得配比;纵向时间性公平是指当代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不能透支后代人的资源与环境权益,在节能减排、环境维护及环境损害补偿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现阶段,由于环境主体的体制性缺位以及相关环保规制不健全,环境权益在收益分配过程中容易被忽视,而环境破坏所诱发的各类自然灾害,全面扩大了企业的风险边界,提升了企业的风险等级,由此降低企业预期绩效和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需要贯彻成本补偿原则和利润分享原则,这两个原则是将企业收益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前提。成本补偿属于债权性收益,是资本投入企业的参与约束条件;利润分享属于股权性收益,是资本投入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9]。成本补偿原则有助于实现企业收益分配模式变革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而利润分享原则是企业各类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前提。
(一)成本补偿原则
企业收益分配之前,应对资本成本进行补偿。从广义上考察,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投资者,只是投资的资本种类、资本占用时间、资本产权权益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已。资本占用时间越长,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收益的不确定性及预期收益水平就越高。任何投入到企业的资本都希望能够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资本保全是资本投入企业的参与约束条件,资本增值是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资本保全要求在进行收益分配之间,首先补偿资本成本,包括物质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等。企业收入在扣除以上成本费用后得到利润,按照国家要求提取各种基金,然后才根据风险报酬合约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企业剩余。
以人力资本的成本补偿为例。传统的企业收益分配重视对物质资本的成本补偿,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成本补偿,错误地将“工资”作为劳动者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形式。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工资的本质,强调“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⑨。“工资”实质上就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转化形式,是对劳动力消耗的必要补偿,用以维持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所以,工资是人力资本成本,而不是人力资本收益。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费用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繁育后代所必需的各种生活资料的费用,具体包括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费用、劳动者繁育后代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以及劳动者必要的教育训练费用。所以,工资是劳动者维持自身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劳动者在劳动前后必须消费一定形式、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量,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小于一定值,劳动的耗费量大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受到损害而逐渐萎缩。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企业收益分配成本补偿原则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胀情况下,一定量劳动力消耗的生活资料的成本升高,此时应考察实际工资而非名义工资,“涨工资”的幅度至少应等于物价上涨幅度,以维系劳动力存量的必要价值补偿。对人力资产耗费的工资补偿在性质上类似于对固定资产耗费的折旧补偿。既然折旧不能算作物质资本投资者的收益,同理,工资也不能算作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折旧和工资都只是补偿资产耗费、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分享企业剩余收益才是投资的目的。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工资”是员工用以维持生存的最低层次需求,获得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分享企业利润)是劳动者的劳动被尊重和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的高层次需求。
(二)利润分享原则
利润分享是指各利益相关者按照合约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分享方式可以是固定索取,也可以是变动索取。利息、税金本质上属于企业收益分配的范畴⑩,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利息费用和所得税费用分别是债权人和国家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形式,利息税前扣除的做法是国家对企业的一种税收优惠,能够减轻企业税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资本的通性——逐利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者获得资本成本补偿后,凭借资本产权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企业收入在扣除成本补偿后得到企业剩余,如果协作产生的剩余不能合理分配,容易导致后续合作失败或低效。这里需要厘清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关系,虽然企业剩余源于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企业剩余不能由劳动独占。“按生产要素分配取得价值,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了新价值,而是因为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是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凭借对这些物质要素的所有权,取得相应的份额”[10]。此外还需要区别“收入”“收益”“利润”“剩余”等概念,收入是指企业的经营收入,收益是指企业净增的财富,等于全部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后的余额,包括已实现收益(利润)和未实现收益(利得)。企业剩余是指用收入支付了工资、利息等其他要素价格等固定支付之后所剩余的那部分,如果剩余为正,就是利润,反之就是亏损。可供分配的收益限于已实现收益,即“利润”(正的“剩余”)。应改变将利益相关者权益支付作为固定成本费用加以扣除的做法,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利率、税率、剩余分配比例等)分享企业收益。
以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利润为例。依据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人力资本在实现成本补偿后,要求取得与自身风险、业绩及努力程度相匹配的利润份额,实现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当前,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利润只是作为资本激励劳动的手段,但人力资本按照实际贡献取得相应的剩余索取权是必然趋势。主流企业理论认为经营者是风险中性者,工人是风险厌恶者,资本家是风险偏好者。工人将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转嫁给资本家,同时向资本家支付“风险佣金”,自己却自愿领取一个固定的确定性等价工资;相反,资本家因承担了市场不确定性风险而成为剩余索取者,享有风险佣金,这就是所谓“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杨瑞龙、杨其静,2000)。该命题掩盖了三重真相:其一,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面临的风险水平今非昔比。物质资本所有者日益成为企业风险的逃避者,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11],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物质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特征使得物质资本的流动性明显优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类交易市场转换其资本形态来规避投资风险,人力资本由于在自然形态上具有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特征,在社会形态上具有专用性和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难以在不同资本类型中迅速转化,人力资本流动性受到较大限制,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的风险不断加大。其二,笼统“规定”他人承担风险的意愿程度是不科学的,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工人中也有风险偏好者,即使部分工人愿意承担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但由于人力资本出资并未得到相关法规的支持,企业的收益分配制度安排中也没有变动剩余分配合约供其选择。其三,掩盖了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真相。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人力资本理应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资本独占剩余,是对劳动的压榨和剥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人力资本获得产权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并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理论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利润提供了理论支持。“工资性所得根本就不是收益的分配,而仅是与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需要扣除、补偿一样,是消耗掉的人力的补偿价值……如果只给工资性补偿而不进行剩余产品的分配,就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1]人力资本既是劳动的人格化主体,也是资本的人格化主体,前者要求补偿其劳动消耗,获得固定工资收入,后者则赋予人力资本以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企业利润。而且随着人力资本层次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价值创造能力、博弈能力显著增强,工资和分享利润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但后者上升的速度快于前者,即人力资本层次越高,分享利润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就越大。
四、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模式
(一)各类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基本框架
按照成本补偿和利润分享原则,企业收入在补偿了物质资本耗费、人力资本耗费、环境损耗、扣除其他必要的补偿性支出,以及提取人力资本基金、环保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后,形成可供分配的利润,在人力资本所有者、物质资本所有者以及其他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表1列示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的成本补偿和利润分享模式,与资本类型对应的利益相关者(或资本提供者)是成本补偿和利润分享的权益主体。
物质资本投入企业,既可以采取一次性转让方式,取得成本补偿及固定利润,也可以折股并据以分享企业剩余,采取何种投资形式需要协商并在合约中加以明确。社会资本依附于企业整体,包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其成本补偿在于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利润分享在于从收益中提留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这部分利润不分配给利益相关者,而是转化为本金,通过社会责任投资等形式,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整体创造可持续的增量价值。关于环境资本,目前探讨较少,狭义的环境资本包括土地、矿藏、水资源、天然能源、天然生物资产等自然环境资本,广义的环境资本还包括政治、法制、文化等社会环境资本。这部分资本由政府(代表国家)和社区公众享有,通过向企业征收环境补偿费和所得税等形式实现环境资本权益。企业应对由其造成的环境损耗进行必要的成本补偿,条件允许的,还可以进行环境投资。

表1 各类资本的收益分配结构
企业收益分配应考虑到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对企业经营活动施加影响的强势利益集团,也包括受到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弱势利益群体。传统企业收益分配模式注重维护少数强势利益集团的权益,而忽视了对其他弱势利益群体的权益维护。失去道德基础的市场竞争容易导致“弱肉强食”,这种情况下,资本之间以及资本内部的权益之争不仅不能将资本配置到整体效率最高点,反而使得企业财务关系更加紧张,降低企业财务活力和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物质资本所有者内部,收益机制失衡引发的矛盾比较突出,表现在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权益。有些企业口头上宣称“顾客是上帝”,但实际上把消费者当成“提款机”,商品质量低劣,更不用说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或其他增值服务。物质资本对其他资本的权益侵蚀现象也很突出,物质资本的过度权益主张损害了人力资本的权益和环境资本的权益。人类所有的物质财富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以及人类劳动的积极介入,“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1),然而,收益分配的天平始终向物质资本(即社会“财富”)倾斜,反而创造财富的“劳动”和“土地”的权益被挤占。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人的劳动则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整合,使之转化为各种能够满足人类需求、具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品。许多企业为了追求所谓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忽视对劳动者权益和环境权益的补偿与维护,向“财富之父”和“财富之母”索取太多,而回报甚少,是严重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不“孝”行为。随着人口增长以及人类活动对社会、环境影响日益增大,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相互制约及影响凸显,物本位的收益分配关系使得劳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升级。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要求企业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不仅仅是企业收益分配模式改革的问题,还需要国家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综合治理措施的联合推进。
(二)当前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两个误区
1.重视物质资本产权收益,轻视人力资本产权收益
传统的收益分配理论将企业剩余全部归于物质资本所有者,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只承认物质资本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否认人力资本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这是历史的颠倒。按照科斯和阿尔钦等人对企业的定义,企业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所有者形成的合约,企业的要素从大的方面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周其仁(1996)将企业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并论证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认为“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12]。产权是由多种不同权利构成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但不等同于所有权(12),人力资本收益权是人力资本“权利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权能。人力资本收益权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享有的、由人力资本使用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权。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是对劳动消耗的必要补偿,而不是人力资本收益权的表现,“获取利润是人力资本收益权的本质所在”[13]。人力资本产权具有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为建立“工资补偿+利润分享”的人力资本产权收益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本都具有债权和股权的双重特性,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及专用性程度决定了资本权益属性的具体安排。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获得工资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产权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不仅有助于企业履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声誉,也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更多的企业剩余。同时,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使得劳动者突破基本工资的“消费”制约,促进其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实现和谐发展、多方共赢。
2.重视高级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忽视普通人力资本产权收益
近年来,人力资本产权收益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普遍关注企业家、管理层、技术人员等高级人力资本,对普通人力资本缺乏考虑。传统收益分配模式下,劳动受雇于资本,员工被迫接受物质资本利益集团对其人力资本进行定价,部分用人单位确定劳动者工资水平随意性较大,分配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平等,“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13)。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而人力资本定价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涉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定价必须考虑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14]。所以,人力资本定价既受过去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影响,也受人力资本未来预期收益的影响,还受历史和社会因素影响。普通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较低,普通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大多属于确定条件下的简单劳动,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收益相对有限,高级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较高,其劳动多属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复杂创新劳动,能够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收益较大。所以,从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贡献)水平来看,高级人力资本理应在企业分配中获得比普通人力资本高的收益,但由此将普通人力资本排除在企业剩余收益分配之外,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对实践也十分有害。在参与企业价值创造方面,普通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具有同质性和协同性,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区别;在企业收益分配上,两者也应具有同质性和共享性,只是在收益水平上有所区分。“企业的剩余必然会由资本家独占演变为在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和中低层员工之间进行分配”[15]。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人力资本的产权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人力资本劳动耗费补偿(V)和人力资本应分享的那部分企业剩余(m的一部分),前者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债权性收益,后者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股权性收益。我国人口众多,普通劳动力供过于求,劳动者容易被物质资本投资者和经营者“敲竹杠”,劳动力价格一再被压低,这是十分不公平的。马克思认为,工资不仅取决于社会发展条件,而且应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如果认为普通人力资本不具有稀缺性,用就业机会迫使员工接受苛刻的固定支付条款,那么,丧失伦理性的企业收益分配模式必然严重损害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激化劳资矛盾,引发社会危机。这不仅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相悖,而且与现阶段我国建立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三)人力资本以股权化方式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1.人力资本股权化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具有报酬递增性特征[16]。物质资产在储存、运输、加工等过程中容易产生损耗,其价值转化效率小于1,此时,人力资本的价值转化效率大于1,才可能产生企业剩余。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级人力资本例如企业家型人力资本的转化效率可能远大于1,所创造的新价值可能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数倍。所以,人力资本股权化在理论上是必要的。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所有者相分离后,持有股票可以作为一种所投入本金的物权凭证(包括所有权、表决权和收益权),持有期间藉此参与企业管理和收益分配,而且可以转让股份,将收回的资金投向资本回报更高的企业。人力资本具有无形性、变动性、异质性、依附性等特征,人力资本产权天然地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而且难以用一个固定的金额衡量人力资本的价值,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持有该种“物权凭证”变得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人力资本虽然难以货币化(金额),但却可以股权化(份额)。有研究表明,具有特殊价值的经营者才具有人力资本谈判的优势,但如果最初的人力资本不转化为股权,则会在二次谈判中失去优势地位,从而逐渐失去控制权的地位[17]。股票价格除了包括物质资产价值外,还包括人力资产价值,仅仅将股票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产权证明从而使之独占剩余,对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而言是不公平的,人力资本股权化有助于破解这一困局。
人力资本股权化可以在市场博弈基础上进行,博弈重心在于人力资本能否参与收益分配以及分配的比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通过反复多次博弈完成定价过程,并商定各自的剩余收益份额。双方的博弈能力取决于各自资本的稀缺度、重要性或贡献、退出成本、风险承担能力、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历史条件等。物质资本投资形式较多,有债权性投资,股权性投资,以及介于债权性投资和股权性投资之间的投资(债转股),相比于物质资本投资而言,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比较单一,由于人力资本是一种“主动性”资本,且与其所有者之间不可分离,经营者无法依据人力资本投资期限来决定其产权属性。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刚刚进入企业尚未创造剩余价值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担保功能受到限制,企业收益分配合约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剩余风险。“工资补偿+利润分享”作为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方式,取代单纯的工资模式或剩余分享模式,不仅体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债权特性,也体现了人力资本的股权特性,分配的主要依据是人力资本投入与贡献,人力资本投入和“工资补偿”挂钩,人力资本贡献和“剩余分享”挂钩,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实现人力资本自我激励的长效机制。该分配模式不仅可以降低人力资本的道德风险,也可以避免物质资本所有者作为委托者的败德行为。分配和奖励在性质上差异巨大,分配的主体是市场交易产权主体,人力资本的产权收益是完整的;而奖励则意味着人力资本受雇于、受制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权收益是不完整的。
2.人力资本股权化对革新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
革新公司治理结构是推行人力资本股权化的前提条件。《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可以为人力资本股权化提供制度平台,提升工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股权化方式维护企业劳动者尤其是中低层员工的权益。当前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片面推行人力资本以持股方式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将激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冲突,阻碍企业发展[18]。新《企业财务通则》从政府宏观财务、投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三个层次构建了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和企业财权配置框架。政府、大股东、经营者分别通过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企业实际控制权成为企业收益分配制度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中小股东、普通员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社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公司治理和财权配置中被边缘化。当经济权力用于代理人激励约束时,可实现企业效率和利益保护的双重功能[19],所以,要实现对普通员工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应赋予其足以制衡强权主体的经济权力。应该从法律层面维护企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及其产权收益,赋予职工收益分配权以及选举工会成员的权利,赋予工会代位行使职工财权,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增强工会组织的活动能力和谈判能力,使工会和董事会、监事会一样,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代表企业员工的利益。传统的收益分配模式下,工会容易被管理当局收买,不仅不能代表职工利益,反而可能沦为经营者压制员工的机构,当员工个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时,难以对抗高度组织化的单位,高昂的诉讼成本也让其望而却步。改组工会,使之代表企业员工参与到公司治理过程,有利于提高员工整体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博弈能力,维护劳动者权益。
3.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三种股权化模式
(1)人力资本的“干股”模式。人力资本股权化可以采用“干股”模式进行,干股是一种虚拟股票,持有人除了没有所有权且不能出售或转让外,在表决权和收益权上与实体股票同股同权。企业按照人力资本等级及其对企业的贡献程度,将不同数量的干股划到员工(含经理)名下,持有人在职期间按照股份比例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收益,在离开公司时自动失效。公司支付给持有人收益时,既可以支付现金、等值的股票,也可以支付等值的股票和现金相结合。干股通过其持有者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将他们的长期收益与企业效益挂钩,企业股票市场表现和实际经营业绩的关联度更高,有助于鼓励健康投资、抑制股市投机。人力资本获得干股会对实体股票投资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短期来看,由于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将会导致实体股票投资者享有的剩余分配减少,促使股价下跌;长期来看,人力资本股权化会产生劳动激励效应,将“蛋糕”做大,虽然物质资本投资者的分享比例降低了,但是分享剩余的基数变大,促使股价上升。干股没有所有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公司时自动失效,这是由于人力资本不能直接抵押给企业,但并不妨碍人力资本流向其他企业,只是相比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的流动往往受到签约时间、所在行业、职业经历、工作年限、教育程度、年龄、籍贯甚至性别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决定了其所承担的流动性风险比物质资本更大。

(3)“动态股权制”模式。“动态股权制”模式被称为国企改革襄樊模式,其改革的关键内容是企业分配制度。基本做法是,针对企业关键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以及生产、技术、销售、财务等关键岗位的人员)设置岗位股、风险股和贡献股,形成“劳动者有其股、关键人员多持股、经营者相对持大股”的局面。岗位股是根据岗位的重要程度设置数额不等的股份,采取实体股票形式,职工在岗期间享有岗位股表决权、收益权,没有所有权,最终产权仍归国有。风险股是指关键人员按不少于岗位股的数量以改制时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出资购买的个人股,拥有完全产权,风险股资金可由购股人向银行或地方财政贷款,用年终个人收益分期偿还。贡献股从企业当年新增所有者权益中划出,对关键人员及其他有特殊贡献员工进行业绩配股奖励,个人享有完全产权,如果企业出现亏损,则按相应的原则扣减原有的贡献股。“动态股权制”模式坚持按劳动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让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样具有收益分配权,实现了产权清晰化、主体多元化、资产人格化,降低了“内部人控制”及企业经营短期行为的倾向,具有较好的应用推广价值。按劳动分配所指的“劳动”,包括主要与劳动时间相联系的基本劳动(发放“基本工资”)、与岗位职责相联系的劳动内容(设立“岗位股”)和与劳动成果相联系的贡献大小(设立“贡献股”)。所以,仅对“关键人员”进行激励是不够的,且有歧视普通劳动之嫌疑,有必要对动态股权制的襄樊模式进行改进,面向包括经营者和一般员工在内的全体人员设置岗位股、风险股和贡献股,根据岗位特定确定岗位股和风险股的份额,既然岗位股所有权终归国有,那么可以将岗位股设置为“干股”形式,体现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贡献股是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调整(调增或调减),也应采取“干股”的形式。另外,人力资本的流动机制(包括人力资本在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流动)可以使人力资本获得岗位股变动的激励和约束。风险股将人力资本与企业风险绑定,宜采用“实股”形式。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以上三种模式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对于干股而言,人力资本所有者持有实股不仅享受企业业绩提升带来的分红好处,同时在离职或退休时还能够分享股票市场上的增值好处,但承担的风险水平也相应增加,具有显著的绑定效应和长期激励效应。采用干股或实股模式时,企业剩余先在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根据股份结构比例进行初次分配,然后在物质资本所有者内部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内部进行二次分配。在激励的同时还应引入约束机制,防止团队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在人力资本团队化的今天,如果单个人力资本所有者仅仅依靠持有的股份就能获得收益,那么“滥竽充数”现象就在所难免。在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二次分配应与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及业绩挂钩,从表现不合格者的股份收益中提取一定比重,用于奖励先进。初次分配按照股权结构进行,体现公平,二次分配按照绩效系数进行,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效率,也体现了公平。采用动态股权模式时,建议将岗位股、风险股和贡献股加以推广到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使每一位员工的人力资本股权结构中都包含这三种股份形式,使之在全体员工中发挥激励与约束的双重效果。
五、结束语
以人为本的企业收益分配是对股东主导的物本收益分配模式的扬弃。在我国,物质资本的稀缺性有所下降,而知识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使得未来我国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不断上升。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产权收益,也要重视人力资本产权收益,尤其是普通人力资本的产权收益。此外,对于不能直接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弱势利益相关者群体(例如社区公众、“后代人”等),也应给予足够的补偿。当然,企业收益分配的“人本导向”不能完全等同于“人力资本导向”。“人力资本导向”重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价值创造与权益分配,而“人本导向”则进一步地承认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性作用或制约性作用,并维护其权益,这些利益相关者之中,既包括经营者和普通员工,同时还包括政府、债权人、消费者、社区等。毋庸置疑,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改革是企业财务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赋予人力资本以产权收益是企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收益分配的重要条件,将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企业经济发展成果起到示范作用。
企业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亟待重组企业工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修订包括《公司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和《企业财务通则》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承认人力资本的产权及其权益,真正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从法律上保障其参与企业共同治理和企业收益分配的权利,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此外,配套的机制和体制改革也应及时跟进,包括大力发展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人本企业文化和人本管理制度,为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提供“孵化”平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和人才制度,为人口生产及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扫清制度障碍;研发广义资本动态估价技术,将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等新兴资本类型引入财务资本结构并纳入会计核算与报告框架;建立企业的健康、环境与安全(Health,Environment and Safety,HES)管理系统,对企业人力资本风险、社会责任风险和环境风险进行有效管控。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探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适度嵌入到收益分配过程的机制和路径,防止嵌入不足导致的公平缺失和嵌入过度导致的效率缺失。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企业收益分配中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国家财务管理体制和企业财务分配制度的“革命性”变迁。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刘仲文主编《人力资源会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215~216页。
② 参见凤凰网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文章标题“中央党校专家:中国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型,比金字塔型还糟糕”,《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6月12日。
③ 数据来源:经济学家-世界经理人社区http://bbs.icxo.com/thread-227218-1-1.html
④ 数据来源:《藏富于民的重大意义》,中国日报网,2010-8-8 http://www.chinadaily.com.cn
⑤ 数据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2115
⑥ 岳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6月3日,第5版。
⑦ 资本的经营功能是指企业持续期间资本参与经营及价值创造过程的功能,起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资本的担保功能是指企业破产时资本用于抵偿债务的功能,起到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
⑧ 对于机械化、流水线性质的重复简单劳动而言,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弱,“用脚投票”形式一般是辞职、请病假等。人力资本层次越高,“用脚投票”能力越强,甚至可以形成内部人控制,即“用手投票”。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年,第3卷,第17页。
⑩ 国家税收在本质上属于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形式,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涵盖未实现的收益。
(11)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300多年前的著名论断。这里的财富不同于价值,财富包括自然财富和劳动创造的财富,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而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12) 所有权是一种物权,是指法律赋予某人拥有某物的排他性权利,它可以是纯粹法律意义上存在。产权是使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德姆塞茨,1991),它只有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时才有存在意义,产权比物权有着更广的外延。
(13) 资料来源:中国网,文章标题:“专家: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政府企业个人均涉及”,2008年1月15日,原载《瞭望》新闻周刊。
[1]阎达五,徐国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与劳动者权益的确立[J].会计研究,1999,(6):2-6.
[2]程仲鸣,王海兵,陈芳.管理层寻租还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基于伊利股份股权激励的案例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38-44.
[3]王海兵.人本财务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2:13.
[4]Alberto Alesina,Roberto Perotti.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invest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6):1203-1228.
[5]Douglas O Walker.Pattern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world regions[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4):643-655.
[6]Yang Jun,Yang Zhong-kui,Sheng Peng-fei.Income distribu⁃tion,human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empirical study in China[J].Energy Procedia,2011,(5):1689-1696.
[7]Donald V Coes.Income distribution trends in Brazil and Chi⁃na:evaluating absolute and relative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8,48(5):643-655.
[8]张红凤,孔宪香.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分配的价值测量——兼对传统人力资本价值测量模型的修正[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4):165-176.
[9]王海兵,伍中信,李文君,田冠军.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J].会计研究,2011,(7):59-65.
[10]陈征.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7.
[11]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兼与张维迎博士商榷[J].经济研究,1997,(6):36-40.
[1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79.
[13]石婷婷.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9.
[14]段兴民,张志宏.中国人力资本定价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
[15]冯巨章,李孔岳.企业剩余分配的演变与剩余指标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03,(8):15-19.
[16]冯子标.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1-12.
[17]王冰洁,弓宪文.企业产权的动态安排及企业剩余分配的均衡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2004,(5):143-146.
[18]焦斌龙.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误区及其对策[J].经济管理,2004,(3):50-53.
[19]李富强,张屹山,董直庆.企业剩余分配:一种以经济权力为状态依存特征的动态均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12):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