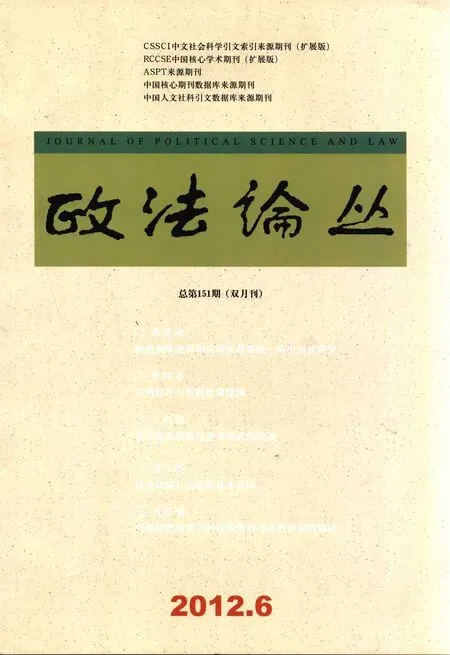气候变化背景下外国投资者与政府争端的解决*
——以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为例
刘万啸
(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气候变化背景下外国投资者与政府争端的解决*
——以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为例
刘万啸
(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一般都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尤其是晚近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多数允许投资者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是,在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有义务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这些环境规制措施可能会损害或影响到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利益。根据双边投资协定,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我国有可能被国际仲裁庭裁定为此对外国投资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面对新形势,我国必须重新审视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相关规定。
气候变化 低碳 投资协定 投资争端 环境规制措施 国际仲裁
国际投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对世界和各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尚未形成全面的关于保护和促进国际投资的多边协定,因此,多数国家往往签订了大量双边投资协定来规范国际投资。为了吸引外资,自1982年我国与瑞典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以来, 迄今为止我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数量已经达到130个。[1]大量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为我国引进外资和海外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双边投资协定中一般都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尤其是晚近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多数允许投资者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是,在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大背景下,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为保护大气环境,我国有义务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损害或影响到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利益。根据双边投资协定,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我国有可能被国际仲裁庭裁定为此对外国投资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
一、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现状分析
在国际投资法全球化、自由化的影响下, 我国近期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开始全面接受国际仲裁(包括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①或者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等设立的专设仲裁庭)的管辖。我国在1998年以前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在投资者与缔约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方面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有的双边投资协定没有规定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条款;有的则规定,如果争端当事方同意,可以将争端提交ICSID仲裁。双边投资协定并没有做出一般性的同意,投资者只能以个案同意的方式将“与征收的补偿额有关的争议”提请ICSID仲裁。然而自从1998年与巴巴多斯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始,我国政府所签订的新式双边投资协定在投资者与缔约国之间争端解决方面就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有多个双边协定全盘接受ICSID的仲裁管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范围扩大。如中国与芬兰原来的双边投资协定只是在其附加的议定书第2条规定,投资者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范围仅限于“对其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补偿款额”,而2004年中国与芬兰新的投资协定中提交仲裁的范围大大突破了之前的限制,将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范围扩展到“因投资发生的任何争议”。新协定第9条规定,缔约国一方与投资者“因投资发生的任何争议”,若在3个月内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就可以提交当地法院或国际仲裁解决,除非争议当事双方另有其他一致同意。(2)投资者有权选择争议解决方式。中国以前签订的某些双边投资协定规定,如果投资者在东道国内求助于行政或司法解决时,该争端就不得提交国际仲裁。中国与芬兰的新协定第9条规定,国际仲裁与当地司法解决二者由投资者选择其一。若提交国际仲裁,就不能再提交国内司法解决。但若已将争议提交国内法院的投资者仍可诉诸该条提及的任一仲裁庭仲裁,该投资者在提交的争议判决做出前已经从国内法院撤回案件。在此情形下,作为争议一方的缔约方应同意将其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的争议根据本条款提交国际仲裁。(3)投资者可根据协定中东道国的事先同意提起国际仲裁。在关于同意问题上,从中国以前的实践看,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提交国际仲裁的争端,绝大多数投资协定规定只对“征收补偿”采取事先单方同意, 对其他事项需要经过争端双方同意,并非将所有投资争端都事先单方同意交给国际仲裁。根据许多新协定,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有关东道国领土内投资的任何争议,应该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6个月仍未解决的, 可应投资者的请求提交国际仲裁。对投资者与缔约国的任何投资争议,投资者只要选择提交国际仲裁, 有关国际仲裁庭即可根据缔约国在此协定中表示的事先同意而享有管辖权。如中国与瑞士1986年旧投资协定第12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发生争议,并且未能在6个月内友好解决,投资者可将下列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一)有关本协定第7条所述的补偿额的争议;(二)当事双方同意提交国际仲裁的有关本协定其他问题的争议。换言之,有关本协定其他问题的争议,如需提交国际仲裁,必须经当事双方另行同意。但根据中国与瑞士之间的新投资协定第11条,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的争议,如果自书面请求磋商之日起6个月内磋商仍没有结果,投资者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而且明确规定,缔约方在此同意将投资争议提交给国际仲裁。(4)无需先“用尽当地救济”即可提交国际仲裁。许多新投资协定将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的投资争端,无需先“用尽当地救济”,即无需用尽我国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即可以直接提交国际仲裁来解决,②或者只要求先用尽我国的行政救济手段,而无需用尽法院司法手段,即可提交国际仲裁。③以上投资协定中这些争端解决方面的发展变化的确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却忽视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管制措施的主权权利,将东道国对外资进行管制的这种涉及公共利益的国家主权权利交由一个适用于商业仲裁规则的国际仲裁机构来评判其合法性,无论是从其程序的合理性上还是从实践结果上来看,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存在对东道国政府不利的现象。[2]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会使东道国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采取相应环境规制措施以履行减排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却面临着这些为履行国际义务而采取的环境规制措施会被国际仲裁庭裁定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危险,这会妨碍东道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一些环境规制措施,阻碍东道国政府履行减排义务,不利于东道国和世界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仲裁解决投资争端方式的再思考
(一)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许多自然系统正在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温度升高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已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无论未来20~30年期间的气候变化减缓规模如何,仍需要采取额外的适应措施,以减少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于能源厂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资本金的使用期长,未来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将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产生长期影响,预计从2005年至2030年间投资将至少达到20万亿美元。因此,投资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全球应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转变投资方向和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已有一系列政策和手段可供政府用于制定旨在鼓励采取减缓行动的激励措施。全球气候变化引起全球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等有关国际文件建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促进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创建了全球碳市场和新的体制机制,这为未来的减缓努力奠定了基础。[3]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努力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有关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4]2009年11月26日,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中国向世界做出了负责任的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为实现这一减排目标,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5]
(二)环境规制措施争端的国际仲裁实践结果对东道国政府的不利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缔约国当初之所以同意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主要是考虑到仲裁的自身特点,期待通过仲裁能使投资争端得到迅速、有效和公正的解决,以维护双方的利益。然而,在近些年的投资条约仲裁实践中,有些仲裁庭不仅没有很好地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的权益,反而片面强调并强化了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甚至将投资者的保护推至极端,其裁决纯粹以维护投资者权益为使命和目的,在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与投资者私人利益的权衡中,它们选择了维护投资者的私人利益;在处理东道国国家根本安全利益与习惯国际法国家责任条款间的关系时,它们置前者于不顾而强调后者;在扩大还是限制仲裁庭的管辖权和审查权的权衡中,它们选择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从而导致东道国权益与投资者保护二者间的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了有关国家对于国际仲裁的信任危机。[6]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会涉及或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国际投资协定关于保护和促进投资者利益的相关条款会妨碍在东道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许多国际投资协定中都有通过仲裁解决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争端的规定,可能会导致东道国对其为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公共政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仲裁庭裁定为违反投资协定,要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这将不利于东道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不利于世界气候问题的解决。仲裁解决投资争议的方式使得东道国政府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的措施受到影响和威胁。东道国采取缓解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会否被裁定为违反投资协定,在国际仲裁中没有先例原则,这会因不同投资协定的具体规定和被诉的东道国而得出不同的结果。[7]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仲裁案件已经做出裁决,裁决东道国政府为其采取的环境规制措施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以下几个典型的案件似乎足以表明: 东道国环境规制措施易被争端机构裁决为间接征收,从而对东道国环境保护起抑制作用,更对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权提出了巨大挑战。
Tecmed v. Mexico案原告为在墨西哥注册的子公司“Cytrar”的西班牙母公司,即投资者“Tecmed”,被告是墨西哥政府。1996年,墨西哥联邦政府负责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规制机构给“Cytrar”签发了一年期的许可证,允许其对危险废物进行垃圾掩埋处理,许可证应申请人要求可以续签。“Cytrar”的许可证如期续签了一年。但是,当该公司再次申请续签时遭到拒绝。于是,作为外国投资者的母公司“Tecmed”于2000年7月28日向ICSID申请仲裁,主张墨西哥政府的这一拒绝构成了对其投资的间接征收,违反了西班牙与墨西哥两国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该案仲裁庭接受了原告西班牙母公司“Tecmed”的主张,即其是未得到墨西哥补偿的间接征收的受害者,但驳回了墨西哥政府关于其拒绝给予原告续签许可证具有正当理由的主张。[8]
在Metalclad v. Mexico 案中,原告美国废品处理企业Metalclad公司打算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危险废品处理厂,并且墨西哥联邦政府当局已经正式批准了该项目。在Metalclad公司进行了重大投资后,墨西哥地方政府未能向它颁发经营许可证,理由是该处理厂可能破坏当地环境。Metalclad 公司因此认为墨西哥政府违反了NAFTA关于最低待遇标准和征收的规定,要求赔偿4300多万美元。根据ICSID附加便利程序的特设仲裁庭程序开始后,墨西哥又颁布法令,将处理厂所在地定为生态保护区。2000年8月,仲裁庭裁决墨西哥政府违反了前述规定,赔偿投资者1670万美元。[9]
当然,也有支持东道国环境规制措施的仲裁裁决。如Methanex v. United States案就是其中一例。但与不支持环境规制措施的仲裁实践相比,支持环境规制措施的仲裁实践要少些。总体而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仲裁庭往往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私人财产权,而忽略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导致其裁决的争端绝大多数以东道国败诉告终。在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仲裁中,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措施要想被裁定合法是比较困难的,往往需要符合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只有东道国政府的环境规制措施程序正当合法、符合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符合非歧视、比例原则和善意要求,且有科学报告为依据,才能够得到仲裁庭的支持。[10]
(三)国际上对仲裁解决投资争端方式的态度变化
虽然国际投资仲裁仍是解决投资争端的主要渠道,但争端解决体系中,各种系统性挑战日益凸显。于是,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其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条款,设法降低相关条款易于使投资者提出请求的可能性,或提高争端解决程序的效率及正当性。此外,几套国际仲裁规则,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国际商会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规则,已得到修订或正在修订。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或正在考虑适用其他争端解决及预防机制。[3]
有学者提出,对于东道国政府出于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原因行使监管权力而对投资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导致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仲裁案件,仲裁庭作为一国具体行为的审查机构,应当运用比例分析或者其他的公法审查方法来应对投资者保护、国家环境以及经济政策选择在公共利益上难以平衡的情况。[11]
(四)国际仲裁解决我国投资争端的现实思考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义务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发达国家有强制性的具体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性的具体减排目标。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无需做出具体的强制性减排承诺,但我国也有义务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何况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居世界第一,④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影响举足轻重。另外,从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现实状况而言,我国也必须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为实现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国务院决定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5]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十二五期间的减排主要目标,大幅度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主要包括:1.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严格控制新建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制定并落实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2.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突出抓好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加快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3.积极发展低碳能源。4.努力增加碳汇。5.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6.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一些外资企业项目必然会受到这些控制措施的影响,但是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给予了这些外资企业一定的保护性待遇,他们可能会指控中国违反了双边投资协定,根据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的有关规定,将与中国政府的这些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2011年12月11日在南非德班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批准设立的德班平台将主要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2012年上半年着手,不迟于2015年完成。然后,根据这一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各缔约方2020年起探讨如何减排。⑤这意味着2020年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可能要承担强制减排目标,中国将来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中国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减排措施。
无论是政府自愿采取的环境规制措施,还是在公众压力之下采取的环境规制措施,都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外国投资项目,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外国投资者有可能会就环境规制措施引起的损害提起国际仲裁。虽然这些规制措施至今未被提交国际仲裁,但其无疑已经或可能引起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的争端。比如,厦门PX项目是由台资(在中国享有外资的待遇)兴建的化工项目,是2006年厦门市引进的一项总投资额108亿元人民币的对二甲苯化工项目,该项目号称厦门“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于2006年11月开工,原计划2008年投产。然而,由于该项目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性及不符合国际组织关于其与城市距离的规定等原因,遭到了中科院院士和厦门市一般民众的普遍反对,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后经过环境评估和公众座谈会等方式,由于民众绝大多数反对复建,建议迁建,最后,厦门市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将PX项目迁出厦门。据说,PX项目的投资者曾威胁要告厦门市政府,但项目迁址的行动表明,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与厦门市政府已经通过和解解决了争端。[10]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地球大气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全球情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在国际组织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全球治理,而不能各自为战,应该结束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政府状态”。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作为构成世界的一个成员,采取切实可行的减排措施保护全球环境,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一个国家的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与东道国和全球的环境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因此,笔者认为,东道国政府为了履行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减排等环境措施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的纠纷,应当排除在国际仲裁的范围之外。
鉴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仲裁作为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首选解决方式。我国也应顺应这一形势,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更好地采取相关环境规制措施,也应重新审视仲裁作为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首选解决方式,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审慎订立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平衡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既要达到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也要顾及东道国采取环境规制措施等公共政策方面的主权权利。
三、新形势下我国对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考量
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应当在投资者保护和促进领域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实现平衡。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方式是通过国际投资协定实现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运动而非抵制减排活动,就要改变传统的从投资者利益出发的立场,需要重新改造现行国际投资法规则,改变国际投资协定将促进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唯一重心的现状,并采纳其他领域的国际法规则,[12]比如《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环境法规则。不得不重新审视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我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关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在将来对现行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修订或者将来签订新的投资协定时,可以在如下方面进行改进:
(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
在投资协定中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即规定外国投资者认为东道国政府的某些行为损害了其依据投资协定应当享有的权益而要求赔偿时,投资者应先诉诸东道国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若该外国投资者未用尽当地救济手段,国际仲裁庭将不会受理其提出的求偿要求。关于用尽当地救济之后再去寻求国际层面的解决方式,实践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作为个人和公司求偿法庭,国内法院更适合和方便;外国人通过居住和商业活动与当地管辖权联系的方式;某种可以用于事实定性与损害清算的程序的实用性。[13]P541
1.晚近国际上关于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管辖的态度转变
前些年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角度出发,在其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关于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争端解决方面,取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规定投资者可不需用尽东道国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而直接提交ICSID或专门成立的仲裁庭进行仲裁。但是阿根廷轻率对待投资争端仲裁管辖权所带来的惨痛教训,给广大东道国敲响了警钟。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开始对投资争端解决提交国际仲裁方式进行重新审视。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或正在考虑适用其他争端解决及预防机制。[3]另外,由于对外资采取相关政府管制措施而被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而被裁定败诉的情况不断出现,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府也不得不纷纷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方式重新审视,对将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开始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近几年由于全面接受ICSID的仲裁管辖权,卷入过多外国投资争端仲裁,许多国家开始担心国际仲裁会过度影响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使,正在逐步推进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改革,增加国际仲裁的上诉机制,改变其以往裁决的终局性,并推进国际仲裁的透明化程度,以求保护其国家利益。目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开始逐步否定国际仲裁庭的全面管辖,并注重对国际仲裁加以必要的限制,开始重视东道国对本国境内涉外投资争端应当在必要的范围和必要的条件下保持优先的管辖权和排他的管辖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开始重新被重视或强调。
美国于2004年11月通过了对外谈判投资协定的新蓝本,通称“2004年BIT范本”。该范本与以往范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注重保护东道国利益,而并非单纯考虑投资者利益。[14]2004年美国BIT范本的这些规定,与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公约》谈判时所坚持“四大安全阀”有所接近,即美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从自由开放地寻求ICSID 解决投资争端正走向有限制地利用国际仲裁机制的道路。
2.我国应采取的态度

(二)尽可能减少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风险
多数投资协定的宗旨和目的就保护和促进投资者的利益,对于东道国采取环境保护等公共政策权力予以忽略,也就是协定内容对投资者利益和东道国利益保护的失衡。投资协定赋予投资者的许多待遇条款,比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征收条款、稳定条款等都会成为阻碍东道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障碍。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应加强环境保护条款,明确赋予东道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等权力,以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保护的平衡。[16]为了适应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在将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尽可能减少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风险。
1.在协定中明确订入东道国保护公共安全、环境等公共政策的条款,将此类事项排除在国际仲裁事项之外。在双边投资协定中,除了考虑保护和促进投资的目标之外, 还要考虑公众健康、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从而为东道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留出余地。我国可以在协定中规定:“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和人类环境、健康等社会公共利益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作为整个协定的例外,不得作为争议事项提交仲裁。”这样的例外规定作为安全阀条款有利于保护我国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环境保护规制措施留下较大的空间。
2.在投资协定中将调解作为解决投资争端的必经程序。法律手段未必是解决争端的最优手段,而应该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调解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调解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不伤和气。在中国特有的"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调解制度一直是我国解决争端的主要应用方式。1982年3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在第6条中将“调解为主”改为了“着重调解”,以避免社会产生“审判为辅”的观念。但是在法律人的鼓吹之下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重判轻调”,然而这样做的社会效果并非令人十分满意。虽然法院根据法律对争议案件做出了判决,但往往会出现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结果都不满意的情况,进而产生大量的申诉、上访等各种情况。从当事人通过订立仲裁协议来自愿采取仲裁解决争议的角度看,仲裁具有契约性质,但是从仲裁裁决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这个角度来看,仲裁又区别于调解等其他自愿解决争议的方法,因此仲裁也具有司法性,即强制性。但是,在东道国政府与投资者之间争端的解决方面来看,虽然仲裁具有了强制性,但同时也会出现如前所述的不顾东道国管制措施及公共利益的情形,甚至还会出现当事双方都不满意的情形,从而严重影响双方关系,甚至影响投资环境。现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已经开始重新反思,认为争端的解决不仅仅是要完全按照法律来进行,更重要的是要看争端解决的社会效果,因此应继续重视调解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国内,在各种国际性的争端解决中,也越来越重视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即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通常是指除诉讼与仲裁以外的各种解决争议方法的总称,如调解、协商、谈判、斡旋等方式。在国内争端调解方面,我国有比较优良的传统和经验。在国际投资争端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内比较完善成熟的调解机制,建立比较完善的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实际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也逐渐认识到调解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先天优势,在其争端解决机制中特别强调调解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在解决争端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谅解协议》规定,磋商是解决争端的必经阶段,不经过磋商阶段,不得进入下一个阶段,即不得要求成立专家组。即使在专家组阶段和上诉机构阶段,争议各方也可以随时“庭外”调解解决争端。我国在处理国际投资争端时,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平等与合理的原则,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调解:(1)涉外调解机构调解,即在成立于1987年的“北京调解中心”进行调解。该中心备有调解人员的名册,可由当事人任选并由该中心主持调解。该中心与设于德国柏林的“北京-汉堡调解中心”共同制定了“联合调解”制度,可在北京、汉堡或当事双方与调解方商定的其他地点进行“联合调解”。(2)国内外知名仲裁机构调解,如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这些著名仲裁机构都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丰富经验和掌握丰富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以及良好的口碑,由他们来调解解决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争端,当事双方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3)法院调解,即由法庭调解和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可以挑选经验丰富、品质高尚的涉外法官来进行调解,利用这些优秀法官的丰富经验和调解技巧使得争端能够圆满解决。(4)其他民间机构调解,指的是带有民间性质的各种外商投资服务机构,如投资促进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机构进行调解。
注释:
①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是1966年10月14日根据1965年3月在世界银行赞助下于美国华盛顿签署的、1966年10月14日生效的《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即1965年华盛顿公约)而建立的一个专门处理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性常设仲裁机构,它是复兴开发银行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中国于1993年1月7日递交了批准书,1993年2月6日成为公约和中心的成员国。以下简称“ICSID”。
② 如中国与瑞士之间的新投资协定第11条。
③ 如,2007年新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第7条规定,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争议解决,投资者可以选择提交国际仲裁,前提是争议所涉缔约一方可要求有关投资者在提交仲裁前,用尽该缔约方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
④ 中国新闻网:中国代表回应“中国温室排放居世界第一”提法。
⑤ FCCC/KP/CMP/2011/10/Add.1,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Further Commitments for Annex I Partie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at its sixteenth session.
[1] 新华网.商务部:已与130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1/01/c_12724364.htm, 2010-11-01.
[2] IISD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IEL),Revising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to Address State Arbitrations (February 2007) [EB/OL]. http://www.iisd.org/pdf/2007/investment_revising_uncitral_arbitration.pdf, 2011.2.4.
[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Overview.
[4] Nicholas A. Robinson: The Sands of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Copenhagen Climate Negotiations, Pac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ume 27, Issue 2 2010.
[5] 新浪财经. 中国承诺:到2020年碳减排40%~45% [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1127/04257023484.shtml,2012-05-05.
[6] 余劲松.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1,2.
[7] Fiona Marshall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Aaron Cosbey and Deborah Murphy,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Obstacles or opportunities? March 2010,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8] ICSID. Tecmed v. Mexico, Award of 29 May 2003, para 198.
[9] ICSID. Metalclad Award,ARB( AF) / 97 / 1,Aug. 30,2000,August 25.
[10] 韩秀丽. 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看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措施[J].江西社会科学,2010,6.
[11] 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 作为治理形式的国际投资仲裁:公平与公正待遇、比例原则与新兴的全球行政法[A]. 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8卷第2期[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 KATE MILE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World,July 2,2008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154588.
[13] [英]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M].曾令良等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14] 陈安. 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再论ICSID体制赋予中国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全面拆除[A]. 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4卷第3期[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overview.
[16] Vivian H.W. Wang. Investor Protection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CAFTA[J],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2007, 32 Colum. J. Envtl. L. 251.
DisputeSettlementBetweenForeignInvestorsandHostGovernmentsinLow-CarbonEra——China’s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s Example
LiuWan-xiao
(Law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0014)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signed by China generally provid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investors and host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e majorit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recently signed by China allow investors to submit the dispute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ontex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globally, as a power country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hina has the obligation to control an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o tak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which may damage or impact interests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Foreign investors might submit the dispute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under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erefore China may bear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to the foreign investors for that purpose ru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must re-examin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investment disputes settlement between investors and host countrie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climate change; low carbon;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vestment disput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002—6274(2012)06—095—08
DF964
A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十九批面上资助项目: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低碳时代的国际投资新规则(20110490504)、山东省2012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国际投资中的环境保护法律规制研究(J12WB08)、山东政法学院科研发展计划项目:低碳时代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投资规则演变及对策研究(2012F08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万啸(1971-),男,山东聊城人,山东政法学院经济贸易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环境法学。
(责任编辑:张保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