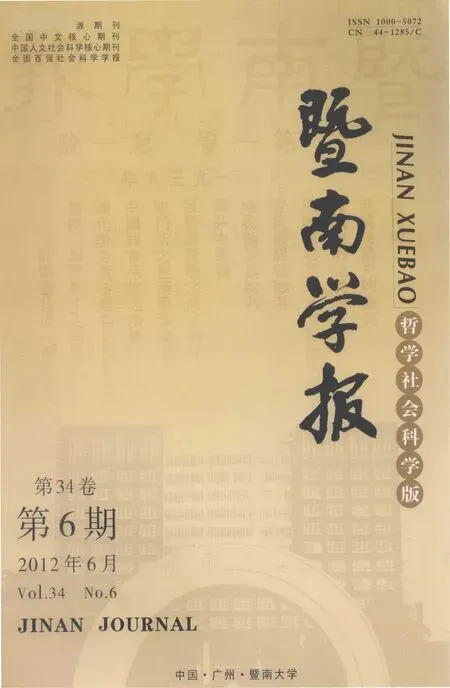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女性个体书写
——论严歌苓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
刘 云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合肥 230039)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女性个体书写
——论严歌苓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
刘 云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合肥 230039)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具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性格特点,也就是既具有传统儒家文化里中国女性温柔、顺从、忍耐的特性,也具有基督式的牺牲、宽恕和博爱精神,而且这两种性格特点是完全“融合于血液里”、难分彼此的。这一特征在她的《少女小渔》、《扶桑》、《金陵十三钗》几部小说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使得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内涵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动人。严歌苓小说中女性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单纯、善良及美好人性,对于人们反思当下社会中堕落、阴暗、污浊的人性很有现实参照性;她塑造这些人物所采用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补共融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严歌苓;儒基交融;女性形象
一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各自以其深厚的宗教、哲学思想在中西方绽放出绚烂的文明之花。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虽然一个主张现世的人本主义、一个主张天国的神本主义,却都共同着眼于对美好人性也即对善的超越性追求,这可以说是两种文化共同的特质。儒家文化最终将人性本善归于“仁爱”,并衍生出忠、孝、悌、慈、恕等等伦理道德观念;而在基督教文化中善则表现为博爱、宽恕、牺牲等所谓“爱的教义”,“爱”也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范畴。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这些方面的内在一致,成为二者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基本前提。实际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从没有停止过,但是,在全球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探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文化在更深入、更理性的层面进行对话和汇通,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现状,也是二者各自克服现实危机、实现内在提升的迫切需要。在当前情况下,任何一种文化想要脱离其他文化“独善其身”、自给自足已不可能,不同文化只能在交流对话中达到互补共融,从而促进各自的发展,这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也是受到举世关注的历史趋势。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就曾经说过:“我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偏于伦理的道义”,缺少西方文化那种“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对于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是什么,他进一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二是伟大的宽恕精神,三是平等的博爱精神。在此基础上,他还认为在培养耶稣式人格和情感的时候可以抛弃基督教“那些古代不可靠的传说、附会”,也不必固守基督教“那些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而是“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1]417。不难看出,陈氏在这里当然不是希望国人都转去信仰基督教,而是希求借助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来重塑礼教束缚下的中国人的心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国旧有儒家文化的不足,创造出一种比儒家以家庭(族)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更为广泛的、更符合人本主义的新文化。陈氏这种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思想在当时效果如何我们已无从考察,但反观当今社会,虽然距陈氏那时过去已近百年,我们却仍然不得不承认,他关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补共融的设想对于现代国人仍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以此来观照严歌苓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恰恰体现出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性格特点。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女性温柔、善良、顺从、宽容、坚忍,总是在男人背后默默奉献与牺牲,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所宣扬的博爱、宽恕、牺牲的精神不谋而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常常既具有传统儒家文化里中国女性温柔、顺从、忍耐的特性,也具有陈独秀所推崇的基督式的“美的、宗教的纯情感”,她甚至会直接采用基督文化中的词语来形容她笔下那些中国女子,比如她说扶桑“母性中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2]92。这是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种自然流露,也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在她身上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这两种特点在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身上往往是完全“融合于血液里”、难分彼此的,这也使得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因而也更为动人。
二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早期小说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奖,在电影获奖感言里严歌苓曾说:“《少女小渔》抒发的是对所谓输者的情感。”按照现代社会功利的眼光来看,小渔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输者,她的善良总是被人践踏,但是她输得心甘情愿,是一种“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输”。小渔就是安徒生童话里那个美丽、善良、甘愿牺牲自己以成全他人的小人鱼的化身。对践踏她善良的人“不是怨愤的,而是怜悯的,带点无奈和嫌弃”,这份怜悯使她比那些处处想占她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更为“优越、强大”[3]129。小渔不是一个基督徒,她只是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普通的中国女子,但是小渔的善良无疑带有基督式的博爱色彩,与传统儒家文化所宣扬的仁爱有明显不同。
儒家对于仁爱的追求,其前提是人性本善论,在这个基础上,儒家倡导人通过自我修养来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道德,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思想体系”[4]76。在儒家学者看来,“通过不断地完善人性、认真地修养美德以及普遍地实际践行爱的方式”[5]95,人人都可以达到“仁爱”的最高境界,从而成为“圣人”。“但是无论是爱亦或不爱,无论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地去爱,无论是为爱而爱或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爱,这些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而如何选择则依赖于人们自己的道德成就”[5]267,缺少外在的推动力与监督,这也容易使所谓“成仁”的过程因为人性中天然的惰性而沦为空谈。当“仁爱”被扩展为“三纲五常”成为一种统治思想时,“仁者爱人”也似乎更趋向于一种政治宣言和策略,成为一种“适用于王侯、君子和学者的政治智慧”[6],因此难免成为陈独秀等新文化战士眼中狭隘的旧文化。另外,儒家把这种自我道德修养的基础首先建立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亲”之上,也即“把血亲之爱看成是普遍仁爱的本源根据”[7]333,这就导致一个明显的道德悖论,即儒家虽然试图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理念把仁爱由血亲之爱向普世之爱推行,并把普世之爱作为最高理想,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血亲之爱,与此同时又缺少对于普世之爱的有力引导及外在推动,所以当血亲之爱与普世之爱发生冲突时,儒家往往舍弃普世之爱而维系血亲之爱[7]335,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自私本性的肯定。由此便演化出一系列的国民劣根性,其中明显的一点就是利己主义盛行,而漠视他人或者公共的利益。
《少女小渔》中的江伟就是一个典型地体现着这种国民劣根性的男人。他为了尽快获得绿卡,竟然可以让自己的女朋友小渔去跟一个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在小渔与这个老头同居期间,他又因为这个事情跟小渔斤斤计较,仿佛自己吃了大亏。与此同时,小渔身上所体现出的善良与宽容却同江伟的自私自利与狭隘形成鲜明对照,更多显现出一种基督式普世之爱的特征。基督教文化中宣扬的爱是一种神性之爱,源自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爱”“是两个方面的统一体:一是对上帝的爱,而另一面则是对他人的爱”[5]247。“爱人如己”是耶稣基督的行为准则,这里的“他人”包含自己的父母、兄弟、朋友、陌生人甚至敌人。《圣经》中有言: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马太福音》5:44)。又言: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福音》5:39~40)。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文化建立起一种基于神爱的普世之爱,明显区别于建基于家庭之爱的儒家之仁爱,在某种程度上恰可弥补略显狭隘的血亲之爱的不足。
小渔曾经为满足一个喜爱了他一年多的垂死病人的渴望,献出自己的身体;为了实现江伟的愿望尽快取得居住证,她答应和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她对江伟无限包容和忍耐,像母亲容忍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她和老男人领了结婚证那天,江伟似乎比她还要委屈,故意找茬子冲她发火、对她粗暴无礼,“她没挣扎,她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恃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8]8。她还以自己的善良、宽容和关爱感动与影响了跟她原本只是一场交易关系的那个落魄、自私、甚至有点无赖的与他假结婚的意大利裔老头,使他重新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感。这些都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具体表现,而且是一种自我奉献的爱。
三
严歌苓在塑造长篇小说《扶桑》中的女主人公扶桑时,也渗透进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文化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小说中的扶桑对于苦难的生活态度上。扶桑也像小渔一样温顺、善良、乐观,而且极其能够忍耐,无论周围环境多么困苦,她都能坦然地接受并使自己乐在其中。她从中国被拐卖到大洋彼岸成为妓女,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却依然能够自足地生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这种智慧与儒家世俗的生活观念有潜移默化的联系。儒家文化重视现世的生活,“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生的过程要尽量做到舒适、愉快,可以享受生活的快乐。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儒家文化要求人们顺天知命,安于现世的生活,从而造就了中国人平和、乐观与忍耐的特性。这种特性在扶桑、小渔身上以及严歌苓所塑造的其他女性人物身上都得到鲜明体现。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一生经历了战争、动乱、斗争、饥饿无数,却始终能够以平和、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困苦,并滋养着身边其他人。《小姨多鹤》中的朱小环、《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继母》中的江璐等等莫不如是。但是,扶桑对于苦难相对于上述人物来说,更带有一种主动迎合的意味,而不只是被动接受,这就与传统儒家文化所谈的“顺天知命”有了明显不同,而更加倾向于基督教文化中强调的“受难”。
受难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重要概念。基督教文化追求生命的超越与永恒,认为追求肉体的享乐会使精神陷入黑暗的迷途,只有摒弃世俗的享乐才可能达致灵魂的永生。《约翰福音》中说:“爱他生活的人将失去他,恨他在尘世的生活的人却保持他的生活至永恒。”因此,受难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人通过主动追求身心苦难的行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方式。严歌苓在小说中用“受难”这个词来描述扶桑,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对扶桑而言,受难虽然不是为了追求灵魂永生,因为她并不追求天国,但受难是她生活的一种常态,是她生命的构成形式,她的生命过程就在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苦难。因此,“她对自己生命中的受难没有抵触,只有迎合。她生命中的受难是基本,是土和盐,是空气,逃脱,便是逃脱生命”[2]222。所以,当扶桑被当地教会组织的拯救会从妓院里“解救”出来之后,扶桑并没有感到从苦痛的生活中获得解脱的喜悦,相反,她为失落了原来的生活感到不知所措。在大勇的帮助下,她又逃回了妓院,因为只有在这里,她的精神与心灵才是属于她自己的,才是自由的。可见,扶桑这样一种对待苦难的态度在出发点上是儒家的“顺天知命”,但却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受难精神形成一定的重合,那就是不愤怒、不逃避,在对苦难的超越中使精神始终保持自由并得到升华。这种精神在扶桑对于自己人生归宿的选择上也鲜明地体现出来。扶桑身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是大勇,那个本应与之结婚的中国男人;一个是克里斯,她心里真正爱着的白人少年。当大勇被判处死刑之后,扶桑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爱情,在刑场上与大勇结婚,然后捧着他的骨灰回中国,这既是儒家伦理道德规约下对婚约的责任感使然,更是一种对于受难的主动选择,虽然这一举动背后意味着扶桑回国后不得不忍受几十年的孤苦生活,但是通过这种受难,扶桑可以得到心灵的认同与灵魂的超脱,这对于她而言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对克里斯这个从十二岁就对扶桑充满好奇与爱慕的男子而言,她用自己充满母性的爱成为克里斯从男孩成长为男人道路上的引导者,并且宽恕了他15岁那年对她犯下的强奸的罪过,她对克里斯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男女之爱,却又带着“圣母一般的宽容”[2]220。“圣母一般的宽容”是成年之后的克里斯对于扶桑的评价,也是以基督精神来观照扶桑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克里斯看来,扶桑身上即具有陈独秀所说的“伟大的宽恕精神”,她以跪着的方式,宽恕了那些轮奸她的白人男子,其中就包括克里斯:
扶桑没有接受过强奸的概念……扶桑只感到那些拖她进马车的男人更粗鲁些、更狂野些,对她更饥渴些。她把它当做无穷尽的受难的一章,不同寻常的一章。……她只接受了那些事情中的受难,而没有接受其中的侮辱,她就那样宽恕了人们。[2]222
宽恕是基督精神中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圣经》中言:“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福音》6:14)。“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马太福音》5:44)。在基督教看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原罪,原罪的产生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消弭了人在现实中向善的能力。在罪与不罪的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有罪的,这也就意味着大家在道德的层面上都是等待被上帝宽恕的罪人,因此宽恕他人的罪过不仅能够拯救有罪的灵魂,也是实现个人救赎和精神升华的一种方式。扶桑心中虽然没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宽恕的概念,但是她的行为却又切切实实使克里斯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宽恕,个中缘由除了扶桑本身即具有的宽容性之外,还有克里斯因为自己对扶桑所犯下的错误而深切地感受到他自己是一个有罪之人,那个罪过虽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却遭受心灵的煎熬,能被扶桑宽恕是他心灵得到救赎的重要途径。对扶桑而言,这种宽恕消解了罪恶行为给自身带来的肉体及精神伤痛,弥合了地位、阶级、肤色、性别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她得以在灵魂层面实现超越。这是基督教文化之博爱精神最崇高的体现。
四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又一部以妓女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这次,严歌苓把这些妓女放到了1937年底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中,在非常态的时空中凸显人物非同寻常的精神。《金陵十三钗》中以赵玉墨为主的十三位妓女身上,也蕴含着较为鲜明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融合的文化特点。
这些妓女们虽然出身卑微、身世凄惨,但是这并不妨碍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对她们的影响,肮脏的环境也没有磨灭她们内心纯良的本性。天真的豆蔻为了能在小兵死前为他弹奏一曲《秦淮河》而冒险回妓院取琴弦,结果命丧日本兵手下。在最危急的时刻,赵玉墨和她的姐妹们愿意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女学生们的清白,也是因为她们心中保有“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传统道德观念,她们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报答教堂对她们的收留。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的妓女身份有着深刻认识。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之下,妓女无论如何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负载着深厚的道德罪孽。对于这一点,赵玉墨和她的姐妹们都很清楚。赵玉墨下面的这番话是一针见血的:
好,有种你们就在这里藏到底,占人家的地盘,吃人家的口粮,看着日本人把那些小丫头拖走去祸害!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藏着吧,藏到转世投胎,投个好胎,也做女学生,让命贱的来给你们狗日的垫背![9]211-212
这番话里充满悲哀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抗拒,但是抗拒归抗拒,她们还是心甘情愿地认了命,并且以自己“低贱的命”去为那些“高贵的命”“垫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显然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然。但是这一行为又明显带有基督式自我牺牲的色彩,尤其这样一种行为是发生在一座教堂里。虽然英格曼神甫对于要进入这所教堂避难的中国人最初的反应都是极力排斥的,但是当他们真的进来之后神甫的态度就悄然发生转变了,又是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并且尽一切方法和能力保护他们,给他们提供食物。对于这些,赵玉墨不可能不看在眼里。尤其是神甫面对凶残的日本兵仍极力保护中国军人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会为之感动。神甫的行为感化着赵玉墨们,也就是上帝在感化着她们。教堂里的人们最后成为一个患难与共的整体。所以当神甫希望这些妓女能够救那些女学生却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而迟迟不能开口之时,赵玉墨自己首先提出去顶替女学生到日本人那里。我们不能否认上帝的影响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小说是这样描写她们最后的离去的:
二十分钟后,厨房的门开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她们微垂着脸,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每人的胳膊肘下,夹着一本圣歌歌本。
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了梦的美化。
……她们个个夺目。[9]214
这是一段富有象征意味的描写,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人类甘愿走向十字架牺牲自己,赵玉墨和她的姐妹们为了救下女学生挺身而出奉献自己。她们通过这种行为在上帝面前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救赎,因此变得高贵而美丽。在临走之前,英格曼神甫给每个女人划十字祈祷,这些女子也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五
严歌苓是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作家,因此她对生活中的弱者更为关注,女性在生活中常常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善良的女性尤其如此。严歌苓推崇女性身上类似原始本能的“善”的特质,她认为,每个女人“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3]129。她为某些现代女性出于某种功利性目的而失落了这样原初的本性扼腕叹息,因而她要为那样善良美好的处于弱势的女性书写,唤回现代生活中失落的古典美。由此可见,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极力表现女性身上的柔顺、善良的特质,这种特质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所赞赏的,严歌苓把中西文化中最美好的特质融为一体赋予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在她们身上展现一种超越功利性的温柔、善良之美,宣扬甘愿牺牲与奉献的纯爱,把陈独秀百年前所希求的西方“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孕育的中国女性之善良完美地结合起来,将陈氏所言的“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融合到她笔下中国女性的血液里。严歌苓认为“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3]129,所以,严歌苓小说中女性的善良不仅仅包含“亲亲之爱”,而且扩及他人乃至世界,具有普世价值。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爱是传统儒家文化所欠缺的,也是当下中国社会越来越稀少的。陈独秀批判中国的伦理道义缺乏情感,即使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色彩”[10]88。这种批判放到当下社会似乎仍然没有失掉其现实针对性,他所言的物质的、功利的色彩不仅在文学中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也愈演愈烈。从这个角度来看,严歌苓的小说对单纯、善良、美好人性的塑造,对于人们反思当下社会中堕落、阴暗、污浊的人性是有很大意义的。
与此同时,严歌苓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所采用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补共融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基督教文化中以博爱、宽恕、牺牲精神为内涵的“爱的教义”在弥补儒家仁爱文化的不足,重塑国人被物质、功利扭曲的心灵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基督教文化中由“上帝之爱”为出发点的“神爱”所隐含的宗教仇恨,却也是造成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的思想根源。可见,无论是儒家之仁爱还是基督教之神爱,最终都没有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窠臼。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单靠一种文明已经难以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由神学家孔汉斯(Hans Kung,也译作汉斯·昆)倡导的“全球伦理”观念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响应,并且签署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倡通过宗教、文化的对话交流建立一种“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或态度”[11]171,以解决目前存在的全球性危机。《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另外一位重要倡导者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在《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中也深入探讨了全球伦理的问题,并且提出一种基于人类文化共性或者说共同人性的“金规则”,即“自爱与他爱”[12]46-49,都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严歌苓小说中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交融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纯爱、纯美与孔汉斯所说的全球伦理以及列奥纳德所提倡的人性“金规则”不谋而合,有助于我们在伦理道德失序的今天用一种更为开放、积极的文化观念重塑我们的传统文化,唤醒失落的人性之美,如是,则善莫大焉。
[1]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M]∥独秀文存.上海:亚东书局,1922.
[2]严歌苓.扶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3]严歌苓.弱者的宣言[M]∥波西米亚楼.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4]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姚新中.儒家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M].赵艳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美)谢大卫.“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J].文史哲,2011,(4).
[7]刘清平.论普遍之爱的可能性[C]∥罗秉祥,谢文郁.耶儒对谈(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9]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10]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M]∥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1]孔汉斯,库舎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2](美)L·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M].刘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106.4
A
1000-5072(2012)06-0037-06
2012-01-06
刘 云(1978—),女,安徽淮北人,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