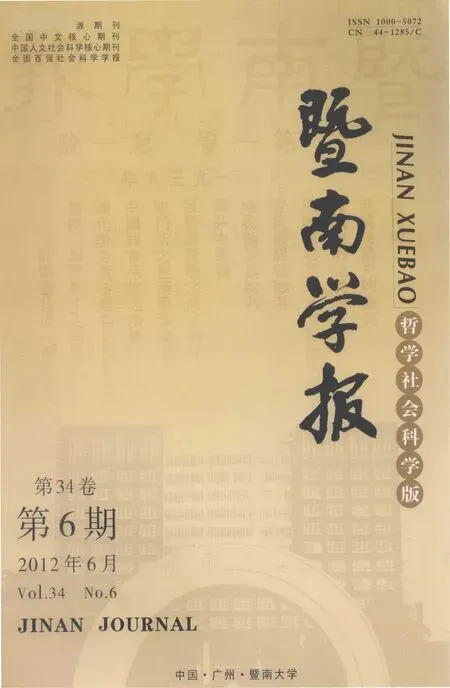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
孟 琢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
孟 琢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长期以来,语言文字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主流论断对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出现了误读或误解。太炎先生的国学包括国学、国粹、国故三个重要概念,语言文字学是其基础,思想史是其核心。通过对其国学概念原旨的阐释,对其学术思想和国学实践的追根溯源可知,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具有高度的实践品格与自觉的现代精神,他的国学研究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国学实践与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密切相关;在弘扬国学的同时,他对国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现代反思,积极探索国学的现代形式。当然,他在推广国学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教训。太炎先生的国学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章太炎;国学;语言文字;小学;国学研究
国学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文化命题。在学术史上,章太炎先生是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他的学术体系恢宏博大,占领着国学诸多领域的前沿。遗憾的是,学界对章太炎的国学一直存在三方面误解:其一,多从狭隘的“小学”角度审视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术思想,或责之过苛,或不见其全;其二,自鲁迅以来,学界多认为太炎先生晚年成了与社会隔绝的学者,指责其国学研究脱离社会实际;其三,认为太炎先生是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其国学研究被视为复古守旧的文化立场。本文将着重阐述太炎先生国学概念的原旨,梳理其国学思想的实质内涵,探讨其国学研究蕴含的实践品格与现代精神,以期澄清对太炎先生认识和评判上的偏颇,准确理解太炎先生的国学特性与意义,为我们认识国学的实质、处理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提供启示。
一、章太炎的国学基本概念原旨
章太炎的国学体系体现在他对“国学”的界说中。在章氏论著中,“国学”、“国粹”、“国故”等概念并出错见,用来指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具体而言:
“国学”指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讲学科目为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1912年,章太炎任国学会会长,讲学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和子学;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讲授内容为国学之体、治国学之法(辨伪学、小学、地理和人情社会之变迁)、国学之派别(经学、哲学和文学)和国学之进步;1934年,章太炎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授课内容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我们看到,太炎先生所主持的传统文化教育组织皆以“国学”为名,其讲学内容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方面。
和国学相比,“国粹”偏重于特性,指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成分,即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1902年,章太炎在《訄书》中指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1]323认为国家、民族的维系在于语言、风俗和历史,这一论述是其国粹思想的滥觞。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表演说,号召“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2]276此处的国粹指广义的“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由于后两者属于历史的范围,章太炎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中国之小学及历史”,强调“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3]295至此,章太炎对“国粹”的界定基本定型:
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3]345
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4]444
《自述学术次第》撰于1913年,是章太炎对前半生学术的总结。《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撰于1933年,更为晚年定论。在这两篇时隔二十年之久的重要文献中,太炎先生指出,“国粹”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是民族的特质所在,足见国粹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一贯性和重要性。至于“国故”,则偏重于传统方面,与“国学”、“国粹”多有交叉。它或指语言文字,或指历史,还包括了诸子学和文学,这一概念和“国学”基本上是等同的。
章太炎对“国学”、“国粹”、“国故”的界定涵盖了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具有清晰的学术逻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小学”和民族历史是核心部分。
首先,由传统“小学”发展而来的语言文字之学,是章太炎国学的基础。太炎先生是乾嘉朴学的殿军和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开创者,他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语言学学术思想意义。对此,陆宗达、王宁在《章太炎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论章太炎、黄季刚的〈说文〉学》等文章中进行了精审的论述。章太炎使“小学”真正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发展出一门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把旧小学转变为近代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章太炎应当是有功绩的第一人。”[5]327在《訄书》、《国故论衡》等著作中,他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论体系,包括语言文字的发生、发展的理论,汉语和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理论,语言文字演化、统一的理论,等等。[5]326-329在《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等著作中,他以《说文》学为核心,在“小学”的各个领域充分拓展了前人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学术业绩。“小学”在章太炎的国学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他指出:“合此(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种学问,汉《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字古言,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6]9在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同时,“小学”和史学、子学、文学建立了全面的联系,成为一切传统学术的基础。这一转变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小学”的研究对象充分拓展,不再限于解读经籍的工具,这为其注入了新的血液,实现了“小学”的新生。另一方面,语言文字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科学的语言文字学能够准确地还原典籍、追溯思想。太炎先生把“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这就使国学研究具有了充分的实证性与可信性。
其次,“历史之学”是国学的基本属性。实际上,由文字、音韵、训诂构成的“小学”,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对语言文字历史和变化的深究,通过语言文字的历史探究,去研究它所承载的深厚的民族思想历史。章太炎对历史的界定较为宽泛,在他的国学体系中,经、史、子、集均为先人之遗迹,具有“史”的性质。这一态度与他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有关。在当时,康有为等人主张今文经学,站在经世之学的立场上,强调经典的现实应用。太炎先生则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古文经学,站在历史之学的立场上,强调经典的客观还原。他指出:“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4]104“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4]148从“史”的角度理解国学,使国学避免了追随时政、牵强附会的弊端,成为了还原历史、探究本来的实学。
以“小学”(语言文字之学)为基础,以史学为属性,构成了太炎先生的国学体系,奠定了其国学体系求真务实的基本特色。
二、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的实践品格
鲁迅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了一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这篇文章在学界影响很大,学界往往将鲁迅的评价作为对太炎先生的“盖棺定论”,认为太炎先生晚年“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7]545学界也经常将太炎先生的革命行为和国学研究区别开来。事实上,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始终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现实指向。在他投身革命之际,对国学和革命的关系已有清晰认识。他自称“兄弟从前主张推倒满清,所以要研究国学;因为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推翻满清。研究国学与推倒满清,表面看来是两项事,其实就是一项事。(《我们最后的责任》)”[3]828认为国学研究和社会改造互为表里、不容割裂。这一思想贯穿了太炎先生的一生,他在对平生学术的回顾中指出:“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4]254汪荣祖先生指出:“转俗成真是求是的过程,回真向俗是致用的过程。‘真’指思想体系,‘俗’指实际问题。”[8]94章太炎的国学研究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始终与社会改造互相推动、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这是其国学的基本特色。正如王宁先生所论:“章太炎的国学研究与传播,是他从精神层面救国图强方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他创建新型民族文化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的。”[9]17具体而言,章太炎国学的实践品格体现为两个层面: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前者是他对国学的思考与探研,后者是他对国学的传播与讲授。在这两个层面中,“小学”和史学均有重要的意义。
在思想层面,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抱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他把国学、国粹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认为一旦国粹沦亡,必将亡国亡种。因此,章太炎的国学是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的①章太炎早期用“民族主义”来指称这一思想,与当时的思想环境密切相关。但“民族主义”多被误解为“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而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主张种族平等的。故本文不采用“民族主义”这一称谓。: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国学讲习会序》)[3]215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重刊古韵标准序》)[10]203
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辟之于身,支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澌。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孽,国粹沦亡,国于何有?(《华国月刊发刊辞》)[4]347
章太炎的民族独立思想形成于他的青年时期,他激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获得近代民族意识,从而参与变法、革命的运动。因此,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号召中国各民族和衷共济,反抗清政府的专制压迫和国外殖民势力的侵略,建立独立自强的近代民族国家。章太炎的国学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具有以下原因:其一,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危机的积极回应。在西方文化殖民的冲击下,“外人所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清美同盟之利病》)”[3]282章太炎倡导国学,是要以民族文化与列强的文化侵略相抗衡,抵制仰慕西方物质文明、盲目数典忘祖的时潮。其二,这是他对顾炎武、戴震等清代思想家的深刻继承。“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3]265章太炎自幼尊崇顾炎武,顾氏在明亡之后对语言文字和历史遗迹殚精考索,是要通过“小学”和史学来弘扬民族意识,抗清排满。章太炎把语言文字和历史作为“国粹”,以此追求民族独立的理想,无疑受到了顾氏的内在影响。其三,这是他对世界历史深入考察、反思的产物。在历史上,侵略者想要奴役一个民族,往往先扼杀其国粹:“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1]323而一个民族的语言和历史更是其得以复兴的精神基础。波兰被俄罗斯侵占期间,“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间,犹私习故言以抒愤懑,故露人侦伺虽严,而波兰语犹至今在,其民亦忼慨有独立心。(《规新世纪》)”[11]3784“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10]366波兰独立的史实、印度思想家的观点,均与太炎先生遥相呼应。他把民族独立思想作为国学的核心,实具有世界性的视野。
具体而言,章太炎对语言文字和历史在民族独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在语言文字方面,章太炎提倡“小学”,是为了唤醒“爱国保种的力量”,通过语言文字之学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12]26《文始》旨在探求汉语的语源系统,“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小学答问》旨在规范汉语的书写方式;《新方言》旨在考证汉语方言的历史源头。这一系列的研究都具有追源溯本的特点,太炎先生的用意是要发掘语言文字背后的久远深厚的民族历史,从而深化民族情感、树立民族精神。他把汉语和文字视为民族和国家的特性。针对吴稚晖等人废除汉语、采用万国新语的观点,太炎先生激烈驳斥,指出:“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民弃国语,不膏沐于旧德,则和悦不通,解泽不流,忘往日之感情,亦杀其种族自尊之念焉,得不比暱白人而乐为其厮养耶?(《规新世纪》)”[11]3784强调废除汉语的结果是丧失国性,使中华民族沦为异族的奴隶。在历史方面,章太炎认为历史是“民族意识”的基础,维系着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民族意识之凭借,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论经史儒之分合》)”[13]249章太炎指出,读史能够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2]279中国历史肇端于《春秋》,“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伯于禹邪!”[12]305因此,孔子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是中国史学的奠基者,而不是康有为等人所说的“孔教”教主。在章太炎的一生中,他不断用历史来鼓舞人心、唤醒民众。1902年,他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写道:“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10]189用抗清志士的流风遗韵来唤起革命的激情,这是章太炎对这一理念的首次尝试。1935年华北危机,太炎先生已是68岁的老人,仍力倡历史对于民族的意义。“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磅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3]211次年六月,太炎先生魂归道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仍然饱含忧患地提倡民族历史、唤起爱国之心,实是历史留下的感人一幕。
在实践层面,章太炎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毕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他的社会改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参与、精神建设。前者是他投身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独立民主的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后者是他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通过著述、讲学等方式来弘扬国粹、传播国学,创建新型民族文化的文化实践。在太炎先生看来,精神建设无疑更为重要,“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恃所有之精神。(《驳康有为论革命书》)”[2]206因此,章太炎的国学不仅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更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孜孜践行,他以毕生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光辉榜样。
王宁先生对祖师太炎先生1911年以前的行年做了考证和研究,证明太炎先生将革命与学术融为一体。[9]3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更为复杂,太炎先生常处迫害之中,但初衷未改。此处谨将其1931年以后的行年略述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章太炎身处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之中,不得不保持缄默,但心情极其愤怒。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章太炎忍无可忍,会同熊希龄、马相伯等人联名通电,痛斥当局;2月,赴北京会见华北各地将领,用历史上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的事迹打动他们抗日;3月,发表《论今日切要之学》的讲演,强调“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3]919;6月,在苏州组织国学会。
1933年,章太炎多次发表宣言、通电,呼吁抗日,支持冯玉祥领导同盟军抗战;1月,发表《国学会会刊宣言》,提倡“行己有耻”的道德;3月,发表《国学之统宗》、《历史之重要》等演讲,提倡“气节”,指出“设日人一旦进灭中国,使汉儒在,决不屈服于日人,若在南宋轻视气节时,则未可知矣。”[13]166主张国学以四部经典为本:“《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4]438
1934年,章太炎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多次讲学。
1935年,章太炎继续围绕读经、读史的问题进行讲学,强调通过读史“发扬祖德,巩固国本”;8月,讲习会刊发《制言》杂志,以“复兴国学”为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要求保护学生,命汤国梨夫人率章氏国学讲习会代表慰问请愿学生。
1936年,章太炎鼻症加剧,仍讲学不辍。5月,复信蒋介石,奉劝国民政府切实抗日;6月14日,太炎先生逝世,在去世之前数日仍坚持讲学,并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言。
以上仅为太炎先生晚年国学实践、社会活动的吉光片羽。在民族的危难关头,他并没有与时代“隔绝”,而是讲学不辍、阐扬国粹,辨明民族大义,树立爱国情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中去。章太炎的晚年讲学重视“气节”,大力弘扬《儒行》中刚烈勇毅的精神,提倡范仲淹、顾炎武的志行。这与他早年所讲颇有不同,均针对日寇侵华、民族危机而发。由此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讲学实为救世之论,他的国学积极地回应着时代的要求。
总之,太炎先生的国学思想以民族独立思想为核心,始终关切着民族、国家的命运。他的国学实践与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密不可分。因此,章太炎的国学研究是“回真向俗”的,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从未和时代隔绝。与此同时,革命和社会改造又为章太炎的国学提供了潜在的滋养。“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4]145对革命成败的反省、对中国历史的思索、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全面影响了章太炎的国学思想。可以说,正是国学与社会改造的融合,成就了太炎先生恢宏博大、深刻精微的国学体系。
三、批判与反思:章太炎国学的现代精神
章太炎主张弘扬国粹,多被批评者误解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事实上,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不仅是继承的,也是反思的。前文指出,国学研究与章太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他弘扬国粹并非复古,而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略。在这一过程中,章太炎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下①章太炎早年担任《译书公会报》主笔,广泛涉猎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语言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论著。如此系统地吸收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并不多见。,以史为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现代反思,并积极探索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形式,体现出自觉的现代精神。
太炎先生对国学进行了自觉的批判与反思。他要通过对国学的反思探求现实弊端的历史根源,从而达到清源正本的目的。以儒家为例,1906年10月章太炎发表《诸子学略说》,对传统儒家进行深刻反思,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3]218同月,章太炎发表《革命之道德》一文,指出以往社会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懦怯庸俗,立足于历史教训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的革命道德。次年,他再度申说此义,指出“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14]179从热衷利禄的角度对儒家进行反思,切中了历史上众多儒者的弊病,并为当时的革命者敲响了警钟。从时间和内容上来看,章太炎的儒学反思与他对革命道德的思考融为一体,这也体现出其国学研究的实践品格。太炎先生的国学反思是全面而深入的,对孔子之后的儒家,他认为西汉儒者杂糅阴阳、墨、法之学,对封建专制阿谀逢迎,开启了严刑酷法的恶例;清代汉学的流弊在于“病在短拙,自古人成事之外,几欲废置不谈。(《致国粹学报社书》)”[2]498至于清代今文经学,更“以文掩实,其失则巫”,背离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除此之外,他对道家思想、“小学”、史学、古典文学均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鞭辟入里的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太炎先生堪称第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仅对国学进行反思,对自己弘扬国粹的文化立场也进行了自觉的思考。他秉持多元的文化理念,早在1894年,章太炎在《明独》中指出“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15]2开始思索特殊性和多元性的辩证统一。1901年,他在《征信论》中批评历史研究中的“平议”,反对用体系和教条来割裂历史,强调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是对这一思考的延续。1910年,他在《齐物论释》中系统阐释了庄子“以不齐为齐”、“物畅其性,各安其所安”的思想,在哲学高度上阐释了多元文化观。我们认为,太炎先生弘扬国粹的实质是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他对国粹的坚守不仅源自深厚的国学素养与诚挚的民族感情,也来自理性、宏观的文化反思——这一反思的态度也体现出章太炎国学的现代精神。
在对国学进行反思的同时,章太炎更积极探讨了国学的现代形式。以“小学”为例,在继承乾嘉“小学”的同时,章太炎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小学“滞于形体”的缺陷。在西方语言学的启发下,他将乾嘉“小学”改造为“语言文字学”,确立了它的研究范围,真正确立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在近代科学中的学术定位。他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理论体系,在《说文》学、音韵学、方言学、词源学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突破。在音韵学上,他首次提出了一套声母系统,发现了“娘日归泥”的语音规律,将队部独立,为脂微分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方言学上,他提出了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为方言学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在词源学上,他的《文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对后世的词源学研究影响深远;《成均图》揭示了汉语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内在关系①有人批评太炎先生《成均图》“无所不转”,有失偏颇。关于这个问题,前文提到的陆宗达、王宁的两篇经典论文已有系统评述。两文都收入《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本文不赘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诚如姚奠中先生所言:“太炎先生的学术,不仅是三百年‘朴学’的总结,而且是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总结;不仅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开辟未来。他面向当时的现实,放眼于未来的趋向,无论在政治、哲学、文化、历史,以至语言文字上,都为走向现代化开了端。”[4]4
总之,章太炎的国学研究具有自觉的现代精神,他超越了复古守旧和全面西化的态度,对国学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并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交点,探索着国学的现代形式。正是由于这种现代精神,太炎先生的国学研究从根本上超越了前人,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四、余 论
通过对章太炎国学核心概念原旨的阐释和学术思想的分析梳理,我们看到,以往语言文字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些论断实际上是对太炎先生国学思想体系的误解:其一,“小学”(语言文字之学)是太炎先生的国学基础,撇开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思想,去谈论“国学”,就成了无米之炊;其二,中华民族的“史”是太炎先生国学的基本属性和目的,正是这一属性使他的国学体系浩瀚磅礴。因此,仅限于“小学”研究中个别文字音韵细节,对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学说体系进行过苛批评,显得偏颇笼统、不得要领。其三,太炎先生的国学和社会忧患和改造意识从未隔绝分离过,只有在二者的融汇、互动中,才能准确理解他的国学研究。其四,章太炎提倡国粹,并非复古守旧,而是要在立足民族自身文化本位的基础上进行新文化的建设。他对国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积极探讨了国学的现代形式,我们要充分认识其国学研究中的现代精神。总之,只有立足于章太炎的国学体系,从实践品格和现代精神的层面去理解他的国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其国学的实质与意义。
章太炎的国学具有充分的实践品格与现代精神,正因如此,它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具体而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应该把哪些内容作为国学的核心?在多元文化观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我们提倡国学的意义何在?国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自五四运动以来,思想家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何把这笔精神财富融入到国学中去?这些问题,都是国学必须解答而又难于解答的问题。太炎先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指出了一条值得我们参考的道路。他深邃的思想洞穿了历史的空间,令人感佩不已。
当然,在继承太炎先生国学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他的国学长期被学术界误解?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章太炎逐渐脱离了思想界的主流,他的思想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他艰深晦涩的表达方式有关。太炎先生的文章古奥,多用本义,在客观上脱离了社会大众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内容上,他的国学是实践的、现代的;在形式上,他的国学又是书斋的、文言的。艰深的魏晋文章阻碍了现实关怀,古奥的论说方式掩蔽了现代精神,这无疑是历史的遗憾。与之相反,章太炎的弟子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用白话文写作,追求浅易的表达效果,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相比之下,太炎先生的遗憾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5]陆宗达,王宁.章太炎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M].训诂与训诂学.太原: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
[6]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鲁迅.关于章太炎二三事[M].鲁迅全集(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汪荣祖.康章合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9]王宁.章太炎说解字授课笔记前言[M].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民报[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马勇.章太炎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14]马勇.章太炎书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15]朱维铮,姜义华.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王 桃]
H0-09
A
1000-5072(2012)06-0147-07
2011-10-12
孟 琢(1983—),男,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训诂学、汉语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