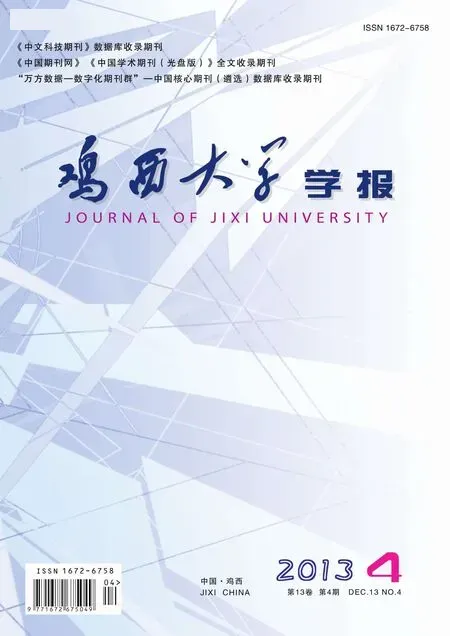《苍蝇》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火花
侯 宁,方 文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苍蝇》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火花
侯 宁,方 文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苍蝇》是萨特早期创作的一部存在主义代表作,是萨特的自由观发生转变时的产物。从分析萨特思想发展入手来分析《苍蝇》一剧中体现其思想转变的内容,包涵了天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火花。《苍蝇》中的无神论思想以及通过实践,“介入”生活来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吻合。
萨特;《苍蝇》;马克思主义思想
萨特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创作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萨特使存在主义由一种抽象的哲学发展成被大众所接受的一种思想,奠定了其存在主义哲学体系领军人物的位置。他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来研究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构造了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因此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探析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哲学价值,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启示。
一 萨特思想发展概况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出生在巴黎。在萨特一岁那年,父亲去世,使他从来没有一般孩子所拥有的“父亲—上帝”的观念,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管束过他,他从来没有感到要服从谁,因为没有人要他服从。[1]萨特后来在自己作品中谈到这个问题,他那时总有一种“没有得到证明的”“多余的”感情。可见,萨特比一般的孩子要早熟、敏感得多,他体验到了许多孩子不可能体验得到的感情。他内心深处一直有强烈的孤独感,而他又忍受不了这“孤独”“多余”的感情,希望能从中解脱,希望能找到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1]1924年,萨特以优异成绩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四年的高师学习,萨特研读了大量古典和现代哲学著作。他尤其热衷于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的著作。“笛卡儿的极其严谨的论证方法及其固有的逻辑力量,使萨特进一步懂得:怀疑一切乃是步入真理王国的开始”。[2]1931年,萨特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一所中学任哲学教师,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哲学家的职责。长期以来,萨特对传统学院式的哲学道路深恶痛绝,认为纯粹的唯心论和用意识以外的东西来解释意识的唯物主义均不能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决心要向传统的理性主义权威哲学宣战,即建立“一种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哲学体系”。[1]1933年9月,萨特被批准为柏林法兰西学院的研究生,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法兰西学院的经历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
战争锤炼人的意志,也造就了伟大的思想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萨特基本上是个“书生”。他那时的著作都偏重于心理分析,偏重于自我内心情感的描述。但战争震撼了他的灵魂,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的自由,不再满足于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解释现实,而且强烈地渴求一种入世的自由,就是一种要深入到现实去的自由”。[2]这一时期,萨特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墙》、剧本《苍蝇》、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部《懂事的年龄》和第二部《延缓》。1943年,标志着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形成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问世。从此,萨特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大战后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吸引了不少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萨特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早在高师学习阶段,萨特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他对马克思思想持复杂态度,甚至对马克思的排斥占主导地位,“至少一直到战争爆发,马克思仍是某种妨碍我的东西,它让我不好受”“我在哈佛尔读过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没记下什么,我看不出这些著作有什么意义”。[3]1946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唯物主义与革命》。在此期间,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明确的,也可以说是矛盾的。1948年,他发表了一部被视为具有反共倾向的剧本《肮脏的手》。1952年,他又与共产党合作并发表《马丁事件》一文。萨特这种不确定的立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一面与法共进行争论,一面又与法共进行合作。直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萨特从此公开与法共决裂。1960年,萨特发表了哲学论著《辩证理性批判》,这部书是萨特的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力作。1968年以后萨特几乎不再著述,而是全力参加活动、支持学生运动。在萨特的最后10年,出版了一部长篇论著《家庭中的白痴》。
二 《苍蝇》解读
《苍蝇》是自由观发生转变时期的产物,这一戏剧可以看做是萨特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的作品之一。
1.《苍蝇》历史语境解读。
1940年6月,德军入侵,以贝当总理和法军总司令魏刚为代表的投降派占了上风,他们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旋即首都巴黎陷于敌手,贝当政府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几周时间里就被德国法西斯消灭了,还未见到战火的萨特便成了德军的俘虏。这次经历使萨特对法军一触即溃的事实“深感惊讶”,也促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自由的思考,开始由战前的抽象的自由转到了处境中的自由上”。[4]于是,他开始用一种新的哲学解释这个世界,并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哲学思想。萨特对西蒙·波伏娃说:“战争教我懂得,我必须承担义务。”[2]对萨特来说,这一切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决意抛弃不关心政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心以笔作武器,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事业中去。[2]
从1940到1943年,在法西斯的侵略下,法国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大多数的法国人灰心丧气。为了“使法国人能从悔恨中解脱出来”,为了“召唤法国人民摆脱战争所带来的萎靡和悔恨的精神状态”,为了“使法国人民重整旗鼓,恢复勇气”,[4]萨特创作了取材于神话、隐喻现实的哲理剧《苍蝇》,试图证明真正可以改变现状走出困苦的途径惟有行动起来去战斗。
2.《苍蝇》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苍蝇》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远征特洛亚归来的阿耳戈斯王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与情夫埃癸斯托斯害死,而阿耳戈斯人不敢反抗,默许了罪行,死神朱庇特派来了苍蝇遍布全城。十五年后,王子俄瑞斯特斯回到了祖国,他站在原本属于他的宫殿前,心中充满仇恨与复仇的欲望。神王朱庇特暗示俄瑞斯特斯不要触动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否则就会引起大灾难,但是俄瑞斯特斯没有顺从这位天神的意思,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复仇之路。最终手刃了凶手,伸张了正义。但这一选择却使他成为了阿耳戈斯人的公敌。他的妹妹以及阿耳戈斯城的城民都反对他的复仇行动。但俄瑞斯特斯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并勇敢地承担了责任。最后,阿尔戈斯人得救了,俄瑞斯特斯却选择了自由并开始了无穷无尽的艰难行程。
《苍蝇》虽然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经典代表作,但我们不难从戏剧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火花。笔者试着从两个方面来谈谈马克思主义对《苍蝇》一剧的影响。
一是贬义宗教。对于宗教,马克思是这样批判的:“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5]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萨特的看法:“神道和国王们感到痛苦的秘密,就在于人类是自由的,上帝却只是别人对于它的神话的恐惧,而决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戏剧的一开场,便向观众展示阿尔戈斯的某一个广场,朱庇特作为万物之神、被人们反复赞颂为“全能、无所不在”的最高权威,却显示出“眼珠发白,满面血污”。[2]这里,萨特有意要冲淡这位万物之神的威风,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权威一贯的蔑视态度。在神王朱庇特暗示俄瑞斯特斯应当屈从命运,放弃复仇尽快离开阿尔戈斯时,他愤怒地断然拒绝,他蔑视神权,面对朱庇特,他大声疾呼“朱庇特,你是众神之王,宝石及星星之王,海涛之王,但你却不是人中之王”。 他拒绝向神妥协:“我不会回到你的法律之下,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在萨特笔下,俄瑞斯特斯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向神权挑战,蔑视神权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重视实践。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国内很多学者都指出萨特的“介入”理论是受马克思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影响的结果,在《苍蝇》一剧中萨特的“介入”思想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俄瑞斯特斯本可以听从朱庇特的诱惑离开阿尔戈斯,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介入”,选择了去实践复仇,最终拯救了阿尔戈斯人。俄瑞斯特斯的妹妹厄勒克特拉则完全是个反面人物。她本是公主,但是在宫里却像奴仆一样地生活着,她心里也充满了反抗和悔恨,她没有一天不盼望着哥哥回来复仇,而一旦哥哥回来手刃了仇人,她又开始害怕,开始悔恨,最终丧失自我,否定了十几年来的仇恨和希望,彻底成为复仇女神的阶下囚。
三 结语
《苍蝇》一剧创作于二战时期,这部借古喻今的戏剧在法西斯占领的巴黎上演时引起了轰动。正如罗杰·伽洛蒂所说:“《苍蝇》这个剧本,是对希特勒占领时期及合作运动的一种讽刺或比喻。”[2]当贝当政府要法国表示悔过时,萨特则通过俄瑞斯特斯的嘴,号召人们保持尊严、进行抵抗。在俄瑞斯特斯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萨特对人的本质、人的意义的肯定,即追求自由。虽然萨特的自由选择论因强调个体的自觉和自由有些矫枉过正,但强调主体的能动选择无疑是他与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因此,在一些思想家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时,萨特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苍蝇》塑造了俄瑞斯特斯这样一个用行动不断进行选择的巨人,他为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安危驱邪恶、撼鬼神。他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的英雄,同时也透漏出马克思主义对其的客观影响。正如波斯特所说,战时萨特的政治思想稳步左移,正是这种左移为其后来走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6]
[1]杜小真.萨特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9,11,18.
[2][法]高宣扬.萨特的密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103,109,112,129,127.
[3]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刘大涛.萨特的《苍蝇在中国》[J].安顺学院学报,2011(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01.
[6]张璐.从《苍蝇》看马克思人道主义对萨特的影响[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4).
ClassNo.:B565.53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MarxistIdeologicalSparkintheNovelTheFly
Hou Ning, Fang Wen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China)
The Fly is a magnum opus of existentialism in Sartre’s earlier work, and it is also the product when Sartre’s conception of freedom changing.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Sartre’s though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ok The Fly, which includes the genius spark of the Marxism. The thought of atheism and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through the living practice in life represented in The Fl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ought of Marxism.
Sartre;TheFly;Marxism
侯宁,在读硕士,云南农业大学。
方文,通讯作者,博士,讲师,云南农业大学。
1672-6758(2013)04-0044-2
B565.5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