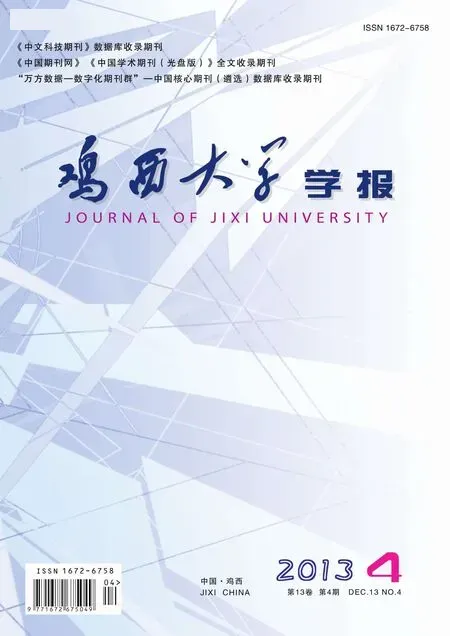试论李翱对韩愈作品风格的接受和发展
施翊飞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试论李翱对韩愈作品风格的接受和发展
施翊飞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李翱作为韩愈后学在接受韩愈古文理论的基础上,实践中进一步学习韩愈的作品风格,从而自成一家。并且李翱进一步发展了韩愈文学观点,弥补了韩愈在作文中的瑕疵之处,对于中唐以及后世的文风改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翱;韩愈;风格
一 李翱与韩愈的师承关系及思想的一致性
李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后世评价颇高。《旧唐书·李翱传》评价他:“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1]皇甫湜在《谕业》中称赞“李襄阳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俾鲜,悠然高远”。[2]可见李翱精于儒学,善做文章。李翱文章师学于韩愈,故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道:“近李翱从仆学文,颇有所得,然其人家贫多事,未能卒其业”。[3]郑獬在《刘舍人书》中说“在韩退之门下,用文章雄立于一世者,独李翱、皇甫湜、张籍耳。”[4]李翱向韩愈学习过古文,接受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文章功底得以大增。本文着重略论李翱对韩愈作品风格的接受、发展。
韩愈与李翱在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理论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韩愈在其论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放皆人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在孟子时早已说了一个大概,但李翱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通过他自己对道统的了解,成为李翱今后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承道统,由此可见,韩、李二人致力于恢复儒家传统道学。但是韩愈较为注重剖析社会时弊和探究人生哲理,而李翱则从《中庸》等先儒的形上之学典籍里面汲取思想资源以回应佛学的挑战,为宋明儒者的理路启迪其端。韩、李二人在哲学上的共同特点是,围绕人性之辩展现他们对儒学的理解与阐释。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过,“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5]可见韩愈之文似荀子,而李翱之文似王通,又“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由此可见韩愈的文风主要是雄健、怪奇,气势浩然,但是同时韩愈也认为文章应“文从字顺”,表明他对文风的要求应该是自然流畅的。韩愈始终坚持文以明道,提出文道合一的作文境界。强调的是为文须“慎其实”,以道德为典范来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若要达到“至于古之立言者”境界,则必须“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华,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答李翊书》),这也就是说,道德修养是写文章成败的根本所在,要以德行为本,文章为末,韩愈以恢复古道为已任,提出这种观点是自然之事。其次,韩愈认为气盛言宜,“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的“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3]再结合他对道的强调,便可得知气之本意,道德修养是一个要素,韩愈提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3]而另一部分,则应是对时事的了解、对道统的尊崇,只有气盛,才能写出皆宜之的文章。
李翱接受并继承了韩愈雅正敦厚,平易自然的风格之长,李翱作为韩愈的学生,是唐古文运动的追随者,他“不协于时而学古文”的理由就是要坚持古人的行为,遵循古人的道德,践行古人的礼法,然后用古文的形式传之于后人。因此,李翱的文章就呈现出各体兼长,说理严谨、透彻,言情生动,语言精炼等特点。他的文风神似韩愈,却又独具风格。翱之文章从韩愈之正,坚持文以载道之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韩愈在古文创作当中好为奇崛之短。这主要体现在李翱的古文创造当中。苏洵评价李翱文章“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6]即赞美他平铺,简易的文风。李翱倡导文以致用,主张从单纯的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干预生活,他鲜明的文学主张在其文学创作中皆有忠实的体现。
二 韩、李二人对文章内容的认识与表达
韩愈为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宰相董晋也写过一篇《赠太傅董公行状》,其中,《行状》插叙了一段突出董晋的逸事:“回纥之人来曰:‘唐之复土疆,取回纥力焉。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惧不敢对,视公。公与之言回:‘我之复土疆。尔信有力焉。吾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赐不既多乎?尔之马岁至,吾数皮而归资。边吏清致诘也,天子念尔有劳,故下诏禁侵犯。诸戎畏我大国之尔与也,莫敢校焉。尔之父子宁而畜马蕃者,非我谁使之?’于是其众皆环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两举手曰:‘不敢复有意大国。’”司马光《资治通鉴》于卷二二四载此事,胡三省注:“此晋吏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全祖望也说:“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困学纪闻三笺》卷十一)《行状》以叙述手法溢美董晋。在另一篇文中,韩又以议论溢美:“天子之武,维陇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维陇西公是宣。”(《汴水东西水门记》)溢美不实,描述略有过分,所以刘禹锡有“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祭韩吏部文》)的讽刺了。董晋为节度使,是韩愈的幕主,所以这些谀墓的溢美之词又有了谄权贵之嫌。
但以李翱《韩公行状》为例,此篇文章是记述韩愈一生事迹的文章,全文以事为轴,纵向展开,全文没有对韩愈的所作所为进行夸饰,没有铺排,整篇文章详略得当,李翱虽为韩愈后学,却无溢美之词,对韩愈生涯的关键处重点揭示,使韩愈的功过是非皆显于文章,跃然纸上。在叙写韩愈的成长背景时,《韩公行状》写道“公讳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岁,父殁,养于兄会舍。及长,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年二十五上进士第。”[7]与之相比,同为韩愈后学的皇甫湜所书的《韩文公神道碑》则云:“先生讳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郑氏异而恩鞠之。七岁属文,意语天出。”[2]李翱平铺直叙,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韩愈的生世以及成长背景。而后者记述“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则将韩愈幼年丧父,孤苦无依的状况写得富于形象感,但后面将韩愈文才归于“意语天出”,却让人感到不真实,过于夸大韩愈作文天赋,有违于碑文记实特点。《韩公行状》描写淮西中的表现:“元和十三年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赐三品服及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自唐州文城垒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李翱在叙述韩愈向统帅裴丞相的建言时,将此次战役的背景,韩愈在军事过程中的地位、决策以及结果一一进行了详细地描述,显露韩愈在军事指挥中的运筹帷幄,在描述过程中未多添多增一句褒贬之词,以事实说话,却将韩愈的能力自然展现出来。《韩公行状》字字源于事实,李翱作为韩愈后学,甚至是侄女婿,并不因为和韩愈的特殊关系,而对韩愈大家褒赞,在给韩愈的一篇书信《答韩侍郎书》中也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和告诫韩愈如何对待人才和文章,其记事风格于此得以体现,其人耿直之性使其文章风骨更优于前人。
与此相比,皇甫湜的《韩文公神道碑》也记载了同样事件“十二年七月,诏御史中丞司彰义君讨元济。出关趋汴,说都统宏,宏悦用命,遂至郾城。势审其贼虚实,请节度使裴度曰:某领精兵千人取元济。度不听察。居数日,李自文城果行,无人,擒贼以献,遂平蔡方,三军之士为先生恨。”[2]《神道碑》描写较为简略,只是粗略记述韩愈向统帅提出意见,而未被采纳,没有记述经过,却证明韩愈策略最后是正确的,并没有明确说明韩愈在战役中的地位。碑文说道“三军之士为先生恨”,并没有明确历史依据,有主观臆断之疑,给人夸大其词之感。
三 韩、李关于艺术形式与写作技巧的认识
韩愈重视古人文章,倡导古文运动,意欲恢复传统儒学,但是其文章尊古,学古,却不拟古,其文自成一派,自有风格。昌黎十分重视在文章创作中“陈言务去”和“词必己出”两条基本原则,从而这也影响了其创作风格及内容。所谓陈言务去,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这样说道:“当其取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韩愈要求学习古人的作品要做到推陈出新,切忌人云亦云,究其根本是要创新,然而创新本身则是“戛戛乎其难哉”,所以作文时如果能够去除陈言,学习古文之精髓,则文思泉涌,美文自来。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道:“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见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5]说明韩愈所倡导的概念,不仅仅限于遣词造句,而是从内容、题材、意境等各方面都需要改变,不能重复过去的陈词滥调。正因为如此,才形成韩愈脱俗、险崛为表,醇厚其中的文章风格。
李翱接受并肯定了韩愈陈言务去的观点,并且在具体创作中进一步发展,提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观点。其实就是以儒家之道为根本,但是在创作中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表述,而要达到去除陈言,显露“道”这一核心要素,在李翱看来必须通过“意”和“言”的手段,这与“陈言务去”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答朱载言书》中,李翱详细解释道意与言的重要性,“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义是本,即儒之道;意即所做文章的主题;理则为文意之论据;气则是所做文章的风骨,辞为内容,而文是言语组成。“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并且在文中直接提出“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由此可见,李翱认为创意与造言并存,没有创意就没有文章,文章没有好的语言则理义难现,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李翱的文风较之韩愈更为简朴,易懂之因。其后果则是习之之文较昌黎之文文学性略逊而说理性更强。
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提出:“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在这里,作者借为樊绍述写墓志铭的机会,提出“词必己出”的观点。在有关艺术形式、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方面,指出“陈言务去”与“词必己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词必己出”,则以觉悟指点明津,从正面着眼,从积极方面强调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在他的《答刘正夫书》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但是,文学语言一久,又会因久生弊,代代相袭,缺乏创新从而令人生厌。所以韩愈又有“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何其难也”的慨叹。因此所谓“己出”,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强调文风的个性化,从而进行新的创造。“词必己出”,光景日新,既是艺术上的独创,也是韩文风格的魅力所在。
李翱学习韩愈,其文遣词造句也是字字己出,在他给同门皇甫湜的《答皇甫湜书》中写道:“韩退之所谓「诛奸谀於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7]李翱十分赞同并且始终贯彻韩愈字字珠玑的理念,上至公文辞令,下至书信散文都是以原创的言语反映所思所想,以求能够真实并且深刻概述人、事、物以及观点,他将自己所著文章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蔡邕相比,并认为不次于古人,这不是对自己估量不足的体现,而恰恰是因为贯彻了与前人相同的“道”之根本从而文风相似的体现。可以说,李翱不仅延续了韩愈的文章风格,而且也是韩门弟子中将古文运动的核心理念运用最为纯熟的一位。以韩愈的《马说》和李翱的《国马说》作对比可看出,二者都是借马之名而喻实事,希望能够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教化,但二文立意不同,《马说》想强调对人才的重视,并且一开始就是以理论证;《国马说》则是提倡人们的仁义之心,以国马和骏马的故事为引,篇末指出主题。二文文风相似,但无论是主题还是结构,李翱并没有模仿韩愈,但根本都是旨在以文鉴人。由此可见,李翱是从根本而不是仅仅从表面上领悟和接受韩愈思想的。
李翱以学习接受韩愈作品风格为契机,进而进一步在实践中发扬光大韩愈的古文理论,以理服人,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文学思想地位。对后代,尤其是宋代新儒学的影响意义深远。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A]..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29.
[3]马其昶.韩昌黎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卞孝萱. 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苏洵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7]李翱,欧阳詹.李文公集、欧阳行周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ClassNo.: I206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OnHeritageandDevelopmentofHanyu’sLiteraryStyleMadebyLiAo
Shi Yif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Li Ao, as HanYu’s follower, on the basis of heritage to HanYu’s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has developed Han Yu’s literary writing style . And Li Ao developed his own style of Han Yu literary point of view and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style of writing.
Li Ao; Han Yu; style
施翊飞,硕士,兰州大学。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1672-6758(2013)04-0103-3
I20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