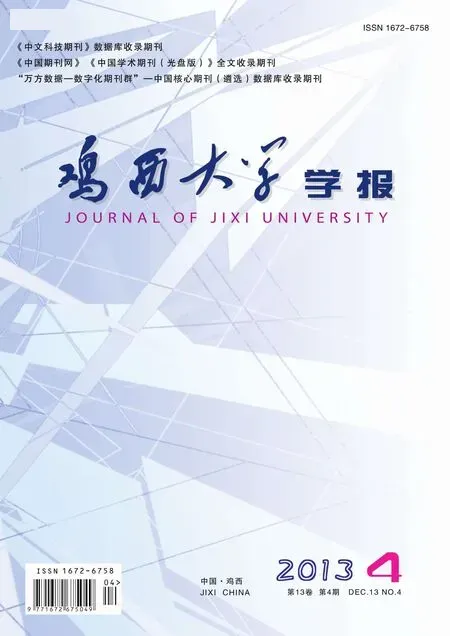萧山方言是非问与上海方言是非问比较研究
叶吉娜,首作帝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在萧山方言中,因为有专表是非问的语气词,因此是非问句比较发达,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试图对萧山方言的是非问进行简略的描写和比较,并就这种问句的性质提出一些浅见。萧山方言是非问句从句子组成出发可大致分为三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如下分法,只是为便于分析,若专门给是非问划类,应采取专家的结构标准。
(文中S代表一个小句,Neg代表否定词,VP代表谓词,M代表语气词,F代表副词。)
一 语调表疑
这类用法中,句式和陈述句结构相同,其差别主要在语调上。若用降调,为陈述事实,用升调,则是要求对方就所提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如:
(1)恩一个人去?(你一个人去?)
(2)丫杜否晓得?(他们都不知道?)
借用语调表疑,在交流中通常要借助诸多因素,如人的表情、手势等,脱离了语境,这类用法所表示的疑问语气就会很微弱,如(2)句失去疑问语调,变成“他们都不知道”,此句也可用在回答“他们知不知道?”的问句上,以至无法察觉疑问导致理解困难。
二 S+M(M表示疑问语气词)
萧山方言是非问中句末语气词主要有“啊、嗒、嘎、抬”。
1.“啊”,“呀”。
只能用于是非句,与普通话“吧”接近,从形式上看,总是在一个表示陈述的短语后面,构成疑问句。这个陈述短语要求较宽,可为单个的名词,也可为动词。如:
(1)猪肉啊?(猪肉吗?)
(2)恩东西否码色回去呀?(你东西不买点回去吗?)
这些肯定是非问句后面的“啊”有两种理解:一种即真的存在疑问,需对方回答,肯定回答在萧山方言中一般用“恩”(“是的”),否定回答用“否是”(“不是”)。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存在太大疑问,日常打招呼、警示性质居多,一般不求十分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
(3)恩来洗衣服呀?(邻居看到对方拿着衣服去河边时说的话,已知对方行为目的,只是打招呼,不一定非要回答“是的”)
(4)恩还否困啊?(妈妈看到孩子夜深未睡,警告孩子应该睡了,不是真正的疑问)
“啊”还可用于反问句,表反诘语气,有不满意味,通常用肯定形式表否定意思,否定形式表肯定意思。如:
(5)葛种事体伊为否晓得啊?(这种事他会不知道吗?即他肯定知道。)
2.“嗒”。
“嗒”的用法同“啊”,也是置于一个表示陈述的短语后面,构成疑问句。与“啊”句不同的是,其一般为主谓结构。如:
(1)饭烧好嗒?(饭烧好了吧?)
从意思上讲,“嗒”相当于普通话“吧”,表示疑问意味很小的句子,只是想通过询问证实自己的猜测。从时态上看,“嗒”结尾的句子多与表示已然的情况连用,如:
(2)衣服已经胡测嗒?(衣服已经洗出了吗?)
“嗒”作为一个意义丰富的语气词,不仅可作为疑问语气词,也可用于感叹句,本文在这里捎带一提:(3)我偏生要类达浪旮儿嗒!(我偏偏就要在这里!)
这时“嗒”作为句末感叹词加强语气。
3.“嘎”。
“嘎”从句子形式上看,总是放在一个表示陈述的短语后面,构成是非疑问句,这个短语多为动词短语,而句子多表反诘语气,如:
(1)恩嘎做伊为同意嘎?(你这么做他会同意吗?即你这么做他估计不会同意)
在熟悉了萧山方言疑问句中的疑问语气词后,我们再来看看上海方言中疑问句疑问语气词的使用。
上海方言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是带疑问语气词“伐”的后加式是非问句:V伐?“伐”的功能很广泛,几乎可以涵盖萧山方言中所有上述提及的疑问语气词。这种问句形式的演变可从“V勿V”谈起,“V勿V”是一种最基本的正反问形式,它从选择问句“V还是勿V”简化而来,而这一格式,为了叙述更加经济,作为两个相同的V,保留了前一个省略了后一个,再于句末加上语气词“啦”,变成“V勿啦?”而“勿啦”说得快一些,就变成了“伐”,邵敬敏与徐烈炯认为这从汉语音韵反切的角度进行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勿”的声母和“啦”的韵母相结合而产生“伐”的音。
在上海方言中,“V口伐?”这类问句大量使用,可分为两类(据邵敬敏、徐烈炯《上海方言语法研究》):A式话题疑问句、B式话题疑问句。
A式:S(NP+VP)伐?
这类问句话题鲜明,将非施事名词放置句首充当话题,对它进行提问。谓词与“伐”紧密结合,名词与谓词往往紧密,有时也可分开,如:
(2)饭吃伐?(饭吃吗?)
有时主事也常充当话题,如:
(3)这个是王先生伐?(这个是王先生吗?)
同时,处所、时间等其他语义,还有受事不出现时,施事也可以做话题,如:
(4)苏州去过伐?(苏州去过吗?)
(5)明早,你有空伐?(明天你有空吗?)
(6)侬想去伐?(你想去吗?)
若施事受事都出现在谓词前,两者谁先谁后都可,只是在上海方言中,受事在前施事在后占多数情况。如:
“侬煤油灯见过伐?”出现的频率没有“煤油灯侬见过伐?”高。
从上述疑问情况我们可知,A式情况,发话人所掌握信息较少,疑惑度较大,问题、目的简明,即要求对方给出明确回答,与萧山方言中以“啊”“呀”结尾的疑问句的第一种类型极为相似。
B 式:S,VP伐?
小句(S)置于最前,陈述、祈使、感叹都可,后用“VP”追问,即先提出一个命题,然后让对方来回答,所以又称为命题疑问句。(VP最常用:是伐、好伐、对伐、晓得伐)如:
(7)王先生,洗头是伐?(陈述句)
(8)帽子叫顶官,晓得伐?(陈述句)
(9)帮帮我的忙,好伐?(祈使句)
(10)这个天气牢牢好,对伐?(感叹句)
就S句的内容征求对方意见,要的是一种证实,不是疑惑度很高的疑问句。如:
(11)过完年你回来,好伐?
通过对比可知,B式与萧山方言中以“啊”“呀”结尾的疑问句的第二种类型、以“嗒”结尾的疑问句很接近,疑惑度不高,发话者在之前已经掌握一定信息,只是想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猜测的验证。这就使得使用不同的疑问语气词得到了同样的表达效果。
但上海方言的这种形式与萧山方言还是存在较大不同的,学界称B式为“附加句”,其有三个与萧山方言不同的特点:
(1)不独立使用,必须得附加在非疑问句之后
(2)疑问句由疑问格式或者疑问词单独构成
(3)回答必须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
形式比萧山方言丰富,是非、正反、个别特指问,叹词独用句都可出现在这个句式中:
(1)你要发誓,过完年就回来,好不好?
(2)张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帮帮我,好吗?
(3)你早点脱军装,我们兄弟俩联手办厂,怎么样?
(4)如果老板满意再正式来,啊?(以上例子出自北大语料库)
相比而言,萧山方言形式就显得比较固定,是非问占绝大多数。
三 F+VP+M
前面有副词的疑问句一般疑问度适中,适用的情况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否扣+……M,“否扣”相当于普通话“不会,会不会”。如:
(1)否扣一个宁去抬?(不会一个人去了吧?)
2.泼嗒+……M,“泼嗒”相当于普通话“难道”,“怎么”,一般疑问的语气较弱,如:
(2)做宁泼嗒嘎没有良心嘎?(做人怎么会这么没良心呢?)
上海方言中,F多以“阿”字作为疑问副词,形成“阿VP?”格式,这种格式主要受苏州方言影响,在老派中使用较多,中派使用频率下降,新派青年人则很少使用了,现多用“阿是”、“阿有”。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一般的特指问、正反问以及选择问不能用“阿”来助问,但在间接问句中可以,这与萧山方言是一致的,例如:
上海话:我否晓得伊阿去勿去。
萧山话:恩泼嗒去否去都要问伊嘎?(你难道去不去都要问他的吗?)
我们引用邵敬敏、徐烈炯以《三毛学生意》(从创作时间来看,相当于中派上海话)为标本归纳的“阿是”、“阿有”例子,发现“阿是”18例,“阿有”5例,后面询问的对象可以是单个名词,也可以是动宾短语或者一个小的句子,如:
(1)阿是这个吴先生?
(2)阿有啥个办法想?
“阿是”“阿有”的用法与萧山方言中的副词用法相近,但是资料显示,“阿”直接用于修饰一般动词的用法很少,在这部作品中只有四例,但在萧山方言中,副词直接修饰动词的用法却很常用,例如:
(1)恩泼嗒去哒?(你难道要走了吗?)
(2)伊否扣跌跤了吧?(他会不会摔跤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两者在F+VP+M中的差异。
本文对萧山方言的研究仅从是非问角度进行,同时在具体细分处将萧山方言与吴语的代表——上海方言进行对比,希望可以找出萧山方言不同于吴语疑问句一般规律的用法与特色。但是事实上萧山方言与古代汉语的相同处、与现代汉语的异同、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远不止这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对比研究,挖出蕴含在萧山方言中的大量文化价值。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丰富人们对方言疑问句的认识,加强方言间的交流。
[1]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邵敬敏,周娟.汉语方言正反问句的类型学比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0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