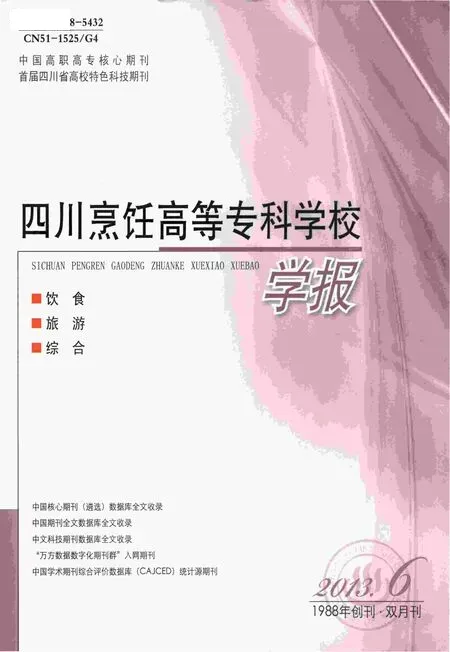试论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饮食文化圈的形成
杨春华 李 想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我国饮食文化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强烈影响,先秦时期我国饮食文化总体格局逐渐形成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南北两大饮食文化区域,即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北方饮食文化区和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南方饮食文化区。[1]这一观点基本已经成为定论。但具体到春秋战国时期,笔者认为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成三个饮食文化区域,即包括三晋、齐、鲁在内的中原饮食文化圈;以秦国为中心包括巴蜀的秦陇饮食文化圈;以楚国为中心包括吴、越的荆楚饮食文化圈(见图1)。这三个饮食文化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而来。

图1 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饮食文化圈示意图
1 自然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由于受生产力不发达因素的制约,古代先民从事生产生活更多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因此自然地理条件就成为影响饮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饮食文化圈的形成亦是如此。
按照4000m以上、1000~2000m、500m以下三个海拔高度划分,我国地势自西向东,逐级下降,大致形成三个巨大阶梯,秦陇地区大致在第二阶梯,中原和荆楚地区同在第三阶梯,而800mm等降水量线又将第三阶梯划分为北方和南方,北方为半湿润地区,南方为湿润地区,这样在地势和气候的影响下就形成了三个饮食文化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单纯从地势和气候的角度来考虑,秦陇饮食文化圈较为复杂,虽地势上处于第二阶梯,但气候上又与中原饮食文化圈有部分重叠,而公元前316年、314年秦人经金牛道翻越秦岭先后灭掉蜀、巴两国后,秦国疆域就扩张到了湿润地区的南方,因此秦陇饮食文化圈的存在还需要其他证据来支持。
一个地区的土壤类型和土质优劣程度是决定该地区适合种植什么样的粮食、蔬菜、瓜果等植物性原料的重要因素之一。先秦时期,各地区土地基本处在原始的先天状态,人为开发程度较低。而较早关注土质优劣的文献便是《尚书·禹贡》篇,其中记载“禹别九州”,即大禹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详细记载了各州的范围、土壤、水文、植被、物产等自然状况,尤其是将九州的土壤质量分成了九个等级。
1.1 中原饮食文化圈土质特点
按照《禹贡》篇的记载,再结合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地理位置大概对应来看,中原西部地区的三晋地处豫、兖、冀三州,三州土质中等:豫州“厥田惟中上”[2]71,兖州“厥田惟中下”[2]58,冀州“厥田惟中中”[2]56。而东部地区的齐鲁地处青、徐二州,二州土质偏上,且盛产鱼、盐等海产品,“海岱惟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贡盐,海物惟错”[2]61,“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田惟上中……淮夷珠暨鱼”[2]63。这样看来,中原地区虽地跨五州,但实际土地面积并不大,而土壤质量较好,故比较适合各类粮食作物生长,又东临大海,故鱼、盐等海产品非常丰富。中原饮食文化圈的这一特点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史记·货殖列传》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3]7592除此以外,极具地域性特征的《诗经》,其国风各篇的相关描写也可作为中原地区盛产各类谷物的佐证,如采诗于洛河流域的《王风·黍离》写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4]175;采诗于淇水流域的《鄘风·载驰》写道:“我行其野,芃芃其麦”[4]140;采诗于魏国地区的《魏风·硕鼠》写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4]276。
1.2 秦陇饮食文化圈土质特点
“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5]306大体而言,泾河流域、渭河流域属于雍州,其土壤质量为上上等,“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2]75。巴蜀地区属于梁州,虽土质较差,“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2]72,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在攻占和吞并巴蜀的过程中,通过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和大规模移民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土壤质量和利用率,使该地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秦国蜀守李冰修建了以都江堰为核心的大型水利工程,“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6]103,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3]7583的天府之国。《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好稼穑,殖五谷……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3]7582因此可以推想,该饮食文化圈内的植物性原料较中原地区应该更为丰富。这一点同样可以在《诗经》的相关描写中找到依据,那首含有大量食材信息的著名诗歌《豳风·七月》就采诗于秦陇地区,其中写道:“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4]365除《诗经》以外,《汉书·地理志》也认为秦人“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5]306,巴蜀地区“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食之饶”[5]307。现代学者彭卫先生还认为,在百谷当中,秦人常吃的是粟,而像麦、稻、菽等作物大抵是看不上的。[7]42《汉书·食货志》中也记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建议在汉中地区种植麦,“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5]162,其后又令农学家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8]123。可见,与粟同属耐旱粮食作物的小麦,其广泛种植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了。
1.3 荆楚饮食文化圈土质特点
楚地处荆、扬二州,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2]68,扬州“筱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2]65,可见荆楚地区土壤湿软,质量最差,不适合麦、黍等干旱作物生长,但却利于水稻的栽种,再加上该地区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使得荆楚饮食文化圈自古就形成了以稻米为主食的特点。例如《周礼》云:“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谷宜稻。”[9]480-481司马迁也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3]7601除文献记载以外,荆楚地区出土的大量稻米遗存更是有力证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为止,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稻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60处以上,这个数字不仅超长江下游地区一倍多,超过其他地区数倍甚至十倍”[10]451。楚人除了以稻米为主食外,还兼食其他五谷杂粮,更喜食鱼类、飞禽等各种山珍野味,这也是由其河泽众多的自然环境特点造成的。比如《招魂》中写道:“稻粢穱麦,挐黄粱些。”[11]219《战国策·宋卫》也载:“荆有云梦,犀、兕、麇、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12]1023根据王学泰先生的统计,在《招魂》与《大招》之中提到的肉食动物“共二十二种,属于家畜、家禽制成的只有类五种(包括牛、羊羔、乳猪、狗各一种,鸡二种),而用野味制成的菜肴有十二种(包括鸿、鸽、鹌鹑、鸹、雀、豺各一种,鹄、凫、鸧鹒各二种),水产品四种(包括鳖、各一种,蠵二种)”[13]69。
2 人文思想的影响
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儒、法、道、墨等各家思想流派,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论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些人文思想的影响成为了形成三个饮食文化区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大致来看,盛行于中原各国的儒家思想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饮食文化表现为崇尚礼节,强调等级制度和宗法观念,秦人重利轻义的国民性决定了其选择法家思想来立国兴邦,在饮食文化上则呈现出简单实用的理性主义特点,起源于荆楚地区的道家思想与该地区“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尚结合促成了荆楚饮食文化圈重乐不重礼,率性洒脱的浪漫主义特点。
2.1 崇尚礼节的中原儒家饮食思想
儒家认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4]268,认为饮食活动中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礼制的开始,因此儒家特别强调通过饮食礼仪、饮食制度来实现教化民众,灌输等级思想和宗法精神的目的,这正是儒家饮食观在社会功能上的直接体现。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代表的“三礼”是儒家礼仪规范和礼仪制度的最集中体现。如《周礼》中就明确记载了管理宫廷饮食的食官制度,其规模庞大,内容琐细,从食材采集保藏(如甸师、兽人、渔人、浆人、凌人等)到烹饪加工制作(如膳夫、庖人、内饔、腊人等),再到餐饮服务(笾人、醢人、人等)和养生保健(如食医、疡医),基本上涵盖了饮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再以《仪礼》为例,在讲到当国君赐酒时,士的礼节应该是“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15]62。又以《礼记》为例,在《礼器》部分就规定:“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14]286“三礼”中的饮食礼仪虽过于繁缛而不切实际,但却成为春秋战国中原各国统治阶级用以制订礼仪规范,维护和巩固其等级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有力工具。在实践“三礼”的过程中,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最为重要的实践者之一。孔子一生都在推行以礼治天下的仁政思想,在饮食行为上更是强调时时事事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如对国君要行礼,“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16]112;对老人要施礼,“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16]111;对祖先要尽礼,“齐必变食,居必迁坐”[16]109。除此以外,孔子主张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不及乱”“食不语,寝不言”“八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等由饮食而引发出的诸多主张更是为人们耳熟能详,这些主张体现了孔子饮食思想崇尚精益求精,重视尊卑有序,提倡安贫乐道等特点。“三礼”的饮食礼仪规范和孔子的饮食思想处处彰显了等级制度和宗法精神,对中原饮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塑造中原饮食文化的最根本原因。
2.2 崇尚理性的秦陇法家饮食思想
由于秦国立国较晚,加之长期与西戎少数民族杂居,呈现出“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道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3]3574的色彩,因此秦人的宗法观念比较淡薄。不仅如此,与中原各国的儒家文化相比,秦人自身缺少可以立国的先进哲学思想,同时秦人较为原始的多神崇拜观念却比较发达,这些都导致了秦国在春秋战国前期学术思想的匮乏。但也正是因此,秦国才能在春秋战国后期更快、更彻底地接受新社会变革浪潮的洗礼,选择了更适合社会进步的法家思想作为立国兴邦的指导思想,其表现就是商鞅变法在战国各国变法运动中是最为彻底的。秦人原本重功利、轻仁义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和法家重农抑商、尊法尚武思想共同决定了秦人在饮食上表现为饮食礼节简单、实用,没有繁文缛节的进食规矩。这一特点从秦人所用食具、酒具可以得到反映,如从宝鸡斗鸡台、宝鸡李家崖、滓西客省庄、半坡等秦墓考古发掘出土的秦人食具、酒具来看,“秦人所用的食器和周人及中原诸国都有很大不同,周人和中原诸国流行的酒器是爵、角、觥、钫、卣等,秦人则只用耳杯饮酒。周人和中原诸国通行的食具如簋、盨、敦、献等在秦地也没有出现”[7]43。同样,记载了大量饮食文化信息的秦地名著《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提出了“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17]417等烹饪理论见解,并分别列举了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和之美者、饭之美者、水之美者、果之美者等各地美食,这些亦说明了秦人更多关注的是水、火、味以及各地物产等具体实在的东西,而礼仪、道德、宗法等问题涉及较少,这同法家反对儒家礼制的主张是一致的。
2.3 崇尚浪漫的荆楚道家饮食思想
自称“蛮夷”的楚人没有像北方诸国那样受过严格的“礼”化教育,也缺少积极治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又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遗俗,这些都使楚人文化不像中原那样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原始的自由精神表现得特别强烈,但又与秦人重利尚武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所不同,楚人选择了一条极具浪漫情怀和哲学思辨色彩鲜明的道路,表现在文学上便是产生了在风格上与北方现实性文学作品《诗经》截然不同的浪漫性文学新样式——楚辞,表现在哲学上便是产生了超凡脱俗、绝礼去仁、清静无为、返朴归真的老庄道家哲学。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同“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共同作用,使荆楚文化表现出浪漫奇谲的艺术特点。荆楚文化的这些特点体现在楚人饮食上便是重乐不重礼、率性自然、嗜酒尚味等。比如《楚辞·招魂》中描写楚国贵族“娱酒不废,沉日夜些”[11]220的宴饮场景,有歌“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11]219;有舞“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11]219;有乐“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11]219;有美酒“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11]219;更有如“肥牛之腱”“胹鳖炮羔”“鹄酸臇凫”“露鸡臛蠵”“粔籹蜜铒”等珍馐美味,却没有中原周人“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14]123,“男女不杂坐,不同槐枷,不同巾栉,不亲授”[14]123的条条框框,有的是“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11]219的放荡不羁。
除以上两个大的方面外,其他诸如民族互动、兼并战争、移民政策、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饮食文化圈的形成,如秦陇饮食圈形成发展的初期,由于西戎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对秦人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饮食结构一度出现了肉类原料为主、粮食蔬菜类原料为辅的情况。
3 余论
饮食文化圈的划分绝不是在地图上画几个圈那么简单,春秋战国时期的三个饮食文化圈其内部和边缘仍有一些极具特色但影响规模较小的饮食文化表现,可称之为饮食文化丛,比如齐鲁、燕赵、巴蜀、吴越、云贵等饮食文化丛。在后世发展过程,某些饮食文化丛逐渐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文化丛的范围,比如齐鲁、巴蜀、吴越三个饮食文化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为跨地区、历时久、影响广泛的饮食风味派系,即我国四大风味流派中的鲁、川、淮扬三大流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饮食文化圈的结论是建立在已有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的。严格说来,过去古人吃什么、怎么吃,以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描写比较详细的绝大多数是上层统治阶级的饮食状况,比如无论是《礼记·内则》中记载的淳熬、淳毋、炮豚(或炮牂)、捣珍、渍、熬、糁和肝膋这八种被称为“周代八珍”的珍馐美食,还是《楚辞》“二招”中所列举的胹鳖、炮羔、鹄酸、臇凫、煎鸿鸧、露鸡、臛蠵、粔籹、蜜铒、豺羹、鲜蠵、甘鸡、醢豚、苦狗、炙鸹、烝凫、煔鹑、煎、臛雀等野味佳肴都是宫廷菜,都是难得的珍奇之物,自然非普通人可以享用。再比如稻米,在春秋战国时期,除长江流域有过大面积种植外,在中原、秦陇地区都是稀有的粮食作物,所以《论语·阳货》记载,宰我问孔子,父母死了,守丧的时间可否由三年改为一年时,孔子反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16]216意思是说,守丧只有一年就吃好的,穿好的,心能安吗?这样看来,稻和锦都是珍贵的东西,绝不是常食常用之物。再如肉类原料,虽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猪、牛、羊、狗、鸡等都已经实现了人工驯养,但由于产量有限和相关礼制的约束,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享用的起,所以当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时,鲁人曹刿讽刺统治集团无能无谋的时候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18]119。这样看来,历史文献所记载的饮食情况多是对王公贵族生活的描写,而对寻常百姓的饮食状况关注不多。因此,要全面把握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的饮食文化特点还需要在将来的考察研究中进一步归纳补充。
[1]王雪萍.先秦饮食文化的区域特征[J].青海社会科学,2006(4):100.
[2]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诗经[M].刘毓庆,李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常璩.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7]彭卫.谈秦人饮食[J].西北大学学报,1980(4):42-43.
[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杨天宇.周礼译注(十三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李玉麟.先秦荆楚饮食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9:451.
[11]楚辞[M].林家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战国策[M].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4]杨天宇.礼记译注(十三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杨天宇.仪礼译注(十三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6]金良年.论语译注(十三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7]吕氏春秋[M].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18]李梦生.左传译注(十三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