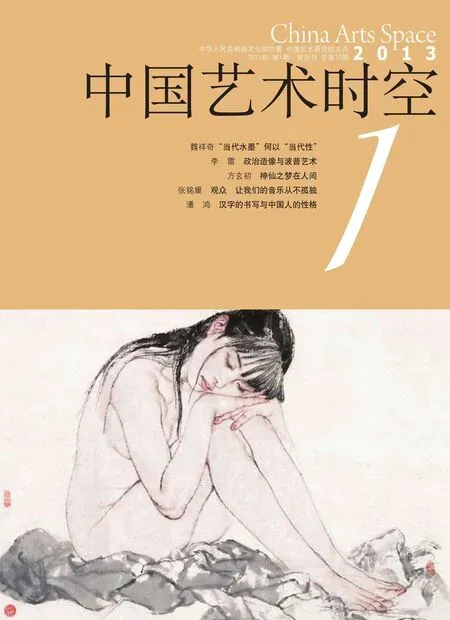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

孙佳山:欢迎大家参加第17期青年文艺论坛。这一期我们讨论的题目是“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首先祝贺我们院的莫言老师荣获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这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为我们全面梳理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讲人是《传记文学》副主编郝庆军老师、《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也是我们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李云雷老师。首先请郝庆军老师来为我们做第一个报告。
郝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我今天主要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首先说明一下这个话题的背景。
其实,我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的专家,谈不上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深入研究,只是因缘际会,碰巧在几年前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梳理和调查。2007年我们院里承担了文化部的一个重要课题,叫做“文化现状调查”,针对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目的是向文化决策部门提出一些有分量的政策建议,这当然是一项应用对策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中有一个子课题,名称叫做“我国文化对外交流与文化软实力的传播研究”,在这个子课题里面我申报的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研究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这么一个分课题。
领了任务之后,我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投入工作。因为这项研究不仅仅是案头工作,还要去调研,去走访。先是看了一大堆资料。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两个文献:一个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这本书,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资料是刘再复写的长篇论文《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这篇论文是在1999年《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当时很轰动,因为论文中多次提到高行健和他的《灵山》,并预测高行健是获奖热门人选之一,而第二年高行健真的就获奖了。所以这篇文章对研究诺贝尔文学奖来说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文献。然后我还翻了其他一些案头材料,多是一些论文,比如说王宁、张颐武的,还有一个南方学者赖干坚老师写的一些文章。
看了一大堆资料之后,我还是觉得一头雾水,除了了解一些规则之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实际情况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就是走访和调查。我走访到社科院,正好有一个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后,叫陈思齐,她到社科院访学,来做当代作家研究,选择了四个作家:李锐、莫言、残雪、阎连科。当时她找了社科院我导师杨义先生寻求帮助,要求联系到这四位作家。杨先生安排我联系这四个人,所以我就带着她走了一路,都联系上了。在这期间,我也让这位学者谈了她了解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她从英国来,当然熟悉西方的标准和西方的价值尺度。我问她,为什么你选了这四个作家?她直言不讳地说,这四个作家是西方喜欢的作家,也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在一路寻找这四位作家的过程中,我在她那里了解了很多书本上没有写出来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奖实际是怎么操作,它的筛选标准和倾向性等等。这是比较有收获的一次调研活动。


第三项工作就是找国内的一些批评家,主要找了社科院的白烨老师,简要地谈了谈这个问题。白老师对中国作家获奖比较悲观,我记得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当代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遥远,中国作家还需努力。
这样,在我的视野内对诺贝尔文学奖就比较清楚了。调研三四个月之后,很快我就写了报告《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交给了课题组。报告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文化部角度和院重点课题的角度来写的,重点谈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和问题,谈了中国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机遇和措施,提了诸如举办论坛、定期让中国作家出访、建立基金会之类的具体建议有六、七条之多。
现在看这个报告,比较“政治正确”,不太学术化,但是里面的内容,以及当时谈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因为我当时就预测了三个人:一个是李锐、一个是莫言、一个是曹乃谦。而且当时我预测说,不会过太久,中国作家可能会很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天看来,这不是“马后炮”,而是“马前炮”了。我报告里的原话是:莫言是最有“诺奖相”的一位中国作家。因为我通过访谈、调研,看了《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之类的资料,大致知道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喜欢什么作家,无非就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作家,他们符合这个标准,获奖是早晚的事。
今天当然不重复我这个报告了,今天谈的题目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的变与不变”。我分三个方面谈:第一部分谈110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简要过程,主要谈它的价值体系,包括这个奖里面的意识形态和西方或者欧美中心主义的问题和缺点,以及它内部评选机制的僵化和问题;第二部分谈198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松动,尤其是它对亚非拉国家的倾斜,给亚非拉国家的作家获奖带来的新机遇;第三部分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何清醒地认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下面我就依次展开来谈。我尽量简短,佳山,半个小时我还谈不完,你就打断我。
先谈第一个问题,110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根据埃斯普马克的分析,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确实是有三个阶段。从1901年到1930年,即前30年,是现实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时期。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世界主流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的,诺奖评选标准就依照这个标准,比方说罗曼·罗兰、萧伯纳等咱们都熟悉的现实主义作家纷纷获奖。从40年代到70年代,这30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主义文学时代,这个时期的获奖作家基本上是以现代主义创作思潮和方法为主流的,代表作家就太多了,比如说加缪、萨特、福克纳等。到了1980年代以来,创作思潮和流派就比较复杂了,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还有后现代主义的,还有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打头的就是1982年获奖的马尔克斯,然后到最近的就是莫言。1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这个发展轮廓基本上是比较清晰的,这三个阶段正好勾勒出百年欧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发展更迭的一个轮廓。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作家风格的筛选适应了这个百年潮流,也就是说,西方文学的发展方向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方向。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另一个方面在于,诺贝尔文学奖随着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形式的变化,会筛选不同的作家,但是不变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它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是欧美中心主义的视点并没有多大变化。我当时在报告中列举了一组数字,就是截止到2007年,10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数中,欧美国家占了93个,其中欧洲是76个,美洲17个,欧美之外的作家仅占了10席。这个数字非常说明问题。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形态性,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对前苏联的态度。前苏联5位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只有一位是前苏联官方认可的肖洛霍夫,其他4位,3位是流亡作家,一位是苏联籍在美国生长、写作的作家。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由于流露出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敌视情绪,苏联《新世界》编辑部拒绝发表。1957年,帕氏把书稿弄到意大利,在那里出版,不久这个版本流入苏联,帕氏遂得到苏联文学界的批判。当然,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出版的第二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另一位“反体制”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现在情况有些改观,但有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还真不好说。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体制的封闭和僵化,我就重点举一个例子。谁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由18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组成,俗称18罗汉,终身制,只有死了一位才能填补上下一位,而且这些人的年龄都很大,平均78岁左右。上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记者曾经采访过埃斯普马克本人,他说我们都是顽固的老头,休想用其他什么方式把我们打败、把我们说动,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标准,休想撼动。他们的这个标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就是西方的标准。1984年,有一个华人学者对这个僵化的评奖办法提出质疑,曾经建议能不能让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作家,先评选出一个名单来,然后你们再筛选,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不能光你们这18个人说了算。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其中有一位院士,叫冷斯藤先生,他撰文说:NO,不可能!这个奖完全由我们自己来评,自己来选择,自己来搜罗,你提名可以,但是评奖我们自己来搞。潜台词是,想夺权,没门!
评奖的程序,也是几十年不变,雷打不动。比如说现在莫言获奖了,我们这里一片欢腾,他们却开始工作了,从现在到明年的2月份,200名提名候选人名单就出来了。评委会的18罗汉里面选出5位来,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料理这200名提名者,用多长时间呢?从2月份到5月份,他们从这200个提名人中选出20个人来,然后用1个月的时间再选出5个人。到6月份,欧洲就进入暑假阶段,整整一个暑假,这18位院士评委开始分头集中阅读这5个作家的作品,封闭起来阅读,一直到9月份。在这一个月的每周四,他们开会,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充分讨论这5位候选人的作品,酝酿、争论、分析,甚至争吵。到了最后18人投票,超过9票,方可算数,评出本年度的获奖者。到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四下午宣布结果。整个评选过程,我们现在看是比较封闭,比较严密,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过程,谁都不知道,保密性比较强,所以说,你想撼动它是不可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你说它严密也好,僵化也好,这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我个人认为是僵化保守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讲一下评价标准。1980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的一代评委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是终身制,只有老评委亡故,才能递补新评委。1980年代以后,新的一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陆续进入评奖班子,其中一个评委就是我们熟悉的马悦然。他的到来确实引起了一些新变化。马悦然对中国文化、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当代作家都比较熟悉。他对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中国古典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翻译了大量作品。他是1956年至1958年瑞典外交部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去职后,到澳大利亚教学,然后去了斯德哥尔摩,创建了东方系,这个系培养了一批汉学家。马悦然是瑞典学者中对中国文学确实比较懂行,对中国文化也比较懂行,所以他的进入意义重大。也许就是因为他,松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评奖旧例,尤其是对亚洲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倾斜。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亚洲三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获奖的是华裔法国籍作家高行健,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奖,今年,我国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新世纪12年的时间,就有三位亚洲的或是亚裔的作家获奖,这与新一代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尤其是与马悦然有密切的联系。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主动走出去,寻找候选人。原来评委会多是在图书馆工作,靠世界各地的翻译来物色诺奖候选人,比较被动。但是8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过去是你给他输送提名候选人,现在更多的是他们去寻找、去翻译自己认为重要的作家作品。就马悦然来说,他上任后,公开到中国来不下10次,不包括秘密来华和私人性质的来访,因为他两个老婆都是中国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了不同程度的容纳。比如说非洲,8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非洲作家获奖,但是近几十年来非洲作家获奖人数在增多。1988年埃及的马哈福兹获奖。南非有两个作家获奖,一个是1991年的纳丁·戈迪默,另一个是2003年的库切,加上1986年获奖的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非洲就占了4个席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当然,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状况的这种转变,似乎不应该过高估计。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战略,是冷战以后西方重新看待世界大潮流的一种趋势。就像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公司一样,我到你这里开工厂,不等于我屈从于你的价值,相反,我用你廉价劳动力和宽阔的市场会获取更大的利益,况且资本主义价值观对你的渗透和冲击,是冷战时代达不到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价值,对这一点要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诺奖评委会的评价标准和我们一样,既讲思想性,也讲艺术性。他们在思想上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具体的词都很漂亮,什么温暖啊、和平啊,然后就是爱啊、荣誉啊、同情啊,但这些东西很抽象,很飘渺;是你一接触他们的标准,就知道他们的这些价值背后有许多否定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要冒犯我的利益,一旦冒犯,他们就视你为另类,写得再好,再有成就,再受欢迎,都不会给你这个奖。
举一个例子。列夫·托尔斯泰两次提名都没有获奖,我看了《诺贝尔文学奖内幕》那本书以后,才知道他为什么没获奖,不是他写得不好,而是托尔斯泰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是他对宗教,尤其是对圣经,颇有微辞,在他的小说里面对《新约》有不敬的言辞,这是犯西方社会众怒的,对“18罗汉”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就是《战争与和平》里面,他们认为托尔斯泰的战争观是错误的,认为盲目的机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不对的。还有,他们诟病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抵抗问题,诺奖评委会认为,对邪恶、对专制要抵抗,不抵抗不行。诺奖评委会认为:托尔斯泰不承认国家有惩罚权,甚至不承认国家本身,宣扬一种无政府主义理论;他以一种半理性、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尽管他对《圣经》极为无知;他还认真地宣扬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自卫和防护的权利。你看,再优秀的作品,政治不正确,思想“反动”,触动了资产阶级最敏感的神经,是决然不行的。
然后就是技术标准,或者说艺术性。诺贝尔文学奖也非常看中这个。写作是个技术活,既要有思想深度,在艺术上也要有一定的难度和高度,要符合文学发展的潮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不断创新。正如刚才说的,诺贝尔文学奖视野中的作家都是那个时代文学思潮的领军人物,是文学技术改革的急先锋,是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法的能工巧匠。诺奖评委个个是文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熟谙当代文学的各类技巧,对文学发展到哪个程度,作家探索写作技巧在哪儿比较吃力、在哪儿比较费劲,谁的方法优秀,可以说门儿清。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不会把奖授给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们会给托马斯·曼、高尔斯华绥这样既有现实主义技巧,又有新手法、新做派的作家。而到了4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盛行期,诺奖就不会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青睐有加了,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黑塞、艾略特、莫里亚克、斯坦贝克这些现代主义健将。80年代以后,世界文学潮流又为之一变,技术标准呈现多元竞生、五花八门的局面,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不断涌现,你看,从马尔克斯之后,莫里森、达里奥·福、大江健三郎、略萨,一直到今天的莫言,都是文学领域的革新者。莫言获奖就是评委对技术的考量,是对他那种大体量的,如推土机一般的叙述方式探索的褒奖。莫言是在小说叙事艺术探索方面走得最远的中国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没有看走眼,莫言的辛苦和老牛一般的执着,正好符合诺贝尔文学奖对技术的高要求,他获奖不是偶然的。

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一直是随着世界文学创作思潮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不变的是他们价值体系,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思想第一、技术第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且只要这两条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肯定不会获奖。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庆军主要讲了诺贝尔文学奖运作的机制和倾向,我主要想谈一下莫言获奖可能对国内的文学界与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界及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自1980年代开始,“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梦想,在中国作家心中普遍存在着“诺贝尔情结”。莫言获奖或许有助于中国文学舒缓这一焦虑,也可以让我们更从容地审视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但并非代表着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作为一个文学奖项,它也受到一些诟病,比如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与冷战思维的影响,比如遗漏了托尔斯泰、乔伊斯等文学大师,等等,而在具体的评选程序中,以翻译文本评选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也存在着先天不足。尽管如此,莫言获奖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却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世界性影响。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文学领域正如其他领域一样,由西方世界掌握着游戏规则与评选标准,何为文学,何为优秀的文学?是被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所确定的。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体的中国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是双重意义上的“他者”,而中国文学要为西方世界所认识和欣赏,需要穿越重重障碍。莫言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存在重重障碍,他却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的大门,当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莫言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在1980年代就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重要位置,但中国文学界还有另一些重要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韩少功、余华、王安忆、张炜、刘震云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只有深入阅读他们,才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中国作家的重要性愈加突显,我们必须摒弃1980年代以来追赶与迎合的心态,以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方面需要具有更加开阔的世界视野,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表现。我们应该具有主体性与主动性,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另外,在“文学奖”之外,中国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追求,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形式,其重要性不在于奖项的肯定,而在于它对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在这方面,中国作家既应该充满自信,也应该具备文化自觉,不满足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而应该像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者拉美的“文学爆炸”一样,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中国的形象,讲述中国的故事。
其次,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在中国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都在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80年代文学更成为整个社会瞩目的焦点,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热情与梦想,莫言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写作的。但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中,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文学失去了“中心位置”,越来越边缘化。对于缺乏宗教情感的中国人来说,文学事实上承担了一种教化功能,它不仅培育美感,而且培育向善的心灵,在20世纪,文学更承担了“启蒙”与“救亡”的功能,成为建构人们精神生活与心灵生活的重要形式,进一步成为改变现实世界的重要力量。当文学的地位逐渐衰落时,整个社会便愈趋世俗化与功利化,缺乏一种平衡物质现实的精神力量。当莫言获奖让整个社会瞩目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文学的边缘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害,重新认识文学的重要作用。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在于它通过作家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艺术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来自于现实世界,但又不同于现实世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构与反观现实世界的艺术空间,可以让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紧张节奏中停下脚步,倾听灵魂的声音,反思世界以及我们自身,让我们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探寻未来的道路。
再次,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纯文学”的力量。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俗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在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文学的娱乐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挥。与此同时,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事业的“新文学”传统日渐式微。莫言获奖将会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样的文学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会让我们在甚嚣尘上的商业化浪潮中保持清醒,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让我们看到那些真正的“纯文学”并非是“无用”的,它们虽然不能为我们带来即时的娱乐,但却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思考和把握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独特的美感,为我们带来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莫言获奖便是“纯文学”的胜利,这位30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文学道路的作家,将为无数青年作家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看到,如何在喧嚣的社会中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如何在艺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如何建构起一个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艺术世界?我想,只有更多的青年踏上追寻文学梦想的道路,才能让中国文学迎来更加繁荣的明天,也才能为世界理解中国打开更多的窗口。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莫言获奖这个事情,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这个事情本身,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莫言的作品,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很担心我们只关注这个事情本身,而缺少真正的对文学的关注,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莫言真的是陷入了我们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里面,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巨大的“成功者”被炒作。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如果我们通过莫言获奖真正的进入莫言的文本世界,也进入我们当代文学的内部,去发掘生长性因素的话,可能对我们文学将来长远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