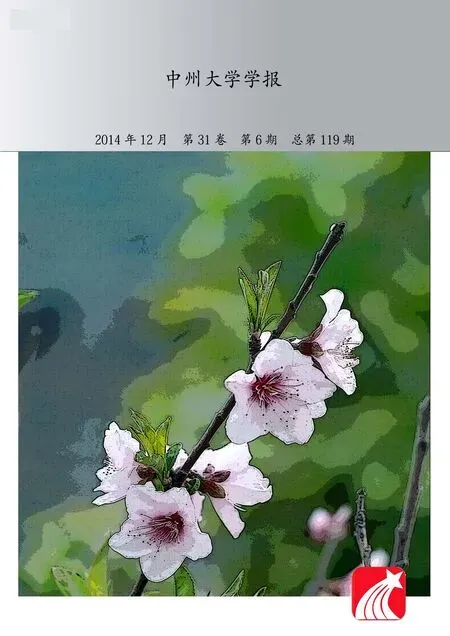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流变
——兼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
方向真
(自由撰稿人,上海 200003)
对于长篇小说,传统的评论似乎更青睐具有史诗性内涵的作品。无论作为古老的文学样式——诗歌,还是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源流,《荷马史诗》都堪称经典。史诗这一早期的文学样式终结之后,一些长篇小说汲取了史诗的宏大叙述元素——重大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凸显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及时代风云中人的命运等, 由此呈现历史的风云变幻,人在特定历史格局中的生存,人的心灵的艰难历程等。汲取史诗叙事的大格局及英雄内涵的被称为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出现在古希腊时代结束以后,其内容是剔除神话之后的英雄史赞,以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小说为代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大格局地反映社会生活,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从雨果的《九三年》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此后的维拉·凯瑟的《啊,拓荒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赛珍珠的《大地》,戈迪默的《伯格的女儿》…… 可以开出一长列书单。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长篇小说中引以为骄傲的史诗性元素——宏大叙事中的英雄主义成分及主人公理想的热度逐渐消解、降温,占据了长篇小说更大篇幅的是人生存的困境,人的挣扎、绝望、麻木、无奈等等。当自然对人类的威胁减弱,当战争、厮杀逐渐成为历史的烟云,人类转而投向看不见硝烟的商战——货币的、资源的、信息的、网络的竞争,当今人类面对的更多是平庸的、琐屑的生存情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推动着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化。长篇小说的史诗性消解与此有关。
工业革命后半叶,与史诗性作品分流的反英雄主义小说,亦即现代派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开其先河的现代小说,摈弃了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念,或走向人性及人的意识的深度开掘,或走向对现实的批判,从而形成诸多的文学流派或创作倾向,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意识流、现代主义等。当然,更多的人文内涵极为丰富的作品,远非文学流派的概念所能涵盖。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莱辛的《金色笔记》,莫言的系列长篇等。
上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或提名的作家作品,虽然叙事的历史跨度大,反映的社会生活广阔,但已与以往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迥然不同。作家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不像昔日的作家们怀着歌颂、敬仰一类的宗教式情感,他们审视、质疑、静观历史的荒谬,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痛苦、无奈甚至绝望。
今天看来,传统史诗性长篇小说所表现出的人物高度的道德自觉,及作品所展现的人性极致,极度地完美、神圣或者极度地卑鄙与丑陋,已经明显与当今人们的价值及审美见出分野。当今我们再审视这些作品时,甚至感觉有些虚假,有些审美上的不自在,尤其是我国1950年代—1970年代的一些所谓的史诗性长篇,令人读来有些难为情。现代人似乎不屑于昔日道德、理想的强劲,他们更愿意以举重若轻的姿态面对社会的林林总总。
如今,即便是史诗性的作品,也不再过分专注于所谓的宏大历史叙事,也不再聚焦于帝王和英雄的所为。长篇小说转而从大时代的普通人的生活事件入手,写出时代大格局中普通人的命运。对普通人的生活和磨难的揭示,能更真实更动人地展现普遍的人性。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再期望伟人之举、英雄之举来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走向,也不再奢望未来。于是,对传统历史叙事机制的叛逆与逃逸成为当代小说的共象——不再追寻终极意义,不再有固化的价值体系,叙事对象转向个人和民间。
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虚拟的马孔多小镇,百年来布恩斯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马孔多小镇从沼泽地上兴起,最后被旋风卷走,布恩斯亚家族的最后一代人被蚂蚁吃掉。小镇的历史映照出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百年多的历史。其奇特的象征、隐喻,生动神秘的语言,传达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民族文化内涵。莫言的小说创作与马尔克斯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家的笔触一旦深入到民众的、家族的生存底脉,实质性的生存之象便生动地显露出来。被西方世界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国度里,确为真实的存在。作家以他悲天悯人的大视界,看似幽默地叙述出一种奇异的生存状况。莫言的《红高粱》《生死疲劳》《蛙》等,或是血脉喷张的高密东北乡的民间野性及其压抑扭曲,或是民间纷杂的生存众相,如同白话的志怪小说,又间杂着世俗的欢乐和民间的逻辑。用中国文坛熟知的话来讲,他们的作品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如果将他们的作品冠之以“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是说,他们的创作开辟了文学创作的新维度。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可谓现代小说的滥觞,他的一系列作品至今仍是令人景仰的文学高峰。他的《罪与罚》对人物痛苦的深层心理的展现,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革命活动,又经受了十年苦役,他从激情的乌托邦跌入绝望的深渊后,又经历了自我救赎的精神炼狱。他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互为交织、印证。此后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用他的生命体验进一步拓展了这条通向内心的特异空间。他的长篇小说《审判》等,主人公空前地被置于存在的困境及反抗的绝境中。卡夫卡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世界的景象,这里不再有神圣的遮蔽,也不是俗世里的苦辣酸甜,而是人在无法料想的境况中,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困境。人们昔日构筑的观念框架,在卡夫卡唤醒的体验中摇摇欲坠……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多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写尽巴黎上流社会的精致生活,却也见出另类的史韵。而且,作品对沙龙场景及人物心理的精微洞察,将贵族式的感觉系统细腻地铺展到了完美的极致。这种鸿篇巨制地写人的意识和感觉,与重大历史事件无什关联的上乘之作,还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尤利西斯》虽然全书三章的结构与荷马的《奥德赛》发生着对应,但故事的主角是普通人,他们的心理活动被聚焦在18个小时之内,人的活动范围缩小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长篇小说至此,史诗性的精神元素荡然无存。
与反英雄主义小说(非英雄小说)相伴随的前苏联革命英雄主义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新中国左派作家们的作品(《红日》《红旗谱》《红岩》《暴风骤雨》《欧阳海之歌》),表现的对象是所谓的历史先驱、英雄,他们以抛弃亲情、放弃世俗享乐、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进行着救世之举、奉献之举。这类作品对极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怀着由衷的礼赞。如果说《荷马史诗》的叙事立场在当时是民间的价值取向,那么上述英雄主义作品则反映出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扭曲的、违反人性的价值观。它与强权政治共生于专制的土壤,是与强权政治异体同构的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在反英雄主义和伪英雄主义之间徘徊,期间的一批优秀长篇小说,如李锐的《厚土》,张炜的《古船》,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陈忠实的《白鹿原》,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如果说《古船》在对历史的反思、批判中还尚存理想和信仰的余韵,那么更多的作品则体现出了对昔日价值的质疑与解构。对历史与现实的重新讲述,显而易见地表露出作家们与以往的不同。因此,任何以往观念框架的批评,面对上述一类作品皆会显得无力,很难对作品做相应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优秀长篇也有着共同的显而易见的创作取向:于宏观视野的构架中,来重新读解历史和人性。
近年来,随着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和网络的影响,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受众日趋衰微。显然,在镜像和读图时代里,电影、电视剧已取代小说成为人们的主要欣赏对象。当更轻松、更能吸引人们眼球的电视连续剧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们对长篇小说的阅读时,中国小说回归到它的本源——“街谈巷议、引车卖浆者流”的言说,又何足奇哉?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将进入孤独的守望者的领域。
长篇小说显然逐渐在向人文的深度和广度掘进,且全方位施展自己的语言魅力。它以不屈服的姿态,昭示着自己的合理存在。孤独的守望者是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相信那终极意义上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追求。任何时代都有这么一批执著的守望者,他们用微弱的心灵之光传递着精神之火。守望者之一旅居海外的女作家张翎,其长篇新作《阵痛》“创作手记”里的话语,虽然关联的是她作品里的女人,却也显出更广大的道理: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乱世,每一个乱世里总有不顾一切要出生的孩子。正应了英国十八世纪亚历山大·蒲柏的名言,“希望在心头永恒悸动,人类从来不曾,却始终希冀蒙福”。
《阵痛》是张翎于2014年新出版的一部长篇力作,作品隐约传达着史诗性的精神。这部长篇小说以极富魅力的、几乎是锤炼成金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女儿的女儿,三代女人乱世里的人生。濒于灭顶之灾的女人的痛,更是家国之痛,人类之痛。吟春、小桃、武生三代女人都生在劫难中,又都在劫难逃地经历了生育时男人缺席的痛楚。
浙南藻溪乡年轻女子上官吟春,被日本鬼子凌辱后怀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她与丈夫从此在阴霾中度日。腊月的一天,吟春独自在山洞里用石头砍断了胎儿的脐带,生下女儿小桃。却意外发现,小桃竟然是丈夫大先生的亲骨肉。在屈辱与病中纠结的大先生竟未及看上孩子一眼就去世了。吟春用柔弱的肩膀支撑着艰难的日子。小桃长大成人,考上了大学。小桃爱上了越南留学生黄文灿(其母亲是法国人)。正值越南战争,黄文灿必须提前回国。二人依依不舍,互交信物。时局动荡飘摇,二人音信隔绝,意外怀孕的小桃义无反顾地生下腹中的孩子。母亲吟春请人找来“右派”谷医生,在一盆开水、一把剪刀的陋劣中,小桃产下与黄文灿的私生子武生。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赴美留学,由于突来的生存困窘,武生嫁给了一直关爱她的杜克。本不愿要孩子的武生,发现自己意外怀上了杜克的孩子。一天,独自在巴黎度假的武生忽然接到杜克的电话,巨大怪异的噪音里是杜克断断续续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爱你……只爱过你……”晚上的电视新闻一直重复播放着:两架飞机一头扎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烈火和浓烟遮暗了曼哈顿的天空。临盆的武生裹着斑斑血迹的床单,挣扎着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医院,将这个没有了父亲的女儿生在了路上,武生为孩子取名杜路得。
小说里的1942—2008年,近七十年的时代风雨,生命频频被抛出生存的正常轨道,遭遇灾难性的打击。乱世里社会文明突然坍塌,生活的秩序不复存在,人类仿佛重回洪荒,骤然落入黑暗的深渊,不得不面临赤裸裸的自然困境(吃、住)和生育困境。在极其困苦的遭际里,女人的生育又回到了人类最原始、最原初的状态。由于人的哺乳期较长,女性的生育就特别需要呵护。而女人的生产及孩子成长时期丈夫的缺席意味着什么?人类生活的扭曲?文明的坍塌?存在的无奈?乱世里女人的痛是双重的,血泪、背叛、羞辱、食物的匮乏、生育的艰难…… 然而,《阵痛》里的三代女人都不曾放弃延续生命的期望,“只要活着,总见得了天日。”
《阵痛》选取了一个并不起眼的视角——妇女生育,好似取材于历史的“边角废料”。她们的遭遇却恰恰深切展现出历史的苦难、人的苦难。濒于灭顶之灾的女人的痛,更是家国之痛,人类之痛,揪心之痛。而一些貌似宏大的叙事,烟云般地飘过去了,在读者心上不留下印痕。《阵痛》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以下启示: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还能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网络时代里小说自身的重新建构。
小说最后一部分的“论产篇”意味深长。仅仅一个页码的论产篇——杜路得——(2008),与前面的三个篇章:逃产篇——上官吟春——(1942—1943)、危产篇——孙小逃——(1951—1967)、路产篇——宋武生——(1991—2001)在结构上平分秋色。作品末章的“论产篇”,开创了一种意味无限的形式,一个堪称完美的隐喻。这一篇写的是这样一个场面:上海市一家国际学校的一年级新生班里,在进行即兴演讲的课程,题目是“我长大了做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有的说做超市的小工,可以抓小偷;有的说要在月球上搭一个帐篷睡觉。老师注意到后排一直沉默的高瘦亚裔女孩,就微笑着鼓励她发言。
女孩沉吟半晌,才说“医生”。
老师心想终于有一个靠谱的了,就问你想当哪个专业的医生呢?
女孩这回没有迟疑,开口就说“接生”。
老师吃了一惊,很少有七岁的孩子会说出“接生”这个词。就问你是不是昨天看了企鹅爸爸陪企鹅妈妈生孩子的动画片,才有这个想法的?
女孩深深地看了老师一眼,眸子里的忧郁刺得老师退后了一步。
“那部电影在撒谎”,女孩严肃地说,“我外婆和我妈妈都说,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啊!?
老师暗叹。
从结构和意义的能指上看,“论产篇”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的论篇。七岁的杜路得成年之后生育时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她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路途?怎样的命运?未来可能不是战争,更应是男权的文明等。
张翎是一个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她没有攻击谁,没有批判什么,却以横跨两个世纪的血淋淋的三幕生活场景告诉了所有读者,以丈夫——英雄为标志的世界将不复存在。而作为作家的她,在另一向度,发掘着人的隐忍和不屈服的力量——女人的力量。固然人类已经跨越了神话历史,跨越了英雄时代,历史在人们眼中不再是主动的可控的走向,但人类生命延续的生育,尤其在动乱的年代,仍是女人的献身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阵痛》延展了史诗性的精神价值。三代女人的故事,令人读出了潜在的抒情性。
如此跨度、如此深刻的长篇小说《阵痛》,对材料的取舍相当艺术而严格,其谋篇、叙事之精当,显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至高水准。张翎不偷丝毫的懒,她将三代女人经历的人事细腻真切地勾勒出来,或写意或工笔,那些年代里人的生活就完整地呈现出来了。对时间跨度里人与事的林林总总,无论选取故事材料还是讲述,张翎都很有节制。一个资深作家的悟性和力量表现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叙述的段落和每一个细节中。
《阵痛》出版之前,张翎已经出版了多种著作。电影《唐山大地震》就是根据她的长篇《余震》改编的。2009年她出版的《金山》写的是“被人忘却的那段无声的历史”——从清朝同治年迄今150多年的移民史。她用她的笔,让那些毕生行走在黑暗中,却给后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的华工们的灵魂归家。 将目光投向历史,从历史的大事件中发掘人的尊严、人性的力量,是张翎创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所在。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阵痛》携带出的历史内容,作为长篇小说应有的社会生活的和人物心理的信息量,更为丰富,也更具感人的力量。而且,小说的语感极佳,仅从叙事语言,就能获得文学的享受。
如何以新时代的敏感来认识和艺术地把握历史?无疑,张翎的这部新作给文学评论家提出了一个思考的向度。
参考文献:
[1]张翎.阵痛[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2][法]雨果.九三年[M].叶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
[4]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