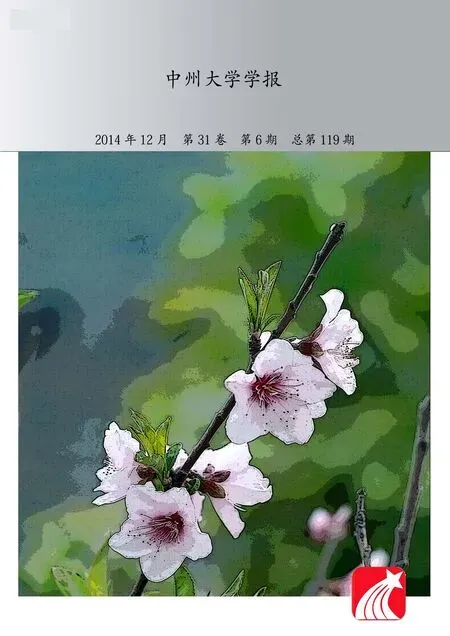姜文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狂欢化”解读
吴 妍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62)
2007年,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上映后遭到了票房和大奖的双重滑铁卢,其碎片化的镜头和复杂多向化的寓意成为观众和评委理解电影的巨大障碍。作为一部挑战观众理解力的影片,它到底讲的是一段混乱社会下的私人史,还是私人领域内的社会史?若看故事的布局和分量,更像前者;若抓住细节向上推理,则更像后者。混乱的结构暗示我们,这不仅仅是个故事,支离破碎的剪辑之后,画面显得飘乎不定,就像人们的记忆,时过境迁。必须寻找一种方法去解读,才能透过许多令人迷茫的意象与情节,达到一种对影片所表达的内涵的理解。
影片采用的是倒叙和插叙相混合的手法,包括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发生在1976年,第四部分发生在1958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相信中国人都会明白其意味。这是一个全民狂欢的年代,失去理智进入荒诞的、游戏化的野蛮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人性中的妥协与反抗、爱与恨以一种奇特的形式上演。解读这部电影,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非常契合的,并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本身就是复调和多义的。
一、“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是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造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狂欢式”指狂欢节庆典活动中的庆贺、仪礼和形式的总和,“狂欢化”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它主张翻个个儿来看世界,把世界的正反面放在一起观察,以快乐的相对性捣毁绝对理念和权威;它也主张以边缘声音的独特价值颠覆等级的一统天下,强调一切东西都具有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处于变更之中。
在“狂欢”作为理论资源被论述之前,人们更关注的是西方传统节日中的狂欢节,它源自于原始祭祀活动,最初严肃的和嘲笑神灵的祭祀活动同是官方的,“但在阶级和国家制度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这两种观点的完全对等逐渐成为不可能,所有的诙谐形式……逐渐变成表现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民间文化的基本形式”[1]7,它成为民间与教会和中世纪的官方文化和严肃文化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平民大众可以在这一天将本我肆无忌惮地展示出来而不受社会契约的束缚,宣泄自己平时隐匿的欲望。狂欢节使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观照和接近世界,人回到最本真的状态,恢复与世界的原始接触。在这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庙堂与广场。在广场上,表演是人类最直接展示自己内心的方式,这里出现的是隐匿于官方权威文化背后的另外一种文化体系——民间文化。这种狂欢节仪式与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了第二种世界的第二种生活,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在这个双重世界中,狂欢的世界是游戏的、诙谐的、没有空间界限的,生活即狂欢,狂欢即生活,但二者之间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游戏关系。
“狂欢化”的影片用独特的视角,狂欢的眼光看待世界;以鲜明的指向性,针对官方意识形态,动摇其权威性和等级的优越感;以革命性混杂的方式表达“狂欢化”的世界观和世界感受。因而,从内容到形式,它都具有颠覆性与重构性。正是在“狂欢式”的镜头与片段中,姜文演绎了自己的“梦”。
二、“狂欢式”的人物
节庆活动永远与时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节庆活动在其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1]10,因此,“狂欢式”的影片中充满了两重性的形象和场景,体现狂欢思维的人物形象都是合二为一,他们身上结合了嬗变与危机两个极端。狂欢使精神可以自由出入而不受限制,每个个体所追求的理想,在被现实摧残后,最终只能以狂欢的形式表达。在世俗的规约中,理想是不被接受的,被压抑的,而在狂欢中,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在这之中,人才真正回归了人,人才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即理想,是狂欢的重要目的。
姜文用消失、死亡与新生的循环表达人物命运的狂欢。影片分为“疯、恋、枪、梦”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形成了一个讽刺的命运的循环:“疯”的最后“疯妈”消失了;“恋”的最后梁老师自杀了;“枪”的最后小队长被唐老师杀了;“梦”的最后狂欢开始了。在影片的第四部分,即1958年,“疯妈”和唐妻在沙漠中相遇,一个是走向噩耗,一个是走向浪漫,但两人的命运是一致的。在一场沙漠狂欢的婚礼上,唐妻庆祝着自己的婚礼,“疯妈”在铁路上也庆祝重新得到了对于阿廖莎的寄托。姜文用飘忽的镜头,闪动的火光和沉醉的人群,表现出了狂欢节的肆无忌惮的气氛,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故事开始。
“疯妈”是故事中最具有狂欢色彩的人物。“疯妈”回到阿廖沙的村庄,她梦见铺满鲜花的铁道上的一双绣着鱼并有鱼须的绣花鞋,这绣花鞋是小队长的隐喻,也就成了她对阿廖莎的寄托,但它随一只喊着“我知道我知道”的鸟消失了。或许这只鸟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是“疯妈”臆想出的阿廖莎。村庄充满躁动与不安:健硕的供销员,焦躁的数学老师,顽皮的孩子,“疯妈”疯了……也有很多时候“疯妈”是清醒的,真正的疯子并不是这样,“疯妈”是因为一份爱才变成这样。姜文或许想要表现她的原始欲望怎样被激发出来,她在树上呼唤阿廖莎,在屋顶吟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些看似疯狂的行为,其实是“力比多”的转移。她守着一份苦恋,只有打破世俗的规约,在狂欢中才能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平常隐匿的欲望,才能表达那一份苦恋。只有在狂欢化的气氛里,抛弃情节的可靠性、生活的可能性,假想性地打破一切,才能淋淋尽致地展现自己,就像中世纪人们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无所保留地展示真的自己。
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生命的狂欢。弹琴唱歌的那个艺术家是妇女们的大众情人,他代表了自然健康的性,当他遭到陷害,并且了解到真相之后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无力和强大的对方斗争。但又戏剧性地被洗刷冤情,有罪或者无罪完全与自己无关,他只有选择死亡、回到自然当中才是快乐的,但也是疯狂的,当然这是他的权利。
唐老师在影片中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他创造美丽的童话与意境,给人以美的想像——路的尽头,沙漠婚礼,天鹅绒一样的肚子,挑逗的信以及信号式的小号,将世界简化为“我与你”的精神世界。他的这些“狂欢式”的豪爽与放纵所突破的正是秩序世界中性无能的灰暗现实。唐老师同时也具有“狂欢化”中“正反同体”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硬汉形象,同时又会给小队长行贿;他宽恕了犯错的妻子和小队长,却又因为小队长一语道破他的谎言而枪杀了他。
林大夫是影片中最具有人的本能状态的角色,她总是处于性亢奋的状态,以至于不能呼吸不能自持。“狂欢节的核心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弘扬和对神学、行而上学的颠覆和嘲讽。”[2]185而林大夫风骚却又自然的步态,总是湿漉漉的身体,则是用性的“狂欢化”对文革时期性压抑的反抗与嘲弄,正如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所描写的,当将性堂而皇之地摆在明处,便没有人敢说什么了。林医生甚至希望通过她去解救唐老师,更重要的是解救她自己不可救药的性欲。
三、“狂欢式”的场景
“狂欢化”理论与狂欢节仪式和它的种种变体有着深厚的渊源,而“狂欢化”在电影中的应用则表现于电影镜头中的舞会、电影院、咖啡馆或热闹的集市等具有广场语言性质的场所,同时由于狂欢节本身的丰富、多变与不确定的形式,电影中也表现为多指向性的意象的狂欢,在心理结构上符合日常生活的压抑性体验和狂欢节仪式上的瞬时感受规律。“破坏一切习惯的联系, 事物间和思想间普通的毗邻关系, 建立意想不到的毗邻关系,其中包括最难预料的逻辑关系和语言关系。”[3]36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姜文营造了令人捉摸不透的意象与场景,以陌生的逻辑方式组合的跳跃的画面,同时又有似是而非的关联,在混乱与不确定性中,将影片剪辑成各种意象狂欢的场景。
“疯”所展示的场景是寓意的狂欢。鱼须绣花鞋、被剪了头像的照片、歪脖子树、山羊、鸟、鹅卵石,“疯妈”麻利健硕的身体、荒远神秘的鹅卵石屋、精心拼凑的碎片,以及电影中轻快欢悦的《前奏曲》都使人捉摸不透,充满了怪诞之感。“在怪诞现实主义中,物质——肉体的因素是从它的全民性、节庆性和乌托邦性质的角度展现出来的。”[4]镜头本身传达的画面零碎而不合逻辑,造成了意象丰富的意指,使观众自己抽象出情感指向。这里就出现了“混乱社会下的私人史,还是私人领域内的社会史”的问题。这些意象可以隐喻“疯妈”的内心世界,破碎凌乱却又坚守爱情的脆弱的内心,鹅卵石屋是她内心的真实映射,摔碎了的盆盆罐罐、算盘、镜子以及照片,一切都不堪一击,一个喷嚏便打回原形;也可以隐喻这一时代中国的一场全民性运动,1958年到1976年,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连任何外族入侵都不曾毁坏过的曲阜孔林都给捣毁了。电影中“母亲”疯了,她打儿子,但儿子们却毫无反抗,甚至说出“你要愿意打就打嘛,真的没事儿妈”。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兴起全民“狂欢化”运动,整个社会秩序被颠倒,呈现出焦灼化、碎片化、暴力化、反伦理化的状态。
“恋”中露天电影场是狂欢节的典型场所,而将这一狂欢空间与时间相联系,就构成了官方世界与第二世界重合的效果。躁动的“文革”时期,每个人都充满了性的饥渴与暴力的冲动,既有压抑的痛苦又有发泄的快感,夜间露天电影场即是这样一种双重世界的演绎场所。黑暗带来了神秘与掩护,公共场合带来了无限的融入与同化,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被压抑的性冲动最容易释放出来,对抗官方秩序的非官方秩序也易于形成。
电影放映的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纯洁的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唐老师哼着小调,轻摇着身体,神情愉悦,妇女们跟着舞蹈欣然学着……一声“流氓”打破了这个双重世界的和谐状态,一听到有人喊“流氓”,就出现了疯狂的追捕,在场的妇女不止一人被摸了屁股,而仅有一人喊了出来。渴望被摸,性的压抑,人性的压抑可想而知。而众人的追逐是为了在秩序世界中掩饰自己在非秩序世界的狂欢,“如果说有人喊抓‘流氓’,你就去追,可是追着追着你就变成了第一个,后边的人就把你当成了流氓。”这样简单粗暴的逻辑便可将一个人置于死地。狂欢节上,这样的逻辑被用来调侃权威,现实世界则是残酷的生存考验。
“梦”中的狂欢是唯美的、纯粹的、崇高的仪式,沙漠婚礼中所有的人都纵情歌舞,而最重要的是这狂欢是庆祝人性暂时性的满足。狂欢节所注重的核心内容:最原始的世界感受,诙谐的、自由的、没有空间界限、阶级界限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演绎——音乐、篝火、烤肉、罐头和疯狂的人群尽情地狂欢。梁老师也出现了,抢走新娘,人群肆无忌惮地跳舞、游戏,疯狂地拍打着异性的屁股,这是对露天电影院事件的颠覆,同时也是对非常态的公共秩序的反抗。点燃的帐篷带着悦动的火光飞过列车,狂欢的人们在为过往的列车、为一切欢呼,“疯妈”在火车的卫生间奇异地生下了儿子,代表着最热烈的生命原发力和最蓬勃的欲望,这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突出其全民性、自由性和乌托邦性。
四、结语
《太阳照常升起》题目本身的寓意已经有了歧义性:是喜剧性的。在新的一天一切都重新来过,不论社会史和私人史多么血腥与残酷,都会有一个与之对立的“狂欢化”的世界释放被压抑的人性。不论是疯癫还是节庆,人总要寻求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方式,双重世界的并行永远不会停止。不论人世经历怎样的腥风血雨,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或许这正表达了姜文独特的历史观:历史的整体是平等的,历史中的人无论怎样都会被扭曲,而在“狂欢化”的第二世界中,人都会回到自然的人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 晓河,贾泽林,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梅兰.狂欢化世界观、体裁、时空体和语言[J].外国文学研究,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