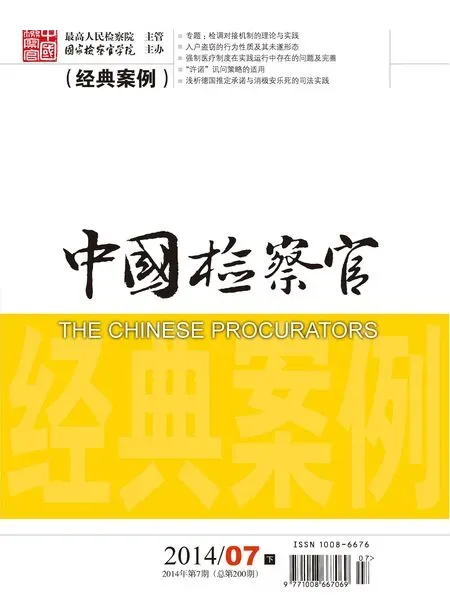“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问题的处理
文◎欧阳文芊
“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问题的处理
文◎欧阳文芊*
本文案例启示:“性保健品”可以成为假药犯罪的对象,行为人只要认知到其所卖的“性保健品”具有药的特性功效,且确定是假药、可能是假药,或可能不是真药的,均可认定行为人具备假药犯罪的主观故意。基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成本考虑,在司法实践中,“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应低于一般的假药犯罪。
[基本案情]2012年11月19日,被告人叶某因犯销售假药罪被上海某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2013年3月14日,公安机关接举报,在叶某无证经营的成人保健品店内,查获其从非正规渠道购入的,由西藏力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为藏卫食准字(2009)第020号的虫草补肾王,和西藏尼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为藏卫食准字(2006)第056号的虫草鹿鞭丸(此两处的批准文号均为厂家伪造),各30粒。虫草鹿鞭丸宣称能彻底治愈早泄及前列腺疾病,并规定了用法用量。虫草补肾王宣称有全面调节人的生理机能之功效。适宜人群:阳痿、早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并规定了用法用量。据叶某供述,这些东西系卖家上门推销到其店里的,虫草补肾王是一盒35元的价格买进,每盒10小粒,以70元的价格卖出;虫草鹿鞭丸每一盒25元买进,每盒10小粒,以50元的价格卖出。由于卖家只上门推销一次,所以无联系方式。而且买卖都是现金支付,也无销售记录。
本案中叶某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制售假药罪,涉及到“性保健品”[1]是否可以成为假药犯罪的对象、如何认定“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是否应完全等同于一般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这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对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处理意义重大。
一、“性保健品”是否可以成为假药犯罪的对象
保健食品同药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使用目的,前者的目的是调节人体机能,后者的目的是预防、治疗、诊断疾病。“性保健品”属于保健食品范畴还是药品范畴,是探讨其是否可以成为假药犯罪对象的前提。目前理论与实践对此问题尙无探讨。
笔者认为“性保健品”不属于保健食品的范畴。根据《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保健食品是指在实质上具备法律规定的27种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形式上必须取得国家正规批准文号(“卫食健字”或“国食健字”)和保健食品蓝色图标的食品。
然而对于性保健品店销售的宣传以增强性功能为目的的口服类商品,有人根据其在性保健品店内销售而将其称之为“性保健品”或者“性保健食品”。由于当前的性保健品市场缺乏监管,尚无有针对性的全国性法规管理文件出台。在法律上并无性保健品的定义。经了解,“性保健品店”是由国外的“sex shop”传演而来。“sex shop”译为“情趣商店”或“性用品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此类商店只限于对外出售一些情趣用品。而本文所探讨的,以纵欲为目的的口服类商品,在国外只有正规的医院和药店才能出售。可见国外实质上并无“性保健品”一说。国外的情趣商店只限于销售性用品,以增强性功能为目的的口服类商品在国外是归为药品类来管理的。由此可知,性保健品实为情趣用品而非食品,但由于人们的买卖习惯,而将店里卖的,宣称以能治疗性疾病、改善性功能、以纵欲为目的的口服类商品,也称为“性保健品”。
总之,在保健食品实质上所应具有特定的27种保健功能中并无改善性功能一项,且“性保健品”在形式上也不可能取得国家批文批号。所以“性保健品”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保健食品范畴,是一类相对独立的产品。
“性保健品”不属于保健食品的范畴,其是否属于药品的范畴得作进一步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102条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可知药品的本质特性是通过药物成分,对人体有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功效。据此得出药品具有实质特点和形式特点。药品的实质特点是指产品本身含有药物成分,形式特点是指其外观上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即对外宣称具有药物效果。笔者认为,具备药品实质特点的产品为药品无疑,具备药品形式特点的产品,因其已达到使人误认为其是药品的程度,故逻辑上也应将其认定为药品。
因而笔者认为,应当将含有处方药成分,且宣称有药物效果的“性保健品”;或者含有处方药成分,但仅宣称有调节作用的“性保健品”;以及不含处方药成分,但宣称有药物效果的“性保健品”认定为药品。
从被认定为药品的三类“性保健品”的社会危害性上看,首先,含有处方药成分且宣称有药物效果的“性保健品”,和含有处方药成分但仅宣称有调节作用的“性保健品”中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不能保证使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次,无处方药成分但宣称具有药物效果的“性保健品”,让消费者当成药物使用而贻误病情;再次,即使药品成分符合标准,但是没有取得国家批准文号,脱离国家监管范围的,产生危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性。而且被认定为药品的三类“性保健品”,均未取得国家药品批准文号,脱离国家监管。应当将其认定为《药品管理法》所规定的“按假药论处的假药”。本案中的虫草鹿鞭丸和虫草补肾王宣称有治疗疾病、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及用法用量,根据《药品管理法》第102条规定,应认定为药品,但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故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2项的规定,应当将其认定为按假药论处的假药。
二、如何认定“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主观故意
“性保健品”涉假药类犯罪中行为人的认知程度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认定其主观明知成立?进而如何证明认知程度已达到主观明知的标准?这是此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两个疑难问题。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常辩称其是在卖保健品而非卖药,知道是药品的话不会卖,知道是假药的话更不会卖,没有卖假药的故意。笔者认为,认定此类犯罪的认知程度应依次达到两个递进层面的标准。第一个层面上,行为人只要认知到其所卖商品具有药的特性功效即达到认知标准。在第二个层面上,由于我国刑法中“明知”的范畴应当涵盖确定性认识和可能性认识这两大认识层面,所以行为人只要认知到其所卖的是假药,或可能是假药,或可能不是真药,都达到假药犯罪主观明知的认知程度标准。
对于认知程度是否达到主观明知的标准,一般应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去证明,而这些客观行为,对于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而言,则属于间接证据。法官在认定被告人主观罪过时,只能运用推定规则,当某些客观行为确定时,指导行为人实施这些客观行为的主观意图通常也是确定而唯一的。[2]笔者认为,推定“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主观明知,在基础事实扎实可靠的前提下,主要需注意基础事实与应证事实之间应具备必然的常态联系。在此类案件中与主观明知有必然常态联系的基础事实有:第一、行为人对所卖商品具有药品的治疗特性有所认识;第二、行为人涉足药品行业的从业背景及其资格,对药品常识、管制制度和假药危害的了解程度;第三、行为人在正常的认知能力下应对药品真实性产生怀疑,而表现出来的希望或放任的态度。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叶某辩称:“送货的人跟我说是保健品。我觉得保健品和药品区别不大,有些保健品也有治疗功能的,”证明叶某已经认识到自己所卖商品具有药品的治疗特性。认识到自己所卖产品如果为假,则有假药的危害后果。其次,叶某曾经因为制售假药罪受过刑事处罚,对药品常识、管制制度和假药的危害应当比一般人有更深的了解。再加上由于正规的药品买卖必须有经营资格证并从正规渠道进货,通过叶某无证经营以及从非正规渠道购入货物等行为,可以推定叶某对其药品的真实性持怀疑而放任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叶某主观上达到明知的标准。
三、“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
《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删除了《刑法》第141条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把制售假药罪作为行为犯进行打击,即一完成制售假药的行为便达入罪标准。对于“性保健品”涉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是否应完全等同于一般假药犯罪的问题,应当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刑法成本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社会危害性上分析。“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的危害量相对其他假药犯罪的危害量要小。这主要体现在行为人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上。相对一般假药犯罪的社会危害后果,“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的社会危害后果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危害生命健康的程度比一般假药类犯罪较小。首先,“性保健品”类假药的买家通常是为了达到提高性生活质量或为了达到纵欲的目的而购买使用,对它的需要通常不是一种迫切的治疗需要。其次,“性保健品”所含处方药的成分较少,通常需要服用达到较多的量或者针对一些本身有心脏疾病的人才能形成生命健康的危害。其对人体的危害通常是一种渐变性的,而不是迅速的危及生命。另一方面,在贻误病情上。“性保健品”类假药至多是因为贻误治疗而影响性功能的恢复,而其他如狂犬育苗、易瑞沙等药品的造假,则可能因贻误病情而危及生命。
第二,从刑法成本上分析。“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若完全等同于制售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则将导致刑法成本投入过大,不利于刑法资源的优化配置。[3]据调查统计,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期间,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办理假药犯罪96起,其中“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案件91起,约占假药类犯罪总数的94%以上。而在“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中金额在200元以下的案件51起,约占总数的56%以上。销售数量在50粒以上的案件56起,约占总数的50%以上。可见销售“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在假药犯罪的涉案金额较低,且在假药犯罪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对其不分轻重一律按照假药犯罪的一般标准入罪,是司法成本的巨大消耗。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相对一般假药犯罪危害较小,而在制售假药犯罪中的占比又极大,耗费的刑法成本多。对“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应当比一般假药犯罪的入罪标准有适当的提高。然而目前,《刑法》只规定制售假药罪为行为犯,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其入罪标准。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标准,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标准。比如,2012年上海浦东新区曾对假避孕药进行严打,当时只要销售1粒假避孕药即达到追诉标准。而2013年,该区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卫生、药监等部门经过调研磋商联合规定,又将追诉标准调整至20粒,把“性保健品”类假药的追诉标准定在50粒。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使得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的追诉标准不一,法律的公平性和权威性难以彰显,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
但笔者认为,此种做法是切合实际、符合时宜的。首先,这种做法在不同的时期和区域内很好地平衡了刑法效益和刑法成本,合理的配置了当时当地的司法资源。在入罪标准上,该区把一般假药犯罪的追诉标准定在20粒,“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的追诉标准定在50粒,是充分考虑社会危害性和刑法成本的理智做法。若将所有制售假药的违法行为都纳入刑事司法程序,既不符合刑法谦抑理论,也不利于刑罚成本和效益关系的平衡,势必使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其次,这种做法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事实上,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限制法官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但并不是限制法官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出罪。[4]
最后,在赞同该区打击“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做法的同时,笔者建议国家应该出台司法解释来统一规制“性保健品”类假药犯罪入罪标准的上限。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应当从刑法干预的客观能力出发,着眼于刑法效益的发挥,使犯罪数额起点设定的合理得当。[5]
注释:
[1]本文所称的“性保健品”是指宣称能治疗性疾病、改善性功能、以纵欲为目的的口服类商品。
[2]姚斌:《如何运用推定方法证明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12期。
[3]陈正云:《试论刑法成本和刑法效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4]陈兴良:《出罪与入罪:罪刑法定司法化得双重考察》,载《法学》2002年第12期。
[5]李亮、杨万顺:《论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依据》,载《行政与法》2002年第6期。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人民检察院[34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