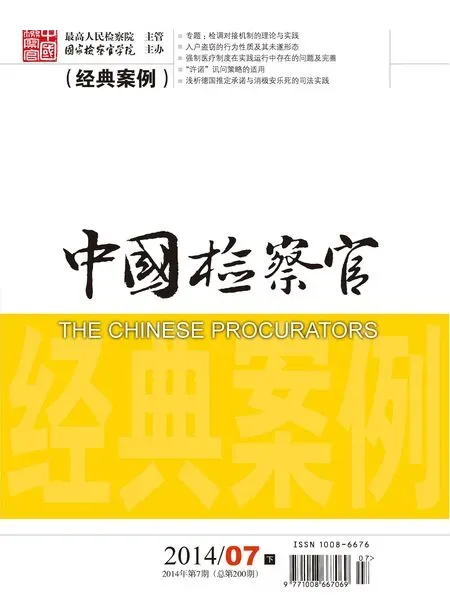入户盗窃的行为性质及其未遂形态
文◎吴海涛许林彬王庭学
入户盗窃的行为性质及其未遂形态
文◎吴海涛*许林彬*王庭学**
本文案例启示:入户盗窃是结果犯,行为人是否实现了对财物的非法占有是入户盗窃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人未能成功入户,或入户后未实施盗窃,或实施盗窃后未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均应按盗窃罪的未遂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还应注意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入户盗窃,尤其是入户盗窃未遂的,可依据《刑法》第13条做非罪化处理。
[基本案情]2012年1月4日凌晨4时许,张某伙同王某、李某等人窜入一居民小区。张某采用攀爬阳台的方式进入一幢居民楼的三楼一户居民家中,王某、李某两人在楼下望风。张某进入房屋后,在户内寻找财物准备行窃时,被户主等人发现并抓住。后被民警带至公安机关。
对此,学界和实务界有两种处理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入户盗窃是行为犯,只要实施入户盗窃行为,不论是否窃得财物均告既遂。理由是:《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修改以后,盗窃数额较大、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或扒窃,是并列的盗窃罪的选择性构成要件。因此,这里的入户盗窃,是入户盗窃未遂或者入户窃取财产价值达不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行为。所以,该案中张某等人应构成盗窃罪既遂。
另一种意见认为,入户盗窃是结果犯,实施入户盗窃行为的必须实际盗得财物才够既遂。原因是:一方面,入户盗窃应和普通盗窃罪以及其他“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将盗窃罪作为行为犯将导致惩治过于严厉。因此,该案中张某等人应构成盗窃罪未遂。
一、入户盗窃行为性质新解
(一)有关复行为犯的前提性理论概述
复行为犯,是以犯罪构成客观方面中危害行为所包含的要素行为个数为标准,对犯罪进行划分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主要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在实行行为中包含数个异质且不独立成罪之行为的犯罪,[1]与之相对的是单一行为犯。复行为犯有以下三个特点:
1.实行性。首先,复行为犯的各个要素行为不是实行行为而是自然行为。复行为犯是刑法中明确规定的一个单一罪名,其客观行为必然只体现为一个实行行为,复行为犯中所包含的“数行为”只是单一复行为的数个构成要素。[2]其次,数个要素行为需均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一方面必须符合实行行为的定型性并对法益侵害具有现实紧迫危险;另一方面,行为人必须对犯罪整体具有一致的、实行的故意而非仅具有帮助故意。[3]这就排除了表面上包含数行为,但实际上前行为并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而仅仅是后行为的预备性行为的情况。例如散布虚假信息类犯罪,真正的实行行为是散布行为,捏造或编造行为只属于犯罪预备性行为。
2.独立性。复行为犯的各要素行为必须可以独立存在,而不是仅仅依附于目的性行为。这意味着,要素行为对认定犯罪要有独立的意义。当行为人仅实施数行为之一时,就产生了社会危害性,即具有了刑法规制的必要,犯罪即告成立。例如抢劫罪,行为人只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时,抢劫罪即告成立,可以认定为抢劫罪未遂,强奸罪亦是如此。但在招摇撞骗罪中,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具体行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4]因此,招摇撞骗罪不属于复行为犯。
3.侵害法益的双重性。复行为犯中的数行为一般可区分为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两个行为均能导致不同危害后果的产生。同时,也只有两个危害后果结合到一起,才能完整地反映犯罪行为对于复行为犯罪保护客体所造成的整体侵害程度。[5]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复行为犯侵犯法益的复杂性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即在多个被侵害的法益中区分主要法益和次要法益。明确这一点对认定犯罪着手、既遂有重要意义。
(二)入户盗窃的复行为犯性质
很多国家都有将入户盗窃纳入刑事法律的立法例,据笔者考察,各国将入户盗窃入罪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即入户盗窃罪,如德国、美国;二是作为情节加重犯列为盗窃罪加重犯的一种,如新加坡、瑞典、俄罗斯、意大利、法国。我国属于第三种立法模式,即把入户盗窃列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达到入户盗窃行为标准的,构成盗窃罪的基本罪,并没有单独的入户盗窃罪。这种立法模式的特点是它既没有完全脱离盗窃罪独立存在,也没有完全依附于盗窃罪的基本罪,而是从属于盗窃罪名下,与普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并列存在的独立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入户盗窃具有复行为犯的性质。
1.入户盗窃包含手段和目的两个要素行为
首先,非法入户是入户盗窃的手段行为。入户盗窃的要素行为中包含了非法入户和盗窃两个行为。毫无疑问,盗窃是入户盗窃的核心,也是入户盗窃的目的,属于目的性要素行为没有争议。问题是非法入户只是依附于目的行为盗窃的一种手段,还是具备实行性和独立性的手段行为?
刑法中的每项犯罪都是由一定的手段或方法实施完成的,但在不同的犯罪中,手段或方法在客观方面的地位却有不同。一般情形下,犯罪手段是实行行为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6]如普通盗窃罪,行为人可以采用各种行为方式完成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盗窃手段就是盗窃实行行为本身,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此时,刑法只关心公私财物被非法占有这一事实,至于是采用什么方式偷盗,在决定犯罪成立的意义上并不重要,因此刑法不会对此单独评价。而在某些情况下,实行行为的方法或手段本身可以分离于实行行为之外而独立存在,此时行为的手段就可以称为手段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抢劫罪中获取财物所使用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由于这一手段本身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与该罪的核心行为——取财行为——相并列且分别认定和评价,使之具有了手段行为的独立意义。当行为人只实施暴力、胁迫行为而没有取财时,即可构成抢劫罪。对入户盗窃来说,其与其他盗窃行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盗窃手段是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方式进行的。《刑法》第245条规定了非法侵入住宅罪以单独保护公民住宅的安全,已表明了公民生活安宁权的重要性。而非法入户的手段本身就造成了对他人的生活安宁权的侵犯,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刑法》将入户盗窃从盗窃罪中独立出来单独作为入罪的构成要件,就体现了该手段独立存在的意义。因此,非法入户不仅是盗窃的手段,而且还具有手段行为的实行性和独立性,是入户盗窃的手段行为。
其次,非法入户和盗窃之间具有手段和目的的牵连性因果关系。复行为犯的复数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不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而且还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且,由于手段行为是目的行为的必要前提,目的行为也要求在手段行为所导致的特定状态下实施才能具备该罪的本质。[7]例如在抢劫罪中,我国刑法要求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和夺取财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必须能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而被害人也必须在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交付财物才能成立抢劫罪,否则可能成立抢夺罪。在入户盗窃中,刑法也同样要求行为人的盗窃行为必须是在非法进入他人住宅的前提下实施的。假若行为人以合法方式进入他人住宅后临时起意盗取财物,则只有盗窃行为而缺少非法入户的手段行为,在此情形下,因为只包含单一的盗窃行为,所以不构成复行为犯,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要根据其盗取财物的数额或其他情节再判断是否构成其他情形的盗窃罪。
2.数行为的主观犯意一致
行为人应在同一犯意下实施非法入户行为和盗窃行为。一般来说,复行为犯要求犯罪故意是在实施第一个行为之前或实施当时产生的,[8]并在同一犯意的支配下又实施了后续的要素行为。在抢劫罪中,这一点表现的最为明显,如果行为人以伤害的目的实施暴力,达至使受害人无法反抗的程度后又临时起意并取财,此时行为人应认定为盗窃而非抢劫。同样,在入户盗窃中也存有相同的情形。如果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时(不论合法与否)并无盗窃的故意,在入户后才临时产生盗窃的意图并实施取财行为,由于其主观犯意不能涵盖之前的非法入户行为,因此此时应以盗窃罪的其他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评价该行为,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
3.侵害双重法益
如上所述,《刑法》将实施犯罪的手段独立为手段行为进行单独评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手段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手段行为必然侵犯了某一法益。具体到入户盗窃中,非法入户作为手段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权,盗窃行为作为目的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权。这一点,与复行为犯的要素行为分别侵犯不同法益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综上,入户盗窃在同一盗窃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非法入户的手段行为和盗取财物的目的行为,导致公私财产权和居民安宁生活权的双重法益受到侵害,其行为特征与复行为犯的特征要求相吻合。因此,笔者认为入户盗窃具有复行为犯的行为性质。
二、入户盗窃属结果犯的理论依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复行为犯并非行为犯的一种,两者处于不同的分类标准之下。复行为犯和单一行为犯是根据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行为数量为标准划分的,而行为犯和结果犯是根据不同的犯罪既遂标准来划分的。我们可以用这两种标准对任何一个罪名作不同的定性划分,例如,抢劫罪既是复行为犯也是结果犯,强奸罪既是复行为犯也是行为犯。因此用行为犯和结果犯的分类标准对复行为犯进行再分类并不矛盾。
在刑法的立法规定中,由于行为的性质和作用机理及其危害结果的属性不同,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依赖性也不相同。根据刑法对行为进行评价时是否需要考虑其危害结果,可以把行为分为两种:需要结果的行为和不需要结果的行为。[9]在复行为犯中,两种行为的结合形成了三类组合方式:(1)需要结果的行为和需要结果的行为的结合;(2)需要结果的行为和不需要结果的行为的结合;(3)不需要结果的行为和不需要结果的行为结合。第一类和第三类行为的性质较好判断,如果要素行为都对结果有要求,那复合行为的既遂也必然要求存在危害结果。因此,第一类行为构成结果犯,反之,第三类行为构成行为犯。较为困难的是第二类行为性质的判断:当一个要素行为需要结果而另一个不需要时,复合行为对结果是什么态度?应以何者为既遂处断的标准?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还应从其侵犯的复杂法益入手。
复行为犯侵犯的是复杂法益,法益之间又有主次之别,其中主要法益可以成为我们判断第二类行为性质的依据。如果需要结果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主要法益,则该行为构成结果犯;反之,则构成行为犯。这一点在刑法规定的复行为犯罪的既遂标准中已有体现。例如,在敲诈勒索罪中,行为人侵犯的是财产权和人身权(或其他权利),其中财产权是主要法益,因此敲诈勒索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只对被害人使用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但未索取到财物的,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而在抗税罪中,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和从事税收征管活动的税务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其中主要法益是国家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所以抗税罪构成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以暴力、威胁的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抗税罪即告既遂,并不要求工作人员的人身权被侵害的结果。因此,可以将此方法应用于对入户盗窃既遂标准的判断。
入户盗窃侵犯的法益一为财产权利,二为安宁生活权利,笔者认为前者为主要法益,后者为次要法益。原因有三:第一,盗窃罪作为侵犯财产权利类罪中最为典型的犯罪之一,其首要保护的客体应是财产法益;而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认定是否构罪首要考虑的也应是是否侵犯了财产法益。第二,就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逻辑关系而言,我们一般认为手段行为是为了实现目的行为而存在的,因此更倾向于将目的行为置于首要位置,所以目的行为侵犯的法益应为主要法益。第三,通过比较盗窃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刑罚设置,我们可以发现财产权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安宁生活权,而重要法益是刑法首先要考虑保护的,因此财产法益应为入户盗窃保护的主要法益。对财产法益的侵犯表现为财物占有的转移,这类犯罪都表现为有具体实害结果的结果犯。至此可以断定:入户盗窃是结果犯,行为人是否实现了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应是入户盗窃既未遂的判断标准。《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虽然取消了入户盗窃的数额限制,降低了其入罪的标准,但仍然要求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人未能成功入户,或入户后未实施盗窃行为,或盗窃行为后未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均应按盗窃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入户盗窃未遂的实践处断
前述问题的研究,只是解决了入户盗窃既遂判断的理论依据问题,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是否所有未遂的入户盗窃都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在未遂的情况下,怎样界定入罪或出罪的处罚标准?
(一)入户盗窃未遂可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笔者认为,并非所有未遂的入户盗窃都能入罪。入户盗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住宅权,而且极易引发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基于入户盗窃的这一危害性,为了加强对人身、财产权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入户盗窃,不论次数、数额,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入户盗窃行为,尤其是入户盗窃未遂行为,应依据《刑法》第13条做非罪化处理。
首先,《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总则性规定,应当对分则中各罪的司法适用具有普遍的制约意义。其次,入户盗窃作为结果犯,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盗窃数额及其他方面的危害后果之间有实际、密切的关联。因此,通过实害结果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刑罚必要性有合理的理论依据。再次,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制对象涵盖了轻微的盗窃行为,对这类行为作非罪化处理既不会导致放纵犯罪,也能结合治安处罚建立更全面和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相比于犯罪化所导致的各类负面效应,对轻微入户盗窃未遂行为处以治安处罚或许可以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最后,在社会资源有限和短缺这一客观条件限制下,刑事审判也必然受到司法资源的制约。实践中,入户盗窃的多发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完全入罪化所带来的诉讼和执行成本激增问题。
(二)入户盗窃未遂处罚标准的实践考察
刑法对入户盗窃没有要求次数和数额,这是基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需要,为了体现立法原意,对入户盗窃未遂的原则上应予以处罚。只有在个别危害明显不大,又不存在情节严重或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时,才可以考虑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刑法总则的规定。刑法总则中,规定了初犯、未成年犯、自首、坦白、立功、积极退赃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入户盗窃未遂中存在上述情形时,可考虑按治安处罚处理。
2.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全部退赃、退赔”、“主动投案”、“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等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在行为人构成普通盗窃罪的情况下,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都可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入户盗窃未遂中,具备上述情形的,也可考虑按治安处罚处理。
3.其他情形。除上述具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之外,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也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其一,行为人正在实施撬锁、爬窗、溜门等入户行为时,被发现或被抓获导致的犯罪未遂。非法入户属于“行为犯”,入户行为实施完毕即会导致安宁生活的法益被侵害。但是,非法入户是行为犯中的“过程犯”而非“举动犯”,即入户行为从着手到实施完毕一般会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行为尚未实施完毕,并未造成法定的侵害结果,因此其社会危害性一般较小。笔者认为,若行为人并非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以孤寡老人、留守妇女等弱势家庭为盗窃目标,也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考虑按治安处罚处理。
其二,行为人误入空宅(室内无任何财物)的情况下,被发现或被抓获导致的犯罪未遂。这种空宅一般不具备居住的条件,因此虽然表面上侵入了住宅,但实际上并没有侵害他人的生活安宁权,所以行为人没有造成法益侵害。对这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应秉持结果无价值的理念,在没有造成法益侵害或危险的情况下,考虑处以治安处罚,如此,既不会放纵犯罪,又体现了刑法的人道、谦抑精神,同时也节省了司法资源。
注释:
[1]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2]刘士心:《论刑法中的复合危害行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3]黄丽勤:《复行为犯新探》,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4]同[3]。
[5]同[1],第98页。
[6]同[1],第92页。
[7]同[1],第100页。
[8]同[1],第102页。
[9]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人民检察院[363500]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人民法院[36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