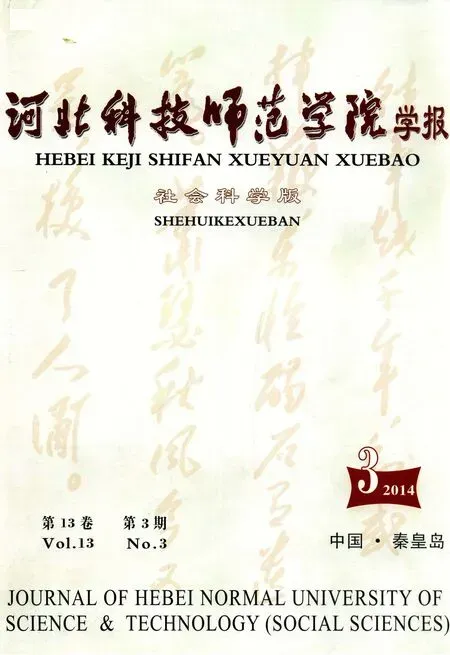结果加重犯的类型化限制*
曹玉玉,吴海峰
(1.江苏省常强律师事务所,江苏常州213001;2.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200042)
一、“加重结果”的类型化限制
我国《刑法》并没有结果加重犯的一般性规定,即使在分则条文中,也没有明显的特征表明那些罪名是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因而,学者间对结果加重特征理解不同,结果加重犯的范围随之也就不同。但是,“致人重伤、死亡”不一定是结果加重犯,“严重后果”则有可能是结果加重犯。因而,在立法语焉不详的情况下,只有结合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借鉴国外的立法规定。来解释和区分结果加重犯与其他犯罪形态。我国现行有效的有关结果加重犯的司法解释有:
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强奸罪解答》)。该解释对“致人重伤、死亡”进了了明确的规定。即强奸“致人重伤、死亡”,是指因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导致被害人性器官严重损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伤害,甚至当场死亡或者经治疗无效死亡的。对于强奸犯出于报复、灭口等动机,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杀死或者伤害被害妇女、幼女的,应分别定为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按数罪并罚处理。
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释〔2001〕16 号《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抢劫罪批复》)。该解释明确规定,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包括为谋财而故意杀人的情况,亦即承认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可持故意心态。
2002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夺罪解释》)第5 条。该解释规定,实施抢夺公私财物行为,构成抢夺罪,同时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犯罪,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抢夺财物致人重伤、死亡的,不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理。
可见,相关司法解释都是针对“致人重伤、死亡”的解释,而对“造成严重后果”、“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则需要进行细致的判断。
(一)加重结果必须是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结果
加重结果必须独立于基本犯构成要件之外,而不应当是基本犯罪的结果。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只能构成一般故意伤害罪,因为轻伤仍是基本犯罪的结果,并未超出基本犯罪的构成范围。可见,加重结果是“超出基本犯构成要件的结果”。如果“致人重伤、死亡”、“遭受重大财产损失”仅仅是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则不是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必须是基本犯结果的升层。例如,我国《刑法》第168 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中,“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是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是加重结果。
(二)基本结果与加重结果间是质的升层关系,并非量的简单增加
加重结果既表征罪质的加重,同时也表征了罪责的加重,而罪质的升级是罪责加重的原因。而认为重情节是量刑情节,则会出现罪质未变,而罪责增加的情况,显然有悖加结果加重犯设置的立法本意。结果加重犯设置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一旦实施基本犯罪行为,可能会导致加重结果的出现,而加重结果的发生也表征了罪质的变化,罪责加重也是情理之中[1]。以故意伤害罪为例,轻伤是基本犯罪的结果,“致人重伤”、“致人死亡或者以其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是加重结果。轻伤与重伤、死亡之间是一种质的升层关系,不仅是罪责的增加,也是量的增加。而《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和“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从字面意义即可看出,没有罪责的升层,仅有罪量的简单增加。
(三)加重结果必须是刑法所阻止的结果
上文论及加重结果应当是基本犯罪结果的加重,加重结果应当属于其他犯罪构成的结果。这只是加重结果的一个特征。除此之外,加重结果还必须是刑法所阻止的结果。随着风险社会、风险刑法概念的引入[2],立法者设置结果加重犯的目的在于提醒行为人,实施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基本行为时应当尽量避免加重结果的发生。即一旦发生加重结果,就应当受到较基本犯罪更重的法定刑。以《刑法》第234 条故意杀害罪为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不是刑法所阻止的重结果,因为,重结果在故意伤害的范围内,是基本犯罪所阻止的结果。因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不能够作为结果加重犯看待,可以考虑情节加重犯。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结果可以做出以下分类:一是“具体的危险犯+实害后果”,比如《刑法》第114 条、115 条,放火致人死亡的,可能构成结果加重犯;二是“抽象的危险犯+实害后果”,比如《刑法》第239 条,绑架致人死亡的,可构成结果加重犯;三是“实害犯+更重法益的重侵害”,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由侵犯公民财产犯罪升层为侵犯公民人身健康权、生命权的犯罪,当然可以为结果加重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下列情形不应该作为加重结果看待:一是财产损失类。正如上文所述,加重结果必须是基本犯罪结果的加重,这种加重是程度和性质两方面的加重,即罪责的升级和罪量的增加。而财产损失类,仅仅是罪量的增减,无法体现结果加重犯立法的意图。二是“抽象的危险犯+ 具体的危险”。如果基本犯罪是抽象的危险犯,而结果是具体的危险,则不能将具体危险作为加重法定刑的事由,仅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即可。例如《刑法》第144 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即是造成了足以产生他人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的危险,也只能在第一个量刑档次内量刑。三是“具体的危险犯+其他严重后果”。例如《刑法》第145 条,基本犯罪行为是具体的危险犯,并未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而仅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这种情况下,重大财产损失不能作为加重结果看待。四是“实害犯+不重的结果”。例如甲强奸乙女,导致乙的丈夫和乙离婚。这种情况下,离婚的结果并不是强奸行为所直接导致的,缺乏“直接性关联”。另外,加重结果必须重于基本结果,从这一点上看,此种情形也不属于加重结果。五是基本犯罪行为是实害犯。导致的结果虽然重于基本结果,但是并非基本犯罪行为本身危险性所导致,亦不属于加重结果,例如甲强奸乙女,乙女因羞愤而自杀。
由上分析可知,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的特征:加重结果必须是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结果;基本结果与加重结果间是质的升层关系,并非量的简单增加;加重结果必须与基本犯罪行为的内在危险性具有“直接性关联”。
(四)加重结果的类型分析
1.“致人重伤、伤残、死亡”类
该类型较好区分,因为转化犯的罪状描述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4 条、232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依照本法第263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三是“……,依照《刑法》第234 条、232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第二、三种情况并未出现“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因而,在此不作讨论。
(1)转化犯。《刑法》第238 条非法拘禁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刑法》第247 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刑法》第248 条虐待被监管人罪,致人伤残、死亡的;《刑法》第292 条聚众斗殴罪,致人重伤、死亡的等情形。
(2)结果加重犯。《刑法》第121 条劫持航空器罪;《刑法》第234 条故意杀害罪;《刑法》第236条强奸罪;《刑法》第238 条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9 条绑架罪;《刑法》第240 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57 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60 条虐待罪;《刑法》第263 条抢劫罪等15 个罪名。
2.“严重后果、情节严重”等综合类
严重后果和情节严重都属于综合类指标,是一种抽象的指标,该种类型的结果是否属于加重结果,立法并未明确,也难以推断。只能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予以推敲。鉴于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规范群中的准立法地位,司法解释对“严重后果、情节严重”的解释,如果符合加重结果的特征,可以认定为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如果属于情节犯或者量刑情节,则不能认定构成结果加重犯。迄今,我国关于“严重后果、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规定有以下几个: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 条;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条;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上述司法解释,对部分条文中出现的“严重后果、情节严重”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基本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具体确定,且与基本结果之间存在罪责和罪量的升层。则可以认定属于加重结果。举例来说,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中的“严重后果”指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但是,对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或者“严重后果”、“情节严重”属于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或者作为情节犯、情节加重犯的,都不能认为是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
二、“罪过形式”的类型化限制
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结果加重犯的一般规定,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总则没有责任主义原则的规定。《刑法》第5 条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应该是责任主义量的规定性。另外,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虽没有明确写进《刑法》总则,但是《刑法》第14 条、15 条和16条等规定,表明我国刑罚贯彻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既然《刑法》总则中有罪过形式的相关规定,且是对一般犯罪形态的规定。而结果加重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也需要具备一般犯罪所应当具备的构成要件要素。可见,结果加重犯也应当贯彻责任主义原则,即主客观相结合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的罪状表述中,并未明确其罪过形式。通常以“致……”、“造成”。仅考察文字的字面含义,很难得出准确且明确的答案。必须结合上文所论及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抢劫罪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可见,故意的杀人行为也包括在基本犯罪中,那么抢劫故意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是否属于加重结果呢?目前学界对此争议不大,认为抢劫罪结果加重犯中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出现,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这是司法解释的扩展。与其相同,《强奸罪解答》在其规定中,明确“导致被害人性器官严重损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伤害,甚至当场死亡或者经治疗无效死亡的”,没有明确只能是过失导致被害人当场死亡,故意也符合上述情形。因为强奸罪的暴力行为要求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行为人对其暴力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可以持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另外,司法解释从犯罪动机的角度区分强奸过程中的伤害行为,以“报复、灭口等动机”,如果出于抑制被害人反抗的动机,实施伤人、杀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应该以结果加重犯论,这显然不合理。另外强奸致死的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而若按照强奸罪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强奸罪的基本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两罪数罪并罚的法定最高刑为20年,而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而数罪并罚的情形,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小,可见,此种规定显然不合理。我国《刑法》第239 条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可见,绑架罪是明确规定对加重结果可以持故意心态。
另外,还有对加重结果持过失的类型,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罪意见》,拐卖妇女儿童,又伤害或杀害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结果加重犯中,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只能持过失的心态。但是,该司法解释也存在量刑不均衡的问题。因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结果加重犯,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而一般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而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可见两罪数罪并罚以后,是确定的有期徒刑,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结果加重犯则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结果加重犯的主观罪过形式主要有两种情况:对加重结果持故意心态;对加重结果持过失心态。诸如:
1.持故意心态。立法予以明确的是《刑法》第239 条绑架罪;司法解释予以拓展的是抢劫罪、强奸罪。
2.持过失心态。立法予以明确包括: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非法拘禁罪、阻止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等。司法解释予以拓展的是“拐卖妇女、儿童罪”。而《刑法》第133 条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笔者认为不应当作为结果加重犯论,具体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三、几个有争议的罪名辨析
尽管类型化思想能够明确《刑法》中的大多数结果加重犯。但是,由于结果加重犯概念、本质、结构等方面争议较大,且结果加重犯与相关犯罪形态的区分并未明晰,所以我国《刑法》中的部分罪名,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争议较大。具体而言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刑法》第114 条和115 条。
(一)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
《德国刑法》第223 条规定一般伤害罪、第224 条规定重伤害罪、第226 条规定伤害致死罪。《日本刑法》用第208 条规定暴行罪、第204 条规定伤害罪、第205 条规定伤害致死罪三个条文规定故意伤害罪;《台湾刑法》也用第277 条普通伤害罪、第278 条重伤罪和第279 条义愤伤害罪三个条文分别规定故意伤害罪。可见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过分述的立法方式规定故意伤害罪。而中国则不同,《刑法》第234 条用一个条文一个罪名来统制故意伤害(轻伤)罪、故意伤害(重伤)。也正因为如此,学界对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存在争论。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肯定论。认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不是独立的犯罪,而只是法定刑的升格,从立法例上看,属于故意轻伤的结果加重犯。[3]
第二种,区分论。认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是否属于结果加重犯,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区别不同情况看待。如当行为人以轻伤的故意,导致重伤的后果,可以构成结果加重犯;而如果是重伤的故意,只造成了轻伤的后果,则不属于结果加重犯,直接以故意伤害罪(轻伤)的既遂或故意伤害(重伤)的未遂即可。[4]
第三种观点,否定论。认为尽管重伤的结果比轻伤重,且刑法为此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但是不属于结果加重犯[5]。
考察上述三种观点,第二种观点除了支持一种情况构成结果犯,其他与第三种观点一致。考察第二种观点可知,以轻伤的故意造成重伤的结果,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原则处理,即以故意伤害(轻伤)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从一重处断。可见,第二种观点所支持的这种情况,并非结果加重犯,而是想象竞合犯。接下来考察第一种观点,即肯定论。其理由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某种结果能否作为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关键看该结果是否超出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范围。我国《刑法》规定,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结果为轻伤,显然重伤已经超越了基本犯罪结果,应当属于加重结果[6]。第二,重伤结果与轻伤结果不仅存在量的加重,也存在质的升级[7]。第三,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理解为结果加重犯,有利于定罪处刑。例如,当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34 条第1 款之规定,只能认定构成故意伤害轻伤的未遂。行为意图重伤致轻伤的情形,认定构成故意伤害(轻伤)罪,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即可[8]。笔者认为,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对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罪结果的界定不准确。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罪的结果应当是伤害(包括轻伤或重伤在内)而非轻伤。故意伤害罪的轻伤与重伤应当是故意伤害基本犯罪行为所能包容的。重伤不是轻伤的意外,行为人出于伤害的故意伤害他人,有可能导致他人重伤或轻伤的结果。而死亡则是行为人所始料不及的。另外,重伤仅是罪量的加重,而非罪责的加重。因而不能认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属于结果加重犯。
(二)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
对于“逃逸致人死亡”能否属于结果加重犯,历来争议较大,其中牵涉到基本犯罪能否是过失,“过失+故意“的罪过结构能否成立不作为犯罪和保证人地位问题。大致有肯定论、否定论和折中论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逃逸致人死亡符合结果加重犯的基本概念,且“逃逸”并非独立的行为,而是基本犯罪行为的自然延伸,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情况下的一种行为选择。可见两者是一个行为,而非两个行为。所以“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9]。肯定论中的另一观点,理由正好相反,其认为逃逸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并认为,“过失+故意不作为”可以构成结果加重犯。基本行为是过失的作为,而后续的加重结果部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故意不作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侵犯同一法益,则以过失犯罪处理就可以吸收后续不作为的罪过。但是如果侵害了不同的法益,如何认定,理论和实务上的观点不一。台湾学者于改之对这一问题做过有意义的探讨,有学者用前行为保证人理论,试图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路径[10]。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论尝试,例如,依照数罪的理论,则因故意只是消极利用前行为作为的因果流程,并没有积极操纵因果流程,因而难以独立的一个行为论断。如果依照想象竞合犯进行处断,则因有事后的故意消极利用前行为的因果流程,以致有额外侵害其他法益的加重结果出现,是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行为,也不无可疑。尤其从一重处断往往无法吸收每个犯罪行为。因此只剩下加重构成犯可资利用。因而许玉秀认为:“台湾地区刑法不承认过失基本犯的情况,但是过失犯也可以衍生较重的结果,或者增加侵害法益的范围、没有不可成立加重构成犯的道理。”[11]因此,虽然行为人于过失之后产生对结果的兴趣,但是整个发生结果的因果流程还是由前过失行为所造成的,事后的故意,并不影响加重结果是前过失所造成的实施,同时事后故意正好可以作为罪责的评价基准,以加重构成犯处理,没有什么不妥的,当然需要进一步的立法补充[12]。否定论者认为,如果将“逃逸致人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将出现没有基本犯罪的结果加重犯,并导致部分案件无法定罪量刑,也可能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13]。折衷说提出“情节加重犯的结果加重犯”[14]。针对上述三种观点,需要澄清“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立法的意图。
首先,有违结果加重犯的立法目的。结果加重犯的特征在于:对重结果的否定和禁止。只要出现加重结果,且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有预见,则应当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而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逸,被害人仍然死了。就不能适用该款的规定,不能适用更重的法定刑。显然加重结果出现了,且行为对此有预见,显然与结果加重犯的本质不符。
其次,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的特征是:从程度和性质上都重于基本犯罪的结果。由此可见,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应当重于普通肇事罪的结果。而根据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肇事罪解释》)第2 条可知,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满足“致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可见,基本犯罪的结果也包含了死亡的情形。因而,不能将逃逸致死的结果认定为加重结果。
再次,根据《交通肇事罪解释》第5 条之规定,逃逸是指行为人为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况。那么司法解释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交通安全,救助被害人,更在于督促行为人协助国家机关确认犯罪事实和责任的认定。这一目的和结果加重犯重在阻止加重结果发生的目的并不一致。
最后,该罪第二个量刑档次,“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属于情节加重犯[15],第三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的复合形态,是逃逸+死亡的复合。
综上,笔者认为,“逃逸致人死亡”不能作为结果加重犯,交通肇事罪具有两个情节加重犯,即对于有逃逸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适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逃逸致人死亡的,适用7年以上更重的刑罚,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
(三)放火罪
关于《刑法》第114 条和115 条的关系,历来争议较大。有赞成基本犯罪与结果加重犯的观点[16]。也有认为属于未遂和既遂关系的[17]。也有根据第115 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115 条属于结果犯的[18]。
首先,第三种观点所认为115 条属于结果犯。第115 条第二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犯的是《刑法》114 条第1 款之罪,由此,将《刑法》第115条定位于结果犯,实属不妥。
其次,114 条和115 条是未遂与既遂的关系。114 条是具体的危险犯,危险本身即是犯罪的结果。认为危险属于未遂,显然混淆了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和未遂犯的危险,前者中的危险已经满足刑罚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而后者的危险并未满足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对犯罪结果的要求。另外,我国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模式确定各种具体犯罪,某种具体犯罪是否存在未遂,由刑法总则予以规定。如果认为115 条是既遂犯,114 条是未遂犯,则导致出现结果是既遂,未出现结果是未遂,那么故意杀人也存在危险犯,可见悖论是存在的。综上意见,笔者赞同114 条与115 条之间属于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的关系。
从加重结果的类型化和主观罪过的类型化限制结果加重犯的适用范围,并区分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不属于结果加重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也不属于结果加重犯;《刑法》第114 条和115 条属于基本犯罪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使得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得到了明确的限制。
[1]曹玉玉.保险诈骗罪第四款解释路径之选择[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3.
[2]李飞.风险刑法及其适用领域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3-55.
[3]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J].中国法学,2001(3):122.
[4]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疑难问题解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2.
[5]田宏杰.故意伤害罪若干问题探讨[J].法学家,2001(4):99.
[6]王志祥.论结果加重犯的构造[J].北方法学,2009(1)53:58.
[7]王屹萱.论故意伤害罪的立法完善[D].吉林:吉林大学研究生院,2007:26.
[8]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25.
[9]李华庆.故意伤害罪的认定[D].吉林:吉林大学研究生院,2007:26-27.
[10]于改之.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的本质及其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兼论刑法第133 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立法意蕴[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5):22-23.
[11]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25-326.
[12]曹玉玉,杜冰倩.加重构成犯的罪过形式研究[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68.
[13]刘艳红.论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质[J].当代法学,2000(3):26-27.
[14]李文峰.交通肇事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144-153.
[15]李翔.情节犯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35.
[16]叶高峰.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与量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93-95.
[17]黎宏.论放火罪的若干问题[J].法商研究,2005(3):120-121.
[18]李邦友.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