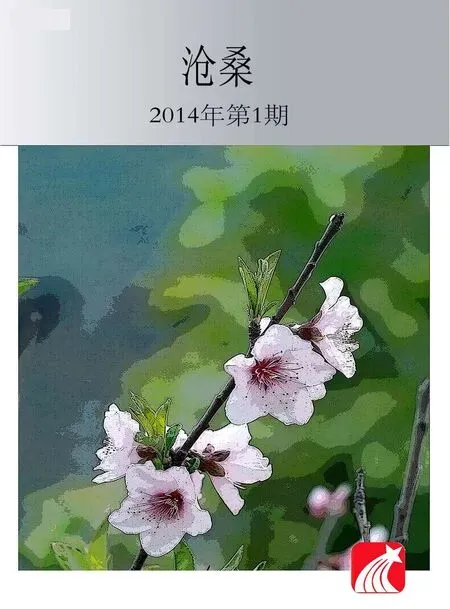晋初的党争与上流社会腐化的原因
史佳绮
晋初的党争与上流社会腐化的原因
史佳绮
司马炎在位期间,朝廷一些政治派别纷争异常激烈,且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也渗透于政党纷争中,武帝也努力为此做出相应的对策。这些腐败风气和党派斗争构成了高层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不但对前期西晋的政治格局影响很大,而且对王朝后来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西晋初期的党争与上流社会腐化这两种现象,以及造成这两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党争 社会腐化 西晋政权 晋武帝
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以后,长达十六年、历经司马氏三代的魏晋禅代道路洒满了亲曹势力的鲜血。似乎司马氏希望代魏代的名正言顺一些,遍访名士也希望能够不费力气不流鲜血地解决问题,可事情似乎无法按照他们所预料的进行,一些名士的亲曹态度特别明显,嵇康即是其中一位。景元四年(263)冬,司马昭借故杀掉嵇康,向天下人发出最后警告,司马氏代魏已经板上钉钉,毫无回旋余地了。两年后,司马炎便在亲曹势力的血泊中登上了帝位,是为晋武帝。在魏晋禅代的过程中,司马氏政权主要是依靠贾充、荀顗等礼法派人士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但也是由何晏、夏侯玄、嵇康等亲曹名士的鲜血染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即位的司马炎,又到了另一个纠结的时期,为了巩固政权,保护好先辈们打下来的胜利果实,自然不能坐视原本拥戴他的礼法派人士政治势力的无限膨胀,进而导致某一位像自己祖父那样政治强势人物的出现,威胁其政权的安全。另外,或许对那些牺牲的亲曹名士还有愧疚,或许他深知他的政权还未实至名归。为此,晋武帝除了大封宗室子弟,加强诸王的权力外,还极力在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采取利用矛盾,互相抵消的手法,使多种政治力量最终形成一种合力,推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权。而从嘉平以来,或者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或者出于司马氏的怀柔,或者因为和司马氏的姻亲关系,一些颇有声望的名士如山涛、张华等人,也逐渐聚拢到司马氏政权的周围,为司马氏所器重。这样,朝廷的两大政治势力就此形成,一以贾充为代表,包括何曾、羊琇、荀顗、荀勖、冯紞、杨珧、华廙、王恂等人,他们都是逼魏禅晋的功臣,是司马炎倚重的心腹;一以山涛为代表,包括和峤、裴楷、任恺、庾纯、张华、庾峻、王戎、王济等人,他们都是当世名士,以自身的声望为世所重。这两派人士都是因利益驱动而结党营私的官僚,在本质上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只是后者立身较为清正而已。他们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纷争不断,在西晋前期的政坛上演出了一幕幕的党争活剧。
司马炎践祚伊始,便任命裴秀为尚书令。裴秀出身于河东裴氏,其叔父裴徽是正始之音的核心人物之一,有盛名于世,宾客满门。裴秀虽与贾充同娶城阳太守郭配女,但他在尚书台真正同僚却是山涛。此时名士力量壮大,贾充等人开始反击。后裴秀果然被明升暗降,表面被升为司空,实际上被挤出尚书台。后党争集中在贾充与任恺两人所代表的集团。《资治通鉴》卷79:“七月,以贾充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充与侍中任恺皆为帝所宠任,充欲专名势而忌恺,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党纷然。”武帝亲自出面调解无效。后贾充等人运用政治手段陷害任恺,“恺既免而毁谤益至,帝渐薄之”(《晋书·任恺传》)。任恺被废,后庾纯代表与贾充一派对抗,结果庾纯被削职改授其他官职。几次党争下来,可以看出晋武帝几次处理都明显地袒护贾充一派。后围绕平吴战争引起的贾充与羊祜的争执,分歧很大。《资治通鉴》卷80:“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勖、冯紞尤以伐吴为不可。……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帝意合,赞成此计。”徐高阮指出:“贾、荀、冯等人‘是一个政治上反对羊祜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当时反对平吴便可以推测不会是根据真正的军事考虑,而是根据深秘的政治谋划,是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吴大功而回到中枢的机会。”(《山涛论》)。最后,平吴战争在武帝的绝对支持下胜利,可算是反对贾充一派的胜利,但结局却有些出人意料,贾充等人同有功者一同封赏。此党争中,可见晋武帝政治的天平一直偏向于世家大族与豪族的大势力。与其说是晋武帝对于政治的一种全面考虑,不如说这是西晋建国以来存在问题的最合适的归宿,西晋禅代曹魏实属不易,又时间短暂,很多势力无法安置,只能放任且平衡。
除了西晋前期的党争,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也很严重,渗透于整个上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晋建国之初,官场内部贿赂现象就十分普遍,受贿人员之多,历代皆少见。与对待党争行为一样,晋武帝对于这些大族与王公大臣的贪浊行为,一贯都采用宽容的态度。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拟于王者”,而“刘毅等数劾奏曾侈靡无度,帝以其忠臣,一无所问”(《晋书·何曾传》)。何曾之后,王濬以平吴之功,“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晋书·王濬传》)。功臣石苞之子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资”,“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衣统绣,洱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厄膳穷水陆之珍”(《晋书·石苞传》)。石崇“与贵戚王恺、羊诱之徒以奢侈相尚。恺以怡澳斧,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袁毅其人在《晋书》中无传,从其他人传记中记载道,袁毅为陈郡人,与华廙为连襟,“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贿赂,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晋书·郑袤传》)。就连号称“清慎”的司徒山涛,也接受贿赂。可见当时朝野上下贿赂之风已经司空见惯。此案涉及范围广、牵扯人员多,朝廷都无法处理,荀勖利用此事建议武帝杀华廙给朝廷一个交代,华廙的死暂且将此案告一段落,却包庇了大批涉案人员。可知腐败风气到了何种地步。另外,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排除异己大肆杀戮。此时“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应运而生。他们以空谈名理和反对立法名教自居,以服药和纵情饮酒为事,行为上放荡不羁,借以与司马氏对抗。西晋以后,这些“名士”中人原来的作风自然没有改掉,但饮酒、服药、空谈的作风又被西晋上流社会其他成员所接受并发扬。但这种方式不再是抵抗政治的方式,而是时髦的做法。他们饮酒、服药并不是要借以摆脱心灵的苦闷,而是当做一种标榜清高,追求醉生梦死和人生享乐的手段。
西晋前期的党争和腐败的社会风气的发生有深刻的政治基础:司马氏是运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政治演变手段从曹魏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司马氏同为士族力量,仅仅作为士族力量的一个统帅者,而并非皇族,没有给其他士族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其他势力的皇权意识相对薄弱。这样的情形便决定了司马氏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必须以世家大族的利益为基础,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新的王朝建立,并不意味着曹魏时期已经形成的各种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或解决。司马氏取得政权时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司马氏在取得政权后,要想统一全国,仍然要依靠世家大族的大力支持。司马炎也深深知道,以他当时的权利并不足以控制世家大族,他只不过是代表其利益而已。而世家大族也在东汉党锢之争之后动乱年代和两次禅让之后君权意识薄弱,转为保全门第以求生存。因此,西晋王朝从它孕育的时候起便决定了它的政权性质,只能完全代表士族利益,况且司马氏也是当时权利最大的士族。此时,晋武帝继承先辈们的成果后,必须在王室和其他士族力量之间,维持某种平衡,才能保障国家的顺利进行,若其他势力过分强大,则会对王室权利造成威胁。西晋刚刚代曹,很多力量都不稳定,避免重蹈覆辙,新的“禅让”重演,必须抬高王室权利,使得司马氏凌驾于各个势力之上。但如果失去了这些士族、豪族力量的支持,却又等于失去了王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司马氏在新的王朝建立起来必须对士族要有力量制约,而且还要对这些家族大力培植。这也就是为什么晋武帝放任党争的士族力量以及腐败风气迅速蔓延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历史渊源。此举在西晋建立之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却为后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党争和腐败的风气与西晋政权结构性质密切相关,它是一种特殊的大族政治的产物,“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的联合统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所以,西晋前期的朋党争斗与腐败风气是经过西晋这一特殊的朝代孕育出来的,只要王朝格局不变,朋党纷争与腐败风气就不可避免。其次,在出儒入玄的思想更替与杂糅下,人们往往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思想信仰,此时西晋王朝的大多数成员往往失去了儒家名士风范,开国起便威望不高、声誉不佳,皇权意识薄弱。这样总是存在与其相对的反对派,并非为了皇室权利,而是自己权利的保护,腐化奢靡的风气也慢慢滋生。另外,晋武帝的对于当时的处境并非不了解,但只因为在其位的无奈以及个人的性格原因,无法采取严厉的态度打击这些行为,或许晋武帝也没有想到他基于政治形势考虑的安抚和制衡,会使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的后代也并没有能力去力挽狂澜。
[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司马光.(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4]刘义庆.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 1955.
[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5).
[9]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J]史学月刊,1997,(3).
史佳绮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畅 思)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