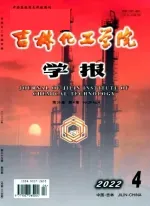从《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看元明清戏剧爱情观变化
(吉林化工学院教务处,吉林吉林132022)
受我国长期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始终是青年男女追求的焦点,被很多作家当作主题来创作,乃至“十部传奇九相思”,并且不同时代亦有不同之特色。从元代至清中叶比较有代表的《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作品,各自反应的爱情观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爱情观也在发生着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步的变化,且每一时期的作品都具有特定的时代特色和典型价值,都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文人对爱情的理解。
一、“郎才女貌”的爱情观
光照千古的元代爱情剧大师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我国戏曲史上描写爱情题材的杰出作品。它以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勇于同封建势力相抗争为题材,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寄托了作者“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1]的美好愿望。
《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之情是标准的才子佳人型爱情。才子佳人剧最常见的是一见钟情式。它们的基本格套是一见钟情,幽会偷期,得官完婚。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也是按照这一套路进行的。张生与崔莺莺佛殿相遇而一见钟情,接着又墙角联吟,道场传情,相悦的是各自的容貌,违反的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以“一见钟情”取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摆脱了门第观念的羁绊。但是,众所周知,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外貌之美从来都是爱情的重要标准,特别是这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更是由外貌美引起的,把外貌美作为爱情的基础。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2],正是崔莺莺具有了倾国倾城之貌才会使张生这位“才高”而偏逢“时乖”,在佛殿上与之邂逅时便为其美丽绰约惊得发呆:“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当时就动了情丝。
同时,为了突出崔莺莺的貌美如花,《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中,普救寺里众人为老相国做法事。作者运用了侧面描写,这样描述众和尚见到美貌的莺莺时不能自持的生动场面:
[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着法聪头作金磬敲。
由此可见,崔莺莺的美貌连已出家的和尚们都难以自持,那么能使张生如痴如醉、神魂颠倒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崔莺莺对张生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在佛殿相遇时崔莺莺就已经为意外的发现心旌摇摇了: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
好一个“回顾觑末”,把崔莺莺对陌生男子一见倾心的微妙心境袒露无遗。此后,莺莺就开始为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和情儿顺”而“每是价情思睡昏昏”,又发出大好春光不应徒然消逝”的感叹,她也希望得到张生的爱情。
可见,崔张二人的相悦只是出于对方的相貌娇好,他们二人的结合虽说是以“情”为基础,但这“情”却主要是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础上。
与《西厢记》同时代的《墙头马上》,也是一部典型的表现郎才女貌爱情观的剧作品。裴少俊与李千金第一次见面就因双方的容貌娇好而互生爱慕之情。
当夜二人就私会,这也是因为他们各自看“好”了对方的容貌。李千金在与裴少俊幽会前,甚至私奔前,除了爱慕对方娇好的容貌外,彼此没有什么其他的了解,对于彼此的家世、性格、人品等都不得而知。他们当夜幽会时,三句话没说完就开始宽衣解带,可见,他们都了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张生的爱中,“惊”崔氏的貌,“慕”崔氏的色就成了全部爱的动机,是完全的以貌取人。因此,他们的爱情都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式的爱情。无论是崔莺莺、张生的爱情,还是李千金与裴少俊的爱情,还是当时如《曲江池》、《倩女离魂》、《东墙记》等其他的“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剧作,都是作家大胆而直言地为“色”张目,这种爱情可以说成是一种原始的、本我的色欲,是一种只为满足生理需求的情感冲动。
二、“生死相随”的爱情观
从《西厢记》到《牡丹亭》的三百年间,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但大多数还是重复《西厢记》的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情。直到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出现,以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3]”。
汤显祖要在《牡丹亭》中极力表现那种“至情”说,他在《牡丹亭》“题词”里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这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说明汤显祖所要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有情”,而是有情中的“至情”。
在汤显祖心中,“情”与“理”是对立的,主张以“情”来反对封建礼制,反对封建势力宣扬的理学,他在《寄达观》中说:“情有者理心无,理有者情必无。”汤在《牡丹亭》中塑造了一个杜丽娘,是天下最有情的人,她能够为情而死,为情而生。通过对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而表现他的“至情”说,也体现了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明代统治者用所谓的贞操节烈这种封建礼教来摧残妇女,用程朱理学对女性高度防范与严厉禁锢,毁灭她们的欲望。可以说,那是一个封建礼教对女性人性完全扼杀的时代,礼教的拘束异常严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4]而杜丽娘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越是受压抑就越易生出反抗之情,她偷读《崔徽传》等禁书;在她父亲和先生看来是后妃之德的《关睢》,却被她直觉地认出了是一首情诗“为诗章,讲动情肠”,大胆地质问:“关了的睢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当第一次违背《闺苑》:“女子深藏简出,无与人面相观之理”的禁令,在侍女春香的陪同下,走出长年拘束自己的闺房到花园中游玩,被花园春景,又被花园春景唤起青春的觉醒,她感叹自己生于官宦名门之家,已到婚配年龄本应该早寻好夫婿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现在却只能在孤独中虚度青春。显然,她对自己单调而又苦闷的生活表示不满。怅然回到闺房后的杜丽娘,在睡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识,他们一往情深,在牡丹亭畔共成云雨之欢,体验了两情相合的“千般爱情”、“万种温存”。丽娘梦醒之后,梦中之事难以放怀,爱情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灵。次日清晨,她独自悄悄向后花园去寻昨日的梦境,却只见一片凄凉冷落。于是她痛苦万分、寝食不安、恹恹成疾,最终痴情而死。
三、“情投意合”的爱情观
进入清朝以后,受前代《牡丹亭》的影响,抒写“至情”的作品还是层出不穷。直到《桃花扇》的出现,才改变了描写爱情类作品专写“至情”的现状,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致使“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5],就在其剧本“流传宇内益广,虽愚夫愚妇,无不知此书感慨深微,寄情远大。”[6]尤其是作品中赞誉了李香君与侯方域的那种新式的爱情方式,把儿女私情与国家安危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剧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是不同于前代的儿女情长,他们的结合是有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原因。我们分别看侯李二人的生平。先看侯方域,他是复社四公子之一,清流的代表人物,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相当的号召力,名震青楼。再看李香君,她是秦淮名妓,才貌双全,却从未接客,是一枝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尤其是深受明末东南清流“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风气的熏陶和影响,痛恨代表邪恶势力的阉党,倾慕代表进步势力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炽热的爱国感情。加之当时清流士大夫出入青楼酒馆蔚然成风,而秦淮名妓也以结识讲气节的才子文人为荣。“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7]正是当时情景的生动写照。由此可见,李侯二人在相识之前,就已间接对彼此有所了解。所以李香君爱侯方域,不仅爱他的才华横溢,风度潇洒,更爱他“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名节和具有民族与家国意识。侯方域后来去协助史可法处理政务,前去调停四镇的矛盾,可见是个有忧患意识的文人。那么,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结合,就不单单是一般的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而是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是志同道合的理想伴侣。也正是在样基础上建立的爱情,才能在变幻的政治风云中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保持忠贞不渝。
如果仅从爱情这一点来看,侯方域和李香君都达到了以相互欣赏、相互爱慕为前提的现代爱情的高度,同纯粹的性欲有着本质的不同。侯方域在爱慕李得君之前,首先尊重她的个人品质,也就是不只是把她当作伴侣,更是当做精神和思想的知己。[8]他们的爱情模式同前代爱情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二人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倾慕的基础上,在政治思想上志同道合,所以他们的爱情一直都是矢志不渝的。侯李二人在正式认识后,就在有着共同政治抱负和追求的基础上建立起的爱情,具有彼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特征。
孔尚任在这部戏剧中,努力去创作出与前人的郎才女貌、才子佳人为爱情基础相区别的,使男女爱情建立在双方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是非观点基础上的爱情故事,体现出了“情投意合”的爱情观,为这之后的爱情作品树立了典范。《桃花扇》以后的很多描写爱情的各类作品,就随之抒写了许多“情投意合”的爱情故事。其中以《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最具典型意义。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经历了相识、初恋、热恋、巩固和破灭等五个曲折阶段。在贾宝玉周围所有的女子中,论相貌,林黛玉不是最漂亮的;论财富,林黛玉过着是寄人篱下的生活,经济上没有靠山和支柱。但是,同样对封建文人庸俗的鄙视;对八股功名虚伪的轻视;对势利龌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环境的厌恶,就成为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勾通心灵的基础,心心相爱的桥梁。他们的整个相爱过程,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纯洁的精神生活。他们吟诗抒情,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在长期的叛逆斗争过程中互相支持,与前代的爱情有本质的区别。
《桃花扇》所开创的这种“情投意合”式的爱情较之《牡丹亭》时代的爱情观又向前进了一大步,与同时代的表现志同道合爱情观的《红楼梦》相呼应,并且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
四、结 语
对《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三部作品做一下简单的比较。
《西厢记》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式的爱情。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纯粹是一见钟情、才子佳人式的。崔莺莺是个沉稳、恬静的少女,有着娇好的容貌,又精丝绣女工,擅琴棋书画。但是受封建家庭的教养,一直在深闺中忍受着空虚寂寞。封建礼教不能完全压制住她的青春情感。她一直都有不甘寂寞的苦闷心情,渴望打破传统的禁锢,寻求和异性恋爱的自由。崔莺莺与张生佛殿相遇后便彼此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互吐心声,陷入情网之中不能自拔。他们相悦彼此的才貌,违反的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西厢记》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反抗。而《牡丹亭》则是在《西厢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从《西厢记》产生的元代初期到《牡丹亭》产生的明代晚期,封建社会又发展了三百年,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和摧残更加厉害,尤其是对女性思想上的束缚和扼杀比前代更加残酷。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男女想要争取爱情婚姻自由也更加艰难。汤显祖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通过“生而死”、“死而生”的离奇跌宕的情节,表现杜丽娘为争取爱情自由而付出的艰辛。作者让杜丽娘出生入死,让她在执着追求中向人们展示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反映了“生死相随”、“情”胜“理”的新爱情观和时代特征。这是《西厢记》中所没有的。
到了《桃花扇》,爱情故事又被注入了新的内质,使爱情内容更丰富和深化了。
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可以说在反抗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婚姻幸福上,三部作品虽然有着共性和继承的一面,但《桃花扇》中的主人公,特别是李香君追求的内容要丰富的多,追求的方式也更大胆,使李香君这一人物性格具有了现代女性的一些特点。
从对社会的历史意义来说,《牡丹亭》让剧是青年男女能够为了爱情出生入死,把追求爱情自由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这种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爱情主题,比起《西厢记》把爱情仅仅建立在反封建礼教,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郎才女貌”的基础上,显然又进了一步。而《桃花扇》更是用新的观点来对待爱情,李香君之所以倾心爱慕侯方域,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高尚的民族气节,由敬生爱。也正是出于这种“情投意合”的感情,她才能在从结识侯方域那天起,就死心塌地,以一生相托,不惜用生命抗拒邪恶势力的欺侮和压迫[9]。尽管《桃花扇》最后以侯李二人双双遁入空门的悲剧收场,但是它所开创出的这种“情投意合”的爱情方式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上,使得爱情描写得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飞跃。
总之,从描写“郎才女貌”的《西厢记》,到抒写“生死相随”的《牡丹亭》,再到开创“情投意合”的《桃花扇》,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继承关系,但又有其各自的较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对爱情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和意义。
[1] 王实甫.西厢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2] 王秀梅译.诗经·关雎[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沈德符.顾曲杂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 鲁迅.鲁迅全集[M].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 沈成恒.重刻桃花扇小引.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
[7] 余怀.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刘秋萍.解读孔尚任戏曲作品〈桃花扇〉中的李香君[J].戏剧之家,2014(4).
[9] 岳振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朵荷花——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J].安徽文学,2014(8).
——从曲中的副词分析崔莺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