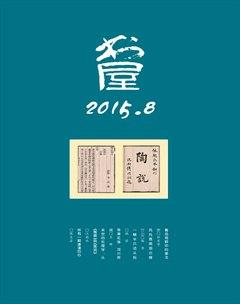不能遗忘的维新志士刘善涵
夏光弘
今年3月,是著名维新志士谭嗣同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在纪念和重温他甲午中日战争后那段在浏阳创办算学馆、鼓吹新学、开湖南维新风气的历史中,似乎总离不开那位实心办事的益友、畏友刘善涵。刘善涵,字淞芙,又字松芙,斋名蛰庐、蛰云雷,湖南浏阳人。他和同县谭嗣同、唐才常两先生是肝胆至交、文字契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中,仍收有谭嗣同给刘善涵的书信十四封,书中析义论文,对刘善涵推崇备至,刘对谭嗣同亦倾心崇敬。刘善涵写给谭嗣同的书札甚多,可惜都因戊戌变法失败后恐遭株连,而在谭被捕入狱前悉数焚毁。
刘善涵与唐才常是少年同窗,但与谭嗣同相识却始于武昌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春,谭嗣同初次与刘善涵邂逅相逢:“前月在龙君斋头晤语,礼让彬秩,言庄容肃,商榷术艺,而终无一语及俗事。窃谓大可以觇彼此之志趣学养。自此愈益钦畏,亦愈爱慕。”〔1〕刘善涵学有根底,嗣同亦“性乐文史”,两人很快结为学术文字之交。随后,唐才常也从浏阳来考入两湖书院,于是三人之间交往日多,切磋愈深,讨论时政,亦是志同道合,大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感。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遭失败而被迫签订割地赔款、屈辱求和的《马关条约》之后,他们更是义愤填膺,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中国仅靠改良已无济于事,而必须通过“变法维新”改变祖宗法度,设计新的方略,才能救亡图存。而要变法,则必须将“变学校、变科举”置于优先地位,从改变旧的教育入手,改习八股时文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才能真正培育出新的济世之才。但考虑到顽固守旧派的势力很大,欲全国一时发动,必然遭遇重重阻力而失败。于是三人商定,将自己的家乡浏阳作为起点,“先小试于一县”,再逐步推广,以此转变全省的风气。他们决定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由谭、唐分别写信给浏阳士绅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先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刘善涵则由武汉动身前往上海,了解国内外“洋学堂”的办学模式,考察新学校的课程开设及教学管理方法,并采购一些数、理、化的新书。
次年(1895)五、六月,刘善涵、唐才常先后回到浏阳,筹划兴算办学事宜。期间,刘善涵经常造访欧阳中鹄先生,与之畅论救亡之道,尤其申述自己对旧书院当革新课程,方能培养有用人才的意见。故,欧阳中鹄先生在为谭嗣同《兴算学议》作批作跋中有言:“唐生才常,刘淞芙秀才善涵,皆吾邑崛起英俊,才气奋发。唐生曾有书来,言必变法,淞芙亦屡面论,皆明白晓畅,得其大旨。盖由敏而好学,又外游,阅历时变,故能知彼此胜负长短之数。”〔2〕并在写给江苏学政龙芝生的信中称刘善涵“天分甚高,所学与唐生同一门径”。
不料他们创建新型学校的主张,竟遭到浏阳名士刘人熙、陈曼秋及一些守旧士子的极力反对。于是,他们决定请求湖南学政江标的支持,饬会浏阳知县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公推刘善涵执笔,向学政撰写禀书。刘先生的这篇禀书写得非常精彩,既高瞻远瞩,又析理透彻、层层深入。他用“算学者,器象之权舆;学校者,人材之根本”开笔,先阐述兴办算学的重要,“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再由旧学之弊端,说明湖南今日兴算之迫切:“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无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等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一节,非但当世之远谟,抑亦湘省之亟务。”〔3〕禀文上呈,得到湖南学政的批准,但浏阳知县碍于当时正值三年一次的科举岁试,担心引起“忿激之辈”闹事,便没有立即执行。后经谭、刘、唐三人继续抗争与努力,才于1896年冬正式成立算学馆。这一创举开创了湖南讲求新学的风气,“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从省会长沙到某些州县,纷纷改书院为学堂,效法浏阳崇实学的做法,流风所及,影响全国。
当时为筹备算学馆开办的经费,还发生过一个在浏阳办矿的分歧问题,也可见刘善涵的过人之处。为走实业救国之路,湖南已于1895年成立了省矿务总局,浏阳也由谭嗣同、唐才常申请“于浏城设立矿务分局”,浏阳矿务由欧阳中鹄主持,唐才常、刘善涵协助办理。矿务前期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刘善涵满腔热情,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地寻找矿源,选定矿址;他还为物色矿师再次到上海,先拜访了被李鸿章称为“海内奇人”的宋恕,再会见了康有为,然后聘请矿师,采购了一些机器设备。一切操持妥当后,在由谁来经营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很大分歧。唐才常赞成官办,认为“硝矿锑矿概由官办,名正言顺”,中鹄先生也表示赞同。刘善涵则主张商办,反对官办,认为与其由官府插手而使其控制企业的管理权,不如让那些地主、绅士入股,团结他们共同管理企业。显然,刘的主张是正确的,按照他的主张去做,可吸引一些地主、绅士投资采矿业,从而向资本企业转化,这是符合当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趋势的。正在唐、刘争执不下的时候,省矿务总局通过抚院接收浏阳矿务,将浏阳锑矿改为官办。这不仅使刘善涵大为不满,连唐才常也大失所望,打算“退避”其事。后经调解,唐表示愿意暂留浏阳矿务局工作,刘则决意离开浏阳,仍赴两湖书院读书,并按照早有的想法,准备与在书院的新化人、著名舆地学家邹代钧共同筹办《湘报》,换一种方式继续自己的维新救国事业。
要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推行制度革新,必须先开启民智,唤醒大众,形成改革的共识,而欲达此目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莫如创办一份全新的报纸。刘善涵有鉴于此,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从上海美华书馆购得《万国公报》一千二百份,每月在长沙太平街“人和”豆豉号发售一百份,改变了甲午战前湖南所阅仅有《申报》、《汉报》两种的状况。而且通过卖报,刘先生产生了自办报纸以满足湘中士绅求知欲望的设想,并给这份即将创办的报纸取名为《湘报》。1896年正月,他起草了《湘报馆章程》,请邹代钧、谭嗣同题跋,得到了他们的热忱支持,谭称“章程”“典赡详实,竟开报馆未有之奇”。后来又在给刘的回信中说:“嗣同于此事应如何办法,实难远度。惟觉足下行数千里,费数千金,孤诣苦心,不计甘苦,在寒士中可谓绝无仅有,总期事必有成,乃不负耳。”〔4〕对刘的努力深表赞赏,并希望早日成功。没料到刘善涵将《湘报馆章程》全文刊出后,登报招股集资,响应者却很少。最后终因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迟迟不能创办而“竟作罢论”。
早期《湘报》虽然流产,但它是湘鄂地区酝酿最早的维新派报纸,对此后湘鄂新报刊的陆续创办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后来戊戌(1898)二月,由熊希龄集资主办,谭嗣同、唐才常等主笔的《湘报》,终于成了湖南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报刊之一。
办矿、办报的接连受挫,使刘善涵维新救国的热情和锐气受到很大损伤,后来又因为对康有为的某种成见、对张之洞存有幻想而与康、梁的激进维新保持一定距离,从而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友人的关系也日渐疏远。1897年返回浏阳老家后的刘善涵继续以教书为生,但对革新社会、根除陋习、改革教育的维新事业仍竭尽全力。他主张男女平等,非常痛恨旧时女子缠足的陋习。女孩子一双本来健康的脚,却从小就用布帛紧扎,使足骨变形,脚形变小,变成所谓的“三寸金莲”,而以此为美。这分明是男权至上欺压女子的陋习,却延至清末仍未革除。刘善涵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与浏阳绅士黎宗鋆等发起成立“不缠足会”。他游走于士林乡绅之家,驳斥各种歪理邪说,宣传和提倡男女平等,得到浏阳开明人士的赞同。广大妇女更是积极响应,原缠足者放足,女孩儿从小不再缠足,使不缠足的风气于辛亥革命前就在浏阳城乡大开,并影响到附近各地。
为了进一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刘善涵后来还出资在浏阳迎佛寺创办了第一所县立女子学校,聘请门人刘涤吾的女儿刘静容为校长,谭嗣同夫人李闰为学监,欧阳予倩的母亲任修身、图画教员。因当时开办女子学校是移风易俗,封建顽固守旧人士极力反对,认为有违祖制,不成体统,故不让家中的女子入学,刘当即命令家中女儿、儿媳和亲族中的年轻妇女都报名入学。对亲友或熟人中有不愿送女子入学的,他必亲自上门劝说,讲明女子读书的意义,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直到达到目的为止。由于他的执著和辛勤工作,加上刘静容姐妹等老师都是德才兼备、有文学修养且思想进步的青年,课讲得生动,很受学生欢迎,故学校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尽管刘善涵回浏阳后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朋友少了交往,但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惨遭杀害后,他悲愤交加,愤世嫉俗,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在《谭壮飞狱中题壁诗》一文中,他直书“戊戌之狱,康有为构成之,而洞察其事上书告密者袁世凯也”,认为康有为倡变法,“乃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是政变之由,刺探其事告密的人则是袁世凯,而死难六君子中谭嗣同“志节最为明伟”〔6〕。并在写给著名诗人易顺鼎的诗中,批评康有为“涂附井田张伪学,潜移宫柄累齐民”,指责康张扬他那套伪装的孔学,害得谭嗣同等人被“金牌枉断三言狱,铁案同归七日诛”。对烈士的死,他哀悼“黄鸟闻歌人百赎,赪麟削简泪双枯”,“空见素丝悲墨翟,更无净土葬田横”〔7〕。在悲愤中,他不忘收藏好契友谭嗣同给他的书信、照片和题跋等资料,在今天的《谭嗣同全集》中收有谭写给他的信十四封,在他《蛰云雷斋文存》中则有《谭壮飞狱中题壁诗》、《题谭壮飞太守小像》、《寥天一阁印录序》、《为创立算学馆上学院江建霞书》、《中日战争诗史》等,这些都成了研究谭嗣同生平与思想的重要文献。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使湖南成为维新变法中最富朝气的省份的维新运动,前期诸如办算学馆、办矿、办报及创办“不缠足会”和第一所女子学校等活动中,真正实心任事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刘善涵却一直鲜为人知。他对当时有些人计划拥光绪、废慈禧的不切实际,而主张持重待时、属意于全面的民主革命的远见与苦衷,更是不便宣传,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重温湖南维新运动这段历史时不当遗忘而值得纪念的。
注释:
〔1〕〔2〕《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71页。
〔3〕〔6〕〔7〕刘善涵:《蛰云雷斋诗文集》,浏阳市松芙文化研究中心翻印本,第122—124、119、18—19页。
〔4〕《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8页。
〔5〕《蛰云雷斋诗文集》载刘善涵女刘豫璇《忆先父二三事》:“先父对康有为的作风有不同的看法。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先父因赴上海物色矿师,曾拜访过康有为。当时,康氏正在组织强学会,宣扬孔子改制学说,企图依靠统治阶级上、中层人物进行改革,而他对于社会地位不高的士子,则俨然以‘南海圣人’自居,要拜他的门,才予以称赏和推毂。先父秉性刚正,雅不欲依附康门以进,同时他看到康氏结纳某些人士为一个团体,又要他们捐款相助,认为这不免使人有植党营私的感觉,因此,他不愿和康氏及其门人多所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