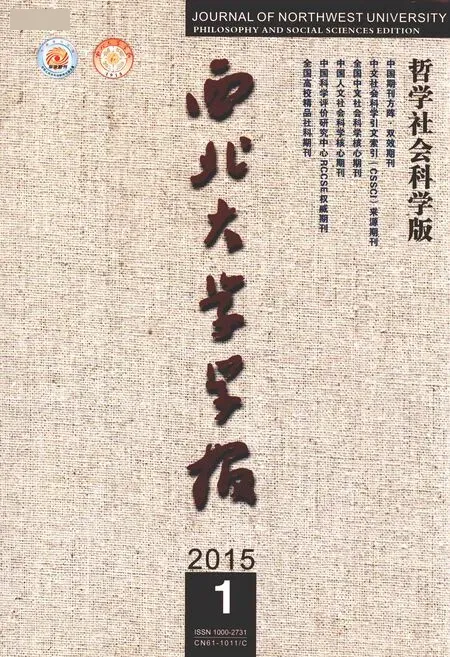论教育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其保护利用
周俊玲
(西安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考古与文物研究】
论教育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其保护利用
周俊玲
(西安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教育遗产是各个时代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学校、图书馆、学术机构等有关教育的遗存。我国现存教育遗产可分为五个类型:孔庙、书院、早期学校遗存、图书馆旧址、其他教育遗产。教育遗产具有文化传承、隐形教育和美育的功能。结合实际,就教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来说,应在保护其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挥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
教育遗产;文化价值;保护利用
“教育遗产”(Heritage of Education)特指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早期学校、图书馆、学术机构等有关教育的遗存。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将2013年4月18日国际文化遗产日主题定为“教育的遗产”,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教育遗产的认知。中国很早就有了文化传习机构,春秋以后,官学、私学协同发展,形成“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景,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遗产。这些教育遗产不仅承载和见证了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的发展脉络,而且内含着中国古代建筑本身特有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蕴等。遗憾的是今人对教育遗产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至于“传统教育大国”只能靠“纸上斑驳的文字”来说话。基于此,加强对教育遗产的总体性研究、保护和利用,可谓意义重大且任务紧迫。
一、教育遗产及其主要类型
“教育遗产”包括各个时代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教育遗存。中国教育遗产十分丰富,在已公布的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宋元到民国的教育遗产120余处,分布于几乎所有省份,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关教育遗产的数目远远超过此数。
根据性质和作用的不同,本文将教育遗产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一)孔庙
孔庙又称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文宣王庙,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它是中国古代集教学与祭祀为一体的祠庙建筑。孔子被尊称为“素王”,故孔庙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孔庙数量之多、规制之高,建筑之宏大、艺术之精美,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堪称一绝。曲阜孔庙是所有孔庙中规模最宏大、气魄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其与孔府、孔林一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此类教育遗产40余家,其中以孔庙为名的6家,如北京孔庙、嘉定孔庙等;其余多以文庙为名,如韩城文庙、平遥文庙、岳阳文庙等;也有文庙和武庙合在一起的,如四川资中的文庙和武庙、云南宾川县州城文庙和武庙等。有的文庙与地方官办学校合二为一,称为学宫,如广州的德兴学宫、揭阳学宫、海南的崖城学宫等。
(二)书 院
书院肇始于唐代,大兴于宋初,废止于清末,是与官学并存、风格独特的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开元十二年(724)设立的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以藏书、修书、校书为主。宋代书院大兴,有白鹿、石鼓、嵩阳、应天府、岳麓、象山等十余所著名书院,不少贤达鸿儒皆讲学其中,形成自由研究、学派争鸣之风气。康乾以降,书院遍及全国,有近两千所之多,几乎所有县城皆建有书院,如陕西安塞县城仅有28户人家,也建有书院一座[1]。清朝末年,随着西学东进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书院大多改制为近代学校。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关书院的有13家,其中第七批就有5家,包括江西吉安的白鹭洲书院、山西阳泉的冠山书院、陕西三原的弘道书院等。受“庙学合一”形制影响,大多书院都设有孔庙作为书院标示和宣扬儒家道统的圣地,有的书院的孔庙形制和规模并不亚于独立设置的孔庙。
(三)早期学校遗存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一些中国传统的书院逐渐演变为学堂,清政府及之后的国民政府创建了一些西式学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些私立学校,国外的传教士也开设了一些教会学校,它们共同构成中国近代教育的雏形。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教育遗产中有关早期学校遗存的共有54处,可分为大学早期建筑、大学旧址、军校旧址、中学旧址、研究机构旧址、革命旧址等。大学早期建筑主要有北京大学红楼、清华大学早期建筑、武汉大学早期建筑、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早期建筑、四川大学早期建筑等;大学旧址主要有东北大学旧址、中央大学旧址、金陵大学旧址、之江大学旧址等;军校旧址主要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等;中学旧址主要有重庆的育才学校旧址、河北保定的育德中学旧址、浙江绍兴的春晖中学旧址等;研究机构旧址主要有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等;讲习所旧址主要有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革命旧址等。
(四)图书馆旧址
中国很早就有了书籍刊印、收藏的场所,许多书院的藏书楼就具有这种功能。福建连城县的四堡书坊为中国最完整的雕版印刷遗存;浙江湖州嘉业堂的藏书楼则为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如北洋政府时期的北平图书馆、湖北武汉的国立图书馆、云南腾冲县的和顺图书馆等等,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类教育遗产不是很多。
(五)其他教育遗产
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如北京的国子监遗址、湘南学联旧址等等;教育家的故居、墓地和纪念馆,如浙江绍兴的青藤书屋和徐渭墓、河南孟县的韩愈墓、广东佛山的康有为故居等。这些教育遗产常常与其他文化遗产交叉,边界不是十分清楚,统计比较困难。
二、教育遗产的文化价值
(一)教育遗产是教育发展的记忆,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主要是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从文字肇始,就有专门传习的机构,当时称之为“成均”,夏朝将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商朝称为“庠”,到了周则称为“序”。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教育也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唐代书院滥觞,到了宋代兴盛一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一直影响到明清。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东西文化并行发展,冲撞融合,各类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竞立于各地,由此存留于今的此期教育遗产也风格各异。有些反映中外文化交流,如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旧址、河北保定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有些承载近代重大事件,如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黄埔军校旧址;有些反映共产党革命事业发展历程,如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陕西泾阳的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革命旧址等等。
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交流,而教育遗产则是教育历程的见证者,每一处教育遗产皆直接见证和镌刻着教育发展的痕迹。基于此,考察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和教育组织,不仅可以从典籍文献中进行搜寻,而且可以到现存的教育遗产中进行在场感受。目前的教育遗存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教育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建筑样态,从孔庙到书院、从启蒙学堂到大学旧址、从教学机构到学术机构,皆内涵有中国教育的基本元素。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遗存,无论新旧高低、典雅平常,均镌刻着中国教育的风雨历程,蕴含着中国教育的特质。明乎此,加强对教育遗产的保护利用,不仅可以还原中国教育的发展图景,再现中国教育的历史流变,而且可以通过这一教育载体的利用,收到文化传承和文化育人之效,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教育遗产根系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隐形教育功能
教育遗产具有浓郁的人文意蕴,公众对教育遗产的热情,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教育的尊重和敬仰。教育遗产通过特有的符号系统和模式化的空间布局,表现出礼仪性、象征性和纪念性的特质,而隐喻在其后的是“礼”“敬”“和”等代表中国文化元素的深层建构[2]。当人们游走于因地制宜、虚实相生、高低错落的教育遗存时,扑入眼帘、沁入心脾的是无形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通过教育遗存,以“在场”的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者面前,可以潜移默化地培育自信、完善人格、提升修养。
教育遗存不同于一般建筑,其本身就内生有一定的隐形教育功能,正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新校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所言:“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标。”[3](P144)建筑遗产是既往事件、时光和记忆等“文化因子”在建筑上的印痕,犹如台阶上的青苔,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人们一踏进校园便可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分量,生活在其中更能清晰地体会到大学的文化气氛、人文精神、价值诉求[4]。它像晨钟暮鼓一样,对人们产生强烈的家园式的精神感召。
(三)教育遗产是传统建筑的重要类型,具有一定的美育功能
目前留存的教育遗产,无论孔庙、书院,还是早期大学建筑多以传统建筑为依托,这些传统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和审美的融合体,它通过格式化的建筑样态向人们传递宁静肃穆、敦和修善的意境,从最世俗的功利诉求到最高远的文化理想。教育建筑类遗产表象丰富、寓意深远,突破了一般建筑的局限,不仅能给学生带来审美享受,而且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具有一定的美育功能。
用美好的自然景观和巧妙的校园布局来陶冶学生情操,塑造美的心灵,在中国古已有之。宋代以来,中国儒生就把书院建筑作为儒家价值传承的物质媒介,讲究“借山水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5],这种书院遗风现在依然可以从教育遗产中的书院建筑得到呈现,如岳麓书院依岳麓山而瞰湘江,体现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景象;嵩阳书院背靠峻极峰,面临双溪河,气度平和而宁静。中国早期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皆选址在园林之中,继承了中国书院的选址传统,使得校园不仅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具有“善美同意”的美育功能。教育遗产通过优美的外部环境,激发学生从美的欣赏到美的创造,从而实现育人目的,这种教育类建筑的设计理念,对现代建筑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教育遗产的保护利用
近年来,随着中小学校大跨度并校,高校大规模更名扩建,社会基本建设的不断增加等,教育遗产和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破坏严重,悠久的教育传统与稀缺的教育遗产形成鲜明的反差。如何利用实物遗存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固态与活态之间取得平衡,是今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就教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来说,基于不同的教育遗产,可以在保护其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挥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
(一)对于孔庙遗存,可以在修复的基础上综合利用
孔庙是传承儒家文化和扩充中国教育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政治教化、文化教育、规劝学习等传统教育功能,孔庙建筑不仅遍及大江南北,而且绵延到东南亚各国,其中以韩国尤为突出。在文革“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国内许多孔庙遭到了严重毁坏,但因其数量众多,此类遗产仍是目前教育遗产的大宗。可以借助文庙遗产这种教育载体,展开多样化的、丰富的特色活动,实现传统文化延续和现代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重构孔庙的现代价值。
其一,建成文庙博物院,发挥其特有功能。作为教育遗产的孔庙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可以将其建成当地文物资源的收藏、展览馆;建成非物质文化展示和研究场地。柳州文庙举行的“传统文化活动月”,都江堰文庙举行的“乡饮酒礼”等活动,都是很好的尝试。其二,恢复祭孔、庙会等活动,发挥其内在的文化功能。祭祀孔子是孔庙的核心功能和特有符号,伴随祭孔也会形成当地独具文化韵味的庙会活动,可以合理、有序地恢复这一传统文化活动。今之山东、南京、杭州等地的孔庙每年都举行大型祭孔活动,对于普及知识、启发民智、培育惯习等都具有积极作用。其三,创新教育方式,发挥遗产教育功能。“庙学合一”是孔庙的特性,也是其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上世纪20年代,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利用番禺学宫作为教学场地的。近年来,这一功能在许多地方创新出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吉林文庙举行成人礼活动、衢州文庙举行“毕业·开蒙”活动;陕西文庙现为碑林博物馆,其依托历史遗存开展的书法教育、书法比赛等活动,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等等。
(二)对于书院遗存,可以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利用
要理解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和艺术,就无法绕过当地的书院[6]。书院建筑既不同于宫殿建筑,也不同于民间建筑,它是中国文人的建筑,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建筑观念和审美情趣,朴实、淡雅、自然、含蓄,正如文人画的水墨写意,清新明快的格调[7],对这一教育遗产的保护利用,应以弘扬地域文脉和学术思想为主线,形成协同创新的格局。
其一,建成书院博物馆。对于一些现存较好的书院,可以在保护的基础上,建成书院博物馆,供民众了解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如岳麓书院不仅是国内保存完好的建筑遗存,而且在其内部还建有中国书院博物馆,展示中国书院的发展脉络。其二,以书院为载体打造学术学派。书院又是一个地方学术派别活动的场所,代表区域文化特性,因此可以书院为载体,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派别,如沈阳以萃升书院为载体宣传辽沈学派,陕西以关中书院为载体宣传关中学派,等等。其三,发挥书院文化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书院这一教育遗产注入现代元素,发挥其在当下教育实践中的作用,如岳麓书院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湖南大学人文学科院系学生教学、实习的场所,这一古老遗产依然焕发着青春的光芒。关中书院地处书院门历史文化街区,是西安文理学院和西安师范附属小学教学区,依然发挥着启智民心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如何依托仿古一条街,以关中书院为载体,推出系列活动,提升这一区域的文化层次,是地方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对于早期学校遗存,可以在保护的基础上继续利用
其一,对于校园内的早期建筑,要以所在学校为主,展开合理有效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发挥其作为学校记忆沉淀和亮丽名片的功能。许多大学皆将学校的早期建筑作为校史馆,展示学校的发展历程和重大事件,使之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校史校情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场所,如复旦大学校史馆、南京大学校史馆等;有的大学的早期建筑依然功能健全,发挥着建筑应有的作用,如南京大学民国建筑群、西北大学礼堂等。其二,对于一些阶段性的教育遗产,要以现存学校为单位进行保护、管理和利用。因为教育变迁,一些学校的校址有所变更,有些学校可能消失,对于这些教育遗产要由遗存所在地学校来负责,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辅仁大学旧址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之江大学旧址在浙江大学校园内,等等,这些教育遗产应由所在学校负责保护和管理。其三,对于一些位于校园以外的教育遗存可由与此相关的学校和文物部门协同管理。现存教育遗产有一些是位于校园之外的早期建筑;有一些是与学校相关的教育家故居,这些教育遗产可由相关学校和文物部门共同保护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对教育遗产进行整体规划、保护,也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教育遗产的遗产教育功能。
教育遗产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各地,有的有保护级别,有的则默默散落于村落巷陌,除少数历史影响较大的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之外,大多数教育遗产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呈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文化的自信自强,这些都要依靠教育发展。明乎此,加强对教育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研究,不仅能够以实物的样态展示中国式教育的发展历程,发挥其文化传承功能,而且能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新提供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元素。
[1] 陈元晖,王炳照.书院制度简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5).
[2] 万书元.中国书院建筑的语义结构与纪念性特征[J].华中建筑,2006,(11).
[3] 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M].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
[4] 王强,周俊玲.大学与大楼的器道合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3-13(5).
[5] 王强,周俊玲.校园建筑的隐形教育功能[J].高教探索,2010,(1).
[6] 张文剑.浅谈中国书院建筑[J].文博,2007,(4).
[7] 杨慎初.书院建筑与传统文化思想[J].华中建筑,1990,(2).
[责任编辑 刘炜评]
Cultural Values of Education Heritage and It′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ZHOU Jun-ling
(ChineseInstituteofArtandArchaeology,Xi′anAcademyofFineArts,Xi′an710065,China)
Heritage of education is such culture that remains as early representative schools, librar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hich produce certain social influence and get a range of recognitions in all times. On the basis of classifying its structure and system, this paper holds that education heritage is with culture inheritance, recessive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function and the paper also builds a new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odel of education heritage combing with practice, which can both protect education heritage as tangible heritage and also play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as non-material heritage.
heritage of education; cultural value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2014-05-20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教育遗产研究(2013C086);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SGH10040)
周俊玲,女,陕西蒲城人,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博士后,从事艺术考古研究。
K872
A
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04
——巍山文庙
——宾川州城文庙大成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