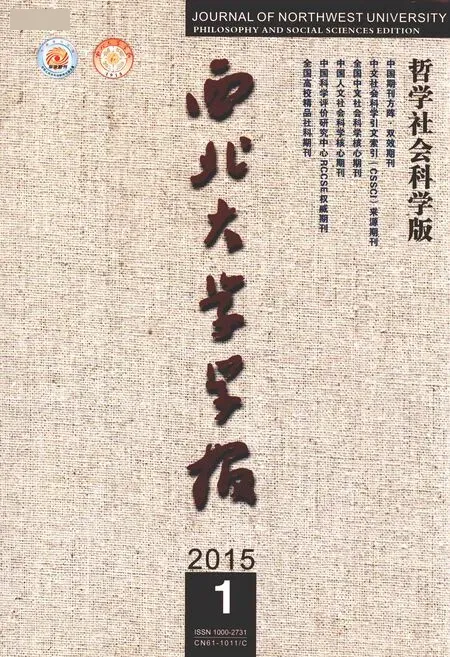长安都市圈与汉文化的世界影响
徐卫民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长安都市圈与汉文化的世界影响
徐卫民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亚洲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1](P141)。今天人们说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字”,都以“汉”为指代符号。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称作“汉学”。可见汉文化的影响之大。
鲁迅在《看镜看感》一文中曾盛赞汉代文化崇尚进取、开放的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魄力究竟雄大”;“简直前无古人”。当时人民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心”,“取用外来事物”,“自由驱使,毫不介怀”,“毫不拘忌”。他回顾“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陶,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又指出至于今世,同样“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2](P208-211)。汉代创造历史“盛事”的“闳放”和“雄大”气魄,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民族凝聚、精神激励和文化整合的作用。
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西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汉王朝的执政者一方面继承秦的大一统帝制,另一方面也积极吸取强秦短促而亡的历史教训,开始探求适合大一统帝制得以巩固的思想文化体系。至文景时期,挟书令已废,儒家的典籍开始为世人传授,士阶层又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卷六,P212)的政策,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强力维护的主导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先后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汉王朝管理的区域内,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抵御灾变威胁,共同创造社会繁荣,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西汉时期的人口增长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经历秦代末年的战乱,西汉初期人口数在1 500万—1 800万之间,《汉书·地理志》记载,到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西汉的人口已近六千万[3](P1640),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高峰。经历这一时期,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以“大汉”“皇汉”“强汉”自称的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保留了光荣的历史记录。
西汉时期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是纸的发明以及丝绸贸易的繁荣。西汉王朝的丝绸纺织技艺精湛,汉地生产制造的华丽的丝织品,受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消费者的欢迎。中国丝绸向西方的输送,使得国际文化交流最著名的大通道被称作“丝绸之路”。西汉时期已经发明了纸,到东汉蔡伦时又改进了造纸术,从而使造纸的技术更为先进,原料更为方便。魏晋以后,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国外。纸的普及,明显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进步。
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西汉都城长安。长安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车马喧闹,人涌如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班固在他的《西都赋》中就描写有长安商业市场的盛况:“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4](P237)
汉长安城市圈的形成有许多值得当代社会借鉴的地方。由于当时长安城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必然给城市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时期在长安城的周围设置了七个陵邑,相当于当时的七个县城,其中有五个在汉长安城以北,另外两个在汉长安城东南,实际上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也是当时大长安理念的一种体现。陵邑是通过迁徙大量人口聚居在陵旁而形成的行政区域。作为西汉特殊的行政区,陵邑不像普通县那样由郡统辖,而是由中央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直接掌管。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陵邑区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陵邑与长安城的关系至为密切,当时在陵邑中政治人物占的比例比较大。由于长安城内的居住面积有限,不少政治人物就住在陵邑中。陵邑还是政府官吏的重要来源地,一些重要官员就是从陵邑居民中选拔出来的。关中地区“群士慕响,异人并处”,九卿以上的高级官吏籍隶诸陵者颇多。
陵邑中的富商大贾云集,茂陵邑商人所占比例高达18.2%,平陵邑占11.5%,杜陵邑占6.6%。从而可以看出陵邑经济对汉长安城的影响。陵邑所徙人口非富即贵,为长安经济的迅速发展注入了活力,人口大量涌入形成的巨大市场也为商贾带来了无限商机。陵邑移民中有许多各地的富商大贾,他们不仅有着较高的经营水平与商业头脑,而且占有较为雄厚的资金积累。他们来往于诸陵邑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京师长安的商业贸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货殖列传》,P3282)。随着迁徙而来的商贾、豪族的增多,陵邑地区的消费水平提高,刺激了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汉王朝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的制度,使官僚豪富纷纷迁居于此,每个陵邑大约聚居5千户到1万多户,茂陵邑的人口甚至超过了长安城中的人口,达到27万人。陵邑直属位列九卿的太常管辖。于是,从高祖长陵起,到昭帝平陵止,形成了若干个异常繁荣的、直辖中央的准都市。班固在《西都赋》中,评述了长安“睎秦岭,睋北阜,挟沣灞,据龙首”的胜状,又说到临秦岭与倚北阜的诸陵邑的形势:“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4](P27)“五陵”“近县”“隆上都”形成的作用,成为长安大都市功能实现的补充条件。这些可以看作卫星城的繁荣居邑与长安共同构成的都市圈。所谓“观万国”,可以理解为在当时人的世界视域中长安都市圈占据领导地位的情形。
陵邑中除了政治和经济相关人才外,还有不少的文化名人,从而使长安城周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圈。各地“豪杰”“英俊”聚萃于“上都”,形成了特殊的文化风景。平陵邑的名士大儒人数最多,占人物总数的24.4%。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司马相如都曾经居住于茂陵邑。据王子今统计,关中从政的文人中,《汉书》中有记载的有42位,其中出身各陵邑的有30人,占71.43%,而《汉书》中专门立传的34位关中人中,有22人出身陵邑,占68.75%[6](P43)。可见,西汉时期五陵荟萃英俊之士的说法,的确是历史的真实。这一地区因此在实际上获得文化领导的地位。
所谓“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痿”[7](《西京赋》,P540),又说明这里甚至成为具有强有力影响的社会舆论中心。正如武伯纶总结五陵人物的文化贡献时指出的:“他们都以迁徙的原因而列于汉帝诸陵。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民族)流动而来,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增殖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这无疑是中国汉代历史上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这种人物的流动促成的汉代某些地区文化的扩散和融合现象,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如果加以研究,将会更加丰富汉代的文化史及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并有新的发现。”[8]其实,由于长安都市圈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的特殊作用,考察相关现象,也可以更加丰富世界文明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
[1] [美]罗兹墨菲. 亚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严可均.全后汉文(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7] 严可均.全后汉文(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 武伯纶.五陵人物志[J].文博,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