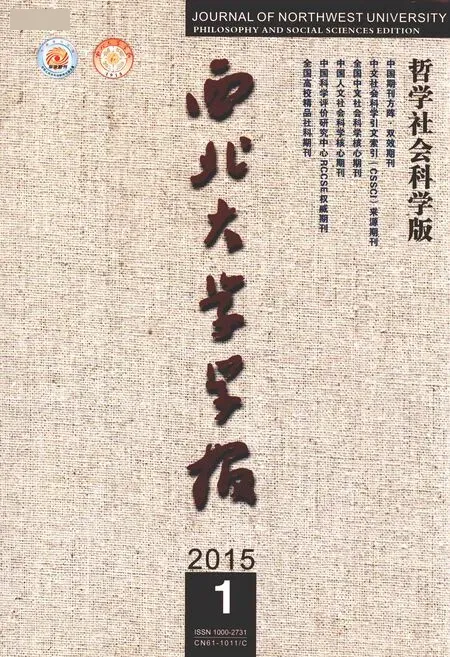商法的双向运动与现代商法的生成逻辑
王延川
(1.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2.西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法学研究】
商法的双向运动与现代商法的生成逻辑
王延川1,2
(1.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2.西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近代立法者以民法思维构建传统商法体系,这为传统商法与民法之间的融合创造了前提条件。民法商法化促使商法规范逐渐替换相应的民法规范,为民法带来活力,同时也使自己面临消解命运。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面商化使得民法展现其适应性品格,从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进行转变。企业家和律师为营业所设计出来的交易模型难以为民法和传统商法所规范,而围绕这些交易模型成长起来的新商法规则体系被称为现代商法。传统商法与民法的逐渐趋同,以及现代商法在交易模型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可以说是未来商法实践与商法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民法思维;传统商法;民法商法化;现代民法;交易模型创新;现代商法
对于近代以来的商法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向上和向下两个运动趋势,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将此形象地比喻为“冰川的融化”:在上部,商法不断创新出新的规则;在下部,商法规范流入民法之中[1](P5)。再具体一点,所谓向上运动就是在传统商法的基础上出现了现代商法;而向下运动就是传统商法规范被日益纳入民法体系中,商法的规范逐渐被消解,民法规范日益实现其现代化。由于商法在体系上开始呈现某种“支离破碎”的状态,需要重新进行梳理并进行有机整合。本文旨在通过展示商法双向运动这一轨迹,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并着力勾勒现代商法发展的逻辑,希望能为我国商法体系的构建做有益的探索。
一、民法思维与传统商法体系的构建
传统商法的基本概念是商人、商行为、商事财产,这三个概念是依照民法的自然人、法律行为、物为参考来设计的,这种依据民法思维所构筑的商法体系被视为民法的特别法。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商事企业、特殊的交易行为和新的商事集合财产,但由于要维护以民法为基础的私法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新的商法规范并未纳入到商法典之中,而是表现为单行法和司法判决的形式。
(一)营业主体的割裂
在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典里,所谓的商人就是指自然人。虽然企业比如股份公司已经出现,但商法典基本对此不进行调整,而是以单行法的方式来进行表现。这种制度架构无疑受到民法理论和实践对于法人概念定位的影响。自然人基于出生而具有生命力,基于生命的维系而拥有人格,法律也承认其人格,并给予周全的保护。法人不具有自然人意义上的生命和意识,其人格的有无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承认法人人格的话,现实中的企业组织难以纳入到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框架之中;如果承认法人人格的话,就会破坏由自然人建构起来的主体逻辑结构。这种两难使得德国法学家对于法人何以产生进行长期的争论,也有了后来的法人否认说、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的不同观点。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学说,企业作为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存在显著不同,这使得立法上出现了将自然人规定在商法典,而有关企业的规定则以单行法的方式出现。
(二)以民事行为模式构建商行为
在传统商法中,商行为是参照民事行为体系而设计的:
第一,民事契约通常按照不同的订约目的和对象,区分为买卖、租赁、互易等。但在商事交易中,对于企业而言,每种交易的目的都是为了营利,在民事人看来的交易标的差异性,在企业家的眼中却具有同质性。就像舒马赫(Kurt Schumacher)所言:“在市场上,所有物与物之间质的区别都被抹去了……一切等于别的一切。”[2](P50)对企业而言,交易标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笔交易的支出和收益的差额如何。但是,在传统的商法典中,还是按照民事契约的构架将交易区分为各种不同类型。典型的如《日本商法典》第502条,按照契约目的区分出12种营业商事商行为,这些商事契约的体系的区分标准并不十分清晰,而且也没有多大必要。
第二,传统商法中的商行为主要被认定为法律行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在我国商法学界居多。参见徐学鹿:《商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版,第135-137页.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张民安、龚赛红:《商法总则》,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郑曙光、胡新建:《现代商法:理论基点与规范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有些学者对于商行为的理解更加宽泛,认为“商行为概念中不仅应包括商事法律行为,而且必须包括商业性事实行为”*对于商行为做扩张解释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参见董安生等:《中国商法总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张国键:《商事法论》,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6-7页。周林彬、任先行:《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将商行为等同于法律行为的问题在于:第一,缩小了商事关系以及商法的适用范围。第二,商事营业的开展需要综合性行为作支持,而不仅仅只表现为法律行为或者事实行为。
但无论是将商行为界定为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实际上都是以意思或者潜在的意思作为行为的基础。法律行为的意思直接引发法律后果,而事实行为的意思引发事实上的后果,再基于该后果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但是,现代商事交易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它并非以意思表示作为交易行为的基础,而是出现了交易“祛意思化”现象,交易不再属于意愿以及意愿的协商,而是某种交易规程。这些规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营业惯例,而非真正的意思。从商事交易的规程化来看,商行为和民事行为之间的区别并非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而是已经没有可比性了。
第三,各国商法典主要是将自然人作为主体的原型而设计的,所以,其更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之间的商事契约体系,对于新出现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组织合约则关注不足*有学者指出,按照交易中的成本支出与交易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同,可以将商事行为分为契约行为、组织合约和联合行为三种类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事行为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商法应该针对不同行为设定不同的规则。参见王延川:《商事行为类型化与多元立法模式——兼论商事行为的司法适用》,《当代法学》2011年第4期。。比如公司设立行为有其特殊性,显然不能用民事合同制度来规范*比如在韩国商法学界,关于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其与民事社团法人设立行为相同,属于合同行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属于以团体性效果为目的而发生的特殊契约。参见[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日本虽然将公司设立行为界定为准商行为,但公司成立后的股权转让、章程制定等问题也并未得到很好的关注[3](P80-81)。另外,对于以特许经营为代表的企业联合行为也未得到立法者足够的关注,使得这些行为仅仅成为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对象。
(三)商事财产的特殊性未被重视
19世纪,商事财产的特殊性开始得以彰显,比如(客观意义上的)企业、无体财产权、货币、证券这些特殊财产已经存在。但是,由于当时民法思维依然占据优势,使得商事财产的特殊性难以在立法层面得到体现。以《德国民法典》为例,该法典颁布于19世纪末,当时的立法者当然知道上述新类型财产的存在,也承认其具有财产价值,但最后还是将物权的客体限定在有体物[4](P266)。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们还较为保守,它们有意识地决定了一个狭窄的物权法而反对一个广泛的财产法[4](P276)。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存在,使得近代传统商法难以与民法之间产生太多的不同。因此,德国著名商法学者卡纳里斯(Canaris)认为商法与民法具有同一性:第一,商法在实质内容上和民法没有深刻的不同;第二,能够为商法独立性提供支撑的“商法特性”实在不多[5](P11)。这也是后来“商法属民法特别法”这一说法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二、民法商法化与传统商法的消解
关于近代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发展,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民法商法化。比较法学家很早就意识到这种趋势的发展,认为商法“更多地被解析并归入民法或者被民法所同化”[6](P104)。但是,从技术层面对此进行纵深解读者却较少*我国很早就有学者研究民法商法化现象,参见徐学鹿:《析“民法商法化”与“商法民法化”——再论“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6期。但总体上看来,研究者甚少,研究内容稍显简单。近年来学者们不再关注商法基础理论研究,对于民法商法化现象的研究也就中断了。。
(一)民法商法化的意义
所谓民法商法化,是指民法规范被商法规范替换的现象,也就是说,由商法规范来调整原先应由民法所调整的民事关系的现象。比如我国《合同法》第157条规定的买卖关系中买受人具有产品检查义务就属于这种现象,将原本属于企业型买受人的检验义务扩张至一切买卖关系中,甚至适用于民事买卖之中,过去那种民事人对于买卖的产品不具有检查义务的规范被上述商事规范所替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商法化和商法规范被单纯纳入《民法典》中的民商合一立法体制和民法规范中追加但书的现象不同。在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下,商法规范虽然被纳入到民法规范,但由于其调整的对象还是商事交易,因此仍属于商事规范,只是被放置到了民法典之中而已*有学者似乎没有明确区分民法商法化与民商合一这两个概念,而且将二者视为相同含义的概念。参加赵万一:《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兼谈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在民事规范中追加但书的情况照顾到了相同法律关系基础上的相异技术操作规范,依然属于民商法立法技术的问题。在我国,有关融资租赁合同的规范纳入《合同法》属于第一种现象。《物权法》中关于留置权的规定,后半段加上“企业之间的留置除外”属于第二种现象。
在我国,民法商法化这一现象非常明显,物权法*我国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从无效到效力待定再到有效的变化充分说明了民法的商法化过程。再比如担保物权的商事化已经非常明显,浮动担保、财团担保和应收账款质押等在担保实务中占据较大比例。、侵权责任法[7]都有所表现。但这种现象在合同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我国有学者通过对《合同法》的研究,发现“民法商法化”的例子比比皆是[8]。《合同法》颁布之前,合同法奉行的是民商分立的框架,即《民法通则》和三部《合同法》规范区分构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是经济合同法与民事合同法分别立法之二元立法模式,各种典型合同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规范,如买卖合同被划分为购销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保管合同被划分为仓储保管合同与非仓储保管合同,承揽合同被划分为加工承揽与非加工承揽等,分别受经济合同法与民法通则规范。2000年《合同法》颁布后,买卖、保管、仓储、承揽等各种典型合同,均统一受合同法分则规范,这种大合同法思维也是合同规范商法化的表现。。随着2000年《合同法》的颁布,民商区分的合同法架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商事化的合同法框架*我国合同法的民法商法化现象之所以出现,最为直观的解释是因为我国的合同法的借鉴蓝本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而这些条约主要是由英美国家主导制定的,所以具有英美法系那种浓厚的商法化特质。。也就是说,法律在规范商人之间和民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时,采用的法律规范是同一的,而并非是区分的。这就属于民法商法化的现象。
(二)民法商法化产生的原因
第一,法律体系原因。传统商法结构必然导致民法商法化:一个原因是商法依靠民法思维来构建,二者之间被认为先天就具有相融性。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的商法的民法化。由于民法典的体系性强大,在制定商法典时,由于对民法典的结构、逻辑、概念进行大量借鉴,导致商法和民法之间产生趋同。再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节约立法成本和避免重复,商法典只规定私法的特殊规范,而私法的一般规范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这样的结果是,商法成文法后需要依赖民法规范,而法典之间的这种配合在大陆法系形成了“民法乃普通法,而商法乃特殊法”的通说。
第二,民法对交易安全制度的吸收。民法与商法同属私法,在自由价值方面是共通的。但是现代民事交易越来越关注交易第三人的保护,交易安全价值在民法中也开始得到确立*有学者将交易安全视为民法的终极价值,认为像公序良俗、诚实信用这样的民法上的“帝王原则”都不外乎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论文辑(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5页。,由于商事交易注重交易安全的保护,因此商法中关于交易安全的制度规范比较全面,这使得商法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法在交易安全规范方面的“资源库”*民法在近代以来的主要价值就是交易自由,但后来也开始关注第三人利益即交易安全的保护。在1939的一个法国民事判例中,法官保护作为第三方的债权人利益,做出了对于善意买受人有利的判决。Boris Kozolchyk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ivil law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Commercial Law ,Louisiana law review, vol40,1979, 36.。比如表见代理原本属于商法规范,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信赖,以实现交易安全,后来也被民法引入,以实现民事交易安全的保护。自由价值是商法和民法能够进行融合的基础,而安全价值的要求则是民法引入具体商法规范的现实原因,两个方面的合力导致了民法对于商法规范的吸纳。
第三,民事人的商化。民法商法化之所以可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事人的“商化”。中世纪之所以有商法与民法的区分,是因为商人被视为“不名誉的人”,民事人宁可陷在宗教信念的约束中也不愿在利益的攫取中打滚,商事交易只在商人中间进行,比如票据只能为商人所使用。19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和民主的发展,出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商化和商化的人”,商事人被“普遍化”了,民事人被全方位地裹挟进入市场,像商人一样成为市场的深度参与者。而过去为商人所使用的票据也开始为民事人所使用。针对这种变化,亚当·斯密指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9](P5)法国学者居荣(Yres Guyon)认为:“我们有一种印象,即使普通个人可以直接运用商法的某些特有技术,但是,在广泛程度上属于‘商人之法’的商法正在得到恢复与重建”[10](P70)。
人们深度依赖于市场,为了自己交易便捷的需要,开始使用商人或企业的惯常使用的交易工具比如票据。为了扩大融资范围,企业开始向自然人进行融资,自然人因此成为融资交易关系中的末端交易者,受到商法的规范。比如公司设立阶段的投资者就受到公司法的规范。公司成立后,股东虽然并非商人,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其目的只是获取股息,但他们依然受到公司法和证券法等商法的规范。
民事人商化建立在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之上:首先,在经济学的假设中,将经济人的假设套用到生活人的身上,经济逻辑开始侵入到社会生活中,这是民事人商化的一个理论基础。其次,随着各种市场风险和投资风险知识的普及,以及网络等信息资源的传播,让人们知道了更多的交易知识和交易经验。最后,许多民事人已经属于“职场”中人,服务于各种企业,也开始对于商事活动有所涉及或者深入其中,具备了对于交易风险的认识能力和防范能力。
三、社会关系全面商化与现代民法的嬗变
关于民法商法化,有两种产生的路径: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形式上的民法商法化表现为技术层面,就是上文所讲的商法规范对于民法规范的替换。实质上的民法商法化表现为结构性的,是指随着商人与企业行为的扩张,民事交易处于萎缩状态,民事规则也逐渐失去规范功能。为了实现自救,立法者将消费者和经营者两个概念纳入民法之中,致使民法对更加特殊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结果使得传统民法开始向现代民法转化。
(一)市场扩张与民事关系的萎缩
在现代社会,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被商事化。“以市场为中心而形成交换的契约关系,逐渐浸透于全体当事人的全部生活中”[11](P185)。企业对于民事开始全面渗透,民事人的自足生活被打破。市场几乎将所有的人都纳入其中,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需要依赖于市场。市场的“市场的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以在市场上出售作为目的,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这种出售”[12](P59-60)。
由于企业与民事人之间的交易取代了民事人之间的交易,民事交易逐渐萎缩。比如纯粹的民事合同越来越少,民事人从交易领域中逐渐退出。当然也有一些传统的民事交易,比如赠予、借用和无偿保管还发生在民事人之间,但是这些民事交易的数量却在急剧减少*比如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借用现象就很普遍。但在物资充裕的时代,人们的购买力较好,借用这种关系被买卖取代就成为一种必然。。民事质权关系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民法对其有所规定,但在现实中还有多大的适用空间则值得反思。事实上,在民事人之间发生以动产进行质押的现象几乎很难见到,人们普遍会通过典当来实现本应由质权实现的借款担保功能。
(二)民法的适应性与现代民法的发展
民事交易的萎缩必然会使民法的规范功能急剧下降,如果民法还要立足于私法基本法地位,除了将传统商法的一些规则纳入民法之中,还需要将消法规范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法律关系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德国和荷兰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概念写进民法典,以此来实现民法调整范围的扩张。但是这种做法明显地破坏了民法的纯粹性,和德国一贯的体系化理念相悖。。 这就出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特别法“逃逸”出普通法的反向运动,即民法逐渐将商法和消法等特别法“拉回”至自己的体系之中。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映。这部法律从两个方面对于传统债权法进行了修正[13]:一是德国的货物买卖规则与联合国货物买卖国际公约的规则更加趋于一致,买卖规则逐渐商事化。二是学者认为消费品买卖和普通买卖之间开始出现趋同。在受到德国债权法现代化立法的影响下,日本债权法的现代化成为热点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民法、商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关系处理问题[14](P247-271)。德国和日本这种私法之间的互动,在根本上是所谓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商法化问题。这既是现代市场经济交易模型发展的必然表现,又是传统私法体系内部的重新组合。民法调整对象的多样性与规范的丰富性,使得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15],民法不仅要实现个人自由,还要兼顾社会正义[16](P125-144)。
发生在民法领域的新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事关系的逐渐式微,二是民法的适用性的扩张。民法这种体系上的转变,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保存。其结果是,交易安全和弱者保护价值开始进入民法,使得民法成为一个非纯净化的法律体系。民法成为一个混合法典,规范之间也成为一个松散的结合。由于不同性质的人都由民法规范,立法将不再占据民法体系运行的核心地位,德国“计算机式”的精密的民法体系受到怀疑。民事活动更多地由司法进行调整,普遍的正义实现不再成为原则,相反,纠纷解决与个案正义则被大力强调。
四、交易模型创新与现代商法的生成逻辑
(一)交易模型的不断创新
20世纪中叶以来,在商事领域产生了诸多新的交易模式,比如经销、特许经营、委托经营、证券化融资、项目融资等。这些交易只为企业所使用,远离普通民事人的生活,民事人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交易模型,更别说具体使用了。这是传统商法所未曾关注的交易模型,它具有特殊的产生路径:
首先,现代商法从交易方式上与传统商法以及民法都存在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根本上是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之间的区别。传统商法的对象是自在和自为的法律关系,当出现商人之间的交易时,交易法律关系产生,该种关系的运行有两种结果:一是运行良好,双方获得各自的权利和利益;二是运行受挫,双方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受损害者获得应有的救济。无论如何,此时的交易关系具有滞后性,企业家与律师难以在交易设计中发挥太大的作用。
现代商法的对象则是交易模型。交易模型来自于企业家与律师的事先设计。企业家与律师在设计某种特定的交易模型时,就将自己的交易风险考虑进去,同时为了实现交易相对方的利益,也会将可能给对方产生的风险性因素考虑进去。这种降低交易风险的设计是经过模拟和路演,最后被应用于具体的交易关系之中。比如资本证券化就是美国证券企业和证券业律师所创造出来的交易模型。为了将企业的风险降至最低,使用资产隔离化的信托机制;而为了将投资者的交易风险降至最低,在交易模型中植入担保机制与评估机制。
其次,交易模型的设计更为精巧和复杂,难以用简单的民事法律关系来解释。比如融资租赁合同、证券投资基金、资本证券化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交易模型,难以为传统的法律来规范。传统的买卖关系逐渐被销售供应链取代,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许多的中介商,由于这些中介商的进入,买卖逐渐成为一种结构性规程,交易中交易者的意志性因素逐渐被消解。这种交易已经不再具有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这一核心因素,这就预示着现代商事交易难以再受到民法规范的调整。
(二)现代商法的生成路径
首先,关于交易模型的设计,由于设计者事先对于交易双方的风险进行各种处理,所以,交易模型本身就能为交易方所接受,其约束力也具有某种正当性。司法机关在原则上也会承认交易模型运用的效力,这会促使立法机关将交易模型纳入立法体系之中,现代商法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成长的。
企业家与律师创造了交易模型,这些交易模型为市场主体所模仿和超越,再推动实践的发展。“自由市场——为营利而进行的持续的个人交易模式——基本上乃依照工业企业家、商人、银行家、借款人和出借人、雇主和雇员以及消费者所设计的各种方式来完成预设目标的产物。”[17](P9)既然是企业家与律师设计了交易模型,那么就应该从他们的预期来解释交易模型的效力,以体现市场的功能,而不仅仅是要顺应法律的逻辑,将超出现行立法范畴的新的交易模型判定为无效。在我国,司法判决对于实践中的交易模型保持观望态度,对于效力也在逐渐进行认可*比如2012年备受关注的海富公司对赌案,历经多次法院审判,均认定投资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无效。但在2012年以后的一些仲裁案例甚至审判案例中,已经逐渐开始承认对赌协议的效力。。司法上对于交易模型的运用效力尽量承认,那么经认可的交易模型就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这种做法可以降低其他交易者的交易成本,并且降低交易风险。立法上对于已经成熟的交易模型进行认可,将其整体性地纳入立法体系之中,这就是现代商法的生成路径。
其次,交易模型为了企业的特殊目的而产生,因此,在规范整体上表现为无机和零散的状态,体系化程度还存在很大不足,需要立法者进一步提炼并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由于交易模型为企业家与律师所设计,而且交易模型灵活多变且发展迅速,各国立法者对其认识相对滞后,难以形成体系化的架构以资应对。围绕着交易模型的规范,立法中虽然有所表现,但主要为政府机关的行政规章,其中一些表现为独立的单行法。这些单行法比较零散,缺乏体系,需要有机地进行整合,以发挥其结构性效应。
最后,由于交易模型具有创新性,因此,在面对纠纷时,司法实践与监管实践中的定性不够准确,难以实现理性化规范。
由于我国实践中对于商事交易模型的认识不足,导致司法实践和行政管制活动出现些许偏差:一方面,以民事交易来理解商事交易,用民法解决商事纠纷的思维方式非常普遍。比如将企业行为视为契约行为*比如在(2012)一中民终字第5883号民事判决书、(2012)一中民终字第12988号民事判决书、(2009)朝民初字第22485号民事判决书、(2009)一中民终字第13311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均将伪造股东签名而形成的决议视为意思表示不真实行为,适用《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而判定为无效。其实,股东会决议被类比为民法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进而也认定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但是这种思路并不恰当。,将特许经营关系视为知识产权关系*比如2008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确定为“知识产权纠纷”中的第三级案由,从而把特许经营纠纷与其他经营纠纷区分开来,纳入知识产权庭的审理范围。。另一方面,以经济法思维理解商事交易,注重对于商事交易的事前调控和相关责任人的事后处罚,不注重对于交易损害者进行救济*比如近几年备受重视的金融法,学者们多从经济法的调控思维出发来研究,而没有注意到金融交易首先是一种交易模型。如果不对交易模型的交易关系和交易风险进行深入分析,既不能实现受损害者的救济,也未必能够实现理性的国家调控。。未来应该更加关注新型交易方式,多从其特殊性入手进行理解,而不能依靠类推相似的交易方式来认定。
五、结 语
商法体系在20世纪以后出现分化。传统商法的一部分依然保持其独立地位,另一部分却逐渐与民法融合。现代商法的一部分已经被纳入立法,另一部分只是在业界形成共识,有待于司法对其进行合法性衡量,更亟待立法对其认可。由于传统商法并没有彻底消失,而现代商法正在形成之中,使得商法在实践中表现为多层次的制度体系。这种二元商法体系逐渐清晰却有待发展的格局给商法的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挑战,也是未来商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 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M].于敏,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 罗宾·保罗·马洛伊.法律和市场经济——法律经济学价值的重新诠释[M]. 钱弘道,朱素梅,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 吴建斌.日本现代商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M].朱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 C·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M].杨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 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 顾培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7] 朱岩.侵权法体系重构——以企业责任为中心[EB/OL][2013-06-05].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2498.
[8] 张谷.民法商法化举隅[J].金融法苑,2005,(1).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0]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1卷[M]. 罗结珍,赵海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1]我妻荣.债权在近代以来取得的优越地位[M]. 王书江,张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2]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李伟.德国债法现代化简介[J].比较法研究,2002,(2).
[14]陈自强.台湾民法与日本债权法之现代化[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
[15]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J].律师世界,2002,(5).
[16]李少伟,王延川.私法文化:价值诉求与制度构造[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7]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美国史上的市场与法律——各利益间的不同交易方式[M]. 郑达轩,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霍 丽]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law and the Growing Logic of Modern Commercial law
WANG Yan-chuan1,2
(1.SchoolofLow,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2.CivilandCommercialLawSchool,Nor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Xi′an710063,China)
Legislators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s had built the commercial law system with the civil law logic, which created a precondition for the fus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civil law.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ivil law promoted the commercial norms gradually replacing the corresponding civil law rules,it has brought vitality for the civil law,as well as made itself in danger. The wholly commerci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 in modern society shows the adaptive character of the civil law,and it achieves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ivil law to modern one successfully. The trading model designed by entrepreneurs and lawyers are difficult to be regulated by civil law and tradi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the new system of the rules of the commercial law which grew up around these trading model is called modern commercial law. With the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civil law,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mmercial law which built on the basis of trading model,it can be said to be the new topic we have to face about the commercial law practice and study in the future.
civilization of commercial law;commercialization of civil law;traditional commercial law;modern civil law;creation of transaction mode;modern commercial law
2014-09-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FX026)
王延川,男,陕西咸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从事商法与公司法研究。
D913.99
A
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