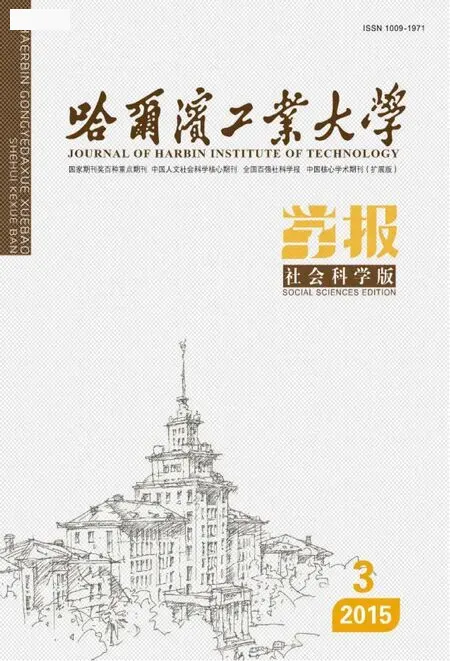作为传统国宪基本理念的“天下为公,立君为民”
——兼及“公天下”与“家天下”之辨
吴 欢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23)
作为传统国宪基本理念的“天下为公,立君为民”
——兼及“公天下”与“家天下”之辨
吴 欢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23)
宪法实为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就是传统中国的国宪。传统国宪的一项基本理念就是“天下为公,立君为民”,这一理念是华夏贤哲对政治共同体的起源与目的、共同体治理者及其治理权的来源与宗旨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堪称传统中国的国制灵魂与精神宪法。这一理念所体现的“公天下”主张与夏禹传子开创的“家天下”体制之间并非尖锐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公天下”是理想的治理理念,“家天下”是现实的统治思维,“公天下”的理想涵盖了“家天下”的现实,并对其进行论证、解释,或者批判、校正,使传统政治实践不致过分偏离华夏治道。
天下为公;立君为民;传统国宪;公天下;家天下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法史学乃至政治学研究范式转换和中国问题意识觉醒,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近现代经典宪法定义并不能确当解释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所有“国宪”或“宪法”现象[1]11。学者们或是提出了“宪法就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等新观点,或是形成了与“规范宪法学”分庭抗礼的“政治宪法学”流派,或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儒家宪政论”的主张,进而开展华夏治理秩序史研究[2]~[10]。①无独有偶,同处东亚文明圈的韩国学者咸在鹤和越南学者Bui Ngoc Son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作为宪政主义的儒家”和“儒家宪政的古典基础”等观点[11],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先生也一直倡导从宪法和国家根本治理秩序的角度认识儒家礼法[12]。②在此背景与氛围下,笔者提出了“宪法就是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就是传统中国的国宪”的命题,并对传统中国国宪(以下简称“传统国宪”)的形态与运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①“安身立命”这个中国固有的词语蕴含着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最重要的政治密码和宪法智慧。这里的“安身”就是维护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与延续,“立命”就是赋予政治共同体正当性与合法性。这两个方面的宪法诉求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共同体都不能回避而必须进行回应的。参见吴欢《安身立命:传统中国国宪的形态与运行——宪法学视角的阐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笔者的研究指出,传统国宪是一个由基本理念、宪制及其规范构成的意义综合体,在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法律治理实践中有着丰富的渊源表现形式和特殊的实施保障机制。
但是,传统国宪在中国古代并非以成文法典形式呈现,作为传统国宪基本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的传统国宪理念也主要蕴含于作为华夏治道本源的先秦经典之中。先秦经典作为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原典和历代钦定政治教科书,对政治共同体治理活动中涉及的诸多“安身立命”性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后世儒家知识分子则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思想指引下,不断总结和发明“先王之教”,作为现实治理活动的合法性来源或者批判现实治理活动的思想武器,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传统国宪理念体系。②这些理念基本上都是先秦政治家和思想家针对政治共同体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做出的思考与回应,后世余响不绝也在于这些理念及其针对的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了这些思想观念所依赖的历史背景和所解决的时代问题,本文试图对此倾向稍做反拨。本文即主要探讨这一体系中“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的基本意涵与治理智慧,及其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并对与之相关的“公天下”与“家天下”之辨做出新的诠释。本研究具有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治理意涵
“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是华夏贤者对政治共同体的起源与目的、共同体治理者与治理权的来源与宗旨这一古今中西基本宪法问题的睿智回答。
“天下为公”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理念是华夏先民对自身所处的共同体及其治理活动所应当具有的基本属性与基本状态的认识,是先民对政治生活的美好追求和期待。欲理解这一理念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先民的“天下”观念。
“天下”,首先是华夏先民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外部物理世界的一种描述和解释。在与残酷的自然条件作斗争以求取生存的过程中,华夏先民逐渐观察到了头顶的天、脚下的地,注意到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花草树木等自然现象。为了解释天地万物的起源和斗转星移、大江东去等自然现象,他们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等神话故事。他们朴素地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之“下”的“地”上,而斗转星移风霜雨雪的天,生长万物承载众生的地,亘古不变岿然不动的天与地,成为他们最先敬畏和崇拜的对象。尧舜以降,随着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治理活动的展开,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居民开始成为共同体的内部成员,先民们又将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世界称为“天下”。又由于共同体治理范围的拓展和先民认识能力的提高,中国、四夷、四海、万邦、万国等词语也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天下”概念的同位语或下位词频繁出现。这一空间认识上的拓展带来的是共同体生活的自觉,先民们不仅注意到了自身所处的部落氏族的治理活动,也关注到了处于四夷、八荒的其他共同体。他们开始思考共同体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重申和强调他们组成共同体生活的用意,以及共同体生活的应然状态,于是发展出“天下为公”的理念。
沿着“天下”的思路,先民们至少发展出两点关于“天下为公”的重要认识:其一,他们作为天地之间生活的“人”,在自然的伟力面前虽然是渺小的,但同时也是天下最为高贵的。人是天地阴阳鬼神交会而孕育的灵秀之物:“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有智慧、有情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因此,人是天地特别关照、眷顾的造物,天行云布雨,地载育万物,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河流,都是天地赐予全人类的,任何单个个体或者单个共同体都没有资格将其据为私有。这就是天下之地理、天下之资源层面的“天下为公”。其二,人虽然是天地之间最贵者,是天地特别眷顾的对象,但是为了生存还是迫不得已组成了共同体。共同体为了治理活动的需要更进一步建立起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以便行使治理权。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共同体、治理权本身却不是属于私人的,而是为了组成共同体的人类成员的共同利益、公共福祉而存在的。换言之,政治共同体之“天下”,并不专属于任何人类个体或者治理者群体,而是属于全体共同体成员,这就是天下之治理、天下之权力层面的“天下为公”。故有学者总结,“在政治史上,‘公’本是一种君主称谓。后来它演变成含有公共、公益、公义、公正、公平等意蕴的政治概念。‘天下’最初是一种常用的国家称谓,特指天子统辖的区域。用现代的概念诠释,所谓‘天下为公’的主旨就是国家为公。”[13]
政治共同体治理权层面的“天下为公”是“天下为公”理念的核心内容,这种主张频繁见于先秦典籍。《尚书》所载尧舜“传贤不传子”的禅让故事,已说明尧舜之天下非尧舜私人之天下,而后世将此引为美德也说明“天下为公”是华夏政治哲学的基本追求。帝舜不独于临老死之际才将共同体治理权公之于众,其在位时期就鼓励大臣举荐贤能,并主动与四岳十二牧、大禹皋陶等九人和高阳氏、高辛氏才子十六人分享治理权,共治天下。成汤有伊尹,武丁有傅说,文王有姜尚,武王有周公,皆是不以天下治理权为一人之私。春秋战国时期,不独儒家怀念尧舜大同之世,就连法家也在积极呼吁“天下为公”。如商鞅曰:“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商君书·修权》)《吕氏春秋》堪称先秦“天下为公”理念之集大成者,其《贵公》、《去私》、《恃君览》篇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法家主张国家公利至上,尤其主张通过严明法度来维护国家公利。任德还是任法是儒法的差异,但二者都强调“天下为公”,都将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属性。
“天下为公”理念解决的是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自身的基本属性与任务的问题,但是在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及其治理权究竟如何起源,以及治理权行使的根本目的与任务的问题上,还需要“立君为民”理念加以补充。
欲了解先民为何结成“天下”共同体,需要回顾前“天下”状态。恩格斯曾热情地赞美前“天下”状态为“黄金时代”[14]。华夏先贤也有类似的表达,如《礼记》之“大同世界”,老子之“小国寡民”。但这样的追忆更多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先民们所身处的更有可能是一个“恐怖时代”。“恐怖”首先来源于生产力低下、人口增殖和物资匮乏。韩非子即指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更深的“恐怖”则是由于没有规则和秩序。管子指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配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管子·君臣下》)商鞅也说:“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商君书·开塞》)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恐怖的人际环境中的先民,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秩序,即使不被自然界的野兽吞噬,也会被内心的欲望所毁灭。
幸而先民不愧是天地间最贵者,他们找到了摆脱丛林状态的办法,那就是“群”,即组成共同体,过有规则、有秩序、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来源。《吕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吕氏春秋·恃君览》)先民“群聚”,即组成共同体共同生活,是为了抵御来自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危险,享受合作和集体带来的利益。所以,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就在于其能够保护人类生存延续,提供一种安全和安定的生活环境,因为这是一种最大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产品。汉人班固更加强调人类结成共同体是因为具有“仁爱”的本性:“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汉书·刑法志》)这样的强调也是非常必要和符合实际的,因为如果不发挥人类本性中的仁爱因素,先民们是无法结成共同体的,或者即使结成共同体,也无法通过互助与合作,享受共同体的福利,也就无法摆脱“以力相征”的争斗状态。有了政治共同体之后,先民们还必须继续维持共同体的生存和延续,因为这决定着人类种族和文明的延续。共同体所具有的功能是人类个体无法企及的,,所以要建立起整套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来保证共同体的有序治理,从而形成治理活动及其规则以及治理权的拥有者——君主。故商鞅曰:“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立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君书·开塞》)既然政治共同体及其治理权、享有治理权的君主以及为行使治理权而创设的各种国家机器均是先民出于自己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动因,那么顺理成章地,先民建立政治共同体、设立君长的根本目的与用意就是“立君为民”。
“立君为民”的理念在先秦典籍中俯拾皆是。如《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荀子·性恶》曰:“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则史事更能说明“民”与“君”熟为目的,熟为手段。史载邾文公为迁都之事而占卜,结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认为:“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他认为君主的职责就是利民,如能利民,有害于君也在所不惜。左右大臣劝谏,认为不迁都可以延长君主的寿命,邾文公回应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于是毅然迁都,不久邾文公就去世。当时的君子评价此事说:“知命!”就是指邾文公深刻地懂得自己作为君主必须利民的使命。尽管各家观点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但是都强调设立君主的目的是为了民众的福祉,故孟子有“民贵君轻”之比,荀子有“君舟民水”之喻。
虽然笔者在此将“天下为公”与“立君为民”分别论述,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天下为公”必然要求“立君为民”,“立君为民”也充分说明“天下为公”,二者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天下为公”侧重于政治共同体的起源和根本任务,“立君为民”侧重于共同体最高治理者及其治理权的起源与宗旨。尽管无法求证二者孰先孰后,但分而叙之也有强调政治共同体本身高于共同体治理权的潜在用意,这也是明末黄宗羲明辨“亡国”与“亡天下”之意。黄氏曰:“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黄宗羲全集·留书》)这就是认为,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本身的生死存亡,要高于共同体治理者治理权的得失授受。
二、国制灵魂:“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地位与意义
政治共同体犹如生命体,有其生老病死,有其传承、延续、裂变甚至消亡。许多古老的政治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的灰烬,但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却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傲然传承并延续发展数千年,其中必有维持和支撑其生命力的特殊“精神气韵”。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各自的精神气质差异,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精神气韵。这种“精神气韵”,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精神宪法,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宪法灵魂,决定了共同体政治生活和政治法律体制的基本面貌和基本走向。“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就是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精神宪法之一,就是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政治法律制度的灵魂,或曰“国制灵魂”。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首先,“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回答了政治共同体的起源与目的、政治共同体治理者及其治理权的来源与宗旨这一根本性问题。人类自有政治共同体生活以来,就必须在政治神学、政治哲学或者宪法学层面解决共同体的起源与目的、共同体治理者及其治理权的来源与宗旨问题。而且,在人类早期的思想观念中,神学、哲学和法学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和明显的界限,所以这一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借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宪法问题,也是任何政治共同体都不能回避而必须予以解答的根本政治问题[1]16-17。古埃及法老宣称自己的治理权来自太阳神的授予,基督教神学认为世俗权力来自上帝的旨意,近代启蒙思想家将国家治理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归结于“社会契约”,当代中国执政党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是“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执政的宗旨则是“为人民服务”。这些回答尽管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乃至阶级斗争立场,但都是在以一种说理的方式论证共同体的起源与目的和治理权的来源与宗旨问题,而不是简单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和镇压。从暴力走向说理,既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回答了政治共同体的起源与目的、政治共同体治理者及其治理权的来源与宗旨这一根本性宪法问题和政治问题,从而在思想和理念层面实现了华夏政治共同体的“安身立命”,并为其开创和奠定了独特的政治法律传统和治理秩序。
其次,“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蕴含或者指引了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治理活动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共同体的治理权及其行使预设了基本方向。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宪制或曰基本政治制度是指从制度上解决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根本性宪法问题的基础性制度构架[15]。此处仅以传统“禅让”宪制为例说明“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对其所具有的指导性意义。传统“禅让”宪制是中国古代政权危机和平化解的基本政制。尧舜时代最高治理权并不固属于一家一姓,而是依据“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传统国宪理念在不同家族的治理者之间传递。这种最高治理权和平转移模式体现了原始氏族民主制的遗风,也对先秦以降的政权危机化解提供了积极启发。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更替几乎都是通过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进行。如何对这种“暴力夺权”的“打天下”行为进行正当性与合法性论证,成为摆在历代开国君臣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一方面继续编造“君权神授”的神话,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真命天子”;另一方面,大部分开国君臣在夺权形式上选择被视为尧舜良法美政的“禅让制”,宣称自己取代前一政权是依据天命接受禅让,以掩饰暴力夺权的事实。据黄晓平博士研究,在传统中国王朝更替方式中,以“禅让制”模式进行的竟占54%,“禅让制”因此成为与“暴力夺权”相并列的传统政权危机化解的重要机制,“天下为公,立君为民”也成为异姓夺取最高治理权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与说辞[16]45。在历代“禅让”实践中,禅位之君、劝进群臣和受禅之君之间,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让贤—劝进—辞让—接受”的程序性“表演”。这样的反复过程,也增加了新政权和新君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消解了其以武力相威胁的夺权色彩。总之,“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是传统“禅让”宪制的重要理论基础,指引和规范了传统“禅让”宪制的历史运行,也为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政权危机的和平化解和优良治理秩序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最后,“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精神宪法的作用。这一理念自先秦以来就存在于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原典之中,是尧舜先王的不言之教和良法美政。在秦汉以降又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断总结与阐发,成为评判后世政权立国精神和执政理念的基本标准,也是儒家士大夫评判共同体治理状况和治理权运用之得失的重要思想武器。西汉谷永批评汉成帝“违道纵欲”,建议其“迁命贤圣”、禅让帝位,其理由就是“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汉书·谷永传》)朱熹也主张“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四书章句集注》)黄宗羲更是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论(《明夷待访录·原君》),这就是将天下视为君主应当毕生经营的事业,如天下有不安宁,君主则是罪魁祸首。这一理念也得到历代君王甚至是外族君主的认同与支持。隋炀帝曰:“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隋书·炀帝纪》)唐太宗曰:“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贞观政要·公平》)这就是将公正作为君主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清初多尔衮攻占北京后所出安民告示亦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明季南略》卷八)不论士大夫的批判是否真的有效,帝王的认同是否真的发自内心,至少在官方政治法律哲学和主流政治话语中,“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都是正统且正当的。如果公然违背这一观念体系,不仅会遭受政治伦理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和非议,还会受到现实政治博弈中各种政治角色的限制甚至制裁。因此,“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理念能够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发挥根本性的“国制灵魂”作用,具有重要的精神宪法意义。
三、“公天下”与“家天下”的辩证关系
一般认为,三皇五帝时代政治权力转移方式属于“禅让制”,夏商以后属于“世袭制”,“家天下”始自夏朝。夏禹之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夏禹之后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二者最大区别在于后者选拔继承人、分配治理权力的唯一标准在于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公天下”即“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家天下”即独家垄断的“世袭制”。正因为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治理者在实际上将整个国家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进行私相授受,其治理国家的基本原理也是家族式的,所以马克斯·韦伯将古代中华帝国类型化为“家产制国家”[17]。古代中国作为“家产制国家”,其典型特征就是将家族统治的伦理与规则当作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而“家天下”理念作为这一套伦理与规则体系的核心,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之一。
在传统国宪理念的研究中,“家天下”理念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近世学人基本认为“公天下”理念只存在于尧舜禅让的美好传说之中,真正在中国传统政治运行中发挥作用的是“家天下”理念,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治乱循环的死结,因此“家天下”理念是传统政治哲学最黑暗、最腐朽的余毒。这样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误解。笔者并不否认“家天下”理念对中国传统政治之实际负面影响,也并无意为“家天下”理念招魂复辟,只是试图对“家天下”理念与“公天下”理念之关系做一番新的解读,试图澄清并阐明二者之间其实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而是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家天下”其实可以被“公天下”所容纳。换言之,笔者认为“家天下”理念没有超出“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范畴,“家天下”与“公天下”是一种辩证关系。
首先,从历史来看,尧舜“公天下”之前华夏先民的家庭财产和公共权力传承模式基本上是“家天下”模式。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民族的幼年时期都经历了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就是为了适应在父系家族内部传递“家产”的需要。只是中国古代走得更深更远,不仅创造了“家产”在父子兄弟之间传承的财产继承模式,也创造了治理权力在父子兄弟之间传承的治理权转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三皇五帝时代的治理权传承模式,既是“家天下”的,也是“公天下”的。先秦以降“家天下”成为主流,但也没有思想家或者学者从本质上反对“父死子继”的治理权转移模式,他们只是秉持“天下为公”的理想,批判治理权的滥用和私用,呼吁以民众福祉为重。也许在他们看来,治理权的转移模式并不重要,关键是治理权的行使必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因为华夏先民选择了“家天下”的治理权转移模式,而这一转移模式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治乱循环”的弊病,就因此轻视和嘲笑古人。须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传统政治哲学范围内,古人已经尽力在追求优良治理之道,他们达到的思想高度固然在今人看来有所局限,但是这已经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极致。事实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甚至直到今天,实质上或者名义上的最高治理权的传承模式也都是“家天下”模式,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经阶段。对此切不可以今人标准简单评价是非优劣。
其次,“家天下”理念在传统政治哲学中可以做两种理解。正面意义上的“家天下”就是治理者以天下为家,治理者作为家长,人民作为子民,家长要像父母一样爱护子女、抚育万民,以民众的福祉作为执政的追求。这就是先秦典籍中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的要求,也是董仲舒“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春秋繁露·郊义》)的含义。“家天下”理念的这些正面内涵绝大部分可以为“公天下”理念所包容。如“家天下”理念所宣称的天子受命于天、所要求的天子作民父母行政、所设计的天子封建诸侯士大夫、所鼓励的天下臣民对天子尽忠尽孝、所追求的“王道大一统”等内涵,均可在“公天下”理论中找到对应的支撑和资源。所以,“家天下”理念虽然也是影响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基本治理权力运行的核心理念,但其所借以构建和论证的理论资源仍没有超出“公天下”理论体系的范畴。就这些正面含义而言,“家天下”理念与“公天下”理念并不矛盾。
最后,负面意义上的“家天下”理念,即认为天下所有权力和资源归于一家一姓,治理者及其家族专有天下并不容外人染指。这可能是历代帝王内心的真实想法,如刘邦向其父炫耀:“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熟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其他守成之君辄称天下为“祖宗家业”者不胜枚举。但即便如此,历代帝王也不敢公然宣称自己治理天下就是为了一家一姓之私利,而是普遍宣称天下是万民公有的,治理天下是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因此,“公天下”才是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和正统,不能因为历代君主没有真正做到“公天下”,就认为“公天下”并非传统国宪的基本理念,这样的道理在今日亦然。从极端角度看,即使中国古代帝王真的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家天下”也有可能反而更有利于督促君主重视并追求共同体的优良治理。因为开国帝王既然视“天下”为私产,是付出了流血牺牲才争夺到手的巨大财产,那么作为产权所有人,他们反而更加重视这份财产的“保值增值”,他们还要为了家族利益将这份家业“做大做强”,并将其作为“遗产”留给后世子孙。而后世嗣君既然继承了父祖创立的“祖宗家产”,自然心怀敬畏,不敢任由“家产”在自己手中荒废,其治理活动也存在着谨慎、克制的可能。也就是说,“天下”之权属确定,至少能够督促君主认真对待自己的“家业”,追求优良治理。
总之,“家天下”与“公天下”并不矛盾,而是一种辩证关系。“在某一姓君权运行正常时,人民可以得到基本的秩序与福祉时,臣民是认同‘家天下’观念的……但是当某一姓君权运行乖舛时,人民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天下为公’观念既是警醒君主的重要观念,也是改朝换代最为正当的理由之一。”[16]56大致而言,“公天下”是理想的治理理念,“家天下”是现实的统治思维。“公天下”的理想涵盖了“家天下”的现实,并对其进行论证、解释,或者批判、校正,使传统政治实践不致过分偏离华夏治道。作为“公天下”理想的核心表述,“天下为公”和“立君为民”也因其所蕴含的对治理权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要求,而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构成了传统国宪的基本理念之一。
[1]吴欢.宪法: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据——兼论传统中国“国宪”研究的现代意义[J].法治研究, 2012,(12).
[2]刘茂林,仪喜峰.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J].法学评论,2007,(5):15-22.
[3]徐国栋.宪法一词的西文起源及其演进考[J]法学家, 2011,(4):29-44.
[4]田飞龙.中国宪法学理论流派的形成[G]//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6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54-77.
[5]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J].法学研究, 2011,(6):20-22.
[6]韩大元.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概念与学术传统[J].求是学刊,2011,(1):89-97.
[7]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8]姚中秋.儒家宪政主义传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9]陈明.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试说[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7-20.
[10]任锋.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J].开放时代,2011,(6): 17-25.
[11][韩]咸在鹤.宪政、儒学公民德行与礼[G]//哈佛燕京学社.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0.
[12]曾明珠.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杜维明教授的对话[G]//哈佛燕京学社.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1:77.
[13]张分田.“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J].阴山学刊,2003,(3):55-56.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5.
[15]吴欢.安身立命:传统中国国宪的形态与运行——宪法学视角的阐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135.
[16]黄晓平.禅让制与传统中国政权危机化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17]林来梵.宪法学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41.
“Tian Xia Wei Gong,Li Jun Wei Min”as a Basic Concept of the Traditional Constitution of China—Also on the Debate about“Gong Tian Xia”and“Jia Tian Xia”
WU Huan
(School of Law,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Constitution is actually the fundamental rules to“An Shen Li Ming”for a political community.The fundamental rules to“An Shen Li Ming”for ancient China w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stitution whose basic concept was“Tian Xia Wei Gong,Li Jun Wei Min”as an answer to the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what was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its governance. It could be seen as the soul of state institution and the spirit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The“Gong Tian Xia”claim from this concept was not really sharply opposed to the“Jia Tian Xia”system.They wer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The former was an ideal governance concept while the latter was a realistic ruling thinking.The ideal of“Gong Tian Xia”covered the reality of“Jia Tian Xia”,and the former carried on to demonstrating and explaining,or criticizing and correcting the latter,in order to keep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 being good governance.
Tian Xia Wei Gong;Li Jun Wei Min;the traditional constitutional concept;Gong Tian Xia;Jia Tian Xia
D69;D909.2
A
1009-1971(2015)03-0039-07
[责任编辑:张莲英]
2014-10-15;
2015-04-02
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基金项目(乙A04)
吴欢(1986—),男,湖北红安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