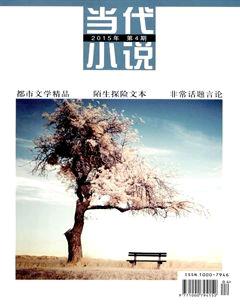乡无郎,晚景凄凉
王莹
如果非要给题目结尾加一个标点,可以加句号,陈述一个乡村无人必荒凉的事实;可以加叹号,慨叹一种发展大势之外的凄清和无奈;也可以加问号,质询“乡无郎”是否必然导致“晚景凄凉”。事实上,可以分开来看,在当下的乡村中,既存在着“无郎”的现象,存在着各种原因导致的“凄凉景”,也存在着那些无法用人员流动、人心不古之类来衡量的乡村温情。
罗伟章《声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
声音史即是乡村变迁史,作者的创作意图非常明显,无非是讲城市化之下中国出现大片空村的现实,事关乡村发展和村民的归属。传统村庄的凋敝,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就地发展的城镇化举措代替外迁奔城,势必成为乡村发展的必要道路。于此立意并不新鲜,但作者却独到地以杨浪这样一个乡村流浪汉式的人物,通过谛听乡村各种声音的方式,来展现乡村在发展大潮中的变化,无疑充满新意。杨浪作为光棍汉保留了童身,也保住了聆听、模仿各种声音的神奇能力。小说以杨浪打扫村庄听到各种声音开始回忆,串起了千河口以杨浪、李成、夏青、光棍汉贵生、九弟等为主要人物的乡村故事。主要情节包括杨浪小时候因模仿房校长声音训斥李老师引起误会而被开除,村人渐渐外出打工,夏青丈夫符志刚外遇事件,李成骚扰干女儿夏青存否,杨浪决心以一人之力收拾整个村庄等。现实的村庄已然凋敝,但杨浪回忆中的村庄却是鲜活的。清溪河、跑跑女,与钱云友情的破裂,和亲哥杨峰的疏离,对李成老友般的依赖,对夏青因“抖搂被子的声音”而生出的淡淡好感。杨浪在乡村社会中的定位是一个有点傻、非常懒的光棍汉,但他本身却堪称千河口最有灵气最接地气的人。他会因钱云害怕古寨上的鬼每逢下雪便送他过山崖,他不抽烟却总在水缸上替李成蓄着烟叶,他同情被丈夫背叛的夏青大风夜里去山上寻她背她回家为她做饭,他心怀对万物的怜悯所以才特意买来毛巾为闷热的佛像擦拭身体,他拒绝接受跑跑女也只是因为怕拖累一个好女人,而不是怕破了童身失了谛听的能力。他“懒”,所以闲有大把时间;他对生活要求不高,所以不会动离开村庄谋生的念头;他能听到乡村中每一缕细微的带有感情的声音,所以他才不厌其烦地聆听着。正是这样的杨浪,才会产生收拾出一个村庄的念头,才会面对日渐破败的村庄产生“如果我把三层院子都打扫干净,那不就还是一个村庄”的想法。小说以杨浪的聆听营造了一种富含情感的乡村氛围,之前恬然的也好后来荒凉的也罢,都成功地循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展开,引起人们对当下乡村发展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小说塑造出了杨浪这个无比鲜活的有着独特生活哲学的精彩人物,充满着精神的魔力。
尤凤伟《魂归何方》,《北京文学》2015年第2期
小说关注人死之后葬在何处的问题,涉及三位女人,分别为母亲、老姨和父亲的情人。三个择地而葬的纠纷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几率较小,但小说将其放到一个叙述时空中,在强化戏剧张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此类情况的普遍覆盖性。小说线条明晰,充分展现了尤凤伟作为成熟作家的叙事掌控力。故事从“我”回乡给母亲上坟开始,以表弟育生的电话、本家侄子延保的电话,东北黑河寄来的信为引,打开故事的情节枝杈,分别引出老姨、母亲、父亲情人的故事,以及三人葬归何处的讨论,前二者详写,后一者略写。老姨嫁过两任丈夫,显然更爱第二任,但第二任丈夫却有死去的原配,第一任丈夫也已孤单地在下面“等了好久”。母亲自小与父亲定了娃娃亲,父亲却在东北有了外遇生了娃,后来更离家又娶了另一房,母亲含恨离世。父亲的东北情人临盆在即时,因母亲的阻挠而与父亲再未重聚,去世后由孙辈在遗物中才发现了远方爷爷的存在。小说虽不像尤凤伟以往开合较大的一些叙事,没有厚重的大背景大变迁,着重写常遍的丧葬事宜,蜻蜓点水地涉及着乡村政治,但仍带有较厚的尤式传奇性色彩,无论在情节还是叙事上,都十分吸睛。母亲与父亲之所以定亲,只因婆婆偶然在路上瞧了年少的母亲一眼,那时二人才八岁。父亲二十七岁闯关东是怎样遇上那个让他忘记家里为他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妻子而情难自禁的女子?而老姨和两任丈夫的感情发展也是在意料之中、之外交织。这样的传奇色彩在时光流逝下拧巴在一个丧葬的点上,亲情、爱情的温暖里丝丝缕缕地渗透着生与死、乐与悲。小说的最后,三个女人终于魂归良地,但留给读者的思索却刚开始淡远地往外散逸。
秦岭《借命时代的家乡》,《中国作家》2014年第12期
小说从董建泉一个狂乱的梦起头,急速滑到现实中,乍读之下令人一时不能从充满地域风情和狂野张力的梦的叙述中跳脱出来。尔后的故事表现上没有延续开始的叙述风格,但在两个主要人物带领各自家族在时代发展的泥潭中挣扎、你消我涨的明争暗斗之中,狂乱化为暗潮完美地延续着。小说从大视角来看是讲一个村庄两个宗族在时代变迁中相互较量的故事,将其定位为严肃的斗争太沉重,而定位为乡村政治、经济纠葛之类又太肤浅。有评论在谈及此小说时从古老乡村的封建余毒入手,认为故事讲的是一种扭曲与荒诞,此类说法又难免有些上纲上线。小说从整体看,展现着乡村变迁,社会在变,经济在发展,村民的思想也在不断转变而非老化固化,宗族的感情凝结或松散,有些你家我族之间的比较是难免的。从小视角、个人立场来看,小说在大的社会变迁中又细碎地思索着爱情与友情。小说涉及的两个女主角,一个存喜,一个彩凤。存喜是董建泉的初恋和童养媳妇,彩凤与董建泉患难与共且共奔小康。存喜后来嫁给了村里有尿毒症的光棍汉甄四宝,彩凤则比较泼辣理智在家族的养牛事业上堪称一把能手。小说讲友情,讲得头破血流,似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董建泉与苟发昌作为董、苟两大家族的经济领首人物,作为发小、好友,斗得风生水起,用现下的流行语来说简直就是相爱相杀。在董建泉的第一人称叙述中,苟发昌在发达之后很多行事都是不堪的,是“尖山的败类”。但董建泉其实与苟发昌相去不远,他为逃避责任离家,抛弃了存喜,直接导致了存喜的生之惨淡。娶了彩凤,“功成名就”之后又意乱情迷地和存喜发生关系,生下甄全富。小说读到董建泉去监狱探望苟发昌一段时,仍似一阵风的狂乱过后,留下一片看似繁华实为狼藉的董姓家族的压倒性胜利。但紧接下来,小说在最结尾处转入了清风阶段。董建泉父亲去世,存喜偷偷带着孩子前来拜祭,并烧掉自己在董家祠堂里代表董家媳妇身份的黄表纸,要董建泉大年初三送先人时将黄表上的名字换成彩凤。董建泉也最终得知,当初给存喜家捐款时,以一块钱微弱之差压倒他捐款数目的人,不是他的大,而是苟发昌。
陶丽群《母亲的岛》,《野草》2015年第1期
这个短篇读起来非常顺畅,独具风味。小说首先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乡村,四面环水,乡风淳朴,时光悠长。但同时,这个村庄的男人们却因娶不起本地媳妇而买外地女人当老婆。小说中,母亲在19岁那年被卖给了父亲,从此过了逃不出去的30年逆来顺受的日子,为父亲生下三男一女。小说的叙述者是这个家庭中的女儿。作为女儿,理应更了解母亲。可在父亲不善表达的大男子汉作风熏陶下,女儿比家中几个男子在体贴对待母亲上强不了多少。家人包括嫂子们,对母亲也从来不放心上,直到母亲宣布要“出去住一阵子”,并且坚决地离开家,到毛竹岛上独居,家里“一下子陷入兵荒马乱”的境况之下,大家才感受到母亲的重要性。一家人翘首以盼,等待母亲的归来。看似对母亲毫不在乎的父亲尤为急切,他长时间在江水对面观望母亲的小岛,甚至连母亲总共卖了16次菜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暴风雨的夜里他惊惶失措地赶去抢救母亲,担心大水淹了毛竹岛冲了她的小木屋。这一夜,父亲的行动浓缩着一个寡言汉子对妻子的爱。母亲在毛竹岛上过着自由的日子,她种菜、养鸭,然后到集市上卖,女儿也因时常去岛上帮忙与母亲更加亲近。再后来,母亲的菜卖完了,鸭子也卖完了,一家人在父亲的指挥下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母亲归来。然而,母亲却自此消失了,整个毛竹岛都在,只少了母亲一人。故事停留在父亲的等待上,他住到了毛竹岛,过上母亲在岛上同样的生活。每年梅雨季节后,父亲会把母亲的衣物翻出来晾晒,“仿佛母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小说以幽默而细腻的表达营造出一种超然世外般的优美风情,一家人的相处充满着闹别扭式的温情,父亲的感情表达也像极了很多长辈的方式。或许因同是感情细腻的女性作家,《母亲的岛》故事开始的餐桌和最终母亲不知所踪的结局,都让人联想到王秀梅的《父亲的桥》和《浮世筑》。但《母亲的岛》酝酿着的诗意更温情,就连母亲最后的彻底离家都带有着仙隐气息。母亲似是下凡的仙女,为父亲养大孩子,就回仙山去了,留下一家子怀着守候的希望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