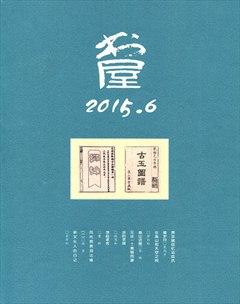一信一世界
在拙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出版一年以前,我将书稿的电子文本传给老舍研究专家、已从上海师范大学退休的史承钧老师,请他提些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即收到史老师写来的一封长信,后此信以《读傅光明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所想到的》为题,发在了李怡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这是一本以书代刊半年一期的杂志。不曾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史老师又传来一篇文章,并写了附记:“这是我应日本友人渡边明次先生约请,为他所译赵清阁的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日本侨报社2006年10月出版)所写的著者介绍。因篇幅等关系,删去了涉及老舍的部分段落。”
被删去的文字有以下一段:
抗战和文艺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战争带来的苦难中他们患难与共、相互慰籍。他们几乎要结成为一对抗战伉俪了——这是在抗战的特殊年代,流落大后方的文人在特殊的情境下每每发生的事,——但由于1943年老舍夫人带着三个孩子突破封锁突然来到而中止。此后他们常常分处两地:1943年后是成都/重庆——北碚,1946年后是上海——美国,1950年后则是上海——北京。然而他们精神相通,藕断丝连,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顺利解决老舍的家庭问题后结合在一起。老舍甚至连安排夫人今后的生活和子女教育的资金都准备好了。但是,他无法取得夫人的谅解,夫人支持他只身赴抗战并代他奉养老母抚育子女的恩情他也不敢忘。同时,建国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也使他们无暇顾及情感上的事。更何况在强势的公众舆论中,个人情感只是小事、私事,而作为名人的形象却是关乎国家的大事、公事,这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幻想,面对现实。为此,赵清阁愿意作出牺牲,不提往事。于是,他们将丝丝的恋情化作浓浓的友谊,仍然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关切,始终不渝,直至“文革”初起,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天人相隔,反而加深了赵清阁的思念。每当老舍生辰或忌日,她都要独自加以纪念;每当在报上读到有关老舍的文章,她都倍加关注甚至剪存;她的许多回忆散文都提到了老舍;她的客厅中悬挂着老舍1960年春写给她的《忆蜀中小景二绝》,书房中书桌上是老舍1939年参加北路慰劳团特地从甘肃酒泉带回来送给她的砚台;正对书桌,是老舍1961年写给她的祝寿联“清流叠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侧面墙上则是老舍1944年写给她的扇面;床头柜上,则是老舍在她患肺结核时送给她的小痰盂。老舍在她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除了个别情况,她绝口不提她和老舍间曾经有过的恋情。她觉得文坛作风不正,成见太深,害怕损害老舍的形象;同时感到人言可畏,害怕扰乱自己晚年的清静。为此,她甚至在临终之前,把珍藏的“文革”劫后残存的老舍的信件也毁去了。她至死都在思念着老舍,维护着老舍。
赵清阁终身未婚,身边也没有亲人,晚年只有保姆吴嫂几十年相依为命。她淡泊名利,以书为伴,在寂寞和辛勤笔耕中度过了余生。
这段饱含挚情而又流露出浓浓凄婉的文字,既是对老舍与赵清阁曾几何时彼此爱情的幽微勾勒,也是对经历了文革劫后余生的清阁先生晚景晚境的一个简笔速写。
事实上,除了史老师这里所写的清阁先生“终身未婚,身边也没有亲人,晚年只有保姆吴嫂几十年相依为命。她淡泊名利,以书为伴,在寂寞和辛勤笔耕中度过了余生”,对清阁先生的晚年,我原本知之甚少。自从2009年底开始,因写作传记《老舍:他这一辈子》与韩秀通信,才得以逐步走近清阁先生和她颇为独特丰富的文学世界,才得以对她与老舍之间“此恨绵绵”的感情有了些较为清晰的了解和理解。2012年4月访美期间,我从韩秀那里得到更多的书信,才更深切地体悟到赵清阁孤寂的晚年生活和不失微妙复杂的写作心理与状态。
赵清阁先生致韩秀的五封信,及另外的五封信,这十封信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海峡两岸开始有了文化交流,此时,身在美国的韩秀以她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扮演起了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她一面帮助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的著名诗人痖弦,约请大陆一些已年届暮岁的现代作家为“联副”写稿;一面帮在“联副”发表了作品的大陆作家转寄稿费。那时,两岸还没有通邮。
从信里得知,清阁先生1988年12月27日发表在“联副”上的《砚田春秋》,是经韩秀约写的。除了清阁先生,其他经韩秀约稿或转寄过稿费和“联副”剪报的作家、诗人,还有沈从文、施蛰存、萧乾、柯灵、端木蕻良、吴祖光、袁可嘉、许杰、雁冀、古华、李锐、叶延滨等。从美国转寄稿费需另支付汇费,韩秀从来都是自掏腰包,她这份自甘自愿辛苦付出的信差,一直持续到两岸通邮以后的1993年。
落款“1988年10月于上海”的《砚田春秋》,是清阁先生晚年一篇非常重要的“漫谈写作历程”的散文,“联副”在发表时,特意在标题之上注明“海峡两岸首次发表”,配发一幅“近影”照片的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秦贤次所写题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赵清阁》的文学小传。
用清阁先生自己的话说,这篇散文纪录下了她“荆棘丛生”的文学道路、“多么坎坷”的写作生涯、“漫长而充满辛酸”的历程。我想,这篇散文的写作初衷一是对自己“从事砚田耕耘已近六十个春秋”做个回望总结,二是为了“让自己有所反思,也让读者对我、对历史有所了解”,三是给自己加油、鼓劲。她在文章最后说:
我热爱文学,我视文学为第二生命,好不容易盼到这个十分珍贵的晚晴,我绝不能辜负它!于是我又锲而不舍地写了十年,这十年我比任何时候都写得勤奋、舒畅。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小说、戏剧、散文、杂文、理论、诗词,这些都是我的心声,写了我的爱和恨,写了我对往事、故人的缅怀和回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向往,理想和愿望,另外还修订整理了一些仍具现实意义的旧作。只是毕竟我老了,思想赶不上时代的新潮流,我的作品恐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而且精力不济,运笔效率也慢了,迟钝了。
我为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然而成绩微末,于国家人民没有什么贡献,感到非常愧疚!但今后我还不愿就此藏拙,还想继续写下去,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职责,也是人生的意义。成败姑且不计,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从文章发表后清阁先生在1989年2月21日写给韩秀的信得知,一方面,她对此文在台湾文坛引起的反应甚为满意。她说:“关于《砚田》,戏剧界反应,承老人们还记得我,非常高兴。”另一方面,大陆这边的情形又让她高兴不起来。她说:
此间戏剧界早已遗忘了我,记得84年你曾问过我:为什么《红楼梦》话剧不予演出?我当时没有回答你,但我相信你会懂得“为什么”。由于你母亲的关系,你接触过他们那个圈圈,“圈”外人一向是被排斥、妒忌的(解放前也如此)。有趣的是美国周策纵教授日前来信告诉我,去年他在新加坡讲学看到那里演出我的一个《红》剧本《鸳鸯剑》,还不坏(但他们没和我联系,我正想法搞点演出资料看看)。听了这消息真有点啼笑皆非!《红》剧不是赔钱戏,可这里就是没人演。书出版后很快卖完,至今也未再印。最近两岸文化交流,大陆出版了台湾作家的书(琼瑶、三毛等),台湾也出版了大陆作家的书,日后他们或愿出《红》剧,我也乐意(送你的那部不全,还少一个剧本,下次重印时即补进)。
出版界也很令人恼火,他们只着眼于经济效益,热衷于武侠、性爱作品。
时间过去一个多月,3月31日,清阁先生致信韩秀,感谢韩秀“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并表示希望通过韩秀帮忙联系台湾的出版社,把她改编的五部《红楼梦》话剧结集出版。如信中所言,“《红》剧虽非创作,也耗费了我一生的心血”。也因此,她对秦贤次那篇作者“简介”的题目,深感知音。她说,“以话剧诠释《红楼梦》,是对我的过誉,但也切中道破了我的迂怀。”
然而,清阁先生始终萦怀的《红楼梦话剧集》,始终也未能在海峡两岸的任何一方以全貌再版,引憾至今!我曾在《赵清阁与〈红楼梦〉的未了缘》一文中提及清阁先生1985年出版《红楼梦话剧集》时,书里独独缺了因一时找不到原作而未收的《禅林归鸟》。找到原作时,书已出版,清阁先生又对结尾做了修改,并将剧名改为《富贵浮云》。这次,从信里得知,在改名《富贵浮云》之前,她还曾拟改其名为《树倒猢狲散》(1989年3月31日)。
现在我们再读读另外的十七封信。我以为对于清阁先生的晚景晚境,或可以用这样五个字来概括——病,孤,勤,愤,疑。
病。清阁先生在《砚田春秋》里写道:“1966年的一场暴风雨袭击,人民蒙受了沉重的灾难。作家、艺术家变成了‘牛鬼蛇神’,剥夺了创作权;因此文苑荒芜,百花凋零。我整整被迫搁笔了十年之久,十年中又患脑血栓,偏瘫了三四年。知道雨过天晴,我才劫后重生,也才恢复写作,可我已经岁逾七旬,垂垂老矣!”
未料1990年9月21日,清阁先生于上海华东医院开刀,手术切除肿瘤(见1990年1月3日信)。术后,“身体极弱,恢复甚慢,稍活动即冷汗淋漓”。为帮助清阁先生恢复体力,韩秀时常从国外买了价格不菲的西洋参给她寄来。这里的十七封信,几乎每封都少不了一个“病”字,病的不断纠缠,自然会影响到心情。她在信中慨叹,“想不到到晚年生这么一场大病!真是菩萨不睁眼,虐我这个孤老太酷了!”(1990年1月3日)
孤。“赵清阁终身未婚,身边也没有亲人,晚年只有保姆吴嫂几十年相依为命”,这句话真切地说明了晚年清阁先生的孤独与寂寞。再如,清阁先生在致韩秀信里说:“我再也想不到,一个我看着自幼长大的孩子,如今竟成了我的同行,我的小友!(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才三四岁,一晃四十几年了!)你使我感到欣慰,可又有些遗憾;遗憾的是,我们离开太远了,如果你在上海多好!真想念你,和你的佐齐、两个孩子。”(1989年3月21日)对晚辈的真切想念,也是孤寂的自然流露与抒发。她把韩秀的儿子小安捷的照片“放进案头的玻璃板内了,朝夕相对,望着他向我笑,十分高兴”(1991年9月15日)。
另外,清阁先生在信中谈到端木蕻良时,这样写道:“据说端木甚健,正写《曹雪芹》,所居舒适,为之欣慰!他有一位能干贤惠的夫人,是他的福气,无论生活上、写作上,她都为端木全力以赴的奉献!因此我觉得端木的成绩,与她的帮助分不开。相形见绌,我写篇‘千字文’就很困难,这封信已写了多日,不是脑子问题,是精力不济!”(1992年3月23日)她在1989年元宵节致痖弦信里又特别提及:“朋辈凋零殆尽,台湾梁实秋、沉樱去年先后谢世;沉1982年曾回国小聚过,梁则竟永诀!唯(谢)冰莹尚通鱼雁,她亦八旬,恐也难能相见了!”故交老友的“凋零殆尽”更是徒增了她心底的那份孤寂。
值得敬佩的是,晚年虽孤寂,但她活得十分淡泊、洒脱,她深知“我余年不多,一切都看得很淡很淡!”因此,她早早地料理好了后事。她将一生所藏经“文革”劫后残余的书画全部捐给了国家。她说:
岁近八十(今已虚度七十又九了),年前病中考虑到生也有限,余年不多;一生独立自主的我,绝不愿把身后之事让别人去随意摆弄。尤其那些贪婪的所谓“亲友”,他们想从一个孤老身上捞“遗产”。他们不知道我早看穿了一切,十年前就写好遗嘱,决定将一生珍藏的书画(即所谓财产)(劫后残余)捐献国家,也只有国家才能永恒的保存。于是新年前夕我处理了这件事,还将自己的早年画作分赠了关心、爱护我的人留作纪念。这样一来,落得两袖清风,一身轻松,活得洒拓荡然,不亦乐乎!(1992年3月23日)
勤。清阁先生于1987年退休,但她认为作家是“退”而不“休”的。“岁进八秩,能再带病延年三五岁,把未完的工作干完,就满足了!”(1990年1月3日)不难想象,自觉受了“压制”的晚年清阁先生,也是力图通过勤奋地写作、编书,既是证明自己,也是为自己正名。“我去年结集的六十年来的散文《浮生若梦》(卅余万字)已出版(这场病与此书的高度紧张有关!),那本《无题集》(改名《皇家饭店》)也出版了,这是病中的一大安慰”(1990年1月3日)。
《皇家饭店》的再版,让清阁先生十分高兴、欣慰。她不无骄傲地说,“我为中国老一辈女作家做了点贡献,她们的作品湮没了四十三年后又得以重新问世”(1990年5月15日)。这是她主编的一本书,是她在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专门约一批女作家写作的结集。《皇家饭店》这个书名即是书中所收陆小曼创作的一篇同名中篇小说。
晚年清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以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年以后,虽因病再无什么长篇大作,却也常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堪称勤奋。
不过,此时的清阁先生已在信中对日趋商业化的出版业表示了无奈。她说:“出版社不愿出版这种严肃的纯文学,认为是赔钱生意,为此作家们稿费都改为买书,我只替海外几位女作家争取了一点微薄的稿费。没办法,这里出版界境况萧条也是事实,只有武侠、色情小说有销路,所以原《无题集》中的珍贵资料——照片、手迹都除没了,为的降低成本。不少朋友表示惋惜,我也是无奈!我虽稿费不取分文也不济事。”(1990年5月15日)
“文学当商品交易,我还不乐意,可已有人在广州颈挂牌子在街头叫卖了,斯文扫地!”(1994年3月21日)
“散文事,我已编就,正在大陆托人找出版处,即使不要稿费,也愿印出,这是我第四本散文集,争取今年面世,也就结束我的文学生涯了!”(1994年5月7日)
不知为何,或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理由,我现在时常感叹,无需再“扫”,地上已鲜有斯文!这大概就是愤,愤激,常因胸中有不平而来。
愤。清阁先生的愤激,源于为女作家、为女性文学而感不平,如她说:“女作家成功不易——要冲过荆棘重重;而到头来还要遭嫉,遭贬,乃致于无地始后已!三毛可悲!二十一世纪依然是男性中心社会,女人永远受欺侮!”(1991年2月3日)
“报上看到张爱玲近作《自传》问世,此人沉默多年,现在已引起文坛重视,实在有些太晚了!埋没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这是文学事业的损失,所以我呼吁重视女子文学。”(1991年8月12日)
因此,当她看到韩秀在文学写作上小说、散文新作迭出,感到由衷的欣喜、振奋。她写信鼓励说:
你为女子文学的活跃、发展贡献力量,不胜感奋!这是文学事业的一新课题,“五四”以来一直未被重视;不仅在中国,也是世界性的;是没有女作家,抑女作家作品低劣?不!是社会对女性的歧形观念作祟,否则何以英国的Emily Bronte的《咆哮山庄》直到她死后很多年才问世,才为后人承认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佳作,于是轰动全球!
不信,你还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为此我很不平;写那篇小文和写苏雪林、凌叔华都基于这种心情。一九四六年我战后到上海,一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即不顾别人的非议在《大公报》上写了篇评介她的文章。女作家太少,有才华的尤其少。”(1991年9月15日)
1993年,病中的清阁先生读完韩秀新出的散文集《重叠的足迹》,即又写信告知:“很高兴,近年中你有卓越的成绩。你的散文使我感觉新颖,从形式到内容你都为女子文学有所突破,你的勤恳、用功的成果,是二三十年代女子文学事业的继承和发展!”(1993年9月11日)
在她眼里,韩秀是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女作家。她寄予了厚望,并明确告知:“你有才华,希望你能成为美国的乔治·桑!”(1988年11月12日)“不要去赞羡那些‘哗众取宠’的歪风,要忠实于艺术的良知!你是有才华的。”(1990年5月15日)“你正当风华正茂之年,又很勤奋,前途无量!”(1993年1月6日)“祝愿你的小说写成功,也相信能成功。小说,重要是写人,‘通过人’反映世态;包括人性的善恶,人情的冷暖。”(1989年5月28日)
疑。对有些自我感觉触动了敏感神经的事情,产生疑心、疑虑,不见得就是有过苦难甚至灾难记忆的老人们的专利。当然,风雨过后的晚年清阁先生,未能幸免此症。如她在信里对海外报导她的病表示出担心,问韩秀:“看到否?不会‘乱弹琴’吧?”(1990年1月3日)
对正在编辑打算请韩秀帮忙在台湾联系出版的散文集《往事如烟》,先是表示“约计七八万字,均未结集过,即使选几篇结过集的,也绝无版权问题”。继而保证“内容属纯文学作品,毫无政治意义,为此我也希望出版对方没有政治背景,最好是商办书局,而非官办。以免麻烦”(1993年12月12日)。
1991年7月15日,台湾《联合报》转载发表了清阁先生原刊《香港文学》上“文字虽有改动,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隔海寄雪林》。《联合报》历来只发表原创,几不转载,因此稿为在台北召开的一个苏雪林研讨会所转,得痖弦先生成全,成了特例。但当尚不知此情的清阁先生,发现文中赫然出现了“反共作家苏雪林”的字样,自然因忧虑而变得紧张起来。她对韩秀说,“推测可能是苏老研讨会干的,然而为什么要在那篇稿子上加写苏老‘反共’呢?这对苏老于大陆的影响不利,于我也不宜。这你一定能理解。由于我的几篇文章提到苏老,已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的小说、散文卷都选了她的作品,我想这也是她晚年的一个安慰,也是我写该文的主旨,但被他们一改,改得我哭笑不得!仿佛我不是纪念她,而是非议她,真正冤哉!”(1991年10月15日)
除此以外,当清阁先生给在美国或随外交官丈夫驻节他国的韩秀发出一信之后,她便计算着收到回信的时间。一旦有了夜长梦多的感觉,她就会担心信有遗失,字里行间透出相当的紧张,想来这可能跟她于198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关。而韩秀直到1997年方知清阁先生入了党。她在1988年给痖弦写信介绍清阁先生时,说:
“文革”之后,清阁阿姨的身体糟透了,手几乎不能拿笔。但她一次又一次试着拿东西,由大到小,终于又握紧了笔杆。她不仅是作家,也是农工民主党成员,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知识分子请命,为创作自由呼吁,她不仅是作家,也是画家,画出她追求一生的自由、祥和。
她是硬骨头作家、画家和为自由而战的斗士。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说不写剧本不给工资(没有工资就更没有饭吃),到底,她也没写他们要的……剧本。
我非常尊敬这位老人,希望一向受冷落的她能在七十高龄时拥有新的读者群——《联合报》的读者群。(1988年10月24日)
也是因为此,到了2010年,韩秀在致董桥信里表露出内心的感受:
在清阁姨的晚年,她并没有完全中断与境外的联络。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97年7月,那时候我们在雅典。我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偶然看到一本大陆出版的有关女作家生平的书,里面有四页写清阁姨和她的创作,并且写到她1984年入党。我在给她的信里只提了一句,告诉了她,我看到了那本书。然后,我便收到了她最后的这封信,没有谈这件事,信里面满是对我的祝福,信里面满是悲伤、无奈、绝望。她瞒了我十五年,心里的感觉当然是凄楚而复杂的。我是她的小友,是那个跑来跑去为她传递信件的最为可靠之人,是那个将她的作品带至境外发表的小帮手,是那个在自己的文字中充满着她熟悉的她喜欢的味道的小写手。我们曾在1984年、85年、86年联床夜话。我知道那《落叶无限愁》的来龙与去脉。
我没有把这封信看作最后一封信,还是写信给她,热情如昔,还是寄新书给她,还是寄参片给她(不是为了滋补,而是她的医生嘱咐她长期服用,治病用的。我从1990年开始寄她,到1998年底是最后一次,我相信那数量够她服用到最后)。但是,我没有再收到她的信。她把自己完全地封闭了起来。两年多之后,她走了。我一直想念她。
是的,我也一直在想念她,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清阁先生。1998年10月,我去上海时,曾有幸在施蛰存、黄裳和王元化三位先生的家里分别拜望并采访过他们;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还采访了病中的柯灵先生,话题主要是由老舍之死说开去,因为那时我还在采写着《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我也曾请陈子善先生帮忙联系清阁先生,诚挚地希望她能跟我谈一谈或许她想聊一聊的老舍。可那时的清阁先生身体已不十分好,故答复子善兄说身体欠佳,次日看情形再定。
我心里依然怀着一丝的希望,并莫名产生了由如果万一可以而带来的些许紧张。但最后,清阁先生还是以身体原因而婉拒了此次相约,因此,这也成了我一个永久的遗憾。不过,这样的遗憾非但没让我觉得可惜,今天想来,竟感觉有了些“此恨绵绵”的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