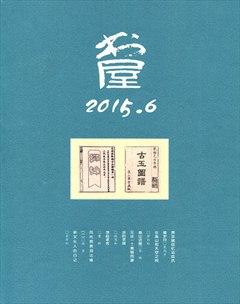谁言良辰轻唤回(四)
胡喜云 胡喜瑞
1935年5月,《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以吕思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议论失当为由,向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控告商务印书馆以及著作人吕思勉、《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等犯有“外患罪”及违反《出版法》。
5月12日,吕思勉与商务印书馆代表人李伯嘉、商务印书馆聘请的律师徐百齐至南京,13日午后至法庭应诉。
5月20日,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宣布判决:
吕思勉所著《自修适用本国史》不依据确定正史推崇岳飞等,乃称根据《宋史》本纪、《金史》、《文献通考》、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褒秦桧而贬岳飞等,其持论固属不当,无怪人多指摘。但在民国十二年初版及十五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各续版皆然,有初版及各续版书可证其间未曾修改,其就古人之臧否加以评论与以现代事实推想古代事实之说,虽未适当,要皆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以法律言,……不构成《出版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罪。商务印书馆印刷人发行人李伯嘉自亦同无犯行可言。……王公弢、赵超构见南京市政府禁止该书,即于《朝报》发表《从秦桧说起》一文,为吕思勉辩者,亦不过系私人之见解,谓盖棺定论之难,岳飞、秦桧等之毁誉难定,并有同时誉此人同时毁此人者,有意弄文,非藉抗令,均不成立违反《出版法》第十九条罪刑,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为不起诉处分。
不予起诉的判决书公布后,龚德柏不服,向江苏高等法院申请再议。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胡诒谷签署《再议处分书》,称“声请再议于法不合,应予驳回”。
6月21日,在(上海)光华大学的吕思勉收到老友庄先识从南京发来的信函,其中称:“兄与商务之被控,案闻同乡吴君言已有判决书发表,(不予起诉)可无问题。(兄当已阅悉)后龚德柏又作二次控告,亦被驳斥,此后当不致再生枝节矣。兹将兄离京后数日之《救国日报》告白两纸附上一阅,大约即作为二次控告之材料也。”吕思勉有收集剪报资料的习惯,遂将与诉讼案相关的材料用旧报纸包扎,上面写着“龚案”收藏起来。吕思勉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从1900年十七岁时开始写日记,每月一卷,年年更改名称,并有序言解释名称的意义。可惜1934年以前的日记随读书楼一起被毁,1935年后的日记被他“悉摧烧之”。关于诉讼案,他残存日记中只有一句简短的记载:“《白话本国史》讼案。廿四年五月十二与李伯嘉、徐百齐入都,十三日午后到庭”,无法更多得知他在此案中的作为。
1952年,吕思勉在《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总结自己的述作,其中提到了《白话本国史》:
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执教)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以增补而成,印行于1921年或1922年,今已不省记矣。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之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
吕思勉的学生李永圻也回忆:“老先生当年曾对我说,‘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龚德柏曾翻译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蹇蹇录》,因该书稿的出版事宜,与商务印书馆有些不快。”
其实,《白话本国史》诉讼案并非吕思勉认为的这么简单。这其中涉及《白话本国史》为何被控犯有“外患罪”、违反《出版法》?龚德柏为何控告吕思勉?龚德柏与商务印书馆有哪些“不快”?《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为何也被一并控告?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流行广泛,影响深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人指责《白话本国史》关于宋、金和战的论述不妥,认为中华民族正面临最危险的形势,吕思勉居然为秦桧翻案,等于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的民族败类辩解,是彻头彻尾的“宁赠友邦,毋予家奴”之最忠实的自供。时势影响之下,吕思勉受商务印书馆之邀,对这一节进行了修改和删节,改褒秦桧、贬岳飞为贬秦桧、褒岳飞,1933年10月出版了第二版,后来又出版了订正版,但市场上各种旧版本仍在流行。
1935年3月5日,南京特别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第2315号,训令社会局严禁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于未删正前在南京销售,并签发公函第2316号致中央宣传委员会,函请严饬吕著删改修正,未删正前禁止其发售。石瑛在公函中称:
查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第三编,近古史下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第一节,南宋初期的战事内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内称:“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又称:“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都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等语。按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该书上述各节摭拾浮词,妄陈瞽说,于武穆极丑诋之能,于秦桧尽推崇之致,是何居心,殊不可解。际此国势衰弱,外侮凭陵,凡所以鼓励精忠报国之精神,激扬不屈不挠之意志者,学术界方当交相劝勉,一致努力。乃该书持论竟大反常理,影响所及何堪设想。拟请贵会严饬该书著作人及商务印书馆,限期将上述各节,迅予删除改正,在未删改以前禁止该书发售,以正视听,而免淆惑。除令本市社会局,严禁该书在本市销售,并通饬各级学校禁止学生阅读外,相应函请查照核办,见复为荷。
除政策和形势影响外,石瑛签发此公函,与他个人的志向确也有一定关系。石瑛,字蘅青,1879年生于湖北阳新县,被誉为现代“古人”、“民国第一清官”。1905年留学英国时加入同盟会,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昌大学校长、湖北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浙江建设厅厅长等。1932年4月9日石瑛就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后,大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格财经手续;多筑平民住宅,举办平民贷款;扶持旧有缎业,大力提倡国货;增设校舍,普及小学教育。同时,他以更大的热情和心力进行“精神建设”,明令禁烟、禁赌、禁娼,整饬社会风气,引导人们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他尤为重视激发市民的爱国精神,在南京年年举行“九·一八”国耻日纪念。翻阅《中央日报》所载石瑛1932年4月至1935年3月间的公开演讲,无一次不提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发此公函半个月后,1935年3月20日,石瑛拒绝与汪精卫合作而向国民政府递交辞呈)。
石瑛发出严禁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于未删改前在南京销售的训令后,媒体一片哗然,对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批评热浪再次被掀起。
1935年3月12日,南京《朝报》“每日谈话”专栏发表署名“沽”的一篇短文《从秦桧说起》,为吕思勉《白话本国史》被禁喊冤。南京《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看到后,在《救国日报》上以初号大字“真凭实据,证明吕思勉为汉奸”为标题,骂吕思勉是“汉奸”,指责《朝报》不负责任,并认定那么“厉害”的文章非赵超构莫为,于是对《朝报》和赵超构进行大肆攻击。
龚德柏,1891年生于湖南泸溪,字次筠,笔名陆齐。1913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后,积极从事反日活动。曾任《中日通讯社》编辑、天津《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上海《商报》东京通讯员。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华盛顿会议后回国,受聘于《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日报》等,后与成舍我筹办《世界晚报》,自创《大同晚报》,“言论激烈,为一时之冠,因此有被捕六次之历史”。“在(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我把数年前已译就之《蹇蹇录》由箱底取出,作一叙文,交商务出版”,“(1932年)八月间创办《救国日报》。由此到南京弃守,五年多间,除至友王新命兄有时代作社论外,该报社论几完全出于我一人之手。至少有四五十万言,曾将其重要者,印成三册。二十九年九月全毁于敌之轰炸,至今一字无存,在我个人殊为重大损失”(龚德柏《我的自传》)。
龚德柏对石瑛很是佩服,1943年得知石瑛病逝还曾撰文加以纪念,称“在我办报期内,石瑛正任南京市长,约有四年。报纸——尤其骂人最厉害的我的报纸,同地方官冲突,殊属难免。但我不但不骂他,有时还替他骂别人,这当然是我对石氏人格佩服所致”。但龚德柏积极热烈地讨伐吕思勉,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大炮”作派。龚德柏曾对好友乔家才说:“我的天性好奇,一生行事不循轨道。”“胆大妄为四字,生是我的美评,死是我的嘉谥。”龚德柏性格倔强而怪僻,新闻界同仁对他多是敬而远之。他的社论经常是通篇谩骂,誉之者谓为笔锋锐利,毁之者谓为哗众取宠,故送他绰号“龚大炮”。1933年《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新年的梦想》中,刊出他的梦想:
余天性愚戆,平日慕汲黯、魏徵、杨继盛、江春霖等之为人。现在经营报纸,不顾时会,危言危行,其目的在维持真是非。余希望余所经营之《救国日报》,势力蒸蒸日上,在最近将来成为全国最有力之报纸,全国一切问题皆须余之一言以判断其是非曲直,而折服横强者;一切贪官污吏,皆畏余如虎而不敢作恶,以促政府之进步。若不幸余所经营之报纸失败,则余希望为一监察委员,将贪官污吏尽量弹劾,其他一切贪污案件,世人亦以得余一查为幸,如清代彭玉麟故事,则余之愿足矣。然此则真为梦想,殊不能实现也。
龚德柏猜得没错,“沽”确实是《朝报》“国际版”主编赵超构。赵超构,1910年生于浙江瑞安(今文成县),读中学时因参加爱国运动被迫退学,后留学日本,1934年夏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毕业后进入《朝报》。《朝报》创刊于1934年月2月,以“提倡朝气”为宗旨,以言论、经济报道与副刊为特色,老板是王公弢,总编辑是朱虚白,“有一个较好的班底”,还有一支扎实能文的作者队伍,仅“副刊”就汇集了张友鸾、张恨水、金满城、董每戡等人(号称“十八罗汉”),不久即在报刊林立的南京脱颖而出,跻身南京五报之一。《朝报》的崛起,直接影响了《救国日报》的销量和影响,这令龚德柏极为郁闷,遂发挥其“大炮”的习性,经常向《朝报》叫骂。民国著名报人绮情楼主喻血轮若干年后曾回忆:
南京报人龚德柏,抗战前在京办《救国日报》,以敢言著称,其实龚往往以忤为直,故誉者有之,毁者亦有之。时与《救国日报》同型者,尚有一《朝报》,为王公弢所办,行销甚广,非《救国日报》所能企及,龚甚嫉之,常向王挑衅,由文字辩论,而至互相诋毁。久之,王颇厌倦,而龚犹兴高采烈,王恨甚!乃使人转语龚曰:“笔墨官司,《朝报》决定休止,龚某如再哓哓,决于街头以屎罐掷之。”时龚意气甚盛,一无所畏,惟闻王掷以屎罐,则为之大惧。
面对龚德柏的挑战,年轻气盛的赵超构哪里肯示弱,立即进行猛烈反击,于1935年3月20日、21日以“沽”的名义在《朝报》上发表《辟某报汉奸论》。这篇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我的立场”,“吕思勉是否汉奸”,“某报才真是秦桧的知己”,“结论”——仅看小标题即可感受到其中浓烈的火药味。3月23日,《朝报》以一个整版刊登了两篇署名皆是“沽”的文章,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极有气势极有斗争性:“用真凭实据证明龚德柏诬陷吕思勉!”其下还有两行大字:“奇蠢极恶之栽赃手段!”“民国二十四年言论界之大笑话!”第二篇文章的标题较为“含蓄”:“杂驳某报”,其中的五个小标题却仍是直冲龚德柏而去:“何以不书出某报名字?”“我是否为赵超构先生?”“你看不起《朝报》,《朝报》更看不起你”“整个《朝报》主张与言论责任”“自比岳飞!你也配!”3月26日,《朝报》再次以一个整版刊登了一篇署名“沽”的文章,标题是“龚德柏之真凭实据原来只有天晓得”。此后数日,《朝报》与《救国日报》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时有论战,比对《白话本国史》各版本之异同,推测吕思勉之用心,常有泼妇骂街之语夹杂其间,真是热闹非凡。
一般情况下,朴实纯粹的吕思勉不怎么会被花哨的报纸和舆论界所干扰,但这一次有些不同了。中央宣传委员会收到石瑛签发的第2316号公函后,发出密函第787号给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遂发出训令(执字1584号),命令商务印书馆修改《白话本国史》。于是,吕思勉对《白话本国史》进行了第二次修改,1935年4月发行国难后订正第四版。但龚德柏与《朝报》之间喧嚣热闹的口诛笔伐早已超越了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一发而不可收之下,龚德柏于1935年5月将商务印书馆、吕思勉、《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告上了法庭,这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曾将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与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视为奇怪乖舛的典型,认为不能将它们作为教科书。张棡于1932年4月30日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议论之谬:“看《白话本国史》,此书为武进吕思勉著,于历史眼光颇具有特别处,然对于唐虞揖让、汤武征诛,皆疑为儒者学说,并非实有其事,则武断之甚。于宋之王安石、秦桧则极口誉扬之,于司马公及韩、岳诸将则任情毁之,皆所谓好恶拂人之性,与近日胡适之、顾颉刚一流,同是坏人心术之作,未可当教科用品也。”陈允洛1935年8月在厦门大学历史讲习班提交论文《教历史经验谈》中称:“或偏重新奇者,如吕思勉之《白话中国史》,计四本,商务出版。顾颉刚、王钟麒合编之《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计三册,亦商务出版。吕著专取前人翻案文字,如称赞秦皇、武后,又谓岳飞无力抗金,秦桧心存君国。以此作史论与教师看,固为新颖,以之教学生,未免与宣传作用者,殊途同归。顾著则推翻旧史料而用新史料,如以虞夏史实为不足信,王莽为社会主义之实行家,新则新矣。但学生于正史尚无根柢,禹、莽为何如人,多未认识,言其为爬虫,言其有新思想,并不觉得奇异。此二书觉得有兴趣者在教师,在学生则不能,而且有流弊。”
吕、顾的著作之所以被人相提并论,除因两书流传广泛、其中皆有一些观点“新奇”外,还因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也曾遭国民政府查禁。顾颉刚1922年接受胡适邀请,为商务印书馆撰写该书,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尧、舜以前的历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其书上册出版于1923年9月,中册出版于1924年2月,下册出版于1924年6月,堪称当时乃至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初中历史教科书。1927年北伐成功,各省设参议会。山东参议员王鸿一据山东曹州重华书院院董丛涟珠、院长陈三亚等人呈文提出议案,弹劾顾颉刚“国史”“非圣无法”,应予查禁。戴季陶见此提案,认为顾著“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写,否则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遂下令查禁顾颉刚“国史”,并对商务印书馆处以一百万元罚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请吴稚晖出面说情,才得以免去罚款,但顾颉刚“国史”从此被禁止发行。若干年后顾颉刚曾回忆:“这是我为讨论古史在商务所闯出的祸,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
顾颉刚此书遭禁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诉讼案,被视为民国出版史上的两大诉讼案。仔细考察,顾颉刚的遭禁,其中有复杂的政治争斗,也有政、学之间的交锋,还牵涉到出版业之间的利益竞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诉讼案则相对简单得多,从而法院被界定为“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起诉处分”。
《白话本国史》诉讼案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小小浪花,看似无关紧要,甚至好像对吕思勉、龚德柏本人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它其实仍在吕思勉平静的心湖里增添了几波涟漪。抗战期间,为满足上海大学文科学生的需要,吕思勉于1940年撰成《中国通史》,其中第四十四章“南宋恢复的无成”,不再持《白话本国史》中之论,而是称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可谓屈辱极了。在这一章末尾,吕思勉发了一通议论:
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可知。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
这段话可看作吕思勉对《白话本国史》相关内容的解释和对《白话本国史》诉讼案的一种思考。
平心而论,吕思勉堪称一位持重的学者,也可视为一个爱国志士。正如他在光华大学的“旧学生”钱钟汉所说:“先生用意不过是当时深感军阀势力之祸国害民,加以南宋史料中对当时军人的用兵自重确有反映,才据以抨击当时军阀,得出一片面的秦桧主和,岳飞类似军阀的错误结论。然尽管如此,吕先生仍不失为一个真正学者,其错误仍不过学术论点之错误。……同时他本人后来的气节表现,还是一个爱国志士,也绝无失足失迹嫌疑,对此学术论点还不妨根据史实定其是非,不应以此一点否定他一生学术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