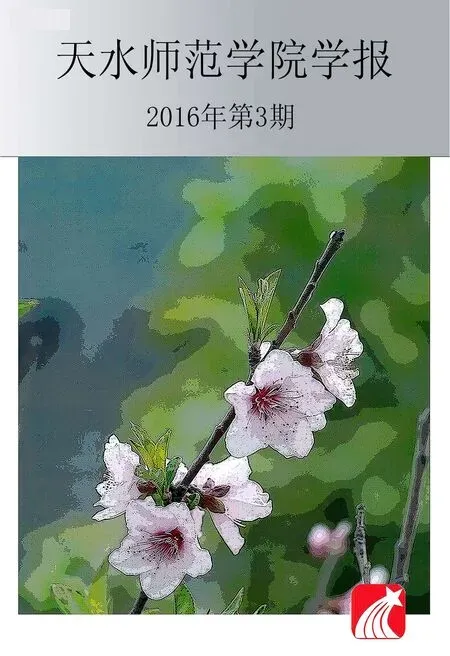北朝的农业政策与陇右农业的曲折发展
张 琳,杨小敏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北朝的农业政策与陇右农业的曲折发展
张琳,杨小敏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北朝时期,执政者尊崇农业,推行增加政府劳动人手、调整土地政策、劝农督课与良吏治陇等有利于生产恢复发展的措施,取得良好效果。但陇右地区民族问题复杂,局势跌宕起伏,正常生产秩序时被扰乱。即便如此,其经济仍然冲破各种阻力和困难,在艰难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
北朝;农业政策;陇右农业;曲折发展
陇右位于泾、渭两大水系的上游地区,地势东高西低,与关中毗邻。关中自古“膏壤沃野千里”,农业经济甚是发达。陇右不仅“与关中同俗”,且“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卷129是农牧十分发达的地区。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区政权林立,胡汉各族统治者相互争雄称霸,导致此地酣战不已。直到北魏拓跋焘击破赫连定,才把陇右从战争的泥沼中拖出来,历经北魏、西魏、北周各族人民的努力,开始走上复苏和缓慢发展的道路。
一、陇右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对于北朝时期陇右的农业生产状况,有学者并不看好,认为“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内迁和战争频仍、政权林立,陇右地区农业开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事实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封建政权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处于封建化进程的北朝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北魏从立国起开始接受农耕生产并日益重视。早在太宗时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3]卷110至孝文帝时,提出“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并把从事农桑纳入国家法令中强制执行,“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并提高农业生产者地位,“与朕共治天下”。[3]卷7上
西魏继续北魏重农思想。先是宇文泰推出24条新制,务弘强国富民之道。大统七年(541)苏绰在宇文泰的支持下,奏行“六条诏书”,提出“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达到“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的目的,亦把从事农桑纳入国家法令中,“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碟名郡县,令长随事加罚,罪一劝百”。[4]卷23
北周武帝为突显农业的重要性,遵从封建古制,多次“亲耕藉田”,[4]卷6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并下诏“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4]卷6要求各级政府注意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做到“三农之隙,别渐营构”。[4]卷6
北朝重农思想的推崇,为陇右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开了较好的局面。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北朝统治者实行多项有利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
(一)朝廷重视增加农业人口
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之一是政府必须控制大量编户农,为国家稳定的赋役来源提供保障,也是封建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保证。故而北朝各政权采取多种手段来解决政府控制下的劳动人口问题。
实行三长制。北魏前期“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3]卷53众多百姓没有登记在册,且“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3]卷110大量财富囤积在地方豪强手中,国家财政收入受损的同时还危及统治。如何限制豪强地主荫占户口,让他们脱离出来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成为北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难题。北魏统治者多次下诏检括户口,劝诱逃户归业,但是收效甚微。针对此情况,政府采用李冲建议,“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3]卷7下规定“五家为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3]卷110由三长有组织地搜括荫户,“隐口漏丁,即听附实”,[3]卷7下搜括出来的荫户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来源。
放免奴婢、杂户。北魏统治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等,习惯于将战俘没为杂户役使或作为奴婢赏赐给有功之臣,故豪强势力蓄奴成风,动辄数以千计,如元禧“奴婢千数”;[3]卷21上高崇“家资富厚,僮仆千余”,[3]卷77且鲜少有放免诏令,仅献文帝延兴二年(472)下诏“工商杂伎,尽拼赴农。”[3]卷7为保证在编人口数量,稳固政府的财政来源,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私自掠人为奴,如高宗文成帝和平四年(463)秋诏曰:“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3]卷5
北周武帝宇文邕开始大规模放免奴婢、杂户。保定五年(565年)将征服地区年高的官私奴婢放免;平齐之后将河南诸州百姓被掠为奴者放免;建德六年(577)更是大范围的放免奴婢,不再有年龄和地域的限制:“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4]卷6下周武帝在放免奴婢的同时还大规模放免杂户,建德六年诏曰:“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4]卷6此次诏书不仅放免杂户,还杜绝了杂户的来源,保障了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灭佛废佛。北朝佛教发展迅速,规模庞大。至北魏末年,全国人口约3000万,僧侣人数达200万,占1/15,寺院共有3万余所;北周人口不到1000万,僧民有100万,寺院1万余所。[5]僧侣广占良田,蓄养奴脾,又免服赋役,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政治压力。北魏太武帝从太平真君七年(446)开始进行残酷的“灭佛”行动,“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沙门无少长悉坑之”。[3]卷114周武帝与之相比,则较好地解决了僧侣问题。建德二年(573)确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4]卷5三年下诏废佛,“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4]卷5把关、陇、梁、益、荆、襄地区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通过这次毁佛,“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6]北周军事、经济实力因此大大加强,废佛成为北周能够统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调整土地政策
北魏初根据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实行“计口授田”政策,以人口数为单位授田,“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馀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3]卷7上但豪强势力为了扩充实力,抢占荫户,且“征敛倍于公赋”,造成“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诏“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初受田者,男夫给二十亩,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7]卷136
通过均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之上,但是打破常规,在授田时直接规定桑田为受田者私用,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北魏后,西魏和北周亦推行均田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些许变化,把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这种在均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以后终于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三)劝农督课,轻徭薄赋
鲜卑拓跋氏本是马背上的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北魏政权建立后,国家封建化过程不断推进,生产方式由以牧为主转为以农为主,农业经济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统治者不断调整措施来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屡次下诏劝农督课来推动农业生产,并把“劝课农桑”作为“富民之本”。[3]卷7上西魏注意劝课农桑,“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4]卷23北周武帝要求刺史守令,“宜亲劝农”,[4]卷6下并把劝农督课的成效作为官吏考课标准,擢用廉吏,贯彻实施劝课农桑之政。
在劝课农桑,敦促百姓从事生产时,统治者还适时调整赋役政策。北魏初期田租户调以“九品混通”进行征收,世家大族和僧侣地主有免税特权,中中以上户的封建负担也并不算重,但是中下户以下随时有“弃卖田宅,漂居异乡”[3]卷53的可能,下下户更是一贫如洗。为了挽回这种险恶的局面,太和九年(485)采取李冲提出的新户调制,规定: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3]卷110
租调减轻到仅存均田前的二分之一弱,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为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手日益增多,这比过去竭泽而渔要更为有利。
(四)良吏治陇
北魏初定秦陇,秦州人对统治者尚怀敌意,一些官员视秦州为畏途,受命后不敢入境,“秦人恃险,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3]卷70为了调和矛盾,执政者十分注重军政长吏的人选,起用良吏治陇。吕罗汉坐镇陇右多年,颇懂威惠之道。在治理秦州时,政绩斐然,“秦、益阻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诸羌恃险,数为叛逆。自罗汉莅州,抚以威惠,西戎怀德,土境帖然。”[3]卷51由于吕罗汉治陇有方,后来的牧守都效法他。元英“在仇池六载,甚有威惠之称”;[3]卷19附传元澄恩威并施,制服桀骜不驯的氐帅后,再许以官职,使之效命,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3]卷19孝文帝时选派的秦、凉镇将和牧守官员,更加注重他们的民族亲和力。如穆亮,治陇时能做到抑强扶弱,任秦州刺史不到一年而“大著声绩”;[3]卷27刘藻任秦州刺史时,“开示恩信,诛戮豪横”,[3]卷70对百姓导以恩信,对一些骄横不法的豪酋进行制载,两手并施,安定地方秩序。
宇文泰与周武帝父子的改革中,整肃吏治一直是重点,实行“勋贤兼取”[4]卷2下的用人方略,要求官吏“夙夜兢兢”,秉承“淳素之风”,[4]卷2使得两朝良吏辈出。独孤信出任陇右十州大都督与秦州刺史时,“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不仅如此,他还平定叛乱,政绩斐然,“即为百姓所怀,声振邻国。”[4]卷16宇文导出任陇右大都督、秦州刺史时,“善于抚御,凡所接引,人皆尽诚。……导抚各西戎,威恩显著”,[4]卷10死后葬于上邽。其子宇文广,在周明帝和周武帝时两度出任秦州刺史,同样因安抚百姓有方而博得赞许。死后,周武帝下诏葬于陇西,以彰其绩。西魏北周时期,大多河陇地方官都以其操守和勤勉成为世之楷模,体现了国家政治清明,为陇右地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经过一系列重农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北朝初期地广人稀的局面大为改观,到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520~524)以前,政府编户齐民达到五百余万户,[6]501垦地面积也有着显著的增加,这对于恢复黄河流域自魏晋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陇右农业生产能力恢复并提升,粮食储量丰富,成为重要的租调征集地和军粮供应地,“秦州殷富”[3]卷52的局面逐渐形成。
二 陇右经济发展的曲折性
天灾人祸不仅破坏农业生产,而且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朝时,天灾时常突发,“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8]卷2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阻碍生产的正常进行。但相对天灾,北朝时人祸给陇地带来的危害更甚。北魏统一北方后,针对河陇地区民族众多的情况,采取改州置镇的办法进行管理。北魏的镇又称军镇,一般由军事统帅驻守。其中缘边军镇除有征服和镇压职能外,还是谪配罪犯的地方,故也是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正光五年(524),因各族人民起义,北魏政府不得不下令改镇置州,宣布军镇制度消亡,但陇右各族人民所受的压迫依然存在。
首先是兵役负担沉重。北魏统治者不仅征发氐羌百姓远征,还拿他们当作“肉篱”。太武帝写信与臧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氐、羌死,正减关中贼。”[9]卷74陇右百姓境况也是最惨烈的,他们被驱以为兵后,兵役遥无限期,还要忍受饥寒交迫之苦。皮豹子看到此情,上书文成帝说:“从戎以来……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3]卷51
此外,北魏将大量河陇人口变为隶杂户以供驱役。439年,太武帝将10万凉州士民迁到平城。其中既有北凉宗室及其官僚,也有河西豪族及一般百姓。北魏将他们中的多数人沦为“隶杂户”,让他们世代承担各种苦役。孝文帝时期推行改革,西北各族人民的处境有所改变,但比之内地,仍不可同日而语,故他们的反抗活动较内地更为频繁。北魏对进行过反抗的人们,采取的手段是变本加厉地奴役他们,同时把镇压能力作为官吏升陟的依据。秦州是反抗最频繁最激烈的地方,因而出了一些极其残暴的酷吏。于洛侯便是其中一位,他“性残酷,刑人必断腕,拔舌,分悬四肢”,[6]卷135导致王元寿领导秦州百姓起义。李洪之也是个臭名昭著的酷吏。他任秦州刺史时,不许百姓挟刀上路,凡违禁者,与抢劫同罪;巡夜时一旦查获犯禁者,立刻斩决。前后被他枉杀的百姓有一百多人。即使到了有“太和之风”的孝文帝时期,秦陇百姓的民族反抗斗争仍是此起彼伏。
北魏统治后期,“自是朝政舒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婪”,[3]卷13随着政权江河日下,秦陇的民族反抗更加激烈。粗略地算,从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440~451)到孝明帝正光(520)以前,秦陇起义不下十数次。之后,大规模的起义有正光五年(524)至孝昌三年(527)由莫折念生领导的秦州起义、万俟丑奴领导历时七年(524~531)的陇东起义等。
北魏末年秦陇各族人民的起义将北魏统治推向了穷途末路。一度复苏和发展的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至西魏宇文泰消灭莫侯陈悦势力后,基本控制了关陇一域,形成关陇集团,同时相继灭掉盘踞在陇地的阴平国、武兴国。但是宇文泰对大统年间岷州梁定、凉州宇文仲和的叛乱进行了残酷镇压,除大批流民被杀外,还迁徙六千多凉州民众至长安,给当地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北周时扫清关陇割据势力,灭掉在陇南的宕昌国。总的来说,西魏、北周在陇地扫清割据势力,采取恩威并施的统治手段,使陇右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农业生产又走上复苏和缓慢发展之路。
三、结 论
北朝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推崇农业,并采取有力手段贯彻实施重农政策,尤其是孝文帝改制实施新政后,陇右经济呈现恢复上升的趋势。但是陇右经济的发展轨迹是曲折的,有起伏和波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北魏在陇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矛盾激化,动乱和斗争此起彼伏,对经济造成极大地破坏。西魏和北周时期,扫清割据势力,注意擢用廉吏,采取的安抚政策得力,社会秩序日趋稳定,陇右经济发展未曾间断,呈上升态势,并成为隋唐关陇集团崛起的核心区。“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7]卷216尽管对这段史料的说法争论很多,认为陇右是唐天宝年间最富庶的地方需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陇右地区比过去富裕,人烟稠密,农桑已成为其社会经济中的主体。[10]89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陈逸平.试论历史时期陇右地区的经济开发[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3).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刘精诚,简修炜.周武帝述论[J].东岳论丛,1983,(1).
[6]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余粮才〕
Agricultural Polic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Tortuou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ongyou
Zhang Lin,Yang Xiaomin
(School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rulers respected agriculture,implemented of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government labor hands and adjusting of land policy and advising farmers class with good management,and having good official to LongYou,and got good results.But the national problem of LongYou area was complex,the situation in the ups and downs,was to disrupt the normal order of production.Even so,the economy still break through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in the arduous and tortuous.
the Northern Dynasties;Longyou economy;tortuous development
K239.2
A
1671-1351(2016)03-0019-04
2016-03-17
张琳(1976-),女,湖南临湘人,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十六国时期甘肃境内民族文化互动与国家认同研究”(14YB097)阶段性成果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