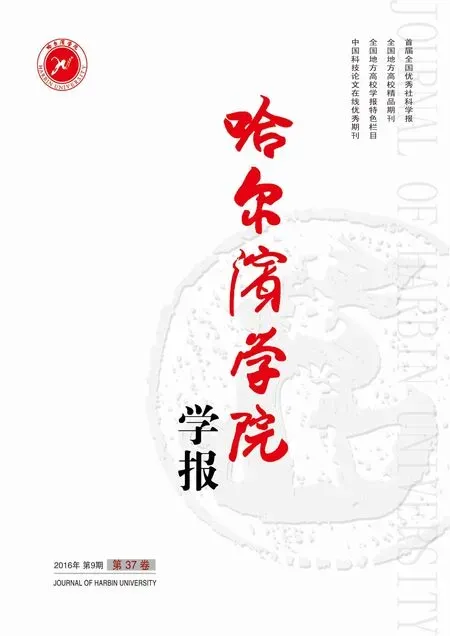王禹浪与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
——我国著名东北流域史学者王禹浪教授与哈尔滨的不解情怀
王俊铮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王禹浪与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
——我国著名东北流域史学者王禹浪教授与哈尔滨的不解情怀
王俊铮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116622)
1999年,王禹浪教授对哈尔滨地名含义潜心研究了整整十年后正式提出了“天鹅论”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他还摸索和总结出东北地区历史地名系统研究的一般规律和研究方法。1994年和2001年,王禹浪教授又先后提出“金源文化”和“京旗文化”两个重要历史文化命题。王禹浪教授积极参与哈尔滨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文庙、呼兰大教堂等哈尔滨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开发,为哈尔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
王禹浪;哈尔滨;天鹅论;金源文化
2015年5月9日上午,黑龙江省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宾客如云,哈尔滨市各界市民共聚一堂,聆听王禹浪教授的“神秘的哈尔滨地名与城史纪元”的学术讲座。王教授的讲座精彩、干练、妙语连珠、富有激情,言辞之间透着不平凡的过往故事和他对哈尔滨这座美丽城市浓浓的深情。王教授的讲座赢得了全场观众的一次次热烈掌声与喝彩。作为王教授的关门弟子的我,在聆听完这次讲座后,总想写点什么,以表达对导师学术成就和高尚人格的钦慕和崇敬之情。我初涉东北史学领域,毫无建树可言,亦愿斗胆对导师数十年如一日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一直关注哈尔滨的历史与文化的学术情结做一番评述。
1978年8月,王禹浪教授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站工作,负责管理全区十一个县的文管所、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期间,先生率领松花江地区文物考察队对所属地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文物普查,其中包括哈尔滨地区的五常县、宾县、巴彦县、尚志县、呼兰县、木兰县、方正县、双城县、延寿县、阿城县、通河县等地,涉及呼兰河流域、拉林河流域、蚂蜒河流域、阿什河流域、运粮河流域、木兰河流域、大通河流域、少陵河、牡丹江左岸部分地区,以及松花江中游地区的左右两岸。在这次文物普查中,先生率领的文物普查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新发现和复查了大量古代遗址、墓葬、碑刻、古城、教堂、庙宇等历史遗存,其中复查和发现古城90余处,丰富了哈尔滨地区的文物“库存”。在先生的倡导下,第一次对普查成果建立了黑龙江省地市级首批文物档案,并得到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的表彰和奖励,荣获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先进集体的称号。这次文普工作是先生涉足东北史文物考古与地方历史研究领域的开端,奠定了他日后在这片广阔的学术天地中大有作为的实践基础。此后,先生先后供职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东北亚研究所、旅游发展研究所,开始了他地方史研究的创新之路。期间他曾东渡扶桑——自费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读卖新闻》著名记者砂村哲也的力荐,被日本亚细亚大学综合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此后先后受聘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AA语言文化研究所共同研究员、日本阿尔泰学会特邀会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理事等学术职务,结识了日本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以及中日关系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其中有衞藤沈吉、神田信夫、松村润、细谷良夫、加藤直人、中间立夫、江夏由树、吉本道雅等学者。1997年,先生被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荣获哈尔滨市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年,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被大连大学引进,参与大连大学第一批硕士点专门史的申报工作,并一举获得成功,为大连大学文科第一个硕士点的申报做出了突出贡献。2004年,先生开始招收东北史研究硕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已招收11批次。同时先生创建了国内外知名的学术机构——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和大连大学东北史文物陈列馆。由于先生在教学、科研、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方面的突出业绩,被大连大学评为教学名师、三育人先进个人。2006年,大连市政府授予先生历史学领军人物称号。
一、哈尔滨地名与城史纪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东北史学界特别是哈尔滨史学界以《新晚报》为载体掀起了“哈尔滨地名与城史纪元”大讨论,王禹浪先生在这次学术大讨论中撰写了一系列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论点。1993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王禹浪先生第一部学术文集《金代黑龙江述略》[1]“下编”中,收录了多篇先生撰写的关于哈尔滨地名含义与城史纪元研究的论文。正是这次学术大讨论及后来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奠定了先生后来的学术地位。
早在先生担任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站长期间,他结识了时任哈尔滨市地方史研究室主任关成和先生。关成和先生是著名中国地方志编撰体例方面的专家和金史专家,他在其撰写的《哈尔滨考》一书中提出了哈尔滨是《金史》中记载的地名“阿勒锦”的音转,为女真语“荣誉”之意。王禹浪先生在与关先生的接触中获知了这一哈尔滨地名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关成和先生的相识开启了王禹浪先生关注、研究哈尔滨地名含义的艰难历程。1985年5月,王禹浪先生调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地方史专家魏国忠、孟广耀、许子荣先生和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专家张碧波先生,开始从事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金史研究和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1986年初的一天,许子荣先生知会王禹浪先生:“哈尔滨地名可能与《金史》中的‘合里宾忒’有关,关成和先生的‘阿勒锦’说可能要发生动摇。”自此,年轻的王禹浪先生开始质疑并深入思考哈尔滨的地名含义。
此前,1985年王禹浪先生参加了由谭其骧、李健才先生总篡,孙进己、冯永谦先生主编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东北历史地理》的课题组,并负责黑龙江金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同时被推选为《东北历史地理》第三卷的副主编。这个项目前后进行了长达近三十年之久,最终于2013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近二百万字数,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在这一过程中有幸结识谭其骧先生、李健才先生、陈述、金啟宗、王钟翰、陈连开、齐心、葛剑雄、周振鹤、孙进己、朱子芳、王承礼、王健群、王侠、干志耿、孙秀仁、张泰湘、林干、周清澍、道尔吉、林树山等众多的一流学者。尤其是得到李健才、金啟宗、王钟翰、齐心先生在治学方面的教诲与厚爱。1988年,32岁的王禹浪先生在初到日本留学的第一年中,在时任黑龙江省海外国际旅行社日本部经理的好友石兴龙先生的引荐下,结识了日本《读卖新闻》资深记者砂村哲也先生。已年近六旬的砂村哲也早年曾在哈尔滨就读,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十分怀念在哈尔滨的生活,尤其对哈尔滨地名含义抱有极大的兴趣。砂村哲也先生与王禹浪先生见面后提出的问题是“哈尔滨地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哈尔滨地名的出始时间是什么,哈尔滨一词是满语还是女真语?”然而,当时的王禹浪先生并不能圆满地回答砂村先生关于哈尔滨地名的一连串的追问。事实上,当时的东北地方史学术界对哈尔滨地名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生在回答砂村所提出的关于《金史》中“阿勒锦”或“霭建”的问题时说:“阿勒锦”是清代点石斋石印本《金史》中的满语注音地名,元代刊《金史》则写作“霭建”,为女真语译名。砂村先生对此十分兴奋,并强烈要求次日一同前往日本国会图书馆查阅乾隆年间刊印的《金史》。王禹浪先生在当天的查阅中,出乎砂村哲也先生的意料,在八大函的线状《金史》中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记载着“霭建”和标有阿勒锦注音的《金史太祖本纪》那张泛着黄色的草纸。虽然王先生一再强调这完全是偶然和巧合,但这一发现着实让砂村先生激动和兴奋不已,并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刮目相看。从此,王禹浪先生开始了与砂村哲也先生因哈尔滨地名研究的忘年之交。在后来的日子里,王禹浪先生几乎每周都要从东京前往数十公里以外的琦玉县大宫市三桥区的砂村先生家里,与他共同进行哈尔滨地名与金史的研究。后来随着《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与《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相继公开,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为研究哈尔滨地名含义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有余,先生曾这样富有深情的写道:“从1989年5月至1990年9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砂村先生几乎每周都在他的书房中,围绕《金史》、《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出现的哈尔滨地名进行着无休止的广泛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时光,阁楼、书房、砂村先生的母亲、他的夫人还有院中的那只可爱的小狗‘太郎’,都成了珍藏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往事!我对那座小楼和院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木都寄以无限的深情。”[2](P10)后来,由于王禹浪先生的夫人王宏北先生病重,他毅然放弃了日本的一切回国照顾妻子。人生有时总要面临许多艰难的抉择,而其中所要承担的痛苦和压力只有当事人才最能够体会。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不知道是否拥有他那样的勇气,但先生与师母相濡以沫、夫妻恩爱的深厚感情,足以让每个人感动。著名东北史专家张碧波先生曾评价我的老师和师母,称他们夫妇为当代的贤伉俪。
王禹浪先生归国照顾妻子的同时,再度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哈尔滨地名的研究工作中。早在1986年,王禹浪先生曾与许子荣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明代《女真译语》一书中找到了解释天鹅之意的“哈儿温”一词。由于先生在日本两年多的研究经历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哈尔滨学术界成果显著,声名鹊起。王禹浪先生自此正式开始从“天鹅”的角度对哈尔滨地名含义进行揭秘,并作为学术领军人物参与到由《新晚报》发起的“哈尔滨地名含义与城史纪元”大讨论中。在此之后的近十年间,王禹浪教授对哈尔滨地名含义的诸家之说如满语“打渔泡”或“晒网场”、蒙语“平地”、俄语“大坟墓”、满语“贫寒小村”、满语“锁骨”、满语“扁”、通古斯语“渡口”等一一进行了考释。先生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坚韧,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遍阅中外史籍和各类文献档案,并多次进行野外实地调查,深入考古发掘现场,刻苦钻研,反复进行证据间的互证和逻辑链条的推理,从历史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个角度综合论证,最终提出了哈尔滨地名源自女真语“哈儿温”,为天鹅之意,是为“天鹅论”。女真语中的天鹅一词是摹声词,源自天鹅“嘎鲁—嘎鲁”的叫声,哈尔滨所在的松花江流域在金代多为湿地,今天的哈尔滨松花江江北地区仍然分布着大片湿地,使这一地区成为天鹅迁徙的必经之地和休息站。哈尔滨地区金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天鹅玉佩饰、骨质天鹅、铜鎏金天鹅等文物更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成为“天鹅论”的重要注脚。“天鹅论”的提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1999年6月6日,《哈尔滨日报》社会时空版著名记者王涤尘对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6月8日的《哈尔滨日报》全文刊发了王涤尘记者的采访记录,分别以“十载求索破800年之谜”、“哈尔滨地名含义有新说”、“哈尔滨——女真语‘天鹅’”、“著名地方史学者王禹浪向本报记者公布10年研究成果”为标题,向社会公布了哈尔滨地名“天鹅论”的观点。该论点在学术界引起了热议,国际知名女真语言学大师金启孮先生、著名东北历史地理学家李健才先生、著名金史学家宋德金先生、北京考古研究所所长齐心先生、著名北方民族文化史专家张碧波先生、著名辽金史专家张泰湘先生、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都永浩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所长赵阿平教授等众多知名学者均对其予以极高评价。金启孮先生为王禹浪教授的《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一书撰写了鉴定意见,导师的好友著名地方史学者伊葆力先生还送来了启功先生为该书题写的一副对联“天鹅九章烛幽隐,冰城十载释灵禽”。
哈尔滨“天鹅论”的提出还引起了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宗璋、副书记王华放、市委宣传部部长姜明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市委宣传部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哈尔滨地名“天鹅论”的学术论证鉴定会,提出应以此为契机,打造哈尔滨“天鹅城”品牌,进行一系列与天鹅有关的经济文化建设活动。2001年,王禹浪教授的“天鹅论”著作《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正式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高水准地方史著作不仅是王禹浪先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东北地名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专著。
伴随着哈尔滨地名含义的重要地方史课题是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王禹浪先生发表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3]一文,他认为,哈尔滨城史纪元应始于金代。无论从当时哈尔滨地区的人口规模、古城性质、形态,还是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看,都说明了金代的哈尔滨已踏上了最初的城市历程,已经形成了具有古代都市文明规模及其城市功能的城镇,使哈尔滨地区的古代城市文明在金代开创了城史的纪元。作为城市形态的代表,位于哈尔滨香坊区的莫力街古城和位于哈尔滨市东郊阿什河畔的小城子古城的建置年代就是哈尔滨古代城史纪元的标志。近年来随着哈尔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阿什河流域的阿城已然由哈尔滨下辖的阿城市变为哈尔滨市阿城区,正式由哈尔滨郊县升格为哈尔滨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哈尔滨城史纪元的问题需要重新看待。2015年5月10日,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召开了“2015年哈尔滨城史纪元研讨会”,来自北京市考古研究所、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地方志办公室、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王禹浪先生也应邀参会。他在会议上就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做了精彩演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阐释。王禹浪先生认为,阿城已然由近郊市县成为哈尔滨区级行政单位,对哈尔滨城史纪元的探索范围应扩大至阿城地区。而这一地区早在金代就已出现了成熟的都市文明和城镇化进程。作为哈尔滨地名语源的“阿勒锦”(霭建)村的地名,早在穆宗统治时期即公元10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在《金史》中。经研究和考证,特别是“塞北马王堆”完颜晏夫妇墓的发现,印证了今阿城巨源乡的小城子村古城正是金建国前的阿勒锦村。在古代行政区划上,哈尔滨一直受金上京城会宁府和清代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管辖,只是中东铁路修建后把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所在地,哈尔滨才脱离了阿勒楚喀的行政管辖范围。因此,现在的哈尔滨与阿城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均属同一行政区划。除此之外,哈尔滨地名的区域化在清末也已经形成,以哈尔滨、大哈尔滨、小哈尔滨地名为村屯的区域称谓在阿什河下游及与松花江汇合附近已经具有特殊的地域范围,这也进一步说明阿什河流域的阿城地区与哈尔滨实为一个地域文化区域。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6月,在阿城金上京东北的小城子村东约300米的阿什河河床内出土了一件珍贵的金代重器——“建元收国”石尊。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哈尔滨城史纪元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该器物为玄武岩质地,状如尊,故名石尊。在其下部刻有“承命建元收国子日典祀”十个铭文。王禹浪先生特别撰写了论文对这一石尊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他从石尊出土地周边的地理环境和重要遗址入手,综合考察了石尊出土地点与阿什河、海沟河以及金上京皇城、小城子古城、半拉城子古城、亚沟石刻、朝日殿遗址等金代历史遗存的关系,认为石尊出土地点是女真人祭祖、祭天的场所,石尊则是祭祀圣物。[4]而铭文中“子日典祀”则是指金代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正月初一建立大金帝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祭祀活动。综上所述,王禹浪先生认为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帝国这一天应作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开篇,哈尔滨都市文明的代表金上京应作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标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认可,在研讨会后,学者们联合撰写了鉴定意见书,对王禹浪教授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哈尔滨城史纪元应从金代算起的观点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可作为定论。先生的这一论点历经二十余载风雨的洗礼,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和时代的认可,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学术界公论。
一个地名“哈尔滨”,虽仅为三个汉字,但其身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岂是三万字能够言及的。一位学者,用了数十年春秋,去研究三个汉字背后的尘封往事,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种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又岂是一百年能够结束的!当我在入学第一天拿到业师王禹浪先生这部沉甸甸的著作《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时,我没有想到,这部著作的诞生竟历经了如此漫长而艰辛的过往。当我研读完这部著作并聆听了先生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动人的讲述时,我才慢慢体会到,先生十年间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艰辛,承受的难以理解的痛苦。当然,我相信,当先生看到他的成果备受认可和尊敬时,他收获的又是怎样一番快乐和幸福,就如同先生陪伴师母治愈病患、牵着妻子的手走出医院病房时,挂在已刻下岁月痕迹的脸颊上那一弯幸福的微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导师王禹浪教授用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精神为他的家乡父老、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反哺出最有营养的养分,犹如那润雨无声的点滴,掉落在日夜流淌的松花江畔,滋润着哈尔滨这片神秘而厚重的黑土地。
二、金源文化、京旗文化研究
2015年恰逢大金帝国建国九百周年,亦是金源内地开发九百周年,哈尔滨社会各界举行了一系列以“金源文化”为主题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现如今,“金源文化”的概念已经深入每一位哈尔滨市民的心目中,金源文化的研究呈现井喷之势,成果显著。金源文化更是以立法形式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市阿城区三级“人代会”确定下来。这一早已为学术界及普通市民耳熟能详的文化概念正是由著名金史学家王禹浪先生提出的。
早在二十多年前,“金源”一词长期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研究“金源”历史文化的学者更是仅有寥寥数人。这一形势在1992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年春季,就在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准备与阿城市政府、黑龙江省农垦师专联合召开、“首届国际金史学术研讨会”之际,时任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所长的王禹浪先生向当时的阿城市副市长洪仁怀先生提出了打造“金源文化”的设想。这一倡议迅速得到哈尔滨及阿城市各界响应,上至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下至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纷纷表示了极大的认可。由此,“金源文化”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的面世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淹没在《金史》中近八百年的“金源”一词正式走出史籍,走向社会,融入当代。如今,金源文化的研究队伍已经成为国际女真学和满学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王禹浪先生可谓金源文化研究团队中的学术带头人,他自1992年首提“金源文化”概念后至今,已在学术界发表了数十篇金源文化的研究论文,参与编著了《金上京百面铜镜图录及研究》《金代铜镜》《金源文物图集》《金上京印符集存》等与金上京和金源文化有关的多部著作。[5-8]2014年,王禹浪教授二十余年研究金源文化的集中展示《金源文化研究》[9]一书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汇集了先生数十年金源文化研究成果,在当代国际金史研究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金源文化”不仅已成为哈尔滨的重要文化软实力,“金源文化节”更是阿城市人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金源文化”的提出与发扬,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促进时代进步的生产力的典范,先生因而被授予阿城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作为女真后裔,满族在哈尔滨地区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清乾隆年间,居住在首都北京的闲散旗人长途跋涉,纵穿东北大地,到达今哈尔滨市拉林阿勒楚喀地区,建旗立屯,开始了全新的戍边生活。在北京旗人居住的二百多年的时光中,在拉林、阿城地区创造了灿烂的京旗文化,成为有清一代哈尔滨满文化的集中体现。京旗文化的提出源自于一件民间历史档案的出现。2000年7月,相关部门在黑龙江省阿城市永源镇一个满族农户家中,征集到一部题为《拉林阿勒楚喀京旗原案》的手抄本,经王禹浪先生等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流散在民间的清代档案。王禹浪先生等学者特别撰写专文对其发现经过及价值予以深入分析和研究。[10]这件珍贵档案的发现意义重大,直接启发了王禹浪先生提出“京旗文化”,并揭开了学术界对“京旗文化”的研究序幕。在《拉林阿勒楚喀京旗原案》被发现后,哈尔滨市社科院组成了专家组,在王禹浪先生的带队下前往拉林阿勒楚喀地区对“京旗”满族村落进行实地调研,他们发现这里的京旗村屯仍保留着浓厚的京旗色彩。2001年5月至7月,在哈尔滨市政府的支持下,哈尔滨市社科院与五常市政府联合组成了“拉林阿勒楚喀地区京旗文化调查组”,深入拉林地区的营城子、兴隆、牛家、红旗、八家子及阿城市的杨树、蜚克图等36个京旗满族屯落进行了系统调查,王禹浪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参与了这次调查。调查收获巨大,发现了大批珍贵京旗文物资料1 120余件,包括谱书、谱单、宗谱、京旗满洲先祖画像、家具、器皿、宗教祭祀用具、雕刻等各类文物。这些珍贵遗物为后来五常市政府打造“京旗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京旗文化引起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中共哈尔滨市委特别做出批示,要求对京旗32屯进行调查摸底,并立专项进行研究。哈尔滨市社科院与五常市政府联合成立满族京旗文化研究所,五常市政府还成立了“拉林地区京旗文化保护开发办公室”,对京旗文化开展专项研究。[11](P1-34)王禹浪先生作为“京旗文化”的提出者和研究者,为研究和弘扬“京旗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金源文化”“京旗文化”犹如两颗璀璨夺目的文明宝石,闪耀在哈尔滨的土地上。作为一名满族同胞,作为一名被哈尔滨赋予了生命的学者,王禹浪先生是在用他的生命去感悟金源地区和京旗地区历史脉搏的跳动,用他的热血去温润尘封已久的过往,他以满族同胞对祖先特有的敬畏之情去发现和理解女真先民曾创造下来的辉煌文明,挖掘故乡历史内涵,打造乡邦文化品牌,弘扬乡邦历史文化。
三、哈尔滨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20世纪初,哈尔滨因中东铁路的兴建,一跃成为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会,曲折多舛而又不失精彩的哈尔滨近代史使这座城市保留下了大量造型各异、美观大方、具有不同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文艺复兴式、洛可可式、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等众多建筑艺术风格在松花江畔这座美丽的国际大都市里交织出别样的绚丽风采,哈尔滨这座近代建筑博物馆因而被赋予了“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称号。如今的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等历史建筑仍然绽放着哈尔滨最夺目的城市之光,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国内外游客驻足留恋,成为哈尔滨城市中一张最动人的名片。然而,殊不知,这些历史建筑和城市景观的保护与研究背后隐藏着一位学者——王禹浪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索菲亚教堂所在的那片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的欧式广场上,中央大街那铺满青石的路面上,哈尔滨文庙那草长莺飞的绿地上,呼兰大教堂那一块块斑驳的墙砖上,都渗透着先生辛勤的汗水。
号称“东北第一街”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都享有盛誉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央大街是目前亚洲最大最长的步行街,始建于1898年,初称“中国大街”。1925年改称为沿袭至今的“中央大街”。整条大街全长1 450米,南起经纬街,北至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塔。长达1公里多的中央大街上汇集着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建筑艺术风格,洋溢着浓厚的西洋气息和浪漫主义格调。铺着青石板的中央大街,常年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不时可见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使这条老街闪耀着异域的风采。临街的商铺常常营业到深夜,灯红酒绿、繁弦急管的夜生活让这条迷人的老街在夜间也散发着高雅的味道。然而,早在1997年前,中央大街仍旧是一条机动车道,机动车常年行驶所带来的震动和尾气污染对历史街区产生了一定破坏,加之附近的历史建筑多已年久失修,私搭乱建严重,对哈尔滨城市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改善哈尔滨的城市形象,保护哈尔滨近代历史街区,王禹浪先生于1997年向哈尔滨市政府提议,要求将中央大街改造成步行街,保护修葺历史建筑,发展旅游业。这一建议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已近百岁高龄的中央大街迎来了新的生命,机动车彻底退出了中央大街的历史舞台,街边的大量历史建筑旧貌换新颜,中央大街也因此成功入选“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成为哈尔滨市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与中央大街直线距离仅600米的索菲亚教堂无疑是哈尔滨城市的标志与象征,作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索菲亚教堂的宗教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教堂始建于1907年3月,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全木结构,通高53.35米,平面呈拉丁十字布局,是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索菲亚教堂是哈尔滨教堂群的佼佼者,但自哈尔滨解放后,索菲亚教堂受损严重。1960年教堂关闭后,曾作为哈一百的仓库、话剧院的练功房等。文革期间,教堂更是遭到了严重破坏,建筑主体破损,教堂内壁画、乐钟、十字架丢失。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饱经风霜的索菲亚教堂已残破不堪,周边被密集的现代楼房包围,历史景观风貌被严重破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王禹浪先生等一批学者再度向市委、市政府提交议案,要求保护维修索菲亚教堂,并对周边环境予以综合整改和拆迁。1997年6月,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开放索菲亚教堂、开辟广场的决定,索菲亚教堂的境况逐渐得到了改善。1999年,黄澄、张竞、王禹浪等学者联合发文,对索菲亚教堂的进一步合理保护和利用提出了创造性的建议。[12]如今的索菲亚教堂,坐落在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的中央,巍峨高大,气势恢宏,拜占庭式的圆顶使整个建筑典雅美观而又不失壮丽。索菲亚教堂已然成为极具旅游和研究价值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感谢王禹浪等学者为保护索菲亚教堂的积极奔走和不懈努力。
哈尔滨虽然洋溢着浓郁的西方文化,但在市区内却坐落着一座规模很大的仿古民国建筑群——哈尔滨文庙。哈尔滨文庙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文庙街25号。1926年由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张景惠提倡,中外各界人士捐助及地方政府拨款于1929年建成的,耗资73万元(哈大洋)。原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现仅存围墙之内的23 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 750平方米,是全市乃至全省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唯一仿古建筑,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文庙。文庙大成殿面阔十一间,这种建筑格局唯有北京故宫太和殿可以媲美,足见其规模之大。但长期以来,哈尔滨文庙都处于荒芜废弃的状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给文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了改善哈尔滨文庙的环境,发挥文庙的社会功效,先生又一次积极奔走,呼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文庙的历史文化价值,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要求合理开发和利用文庙,并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了哈尔滨地区五常市出身的女真状元徒单镒,为打开哈尔滨文庙的南门找到了历史依据。[13]如今的哈尔滨文庙修葺一新,掩映在都市深处茂密的城市绿肺中,游客到此无不惊叹,西洋风格建筑鳞次栉比的哈尔滨市中心竟然隐藏着这样一座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
在哈尔滨市区以北数十公里处坐落着一座精致的北方小城、著名作家萧红故乡——呼兰。蜿蜒温柔的呼兰河从呼兰区北部静静流过,注入浩荡的松花江水之中。呼兰的名声不仅仅源自于这里曾孕育了萧红这样伟大的东北女作家,也是一座雄伟教堂对这座小城的馈赠,这便是著名的呼兰天主教堂。呼兰教堂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东大街路北,是一座建于20世纪初的哥特式天主教堂,造型特别,建筑雄伟,青砖外墙,东西18.3米,南北23米,建筑面积836平方米。教堂双塔造型高35米,与巴黎圣母院外观相似,故有“东方巴黎圣母院”的美誉。1908年,法国神甫戴治达经多年努力建成,在筹建期间曾引发著名的“呼兰教案”,引发了哈尔滨人民的反帝斗争运动,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呼兰天主教堂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面临坍塌,因地处呼兰第五中学校园内,为保证校园师生安全,曾有人提议欲将这座历经近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东方巴黎圣母院”拆除。王禹浪先生等学者闻讯后,迅速驱车前往呼兰,在当地留宿三天,对呼兰天主教堂的历史沿革、建造背景及现状予以综合考察和调研,撰写了《关于呼兰县天主教堂开发利用的调研报告》,[14]就该教堂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八点重要建议,要求保留教堂,并对其进行维护修缮,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与教育价值。呼兰大教堂最终在王禹浪先生等学者们的力保之下避免了被拆除的厄运,被成功保存了下来。当我们再度站在焕然一新、重新开放的呼兰天主教堂前,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双塔,我们应该庆幸并感谢,王禹浪先生又为哈尔滨人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四、结语
写到这里,内心蓦然多了些许感慨,回首导师王禹浪先生与哈尔滨的点点滴滴,学生的心里唯有敬仰和感佩!记得诗人艾青有一句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先生自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为这座给予他生命的城市奋斗奉献了近四十载。今天的哈尔滨以夺目的光彩吸引着八方来客,所有人都为其独特的城市文化赞美不已。当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建设蒸蒸日上之时,而我的导师王禹浪先生却已是满头银发,先生一直以来都不是埋头故纸堆的书斋式学者,而是不断将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对接、与时代接轨,用自己对学术炽痛的爱去熔铸他的生命,积极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建言献策,先生以其半生的心血和成果向养育他的故乡和人民献上了一份最完美、最精彩的答卷。我想,这就是先生对故乡最深沉的爱吧!
[1]王禹浪.金代黑龙江述略[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
[2]王禹浪.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3]王禹浪.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J].北方文物,1993,(3).
[4]王禹浪,王宏北.金代“建元收国”石尊考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6).
[5]那国安,王禹浪.金上京百面铜镜图录[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6]伊葆力,王禹浪.金代铜镜[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7]鲍海春,王禹浪.金源文物图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8]王禹浪,等.金上京印符集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9]王禹浪.金源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0]王禹浪,伊葆力.《拉林阿勒楚喀京旗原案》的发现及其价值[J].东北史研究动态,2001,(1).
[11]王晶.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文化[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12]黄澄,张竞,王禹浪.关于继续开发索菲亚教堂及其周边环境的思考[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5).
[13]杨华,王禹浪,黄澄.如何开发利用哈尔滨文庙的几点思考[J].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3).
[14]梁爽,王禹浪.关于呼兰县天主教堂开发利用的调研报告[J].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2).
责任编辑:李新红
Wang Yulang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arbin——Famous Scholar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rtheast Area Professor Wang Yulang and His Story with Harbin
WANG Jun-zheng
(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Professor Wang Yulang proposed “Swan Theory” in 1999 based on decade of study on Harbin.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udy he summarized the general rules for the geographical name system of the northeast China history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his own research methodology. Professor Wang Yulang proposed the theory of “Jinyuan culture” and “Jingqi culture”. Professor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arbin Central Street,Sofia Church,Confucious temple,Hulan Church and other historical archetectures.
Wang Yulang;Harbin;Swan theory;Jinyuan culture
2016-06-16
王俊铮(1990-),男,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
1004—5856(2016)09—0001—07
K291/297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0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