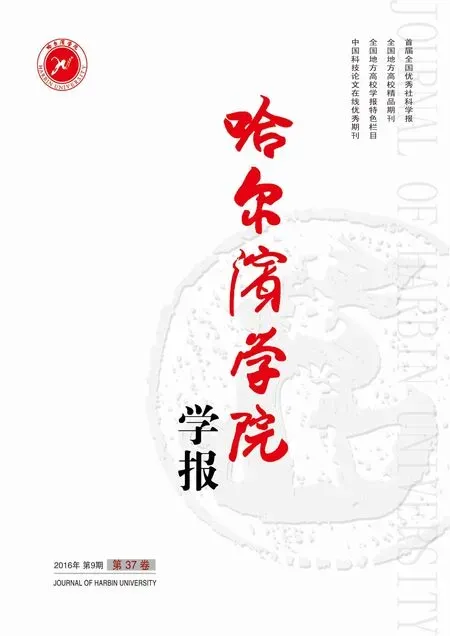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分析
刘 刚,李德刚
(哈尔滨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分析
刘刚,李德刚
(哈尔滨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6)
近年来,国内各地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对此,各地方政府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但由于地方政府在角色定位、服务意识、危机预警机制构建等方面存在着问题,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为此,文章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提出地方政府需要面对的不足和缺陷,强化行政责任追究、改变考核方式、完善预警机制并更多地关注民生,从而对群体性事件早处置、快处置,有效规避其不良影响。
地方政府;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始终是党和国家努力平衡的重大问题。既要通过改革推动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要促进社会稳定。但是,近年来诸多群体事件一再在各地出现,它们在冲击民众视觉神经的同时,也因其巨大的破坏力而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了重大影响。地方政府在应对此类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如何改进,这些都是和谐稳定大局应该努力探讨的。
一、群体性事件及地方政府对其的治理责任
所谓群体性事件,概括说来,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利益分配或调整的过程中,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群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采取不合法或合法的方式,通过规模性聚集的形式,以期向政府施压,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的活动。在概念认定上,“群体性事件”经历了一番变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其一般被称为“群众闹事”,80年代后,作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不和谐音符,它被称之为“治安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紧急治安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群体性事件,党和政府一直是以治安性质来认定。直到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才首次称其为“群体性事件”,其名称得以最终确立。
梳理近年来多次群体性事件,其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参与主体多元。群体性事件仅是一个统称,引起事件的原因并不相同,因而参与主体可能属于不同的群体,但是从整体看,其主体主要是弱势人群,比如,征地事件中的农民,讨薪事件中的农民工,环境事件中的受侵害居民等。当然,也有处于非弱势地位的民众参与其中,比如环境事件中的白领、教师、医生,甚至行政人员。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非弱势群体,他们大多都是利益受损者。第二,维权趋向明显。群体性事件与传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着本质区别,它的目标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向现有政权施压,引起轰动效应,要求政府及社会关注自己的利益诉求。第三,方式手段的多元与激烈性。群体性事件的源起是因为利益受损或利益分配不均衡,且得不到权利救济。因此,很多事件的参与主体存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认识,因而事件一旦爆发,表现一般都较为暴烈,方式手段也呈多元趋势,如在政府门口静坐,甚至冲击政府机关,干扰政府办公秩序、阻碍交通、暴力打砸等。第四,处置困难。群体性事件起初的原因较为明确简单,但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参与队伍壮大和人员的混杂,问题往往纠结在一起,其诉求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甚至还有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来,不为利益维权,专为打砸闹事,致使事件处置起来非常棘手。
当前国内社会局势总体稳定和谐,尽管群体性事件经常在各地上演,但毕竟不是主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对社会稳定的负面作用。对此,政府负有难以推卸的政治责任。所谓政治责任,引用张贤明教授的话讲,就是“政府官员履行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关政策,推动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执行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责任时所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1](P2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告诉我们,人民才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基于人民的委托,与人民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从理论上讲,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存在以及以后继续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代民众行使公共权力,为民众管理公共事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幸福自由地生活。政府的这种政治责任决定了它要努力治理社会,规避类似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稳定的问题,这是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体现,是民众的要求,同时也是取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进而获取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二、当前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频繁在各地上演,引起该类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共同的——它冲击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宪法义务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认真应对。但是,作为特定组织,各级地方政府也存有经济人理性,并且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占有也不一定充分,因此,地方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存在偏差。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仅仅是为民众搭台、让民众唱戏的后台服务者,其所担当的应该是服务性、保障性角色。为此,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为广大民众服务。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各地方政府不禁跃跃欲试,忘记了自身的角色定位,更是从经济人的视角出发,为少数能够为地方创造更大经济效益的企业和投资者保驾护航。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两大矛盾集结点为例:政府廉价征地,是为了能够给为地方经济发展做更多贡献的企业腾出足够的空间;环境污染,是由于那些在政府卵翼下的企业肆无忌惮排污。只要GDP能够实现预期增长,许多地方政府大有不惜代价的架势。由此可见,对于每起群体性事件,如果追根溯源,总能或多或少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当群体性事件爆发,需要政府出面平息事态时,有的地方政府还不忘那本经济账,告知当事民众,如果大家再忍耐一段时间,某某项目上马顺利,就能够为地方带来大量收益,到时候每个人都将是受益者,如此云云。暂且不讲政府的这种游说或解释的效果如何,但它至少反映出各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存在明显偏差。
第二,部分地方政府行政责任缺失。政府所负有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责任要通过各级政府行政职能去实现,履行其行政责任。相对于政治责任的外部特征来讲,政府的行政责任仅仅是指政府内部下级行政机关对于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人员对于各级政府命令的执行责任。从理论上讲,各级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乃至国务院的命令要不折不扣的去执行。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官僚习气有余,履责意识不足。当前,我国的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需要地方政府认真履行责任,化解矛盾,构筑和谐。但有些地方官员却不主动深入民众,不去了解舆情的变化,不想办法进行解释安抚和疏导,有的甚至还想从中寻租。部分群体或民众为此可能会奔走相告,其目的极为简单,就是利益表达,期待能有权利救济。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民主政治发展不足导致的参与渠道狭窄,让他们感觉到,有些渠道因为无权而不好用,有些渠道尽管有权但不适用。现实的困境可能成为他们采取诸如越级上访、示威、静坐等非法、过激措施的原因,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第一要求就是速度快,因为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情势紧急、破坏力大,越快处置,舆情越容易掌握,处置的效果会越好。但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仅仅将其视为工作的一部分,责任缺失,官僚色彩浓厚,下意识的做法就是想封锁消息,随着局势进一步升级,以暴制暴的措施可能也接踵而至。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观上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部分当事人员履责意识缺失,身居官位的他们主观心理上的优越感,以及头脑中“管理就是控制”的传统行政管理思维定势。
第三,依法行政的程度不够。党的十五大报告地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必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这可以有效压缩自由存量权的行使空间,减少政府乃至行政人员被追责的风险,对预防群体性事件有利,对当事地方政府和官员也有利。但是,一方面直接适用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律法规不足。当前还没有出台直接适用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律,距离其最近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尽管突发事件与群体性事件有相似的地方,但毕竟不是一回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范群体性事件,其适用性值得商榷。另一方面,传统的“官本位”,乃至“政府本位”思想长期作祟。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忘记与民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误以为自己就是权力的所有者,当问题较小时不爱搭理,当问题严重了,总愿意武断地使用警力。事态可能暂时压制,但矛盾并没有解决,一旦积聚到一定程度,其暴烈性、破坏性让人瞠目结舌。
第四,危机预警机制不健全。“公共危机在发生之前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且都表现出一定的征兆或迹象,如果能在危机还在萌芽状态或初起时及时发现这些征兆,对其发生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或能防止公共危机发生和升级,有效地控制事态发展。”[2](P113)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来讲,危机预警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有效治理的前提。但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非常态化,“偶然性”较大,地方政府从运行成本出发,难以设立常态化的政府专门机构进行此项专业工作,更多地是各地的科研机构在做这项工作。但是一方面科研机构往往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点,这个兴趣点不见得就和社会的矛盾点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也难以保证科研机构的数据分析的有效性、权威性,因为目标不同,对于数据的选择可能会有不同。另外,“相关部门对社会舆情与信息的报告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哪些信息应报告,应通过什么渠道报告,应报告到什么机关都没有明确的规定”。[3]
三、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水平的措施建议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利益结构出现深层次的分化组合,期间必然产生大量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处置这些矛盾,极有可能引发大量群体性事件,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为此,需要当事的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社会管理,探讨协调矛盾、规避群体性事件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一,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追究。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前,一般都会存在或长或短的预警期,在这期间问题会露出端倪,舆情也会出现变化。如果这个阶段地方政府能够重视起来,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即便群体性事件爆发,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第一时间真诚地与民众沟通,事态也是比较容易控制的。事件爆发后事态之所以一再蔓延,暴烈程度一再提升,其中有法制不健全、无有效法规可依的可能性,但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地方政府乃至官员服务意识不够、责任心不强、措施不当造成的。为此,必须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政治责任需要通过行政责任去落实,而行政责任又有积极行政责任和消极行政责任的区分。积极行政责任是鼓励、引导政府及其官员去履责,消极行政责任则是对其不能有效履责、懒政庸政怠政的惩罚。既然积极行政责任的引导功能失效,就需要发挥消极行政责任的鞭策、惩罚功能,倒逼地方政府和官员提升服务意识,寻找解决问题之道。为此,在坚持“集体决定,分工负责”的同时,要严格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领导责任,同时也要追查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的督察责任。对于在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员,要严惩不贷。
第二,改进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作为特定组织和自然人,都有着经济人理性,有着自身的利益考量。作为行政体制设置的一环,地方政府要听从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其行政官员除了要听从机关部门的安排之外,还有着晋升、加薪等方面的要求。因此,上级如何考核,他们往往就如何去做。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更愿意迎合上级发展经济的要求,注重GDP总量的提升。尽管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不是强项,但他们更愿意为经济主体、投资单位提供方便,乃至保驾护航。“地方政府通过引进污染企业得到了GDP、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一些官员凭借‘政绩’获得晋升,而企业则获得廉价土地,基础设施,及其他优惠政策,赚取高额利润。”[4]在GDP的引诱下,地方政府的“服务者”角色定位悄然发生变异。由此可以看出,要纠正地方政府的角色偏差,就需要改变考核方式。将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指标的“幸福指数”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标准,在预防、规避群体性事件方面似乎更加适合。
第三,完善地方政府危机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侵蚀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做好前期的预警工作,完善危机预警网络。鉴于地方政府人手不足,难以常态化、持续性地紧盯处于偶发状态的群体性事件的现状,政府可以充分调动该领域的专家,以及科研机构的积极性,以服务外包的形式,投入定量经费,鼓励科研机构持续地、专注地做好地方舆情的调研工作,务求实效性。并且设置必要的畅通渠道,保证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上呈,保证地方政府能够对所呈交的意见及时回馈。地方政府在细化应急预案,提升预案的操作性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民众的沟通工作。
第四,关注地方民生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5]其实,民众的要求非常简单明了,就是维护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安居乐业。民众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是因为它与民生密切联系在一起;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是因为社会上有些问题影响了民生。政府在搞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为民众多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其实就是政府角色定位的“复位”。政府关注民生,做好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工作,解决好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以及“菜篮子”“米袋子”等问题,尽管这些工作很琐碎,但民众却享受其中。更多地解决好民生问题,不仅群体性事件因为无人参与而无处生根,政府也因此履行了其政治责任,获取了民众的认同。
总之,当前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大局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此,政府需要在正视存在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并强化行政问责,改进考核方式,完善预警机制,进而提升应对水平。在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方面,只要地方政府意识到位、方法得当,一定会有所作为。
[1]张贤明.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永理,李程伟.公共危机管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陈侃.群体性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策略研究[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4]聂辉华.斩断政企合谋的利益链条[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11-11.
[5]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庆
Local Government’s Strategies for Mass Disturbance
LIU Gang,LI De-gang
(Harbin University,Harbin 150086,China)
Recently,there are more mass incidents in China,which brings great threats to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role orientation,service awareness,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The main problem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solve are pointed out.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change the evaluation method,and improve th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 with fast and efficient treatment.
local governments;the mass disturbance;solutions
2016-05-18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2A002。
刘刚(1974-),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
李德刚(1974-),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1004—5856(2016)09—0033—04
D625;D631.4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0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