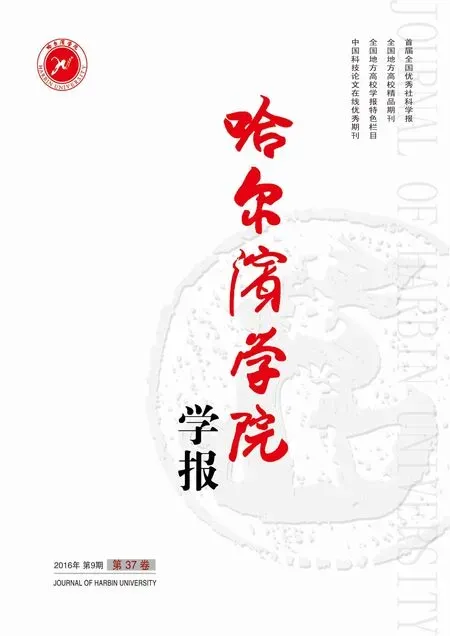现实主义法学探析
周 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38)
现实主义法学探析
周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38)
现实主义法学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具有激进色彩的法学思潮,其发轫于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理论,兴盛于卢埃林与弗兰克,核心理论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将法学研究的重点由规则转向行为,并由此衍生出“规则怀疑论”“事实怀疑论”“法官造法论”“预测论”等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与质疑,并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法学和批判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法学;法律的确定性;法官造法
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法学是一场对现实持怀疑态度,具有激进色彩的法学思潮,它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由当时一批具有共同思想倾向,但却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或者运动。它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并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主张以法的客观现实为研究对象,强调法官的行为对司法判决的影响,轻视甚至否定法律规则对具体案件判决的影响。现实主义法学发轫于霍姆斯,兴盛于卢埃林和弗兰克,其共同点都主张法律的不确定性,区分书本上的规则与行动中的规则,强调法官的个人行为,注重司法的社会效果,这些都似乎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法律究竟在哪里?本文分别从霍姆斯、弗兰克、卢埃林三人入手,对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进行梳理探究,提出对现实主义法学观点的一些质疑,并结合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一些看法。
一、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
(一)弗兰克——从两句话谈起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1](P5)这是霍姆斯在其著作《普通法》一书的卷首语中所写的一句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他对法律的看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律特指英美法系法官所创造的判例法,而非立法机关的成文法。他认为,在各个时代被认为是必要的一些规范,和这个时代有力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及人们表明的或是无意识地探究到的关于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甚至法官与普通民众一起所抱有的偏见等,都对判例法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它们在决定确立社会的各种准则时,远比三段论的经验推理作用大得多。[2](P57)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霍姆斯对传统法学的逻辑分析提出质疑,他认为法律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它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强调法律的本质在于实用的主观经验,认为法官绝不是机械地依据法律规则制造判决的“自动售货机”,公共权力通过法院的工具性活动产生影响的预测。[3](P5)这里所谓的预测,是指一个法官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其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制定法律。
法学的目的是一种预测,即对人对于法院将要对自己做出什么判决的预测,而且他主张从坏人的眼光来看待法律,因为恶人不关心所谓的公理和推论,对他而言,法律只是一套自己行为的代价体系,他只关心法院将要对自己做出什么判决,从恶人的角度来看待法律比较接近法律的实质。因而他主张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官的判决而不是法律规则。霍姆斯的“法律预测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影响深远。
(二)弗兰克——事实怀疑论的提出者
弗兰克法律思想的核心是法律的不确定理论和事实怀疑论。他认为,不确定性才是法律的基本特点,而从传统法学所认为的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神话”,他从各方面来分析这个基本的法律神话是为了论证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法律是行动中的法,法官可以造法,法律是就具体情况作出的判决或者对判决的预测。
关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第一,他对社会上这样一种看法提出了批评:即人们认为法律本身是精准和确定的,只是那些律师们为了贪财等目的才将法律复杂化。甚至一般公共舆论也同意拿破仑的下述看法:“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任何一个识字、并能够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就能做出法律上的判决。”[4](P5)弗兰克对此断然否定,他认为法律本身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律师的曲解,而是源于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即使是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也绝不存在一个可以预测一切纠纷并预先加以解决的规则,再者在庭审中,证人的证言由于其回忆、复述极易出现纰漏。“法律的许多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幸的偶然事件,它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4](P7)可见在弗兰克眼中,一个具有灵活性、社会适应性的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二,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法律确定性这个“基本的法律神话”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们对于法律确定性的依赖就像是儿童的恋父情结,一个儿童从本能上渴求一个稳定的可依赖的世界,而这种渴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父亲的信任和依赖来满足的,但当儿童长大后会逐渐发现实际生活的不确定,因而幻想着重新发现父亲,对父亲的依赖也就从最初适应社会的手段,最终变成目的本身。而这仅仅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或者说是自欺欺人罢了。
关于法律的概念。弗兰克反对法律的确定性,他认为法官在事实上创造着法律,法律就是法官的行为。关于法律的概念在法理学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法律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一套规则体系,只有立法机关享有立法权,法官无权立法只能严格适用法律。二是法官造法论。在弗兰克看来,就任何一批具体事实来说,就任何一个具体的一般人而论,就法院判决影响这个具体的人这一范围而论,法律就是一个法院关于这个事件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之前,唯一可以加以利用的法律便是律师对于有关这个人和这些事实的法律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并不是法律本身,而只是对法院将如何判决的预测。据此,弗兰克将法律定义为: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个已经做出的判决:大概的法律,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5](P335)在这里需要注意,第一,弗兰克的法律概念是就具体情况而论的;第二,他否认法律规则本身是法律,但不否定它们的作用,它们只是用于预测和判断的工具。
关于事实怀疑论,弗兰克断定法律是就具体情况已经做出的判决及对未决案件的预测,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法官实际上是如何做出判决的,由此提出了事实怀疑论。他指出每个法官的个性,如性情、偏见、习惯、信仰等在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影响重大,个性各异的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判决,而法律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初审法院在确定案件事实方面的不确定作为判决依据的事实,并不是在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法官现在认为发生了什么,即法官的主观重构事实。总而言之,法官的个性与心理对判决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此理论,弗兰克还概括了两个公式:神话的公式:R(Rule,法律规则)×F(Fact,事实)=D(Decision,判决),现实的公式:R(Rule,法律规则)×SF(Subjective fact,主观事实)=D(Decision,判决)。[6](P294)基于此,弗兰克认为初审法院在确定事实方面是美国司法制度中问题最多的地方:“正是在那里,法院的工作最难令人满意。正是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司法不公正。正是在那里,最需要改革。”[7](P4)
(三)卢埃林——规则怀疑论的提出者
作为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卢埃林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规则怀疑论。与事实怀疑论怀疑初审事实,其主要关注初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规则怀疑论怀疑在案件事实确定之后,纸面上的规则能否有效地预测法院的判决,其主要关注上诉法院的判决,把注意力集中在力图找到能够准确预测上诉法院判决的方法上。
关于法律的定义,卢埃林在其著作《长满荆棘的丛林》一书中明确将其界定为:所谓法律就是官员解决纠纷的行为。这一法律概念包含了他的两个基本思想:一是解决纠纷;二是官员行为。[5](P314)也就是说,在发生纠纷之后,主要的问题是官员将要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具有一种常规性,因而人们在涉及到自己的案件中可以借此来预测官员将要做什么,与弗兰克相比,卢埃林的法律概念可谓更进一步,将所有的官员行为都视为法律。因此,他提出,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转向对司法人员的实际行为特别是对法官的行为的研究。[8](P163)
关于规则怀疑论,卢埃林坚持认为法律的核心是官员的行为。他指出,传统的法理学认为法律是一整套的行为规则,法学家的任务就是将各种规则整理成内在一致的体系,法官和律师运用规则推演出相应的结论并适用于具体的案件,而他认为关键是要看官员做什么,并看是否存在有关他们行为的规则性,从而使人们能够预测官员的行为。他将规则分为“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纸面规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即帮助我们预测法官或其他官员将要做什么。当然卢埃林怀疑规则但并不否定规则。在《普通法传统》一书中,他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他对法律的表述,他之所以强调怀疑规则,这样做只是为了改变以往对待法律的思维方式——只重视现有的法律规则,而忽视法官和其他官员解决争端的行为。[6](P294)
虽然学界公认现实主义法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体系与概念原则,只是一股学术思潮,但是通过以上对现实主义法学几位代表人物观点的介绍,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有某些共同点:第一,实证主义、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在法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法律不可能是一个完全自洽的体系,不可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相隔绝。第二,“法律的不确定性”,不论是规则怀疑论还是事实怀疑论,都体现出了现实主义法学那种对传统法学关于法律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的质疑。第三,“纸面规则”与“实际规则”的区分,他们认为只有实际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法律,纸面规则不过是发现与预测实际规则的手段,法学研究的对象应当由规则转变为行为。第四,法官造法论。其强调官员特别是法官的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法官的个性特征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十分重要,承认法官依据社会利益自行改变和创造法律,显然,我们应当关注司法而非立法。
二、对现实主义法学观点的几点质疑
现实主义法学的观点对传统法学提出了挑战,“法律的不确定性”表明他们对法律的基本看法:法律不存在于规则,而存在于行为。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广泛的争议。通过上文的一些分析,本文拟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法律的不确定性质疑
长期以来,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法律具有确定性,有的学者甚至还将它列为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按照通说,法律规则对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再者,案件事实是确定的,原因在于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处理案件的过程,就是把确定的法律规则适用于确定的案件事实的过程,因而,一定能够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法律的确定性使人们能够据此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在现实主义法学看来,在法律领域,重要的不是法律规则,而是官员的行为,尤其是法官的行为。所以,法律就是解决纠纷的官方行为,在判决的形成过程中,法官的个性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个性是不确定的,往往要受到环境、伦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现实主义法学将法官个人的行为过度夸大了,而没有看到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从法律规则的产生来看,它们往往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虽说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确会对规则的含义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时期,人们基本上会对规则的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理解。
其次,法律规则不仅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而且具有行为指导的功能。在遭遇纠纷时,我们会依靠法律来解决,这个时候,法院的判决对我们至关重要,但是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可能一生都不会涉足法律纠纷,但我们的所作所为却无时无刻不受到法律规则的指导。若真如现实主义法学所言,那一条从未被适用过的法律规则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已经深入并指导了我们的生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到,法律的作用更多地是通过行为指引来发挥的,在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解决纠纷只是法律的次要作用。[9]
再次,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正是这种确定性,使法律调整机制获得了客观性和稳定性。[10]法律的确定性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秩序。[11]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主要手段,客观上需要法律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正是法治模式优于依靠道德宗教以及习惯等人治模式的重要标志,失去了确定性,法律就会变得朝令夕改,人们就会无所适从,整日惶恐不安,法律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权威。
最后,从司法适用的角度讲,现实主义法学认为,法官在接到一个案件时首先是先假设一个结论,然后将自己认为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则相对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前提(法律规则),小前提(案件事实),结论(案件判决)的三段论推理,而是一个倒三段论,因此,判决的关键在于法官的主观重构事实,而不是法律规则。本文并不否认,这是司法实践实际适用法律的过程,然而现实主义法学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为,法官在大致有一个假设性的结论后,他往往是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则是否契合来检验结论是否正确。所以说,法官最终是受制于法律规则的,判决并非完全因“法官喝了甜咖啡还是苦咖啡”而大相径庭。
(二)法官造法论的质疑
为了突出强调法律过程的重要性,现实主义法学者强调法官在法律过程中的重要性。[12](P40)一个重要的主张便是:法律不是规则是行为,法官的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法官的个性特征决定最终的判决,我们应当关注实际的规则。但是将法官的个人因素无限扩大,贬低甚至否定法律规则,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过分强调法官的个人因素,与权力制衡理论相违背。如果法官真是穿着法袍的立法者,那么如何实现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衡?如所周知,奠基于孟德斯鸠及洛克等人理论之上的权力分立及制衡机制是西方法治国家的基本政治构架,其核心内容就是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审判机关独立地行使。然而,如果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依议会法判决而依自己所造之法判决的话,则显然破坏了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权力分立及制衡机制。再者,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被一个机关所掌控,那么极易造成法官滥权则人们的自由就可能随时受到严重的侵犯。孟德斯鸠早就断言,如果司法权不和立法权、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13](P156)
其次,从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来看,法官不可能自由地对案件进行判决。尽管现实主义法学声称法官的个性特征影响重大,但是,一个社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有着基本相同的知识水平、法律思维、职业伦理和价值观念,长期的法律职业生活使他们自觉的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所以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他们都会受到法律规则的制约,上文中谈到的法官实际处理案件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们不否认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但同样法官也不可能“绝缘”于法律规则而肆意妄为。
再次,整个庭审法官要受到双方当事人的影响。如果真如现实主义法学所宣称的那样,即法官的个性如法官的性情、偏见、习惯甚至当时的心情等因素乃判决的决定性因素,法院就不再可能是进行查明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自由辩论的场所,而仅仅是一种当事人比口才、碰运气的表演剧场或赌场。因为一方面既然法官的个性及情感就可决定判决,那么,控辩各方要做的就是尽情表演打动法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个性难以捉摸,双方当事人打官司就成了打运气,法院就成了双方比运气的赌场。显然这有些荒唐,而实际情况是双方当事人依据对法律(即规则)的理解来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看法,法官依据法律对双方的看法进行衡量并作出判决,并不是由于心情的好坏而作出裁定。
最后,法律规则可以分为一般规则和个别规则。所谓一般规则是针对一类人或者一类行为所适用的规则,个别规则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所适用的规则,其实就是法官针对特定案件的处理。显然,现实主义法学只看到了个别规则,用规则的适用无法离开法官的行为来否定法律规则的存在是不能成立的。再者,现实主义法学耿耿于怀的是规则的模糊性问题,它以为,如果规则是有约束力的,那么就不应该在适用规则时使法官具有灵活的解释权力。[9]但是我们不能以一般规则不可避免存在的模糊性来否认法律规则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指导和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制约。
三、从现实主义法学看我国的法治建设
现实主义法学在美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在学术界,传统的法律形式主义因其自身的僵化封闭而难以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做出回应,实用主义哲学兴起,为现实主义法学的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统计学等学科开始影响法律,法学开始与其他学科相融合。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罗斯福新政,被称为是“修宪式改革”,开始对原来的自由主义宪政进行改造。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激进色彩的现实主义法学思潮的兴起。反观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现实主义法学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的法律又在哪里呢?
第一,法律的确定性思想对目前我国法治建设至关重要,要确立和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僵化与封闭确有道理,但是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更需要法律的确定性,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性质,行政权一支独大,立法权和司法权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尤其是在行政法律法规规范方面。法律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难以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二是导致权力滥用。
第二,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之内,赋予法官自主权,实现法官独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法律规则的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讲它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内应当承认法官的自由权。“徒法不足以自行”,在一个完整的司法过程中,法官无疑是最为核心和能动的主体,就一个法官而言,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其职业操守也不可或缺,法官的良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判决结果和司法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法学十分强调法官的个性决定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的。目前,在我国实行的是法院整体独立,而非法官独立,根本没有建立真正的司法独立制度,这会产生以下问题:司法权威难以确立,民众产生司法信任危机。尤其是在涉及社会敏感案件时,法官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影响,难以独立作出裁决,造成民众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容易引发社会集体事件。
第三,不能过分强调法律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而忽视其法律效果。我国目前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细想一下,根本无法在一个平面上将这三方面统一起来,例如在民事案件中,我们过分强调调解,甚至以调解率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使得很多案件旷日持久,长期拖延,当事人不堪其苦。在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由于过分地强调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搞“民意审判”,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到头来法律尊严丧尽。其实,只要正确地运用已经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规则,实现法治,法律效果确立,树立起司法权威,民众信任法律,那么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自然而然会确立。
第四,现实主义法学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启示:如区分书本中法和行动中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了书本中法与行动中法的疏离,及由此而带来的法律认同问题。如何根据目的、效果及二者的关系来检验和校正纸面规则以使其与行动中的法契合,仍是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11]再如,更加重视法官的个人行为,不仅要重视法官专业水平的提高,也要不断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再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剖析中国的法治问题,上文我们提到弗兰克从心理学的角度(儿童的恋父情结)对“基本法律神话”进行分析,反观我国的法治建设,制度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西方信赖制度而不信赖人相比,中国人缺乏对制度的信赖和好感,我们不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人深受儒家贤人政治观念影响,有着深厚的“父母官情节”,当法律制度难以奏效时,这种思想更为强烈,这也是阻碍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但是,不能保证官员都是贤人,但却可以通过建立一套良好的制度来约束官员,保障权利。
四、结语
法律在哪里?从一言九鼎的皇帝圣谕,到卷帙浩繁的各类法典,再到权威至上的法院判决,我们一直在寻找法律。在自然法学派眼中,法律存在于正义和理性;在实证法学派和法律形式主义者眼中,法律存在于法律规则中;在社会法学派眼中,法律存在于实际的法律运行中;而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眼中,法律在法官的行为之中,在那些判决中。其实,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不仅存在于那些逻辑严密的法律规则中,也不仅存在于法律职业者的行为中,它更植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Holmes.The Common Law[M].Harvard University Preess,1963.
[2]马聪.霍姆斯现实主义法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Holmes.The Path of La w [M].L.Rev,1897.
[4]Jerome 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d[M].1930.
[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何勤华.西方法律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7]Frank.Courts and Trail[M].1949.
[8]〔美〕博登海默.邓正来.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9]刘星.法律的不确定性——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述评[J].中山大学学报,1996,(增刊).
[10]戴云飞,刘勇.法律漏洞弥补方法之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一隅[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7).
[11]曹祜.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J].法律科学,2004,(3).
[12]付池斌.现实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责任编辑:思动
Realistic Jurisprudence Analysis
ZHOU Ka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
Realistic jurisprudence has become popular since 1920s in America. This radical jurisprudence started from Holms’ realistic jurisprudence and got popularized by Llewellyn and Frank. The core theory is the uncertainty of law and hence transfers the research focus to behaviors,from which new ideas,such as “rule skeptics”,“fact skeptics”,“judge-made law theory”,and “prediction theory”,are proposed,which attracted argumen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made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western post-jurisprudence study and critical jurisprudence study.
realistic jurisprudence;certainty of law;-made law theory
2015-12-03
周康(1988-),男,河南永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
1004—5856(2016)09—0064—06
D90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09.015